

地域性诗歌的悖论
文/草树
一个诗人为出生地作传,“以诗写史”,是情感之所至,也几乎意味着一种责任。以地域为题材,这一类诗歌有着显豁的文学传统。我相信当代诗人中有不少怀抱这样隐秘的冲动,甚至有很多诗人已经将之付诸语言行动。文学史上这个传统的辉煌地标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希尼的贝尔法斯特、莫言的高密……这个清单还可以罗列很多名字。这一类诗歌通常可以归为地域性诗歌,小说似乎没有这样的命名。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运动带来的现代性大举“入侵”,曾经近乎静止的故土或出生地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动:现代和传统之间出现巨大的裂隙,地域性诗歌要担负诗的见证的功能去弥合?或者在语言中重建故土的空间以安放无处安放的乡愁?
按照现代性诗歌美学的观念,任何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不过是一个语言活动的场所,地方性知识不论蕴含着历史人文记忆,还是民间智慧,它们都只能作为存在的场域、存在的背景。地域性诗歌任何主体化或伦理化的表达,都不可避免陷入唯我主义或本质主义。对于当代诗歌来说,重要的不是地域的位置,而是语言的位置。我们也不妨说语言的位置就是一个观情睹物的位置,是一个诗人的写作坐标的原点。因此地域性诗歌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是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存在的映照,有可能使传统和现代获得一个微妙的“活接”,有可能使沉默的词语再次出现在语言的秩序中,有可能使逝去的空间再次参与诗的时间的创造;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不自觉演变成反对现代主义,并将地方风物和历史人文作为一种满足主体情感需求的客观对应物,让地域性写作沦为一种虚妄的情怀表达。质言之,地域性诗歌如不能厘清语言的位置,而是“我”的无处不在高居于地理位置之上,那就正应了希尼的那句话,“无所不在而无所在”。
任何一个诗人的审美教育离不开出生地,无论是乡村的自然风物还是城市的街巷人文,除了彰显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回溯——向着个人的童年或人类的天真。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打捞人类失去的天真。
每一个诗人的写作当然不能脱离时代的语境,重要的是在地域性诗歌的惯常写作范式之中有所突破。所谓惯常的写作范式大致有如下情形:一是歌唱故乡,发怀旧之幽情,表现为情怀的地域化或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式抒情;二是将故乡的风物和地方性知识主体化,通过修辞转变为一种主观情绪、思想和意志的表达;三是带着“旧即是好的”的潜意识,有着某种不自觉的伦理化倾向。但凡这样的写作,实际上都没有摆脱唯我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束缚,不是作为一个倾听者聆听故土逝去部分的巨大沉默和当下发生的鲜活声响,而是凌驾于地域的风物之上,做一个悬崖上的眺望者,用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对故土事物的指认性命名和个人化的形而上学抽象,即现代主义二元对立思维、西方象征主义以及表现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消化不良,不是“吾丧我”,而是“我”变成万物的主宰者。地域性诗歌同样需要去中心化,去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这样的写作观念的自觉,无论多么深情,都会一不小心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写作的套式中。
诗关乎存在之道,世界万物皆主体。故土的事物,无论是古老楚国的历史遗迹,还是郊区最新立起的化工厂烟囱,无不是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这一片地域。现代汉诗致力于主体间性的建设,而不是主体性的表达。诗歌的个人化不是以彰显主体性为标志,相反抑制自我才能尽可能实现现代诗学的客观性原则。而对自我的反思和抑制,在西方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才渐成风气,而在中国,古典哲学早就提供了睿智的世界观。当代诗人应当克制主观情绪,到那个既广角又聚焦的视点——当然这本身也像一个悖论——换句话说,一个诗人必须具有开阔的历史人文视野和诗学视野,又能凝神专注于物甚至细节,如此才可能为实现艺术的客观性原则给予尽可能大的保障,真切地呈现存在,或让存在自身成其所是。
当然,地域性诗歌也不局限于出生地,不妨把有关山水行吟的诗歌都纳入这一范畴。而有一些诗歌文本本身则丧失了一个地名所辖的具体性,只是把地名作为一首诗的兴起,或标题。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个抒情主体的声音如不是对应“幽州台”这么一个意蕴深厚的地名,此诗就难免成为无本之木。因为幽州台曾经是燕昭王招贤纳士的地方,地名蕴含的人文历史使“古人”和“来者”自然而然获得了所指,即指向像燕昭王那样的明君,全诗的情感指向就明确了。“前不见古人”在此有强烈的悖论意味,诗人在幽州台正是因为发现有燕昭王那样的明君存在,从而生发出现实感叹,但燕昭王毕竟在时间的长河中早已化为虚无,成为“古人”,连历史遗迹都没有留存,让人倍感虚无和苍茫。
我们可以说此诗是一场诗人和幽州台的对话;因为幽州台有燕昭王招贤纳士那样的历史佳话,诗人的自我对话也得以实现。因此地名是一个语言记号,它可以成为词与物之间一条语言路径的标记,成为敞开显在或隐在的存在。
地方主义难以成为诗歌的大旗,诗歌不需要什么旗号。地域性诗歌,就像打工诗歌、工业诗歌或外卖诗歌的命名一样,实际上还是基于题材标准,是唯物反映论的产物。地域性诗歌若不是在传统和现代、过去和当下、历史和此地的维度真正有语言学意义上的作为,就难以成其所是。因此当代诗人在面对出生地这一亲切而熟稔的语言场所时,必须自觉保持谨慎的距离,从语言本体出发,去展开语言行动,从而让地域性成为存在的胎记——是个人性的也是非个人化的。
(原载于2023年第2期《创作》)

草树,本名唐举粱,1964年12月生于湖南,1985年毕业于湘潭大学。著有诗集《生活素描》《勺子塘》《马王堆的重构》《长寿碑》等,评论集《当代湖南诗人观察》《文明的守夜人》。参加《诗刊》社第十二届“青春回眸”诗会。2012年获得第二十届柔刚诗歌奖提名奖。2013年获得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首届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奖。2019年获得第五届栗山诗会年度批评家奖。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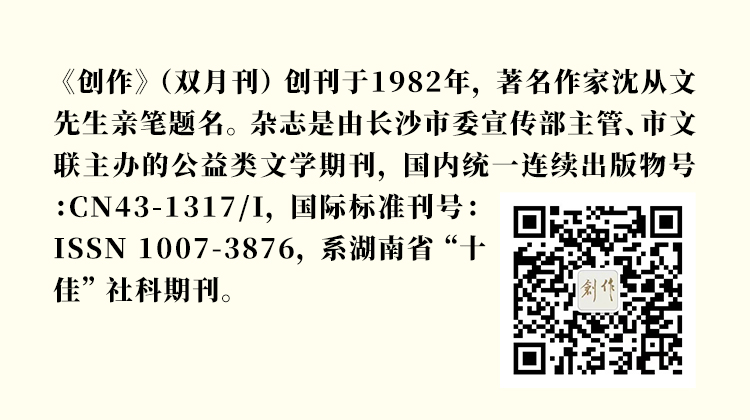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草树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艺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3/61/13094448.html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