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家福
文/王闷闷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老祝的六十岁生日,老祝几次说不过,妻子和儿子不愿,说,人一辈子有几个六十岁,你辛劳这么多年,都没正经过一个生日,这次必须得过。老祝责备妻子跟着儿子瞎起哄,妻子白了老祝一眼。儿子说,你们谁也逃不脱,明年我妈六十岁也得过,而且往后你们每个生日都得过,一切听我安排就是。老两口对视几秒,皆乖巧地无言默许。儿子每次来都是风风火火,他们知道孩子忙,尽可能不给他添负担,饭吃毕,儿子要走,他们一同送上了车。回来路上,老祝说,只要他们过得好,我们怎么样都无所谓。妻子说,你别再说不过生日的话,儿子也是一片孝心,既然安排了,我们听从就是。老祝哀叹了声,说,我不是怕娃累着嘛,这么跑来跑去。妻子知晓老祝在想什么,用手抚摸了一下老祝的肩膀,一同往家里走去。
村上没住多少人,到这里的公交车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儿子是粉刷工,本来一家住在县城,去年考虑到孩子上学,正好市里有活计,就搬到市里去了。从市里回来一趟得三个多小时,老祝不想让儿子跑,一天忙累了还开车,担心路上不安全,毕竟大儿子前些年就是这样走的,他不能再失去仅剩的这一个儿子。可儿子回来肯定带着孙娃,他想见孙娃。
老祝夜里躺下睡不着,和妻子说,你说我是怎么了,想那小娃,觉得可亲了,难不成这就是人们说的“隔辈亲”?妻子嘲笑地说,是谁前两年说不亲的,而且娃娃回来你好像也没多热情,现在娃娃回市里了你又说这话,我看你就是死鸭子嘴硬,成天装不够。老祝用不耐烦掩饰被说中心思的尴尬,说,说着说着就跑偏,我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和你就说不成。妻子获胜地说,算了,你就好好装,那天你去镇上赶集,买了什么?老祝立刻翻身面对妻子,说,我买什么了?妻子说,你就装,你买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蛇皮包里最后有什么没掏出来?
老祝说,有什么没掏出来?妻子故作生气地说,老祝啊老祝,你怎么就这么爱装呢,爷爷亲孙娃怎么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你买了什么,你买了玩具啊,我是不想揭穿你,你还自以为遮掩得天衣无缝。老祝侧转过身子,没再说话。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装什么,也暗暗告诉过自己不知多少次,想亲热就去亲热,那有什么。可每次见到孙子又不好意思那样做,也不知道不好意思什么,一辈子这么刚直。
既然打定主意过生日,那就不能真像儿子说的,他们什么都不准备,就坐等着儿子带东西回来。这天老两口起得早,简单洗漱后,天刚亮,两人就出门,老祝赶着驴车,妻子坐着。天虽冷,但驴儿欢乐,似乎也知道了主人要过生日,一路蹄子碎步踩着地,鼻孔里呼出白白的热气,慢慢悠悠往镇上走。到了镇上,出来摆摊的还不多,来这么早,妻子是为买那老婆婆做的油糕,在他们这里,过生日最应该吃的就是油糕,主要是孙娃爱吃。老祝将驴车拴停在空地上,拿上蛇皮包,跟着妻子去置办货物,没走多远就看到卖油糕的老婆婆,妻子买了两块,说,生日那天咱吃一块,儿子他们走时带一块。
老祝说,买几块都可以,你看着买。
油糕买好,妻子顺路买了宽粉,吃拼三鲜离不开宽粉。老祝指着路对面的猪肉店,妻子说,那里的猪肉不怎么好,我知道前面有家不错,经常在那里买。老祝扛上装有油糕、宽粉的包,嘟囔着说,就你一天事情多,猪肉嘛,吃起来不都是那个味。妻子转头瞪着他,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说话,跟着我就好,我做了一辈子饭还没你懂?别让我在大街上说你。老祝悻悻跟着。
妻子到中意的猪肉店买了猪肉,做丸子光猪肉可以,但做酥鸡,最好是猪肉鸡肉搅在一起,他们又到卖鸡的地方让现杀了两只。
太阳完全出来,集市开始热闹起来,老祝不想再转,跟着妻子边走边说,还有什么需要置办的?没有咱就回。妻子猛地停住脚步,老祝撞了上去。妻子说,你就是这样,来时催得急,来了待不了,待一会儿又火烧屁股似的要回,今儿我告诉你,要回你自己回,我是要细细盘算好,置办好,省得再跑一趟。老祝没了脾气,不情愿地跟着。妻子到调料店买需要的调料,安排老祝去卖葱的摊上买四五把葱,这样能早点回,但前提是要把葱挑选好。老祝信心十足地去买葱。
妻子买完调料出来,看到老祝买回来的葱,说,还行吧,葱就这样。老祝说,还有什么要买的?妻子说,还有鸡蛋,孙娃爱吃鸡蛋泡泡。老祝跟着。
全部置办停当,已是晌午,妻子问老祝饿不饿,老祝说还可以。妻子说,你说的还可以就是饿,我不知道谁,还不知道你。老祝憨笑。妻子指着旁边的羊杂碎店,说,吃那可以不?老祝说,你安排就是,这家里谁不是听你的?妻子说,别嚷我,我又不是听不出,吃不吃,一句话。老祝笑着说,吃啊,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驴儿样跟你跑一早上了。妻子也笑着说,还把自己抬举上了,驴儿可没你这么多牢骚。进店后,妻子给老祝要了碗优质羊杂碎和猪头肉夹饼子,自己只要了碗普通的。
晌午的阳光真是好,置办的东西放在驴车上,老祝坐在前面,赶着驴车,妻子坐在后面,暖洋洋,美滋滋,像是春天。妻子拍下脑袋,说,老祝啊,我就说好像有什么没买,那会儿想不起来,现在想起来了,是孙娃爱喝的那种饮料。老祝不悦地说,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就是个饮料,大惊小怪,在村里的商店也可以买。妻子说,村里商店就没有,镇上也只有一家商店卖,调头回去。老祝说,说不准儿子他们回来带着,已经走这么远了,调头回去又得花费多少时间。妻子生了气,说,还说你亲孙娃爱孙娃,狗屁,现在看不是装的,就是不亲不爱,折转回去买个饮料怎么了?你忙着回家有什么事了?
老祝说,你又扯远了,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别再跑一趟了。妻子说,你就是不想再跑,还装什么装,把驴车停住,我下车,我走着去买,用不着你,我又不是不长腿。老祝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往前赶,妻子半站起身就要跳车,老祝看拗不过,只得折转回去。
二
吃食这些妻子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儿子他们回来。还剩三天,妻子给儿子打了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儿子说当天上午回来。挂断电话后,老祝责备妻子催了儿子。妻子说,人就活个儿女娃娃们,他们不回来,咱俩能吃多少?做就是为了让他们吃。老祝说,我是担心你催他们,他们一着急,扰乱了心神,别开……别把手头的事情做错做坏。妻子知道老祝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是怕她伤心,说,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就你能,就你精。老祝拿着扫帚去扫院子,昨夜刮了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些干树叶和柴草渣子。
第二天上午,听说村里有人杀羊,妻子和老祝商量,去买一块,这是人家用粮食喂养的,贵是贵,但好吃,让儿子他们走时给带上。老祝拿了钱去买,妻子在家里做丸子酥鸡。没用完的猪肉,等儿子他们回来做猪肉翘板粉吃。把肉倒进锅里,翻炒会儿,刚要倒酱油,桌子上的手机铃声响起,她没去接,想着肯定是老头子怎么了,她把肉安顿好再回过去。没想到的是,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她三下五除二安顿好肉,在围裙上擦干净手,到桌子跟前拿起手机,一看是陌生号码,犹豫几秒接起,说,喂,你是哪里?
对面人急匆匆地说,你是祝学通的母亲?她说,是了,我是他妈妈,怎么了?对面人说,我给你们说个事啊,祝学通做活时胳膊被压着了,现在在医院,你和我叔来市里一趟。她的心顿时七上八下,说,情况怎么样?严重吗?对面人说,没有多严重,不过你们还是来一趟。她说,市里哪个医院啊?
对面人说,杏园医院,你们过来了给我打电话,我出来接你们。她再要说什么,对面已经挂断。
老祝提着羊肉回来,进门还想说自己买到这块羊肉有多么不容易,看到妻子呆坐在椅子上,说,怎么了,老婆子?妻子声音颤抖地说,我刚接了个电话,说是咱学通做工时胳膊被压着了,现在在医院,让我们过去一趟。老祝放下羊肉,说,没说严重不严重?妻子急躁地喊叫,我怎么知道,我问人家,人家不说,你问我我去问谁?老祝拿起手机,说,有没有给小敏打电话?问问小敏。妻子当即站起身,说,对啊,我怎么就把小敏忘记了,学通受了伤,小敏肯定知道,肯定在医院。老祝给小敏拨电话过去,没人接听,又拨了几次,还是没人接听,说,是不是骗子?你先不要急,老婆子,你忘记电视上经常播放的,现在这种骗子可多了,让我想想,还能给谁打。妻子嘴唇哆嗦着,说,是骗子,不然小敏的电话怎么无人接听?肯定是骗子,肯定是骗子,咱娃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老祝想起村里和学通一起耍大的二虎也在市里做活,跑去二虎家问得二虎的电话,拨过去,二虎很快接了,说,喂,你是谁?
老祝说,我是你三叔,你最近和学通有没有见面?二虎说,没有见,怎么了,三叔?老祝说,是这样,二虎,你现在不管忙不忙,叔拜托你个事情,你去学通家一趟,我刚接了个电话说学通干活受伤了,在杏园医院,你帮三叔去看看,你三婶现在急得不行。二虎说,能行了,三叔,你们先不要急,我去看,等我电话。老祝说,真的?你知不知道学通家在哪里住?二虎说,我知道,三叔,你让三婶先不要急,等我电话。
挂断电话,老祝安慰过妻子,坐在炕沿上边抽烟边等电话。不一会儿,家里烟雾大罩,妻子被呛着,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抽,一天天就是抽个没完没了。老祝在灶火口磕掉烟渣,收起烟锅,呆坐着等待电话。
一个多小时后还不见来电话,老祝等不住,起身到院子里站着,妻子嘴里不住地说,怎么还不来电话?是不是真出事了?要不我们现在就走……老祝心里也打起鼓,有了不好的预感,正愁急,手机响起,二虎打来的。
妻子抢先接起,说,怎么样,二虎?老祝凑近听。二虎说,没什么事,就是胳膊被板材压了下,不过你们得过来一趟。妻子哦哦几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老祝拿过手机,说,小敏呢?二虎,你让小敏接电话。二虎停顿数十秒,说,医院信号不好,叔,小敏急躁得不行,还要照顾娃娃,估计手机调了静音,你和我婶坐车过来一趟,医院有些手续要家属签字。
锅里还做着肉,妻子提前舀出来,往锅里续了水,老祝拿上积蓄不多的存折,关好门窗,往马路上走去。一时等不来公交车,不管来什么车,他们见车就拦挡,有辆小车停住,问他们去哪里。妻子说,去县城。老祝说,去市里得多少钱?司机说,去市里的话,看你们走不走高速,高速加上过路费得三百,不走高速就二百六。老祝说,三百就三百,走高速,麻烦你开快点,我们有急事。他们上了车,司机开着车一路狂奔,到市里杏园医院花费不到两个小时,比平时快了将近一个小时。下车后,老祝给那人打了电话。那人接了,说,你们在门口不要动,我来接你们。那人出来,脸色很差,吞吞吐吐地说,叔,婶,是这样,我是你儿子他们的房东,我要说的是,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人还在抢救,就是,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老祝意识到事情不对,说,不是做活把胳膊压了?
那人点点头,作难地说,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想发生,你们,唉。老祝说,你就直说,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能撑得住。妻子定定地看着那人,眼泪在眼里直打转,说不出一句话。那人说,我们发现你儿子他们时,他们已经昏迷不醒了,家里烟气很大,灶里还往外冒烟,于是,赶紧拨打了120送到医院,现在是,你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已经不行了,孩子还在抢救,看能不能抢救过来。妻子身体软成了面条,直往下溜,好在老祝眼疾手快给拉住了,说,我们先进去。妻子难过得哭不出来,嘴巴像是被谁封住了,脸色惨白,眼泪哗啦啦往下流,手冰得像玉石。
二虎在医院过道的椅子上坐着,见到他们,站起身说,叔,婶子,你们可要撑住啊。老祝强压住悲伤,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带我们去见见两个孩子。人已经进了太平间,二虎和那人在前面走,老祝扶着妻子跟在后面,进到太平间,来到两张盖着白布的床前,老祝慢慢揭开白布,学通和儿媳妇的脸出现,妻子封住的嘴被巨大的悲伤冲破,哇的一声,趴在孩子们身上放声大哭。老祝抚摸着娃娃们的手,抽泣着说,你们还没有给我过生日,你们说好的,要给我过生日,怎么能说话不算数,我和你妈把所有东西都置办好了。妻子号啕大哭,嘶喊着,你们两个没良心的,这让我和你爸怎么活,活活往死急躁人了,让我们两个老格桩活着做什么?两个没良心的,还说给你爸过生日……
儿子他们再难活过来,现在就看能不能把孙子救过来。老祝和妻子守在抢救室门口,医生们进进出出,老祝问个不停,得到的答案就是耐心等待,还在抢救。入夜,有医生出来,摘下口罩,说,孩子是抢救过来了,但大脑神经受到了损伤,通俗说,就是将来智力低下,恢复的概率很小。妻子说,救过来就好,人在就好,智力低下我们不怕,我们不怕。老祝说,好的,我们知道了,感谢您,您辛苦了。医生说,很是抱歉,没能把大人救过来,大人可能当时意识到了有烟,但身体已经难以动弹,就用最后的力气给孩子脸上盖了枕巾,这才使得孩子吸进去的烟少些,保住了性命。老祝和妻子再次感谢了医生。
老祝找了专业的人和机构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确认了儿子他们就是被烟闷了,没有他人侵害的迹象。房东拿出五万算作赔偿,老祝没有要,只拿了退还的房租。当天连夜找了车,叫来自家人,把儿子儿媳妇拉回老家,孩子还需要住院观察,老祝找来亲戚照看。妻子天天哭,哭成了泪人,谁来劝说都没用。老祝毕竟是男人,不能陷入无尽的痛楚,找来人看坟地和下葬的日子,自家人皆来帮忙,打坟、买棺材寿衣、买办事货物、搬运灵棚架子布等。
四五天时间全部结束,院子里留下办事时的油渍,搭建灵棚及摆放桌椅的痕迹,用不了多久这些就会消失,一切照旧,除了生活,与往日一样的生活。妻子疲累得睡倒,亲戚打来电话,说,医院通知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你看?老祝说,好,我这两天就去市里,正好也搬运学通他们生前租赁的房子里的东西。亲戚说,哦,我就是给你说说,老祝,不着急的。老祝说,我知道,感谢你帮忙,恩情难忘。妻子身体绵软,本说不去,老祝临去时,妻子改变了主意,说,这是娃们最后的生活痕迹,我不能不去,要去看看。老祝心疼地说,老婆子,你还是别去了,去了肯定又难受得不行,别说你,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控制得住。妻子说,没事,到时候控制不住,咱就不控制。老祝说,那不好,在人家院子里,哭泣不好,人家会嫌弃。妻子说,我们悄悄地哭,悄悄地伤心,悄悄地难过。
帮忙拉运东西的三保打电话来,老祝接起,三保说自己到坡底了,不着急,你们准备好咱再走。妻子拿梳子梳了几下凌乱的头发,从暖壶倒了热水,掺兑些冷水,洗了把脸,对老祝说,你也洗洗,老头子,这段时间你忙累坏了。老祝背对妻子站着,声音沙哑地说,我不洗了,我不忙不累,忙了累了好,你收拾好咱就走吧。妻子拿上卷起来的蛇皮包,说,走吧,老头子。三保开的是小型货运汽车,说,稍微挤一下,你们坐在驾驶室,暖和。妻子说,我和你叔就坐在后面的车斗子里,我们背坐着,也不冷。三保要再劝说,老祝看着已经走向后面车斗子的妻子,捏捏三保的肩膀,说,你不管了,有我呢,你去启动车。
车开动,他俩坐在车斗子里,背靠着驾驶室,妻子头依偎在老祝胳膊上,不一会儿,老祝的胳膊就感觉到了渗透棉衣的湿热,说,老婆子,别哭了,这样下去眼睛都要哭瞎了。妻子泣不成声。老祝身体僵硬,心里空荡。三保开得稳,怕颠到他们,三个多小时,到了学通他们租赁的房子。开门进去,看到房子里的一切,他们悲痛不已。三保说,叔,婶,我这里有个朋友要见面,我去见一下,你们先收拾,收拾好了给我打电话,我来给往车上搬。老祝说,好的,你忙你的,三保,我们好了叫你。妻子说,感谢三保,跑这么远。三保说了句没事没事便出去了。
妻子艰难地挪动脚步,用手摸索着房子里的东西,缓慢地哭出声来。老祝拿出带来的蛇皮袋子,看哪些零碎的能装就先装,装到儿子给他过生日买的东西时,积压的悲痛再也无法叠加,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手提不起那些盒子,浑身开始打战,蹲在地上呜咽起来。妻子泪流满面地走过来,蹲下抱住老祝,哭着说,老头子,我们没有儿子了,一个也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孙娃也没了爸爸没了妈妈,狠心的老天啊,你好歹留一个啊,没爸没妈的娃最可怜,都没有了……
老祝哭了一阵,用袖子擦干眼泪,长舒了口气,说,老婆子,我来收拾吧。
租赁的房子里的东西收拾完,三保也过来了,帮忙搬到车上,到医院去接孩子出院。老祝跑着办理了出院手续,孩子痴痴呆呆地看着他们,眼睛里没有光亮,忘记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亲戚抱着孩子坐在驾驶室,老祝和妻子坐在车斗里,妻子抱着装有儿子他们衣服的袋子,说,老头子,他们还在,他们的气息还在。老祝说,老婆子,你要坚强,我们还有孙娃,不能倒下。妻子说着说着又哭了,他们还在,他们还在,两个多好的娃娃,怎么就不能多活会儿,哪怕把我们的活头儿给他们,让他们活着,让他们活着。老祝声音颤抖,说,不能吗,如果能,立马拿去,让他们活着。
来时天还晴朗,这时天阴沉下来,感觉要下雪,冷风吹着脸颊,像是刀割,要割断他们滚烫的眼泪。
三
夜里,关了灯,孩子睡着,妻子躺在孩子旁,老祝胳膊肘放在枕头上,趴着抽烟。
妻子说,老头子,别抽了,会呛着孩子。老祝说,这锅抽完就停,睡吧,老婆子,别想了,活着的人还得活啊,何况我们还有孙娃要照顾。妻子看着漆黑的夜,说,孙娃也是受罪,还没长大成人,就成了这个样子,以后可怎么办啊。老祝磕掉烟锅里燃完的烟叶残渣,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想的和要做的事情,我们两个要商量个对策,做个决定。妻子没接话,寂静铺满老旧的窑洞和院子,不知过了多久,妻子说,你说的对,老头子。
这晚,他们想出了以后的生活要如何过。
村里所剩不多的人,都不敢来他们家,是好心,怕触及他们的伤心处,也是给他们留足时间来自愈。老祝没有闲着,接下来的日子和三孔老旧的窑洞、碎石头插垒的院墙较上了劲,用胶泥搅拌上干草秸,挨个进行修补。离开春还有些时间,妻子说,把院子里的地也重新翻翻,拢出梁子,来年好种,看要不要再在地周围围上栅栏?老祝打量着院子里的地,说,栅栏要的,我看在原来栽种过葡萄的地方继续栽种葡萄,天暖些,我给咱去找苗苗。妻子说,你看着弄外面,我看着给咱弄家里,各自分工,干起来。老祝说,能行,我想把院子外面那些土台子也翻整成地,种上花草。妻子说,你看着弄就好。
开春也意味着娃娃们要开学,孙娃这样是无法去的,老祝看着经常发呆发愣、不时傻笑的孙娃,说,孙娃,想去念书不?孙娃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很快嘿嘿笑起来。老祝说,好,咱才不稀罕去学校,咱在自己家里也能学习,不怕,爷爷虽然文化不高,但教你识字还是可以的,你可别看不起你种了一辈子地的爷爷奶奶啊。孙娃歪着头看他,嘿嘿笑。妻子一直在收拾家,把寒窑里放着不用的老瓮、筛子、簸箕、斗和升等全部拿出来,炕桌也放在炕上,供孩子平时趴着吃饭、写字、玩游戏。重新挪放了老柜子、老门箱,用抹布挨个擦一遍,把水瓮上挂的塑料马勺换成原来的铜马勺。
一场春雨过后,太阳出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老祝开始在院子里拾掇开的地上栽种,依着节气,将韭菜、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豆角、夏瓜、夏玉米等作物分别栽种上。坐在门道的老祝,看着院子,手托着下巴,对做饭的妻子说,老婆子,你有没有发现,还是差那么点意思,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来。妻子站住,环顾了一圈院子,笑起来,说,你真想不出?很简单的,看来你算不上合格的受苦人啊。老祝看着妻子,说,老婆子,你还记得你有多久没笑过了吗?妻子深呼吸了一下,说,不笑能怎么样。你这院子里光有地里长的,没有地上跑的。老祝恍然大悟,说,对啊,是这样,没有地上跑的啊,最近我就垒砌它们的窝舍。
妻子进到窑里,对着独自玩耍的孙娃,说,饿不饿啊,我的孙娃,饿了奶奶给你用铁勺勺炒鸡蛋,香得很,要不要吃?还有,以后咱也不用再去买鸡蛋,你爷爷很快就买回来鸡娃,鸡娃长大了就能下鸡蛋。孙娃自顾自地在炕上玩去年冬天收回来的大南瓜,看到南瓜在炕上滚动起来,便嘿嘿笑。
镇上逢集,老祝天不亮就起来,找来准备好的纸箱子和旧的铁笼子,觉得不够,再拿上蛇皮包。准备差不多了,坐下就着咸菜,吃妻子刚蒸出锅的馍馍和熬出锅的稀饭。吃毕,赶着驴车出大门,驴子哇喔哇喔叫几声,孙娃醒来,哭个不停,妻子只得给裹上衣裳抱出来,说,看爷爷赶着驴车去做什么?让我们来摸摸驴子的长耳朵。老祝拉住驴子,驴子好像也知道老伙计想让它做什么,温顺地凑过来,孙娃的小手伸过来,先是轻轻碰了下驴子的耳朵,随即小手张开抓住。玩了一会儿,老祝说,孙娃,爷爷得出发了,去晚了好的鸡娃、猪娃、兔娃、羊娃、牛娃、狗娃都被买走了。孙娃不愿放手,妻子硬是给掰开,他当即哭起来。妻子说,大概是没睡醒,我哄着再睡会儿,老头子,你路上慢点。老祝应声,赶着驴车出了院子,下了坡道,来到马路上,驴子踩着清脆的铃铛声,拉着自己的老伙计走开了。
到集上,兔娃、羊娃、猪娃、鸡娃顺利买到,狗娃和牛娃没有买到,狗娃应该是有的,往常逢集卖狗娃的很多,不知这集怎么没有,牛娃买不到罢了,因为就算买到板车也装不下、拉不了。老祝不甘心,赶着驴车又转了几圈,还是没有找到狗娃,那没办法,只能下集再说。回去路上,老祝遇到村里也去赶集的三老汉,三老汉见老祝买这么多牲畜,说,老祝啊,你这是要搞养殖啊。老祝笑着说,搞养殖这些哪里够啊,就是自己喂养着解闷,也能给孙娃玩,奇怪的是,集上没有卖狗娃的。三老汉咧着没牙的嘴,笑着说,狗娃我家里有三四个了,你要的话选上个,晚上就来捉走。老祝欣喜不已,说,能行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好三老汉。剩下的牛娃等过几天去邻村问问看,估计也有了。老祝赶着驴车,轻轻哼着小曲往回走。
回到家里,把鸡娃放在搭建好的鸡窝里,猪娃放在院子外面垒砌好的猪圈里,羊娃放在院子里的羊圈里,兔娃简单,放在兔子窝洞里。狗娃晚上去三老汉家捉。家里锅上冒着热气,老祝闻到熟悉的味道,说,老婆子,你在蒸黄馍馍?妻子说,你鼻子还尖,孙娃那会儿玩耍把个老南瓜从炕上推下来,摔成几瓣,现在天还能放,但也不敢放太久,我就弄了点豆豆,包了锅黄馍馍,等会儿就能吃了,甜甜软软。老祝看着还在玩南瓜的孙娃,亲热地说,你个坏种,这几个南瓜迟早要毁在你手里。孙娃不管,正玩得起劲。
黄馍馍确实好吃,老祝选定垒砌狗窝的地方,一后晌从外面搬运来碎石头,担了几筐胶泥,今天来不及,明天垒砌。吃过晚饭,老祝准备去三老汉家捉狗娃,妻子说,就这样去?老祝说,不然呢,还要怎么样?
妻子说,你是越活越憨了,人常说猫狗不白要,白要了不好养活,你给钱三老汉肯定不要,我给装起几个黄馍馍,你拿上。老祝说,老婆子啊,还是你想得周到。顺手提了黄馍馍,出了门。到了三老汉家,老祝选了个白颜色的狗娃,三老汉不要黄馍馍,老祝强给放下,说,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拿上。三老汉收下黄馍馍,让老祝坐了会儿,老祝说家里还有事不敢待,三老汉没多留,送出院子。
老祝把狗娃抱在怀里,狗娃一路上不安分,不是头探出就是腿踢蹬,快到家时,还给老祝身上做了记号,尿了一泡。老祝进到窑里,把狗娃放下,边换衣裳边说,这也是个坏种,也不坚持下,到家了还尿我一身。
孙娃看到狗娃,开心得不行,非要抱到炕上,妻子无法,只得同意。窑里昏黄的灯光下,温热热的,孙娃和狗娃在炕上玩,老祝换上衣裳,坐在炕边的凳子上,妻子双手交叉搭在胸前,看着孙娃,脸上有笑意。
第二天太阳出来,暖和时,老祝用碎石头、胶泥垒砌狗窝,垒好两面墙,去院子外面的石床上坐着喝水歇息,或边吃饭边看路上的车辆行人。歇息得差不多了,
回到院子,看到垒砌好的一面墙倒在地上,狗娃在边上疯跑,孙娃在后面追,老祝拉住孙娃,指着倒塌的墙,说,这是谁弄的?孙娃看着狗娃。老祝指着狗娃,说,是狗娃扑倒的?孙娃看着狗娃。老祝无奈,放开孙娃,重新去垒砌,到三点多,三面墙垒砌好,蹲得腰酸背痛,站起身去窑里喝水。不想,刚进到窑里,从暖壶倒了水,还没来得及喝,就听到轰隆一声,跑出去看,见狗娃和孙娃在倒塌的墙跟前愣住,老祝赶忙检查孙娃、狗娃的身体,没有受伤,严肃地说,你们两个谁做的?是谁?
孙娃看狗娃,狗娃看孙娃。妻子在旁边捂嘴笑,老祝说,老婆子,你笑什么?妻子说,你看他俩装得多好,孙娃装得更好。
老祝顿时明白过来,说,孙娃,是你推的对不?孙娃看着狗娃嘿嘿笑,狗娃对着他吠叫起来。妻子说,算了,你加把劲一口气垒砌好,不然永远垒砌不好,狗娃、孙娃有时都不是好娃。老祝用食指在孙娃鼻子上轻碰了下,说,我看就是你,孙娃带坏了狗娃。
四
天越来越暖和,院子里的蔬菜庄稼先长起来,院子外土台子上的花也长出嫩芽。川地大概有两亩,老祝和妻子商量,说,种上一亩西瓜,半亩玉米,半亩花生,豆子、谷子、洋芋、麻子、芝麻这些种山里。妻子说,玉米不用专门种半亩,西瓜下架时就可以在中间种玉米。老祝说,也行,那就种上一亩西瓜,半亩红薯,半亩花生,豆子、谷子、洋芋、麻子、芝麻这些种山里。妻子说,能行,后面想种的都种山里,山里地多。说做就做,天气好时,老祝和妻子带着孙娃狗娃去川地里翻地播种,提前和村里有牛的人家借好牛,前一天晚上拉过来,第二天给套上犁铧,再把架在驴子身上的两个大筐子架在牛身上,一边放孙娃、狗娃,一边放吃食、种子、毯子。到地里,老祝赶着牛犁地,孙娃和狗娃在犁过的地里跑动玩耍,妻子先歇着,地要犁两遍,第二遍时妻子跟上撒点种子。为节省时间,晌午不回家里,把带来的吃食放在铺展的蛇皮包上,暖壶里装有稀饭,饭罐子里有炒菜、馍馍,各自端上碗坐在地里吃。大人和孙娃端着饭自己吃几口,给狗娃扔一些。
后晌,老祝赶着牛,孙娃、狗娃来时样坐在大筐子里,妻子担心孙娃睡着,就说着话,两个大筐子,一个有吃食,一个有孙娃,哦,不对,忘记了狗娃,孙娃和狗娃都是爷爷奶奶的好娃。孙娃直打瞌睡,老祝说,马上就到家了,回去了吃点再睡。两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轮番着说,回到院子,放下筐子,妻子开了窑门上的锁,先进去按开灯,孙娃直奔窑里的炕上,狗娃舒展开四条腿,跟着狂奔。妻子说,孙娃和狗娃在炕上玩会儿,奶奶给你们做西红柿鸡蛋疙瘩汤,可好吃了,很快的。老祝把大筐子放好,牛拴在棚子里,去寒窑里抱出草料,看到草料,羊娃蹄子架在圈门栅栏上,咩咩叫,牛娃走动起来,哞哞叫,驴子摇着头,哇喔哇喔叫,猪娃听到动静,跟着哼哼……
老祝边往它们跟前走边说,不要急,都有,都有,慢慢来,让我老祝也缓口气。
西红柿鸡蛋疙瘩汤做好,孙娃睡着,狗娃卧在跟前也睡着,妻子推孙娃让起来吃饭,孙娃没好气地推开妻子的手,妻子再推,孙娃继续推开,接着便哭了起来。妻子说,算了,睡吧,等什么时候醒来了,再给热着吃,老头子,咱先吃吧。老祝舀一碗,蹲在地上吃,妻子舀多半碗,站在灶边,边吃边看着熟睡的孙娃,说,今天地里跑累了,晚上可能尿床呀。老祝说,保准尿床。
孙娃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妻子手伸到被子里,摸了会儿,说,怪事,竟然没尿。老祝说,再往下摸摸,孙娃睡觉,有时满炕滚了。妻子再往下摸,停住手,说,果然,就是尿了,还不少,坏小子,真是印地图了,还是世界地图。老祝看着刚醒来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孙娃,说,听见没,你奶奶说你印的是世界地图。
入夏后,院子里外最是好看,村里有人来串门,没进院子就说,你们老两口这是要把这老院子打造成童话王国啊,看看,什么都种着了。老祝到地里摘几根黄瓜,在水管上洗净,递给串门的人,说,尝尝。串门的人说,这要是童话王国,你们老两口就是老国王和老王后,孙娃就是王孙,不,是精灵。妻子前两天去地里看西瓜的长势,顺手摘了两个回来,当天切了一个,吃起来不错,还剩一个,抱出来,放在院子的石床上,说,今儿你们有口福了,提前吃点西瓜。刀子刚切进去,西瓜就砰砰几声,裂出缝来。串门的人说,这会儿的西瓜能有这声响,好啊,以后我要多来吃。妻子把西瓜切成牙状,放在盘子里,让他们自己拿,说,尽管来吃,地里多着呢。
串门的人吃过西瓜,在院子里外转悠观赏,说,现在村里还有几个人喂养和种植这些牲畜和蔬菜庄稼,你们好家伙,样样数数都有。妻子说,闲着也是闲着,种上自己能吃也能卖的,多好的事情。老祝去院子边的空地上扛几根胳膊粗的木棍,经过院门时,对妻子喊,老婆子,把寒窑土台子上放的蛇皮包给我拿出来。妻子说,要那做什么?老祝说,里面装着斧子、铁丝、钉子、锤子这些,我搭棚子用。串门的人帮忙去拿,拿到后边往老祝跟前走边说,老祝,去哪里搭棚子?老祝接过蛇皮包,神秘地说,你们猜?
串门的人说,家里又不是住不下,你搭棚子做什么?老祝要走,不再神秘,说,去西瓜地搭棚子啊,有了棚子好后面照看西瓜。串门的人嗐一声,说,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现在村里有几个人嘛,孩子更是不多,你照看什么西瓜?没有人来偷的。老祝玩笑地说,照看西瓜不是怕人偷了,就是想在西瓜地睡觉,我们是照看自己。串门的人说,还真是童话王国的人,成老顽童了。
搭建瓜棚子老祝下了功夫,搭得结实不说,还给外面做了设计,能推拉,就像敞篷车。老祝自夸地说,我这可比敞篷车高级多了,有三层,一层布,一层塑料,一层防晒网。遇上好天气,白天用布和防晒网,晚上全不要,躺着看天、看月亮、看星宿;遇上不好的天气,用塑料来遮风挡雨,躺在里面听风听雨。孙娃带着狗娃跟着去过很多次,体验了个遍。那天晚上,院子里闷热,妻子说,不如去瓜地。老祝当即同意。孙娃非要带狗娃,妻子为防止狗娃夜里跑不见,给狗娃套了绳,孙娃牵上。几人先到瓜地里坐着吃了西瓜,然后到瓜棚里躺下看天、看星宿,孙娃和狗娃躺在他们中间,孙娃手指着天空,咿咿呀呀,狗娃翻搅,一会儿卧下,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瓜棚里有毯子、枕头,他们没回去,就那么盖着睡着了。睡到半夜,感觉脸上凉凉的,老祝睁开眼,伸手摸了一下脸,竟然是水。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过来阴云,黑沉沉的。渐渐地,雨滴就密集起来。老祝跳下瓜棚,赶紧往开拉布和塑料,妻子醒来,老祝已经拉好了布和塑料。瓜棚口子老祝也设计得好,布和塑料严密地塞进木头架子里,风再大也刮不起来。
随即打起雷,孙娃和狗娃被惊醒,孙娃紧紧抱着妻子。妻子说,不怕,有奶奶在呢,看爷爷的瓜棚好不好。老祝想起棚子里挂着煤油样的挂灯,伸手找到,扭动开关,煤油灯火苗样的灯泡亮起,整个瓜棚被照得黄黄的。外面狂风大作,雨滴落在棚子上,挂灯还不时摇动,越发温馨动人。孙娃慢慢不再害怕,嘿嘿笑起来。
最炎热时,老祝在村里的河流处找到最干净和深浅合适的水洼,保险起见,自己下去又清理了几遍底下的碎石头和淤泥。晌午,孙娃不睡,头也不转地看动画片,老祝说,要不要去耍水啊?孙娃不感兴趣。老祝就带着狗娃走,孙娃看到,站起身追出来。老祝控制好脚步的速度,走走停停地来到水洼处。狗娃先欢快地跑到水边,眼睛里满是想下去玩耍的渴望,身体却不敢,孙娃跟着跑到跟前,蹲下看着狗娃,指着狗娃笑起来。孙娃笑会儿站起身,到边上脱掉鞋和衣裳,重新回到水边,摸摸狗娃的头,“扑通”一声跳进去,然后用手不住地往在水边站着的狗娃身上扬水,狗娃急得在岸边来回跑动。孙娃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狗娃忍不住,前腿在水里轻轻试探,一不小心,跌进水里,孙娃游过来抱住狗娃,狗娃一脸惊慌,看到是孙娃,便也开心地游动起来。
五
上秋最忙,地里种得多,都得往回收割。川地里的都好说,可以套着架子车拉回来,山里的不行,先得收割下来,背到山下的宽路上,然后才能用上架子车。忙起来,妻子就得跟着去,自然少不了孙娃,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也不放心。山里东西多,孙娃也愿意去,老祝冒着给吃坏肚子的风险,一会儿给烤玉米,一会儿给摘酸枣,一会儿给烤红薯、洋芋。孙娃拿着散发着香味的热滚滚的玉米,左右手来回倒换,最后还是没拿住,掉在地上。妻子捡起来给擦了一番,看玉米粒的缝隙里还有少许泥土,说,老头子,给重新拿个。老祝说,没事,就吃那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泥土嘛,又不是别的东西,你说是不,孙娃?孙娃没看老祝,从妻子手中拿过玉米,大口啃起来。
庄稼都收割回来,但拾掇、脱粒得一样一样来,先是洋芋,老祝按大小简单分拣,分别倒进洋芋窑子和地窖里。谷子今年长势不错,谷穗子沉甸甸,老祝整修好多年不用的连枷,甩开膀子挥动,别看是老物件,效率却不低。看捶打得差不多,把大的杂物拣出去,细小的杂物用扇车过一遍,不行再用簸箕扬一遍。妻子当晚就熬了小米稀饭,糊糊的,浓纯的米香味。芝麻没用连枷,用棍子捶打,种得不是很多,毕竟是调料,吃面、吃洋芋撒上都很香。花生的收成是老祝没想到的,就在一块窄窄的地上种了,抛挖时发现一棵比一棵结得多,最后摘了两大包……孙娃狗娃看着院子地上晾晒的花生,定定站着,久久出神。老祝担心孙娃带着狗娃,或狗娃带着孙娃调皮捣蛋,想起前两天三保爸让去打枣,便带着孙娃、狗娃去。三保家枣树多,村里人多时,人们会抢着去打,这几年村里人大部分出去了,剩下年迈体弱的,有心却无力去打,经常是等枣自然熟透掉落。他们来到枣林,挑选几棵枣树,孙娃等仰头看树上红艳艳的枣子,狗娃四处欢跑,不时也抬头看,老祝吆喝着,看好了,枣子雨要来了,用杆子对着枣树枝条一敲,红艳艳的枣子哗啦啦掉落,孙娃嘿嘿笑。老祝把杆子给孙娃,孙娃吃力地拿着杆子敲打……
地里拾掇完,天就转凉了,院子里的蔬菜蔓子老祝没有清理,就那么放着,这样看着不会很空。开春那会儿,为给孙娃喝羊奶,老祝就买了只母羊,母羊不知何时受的孕,怀了羊娃,就这几天生产,老祝和妻子皆打起精神,孙娃指着怀有羊娃的母羊肚子,咿咿呀呀不知说什么。妻子夸赞着说,我孙娃现在可以咿咿呀呀说话了,你是问这是怎么了吗?孙娃面露恐惧,指着羊肚子,仍旧咿咿呀呀。妻子说,孙娃不要怕,这是羊妈妈生育小羊娃了,用不了几天你就能看到可爱活泼、白花花的小羊娃。老祝抱起孙娃,将其放在羊圈土墙上坐着,看得更清楚,羊妈妈难受地时站时卧,眼睛里却有光,估计是也为自己即将生下新的生命而激动欢喜。孙娃看了会儿,打起了瞌睡,妻子带他到窑里去睡觉。
羊妈妈生下小羊娃是在两天后的早上。
保险起见,老祝叫来兽医。为了看羊妈妈生小羊,孙娃起床穿上一只鞋就跑出去了,老祝还是把他放在羊圈土墙上,孙娃盯着看。小羊娃从头到脚慢慢出来,瘫卧在地上,羊妈妈要看,老祝给抱到眼前,羊妈妈用舌头舔着刚出生的羊娃,等第二只羊娃出生时,第一只羊娃已经可以颤悠悠地站起来了。孙娃开心地拍手,妻子一把抱住孙娃,说,孙娃能知道这是好事,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后羊妈妈生养了六只小羊娃,有一只夭折,剩下五只。接下来的时间,羊妈妈没有那么多奶水,小羊娃也虚弱,老祝买来奶瓶和奶粉,每天给喂。孙娃就跟着看,有时也拿着奶瓶给喂,还用手抚摸,嘴里咿咿呀呀。
入冬,妻子早就给孙娃做了暖鞋、棉袄和棉裤,孙娃穿上亲得厉害,每次做完饭,灶里有火,老祝就拿两颗洋芋和红薯,顺手抓把花生,放在灶上的铁盖子上烤。后锅里的水滚得咕嘟咕嘟响,妻子坐在炕上纳鞋底,老祝扒拉翻动花生、红薯、洋芋,孙娃在炕上玩玩具。门紧闭着,窑里暖融融,空气迅速被快烤熟的红薯的香甜味占据,妻子利用穿针引线的间隙,说,红薯这些烤熟了吧?老祝用手指戳戳红薯和洋芋,说,差不多了,你们过来吃吧。孙娃和妻子过来,老祝掰开红薯和洋芋,分别递过去,说,慢点吃,小心烫嘴。吃时,老祝说,老婆子,再不多久就是你六十岁生日了。妻子说,不过了吧,这状况。老祝挖锅烟叶,点上抽了口,说,你忘记我们说好了的,不仅要过,还要好好过,而且往后咱们的每个生日都得过。妻子说,那就过。
生日临近,老祝和妻子带着孙娃,赶着驴车去镇上集市置办货物,还是那些,一样不少地置办。路上妻子偷偷抹眼泪,老祝说,老婆子,做我们能做的,不要过于责怪和勉强自己。妻子叹了口气,搂抱住旁边坐着的孙娃,在他额头上亲吻,说,我们的好孙娃,狗娃今天没被带出来,估计要生气失落了。老祝说,没事,今天给狗娃买点肉肉,回去给喂上,这个事情让孙娃记上,免得我们忘记。妻子对着孙娃说,听到你爷爷说的了吗?你给咱记上,我们要给狗娃买肉肉吃。孙娃不知看着哪里,小手指着,嘴里咿咿呀呀,然后嘿嘿笑。
置办完货物,老祝提醒妻子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买,妻子想想,说,好像没有了,都置办了。孙娃手摸着肉肉,老祝说,肉肉等回去了,奶奶做熟了吃,生的不能吃。孙娃还是摸着,妻子说,置办好了咱就回,一会儿怕是要变天,像要下雪了。老祝赶着驴车,妻子和孙娃坐着,驴子脖子上的铃铛摇响得清脆悦耳,路上过往车辆里的人皆投来惊异和羡慕的目光。回到家里,老祝往窑里提东西,狗娃跟着跳着闻嗅,妻子看到肉,叫喊着说,老头子,我就说忘记什么了,忘记买狗娃吃的肉肉了。老祝说,对啊,就说少买了什么,我想起了,是我们不对,要回来时,孙娃当时用手摸肉肉了,那可能就是暗示了,是我们太迟钝了。妻子抱起孙娃,说,是不是这样,孙娃?孙娃心在狗娃那里,挣扎着要下去,狗娃跑到院子里叫着,像是催孙娃快点出来玩耍。
六
生日那天,老祝和妻子忙活着做吃的,前锅炒着菜,后锅蒸着酥鸡、丸子、米饭这些,孙娃和狗娃在院子里玩。听到狗吠叫,老祝就喊,孙娃,不要和狗娃打闹,外面冷,回家里来玩。话音刚落,门被推开,窑里水汽笼罩,难以看清人,妻子说,到炕上去,一早上也不知道冻,要玩也要等太阳出来啊,暖和点。人站在门口,没有要进来的意思,老祝正蹲着剥蒜,抬起头想说要进就快进来,却停住,隐约看到是个个头高大的人影,站起身,把剥好的蒜放在锅台上,边往外走边说,你是哪个?切油糕的妻子也停住手中的活儿,怔怔地看着。人影说,我是走街串巷给照全家福的,路过你家坡底,你家孙娃给我招手,我说要照相?你家孙娃点点头,我就上来了。妻子说,我们不照全家福,不好意思啊,是孩子胡闹了。照相的人说,没事,没事,打搅了,便退出去。
一会儿,孙娃和狗娃前后脚地进来,疯头疯脑地在窑里跑一圈,又跑到院子里。老祝担心他们摔倒,等孙娃再跑进来时,说,你们两个跑慢点,这是做什么呢,跑进来跑出去。孙娃跑过来,拽住老祝的衣裳,直往外拉。老祝说,外面有什么啊,孙娃?孙娃不管,就是往外拉拽,老祝无奈,跟着来到院子,没见有什么,说,孙娃,什么都没有啊。孙娃继续往院子外面拉拽,老祝跟着出去,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孙娃,怎么了?
你要什么?孙娃小嘴咿咿呀呀,小手拉扯老祝太用力都红了。老祝看着心疼,说,要什么给爷爷说,爷爷带你去找。孙娃红红的小手指着能绕转到前面大路上的小路,再次拉拽,狗娃像是明白过来,赶紧跑出去。老祝喊,狗娃,回来,别瞎跑!孙娃使劲扯拽老祝的衣裳,老祝看狗娃跑得不见了,抱起孙娃去追,狗娃是孙娃的命,不能跑丢。
老祝抱着孙娃边追边叫狗娃,绕转几个弯,老祝看到了狗娃。老祝呼喊狗娃站住,狗娃不站住,时不时回过头朝着他们吠叫几声,继续跑。老祝自言自语,狗娃今儿是翻天了,跑那么快、那么远。孙娃却一脸镇定和开心。快到大路上时,狗娃放慢了速度,老祝也追上,正要训斥狗娃时,听到转弯那边传来声音:照全家福,上门照全家福。狗娃看老祝追上来,继续往前跑,转过了弯再跑一会儿,看到了刚才来家里照相的人。照相的人看到奔跑的狗娃和抱着孙娃气喘吁吁的老祝,便站住。狗娃跑到照相人跟前停住,老祝也到了跟前。照相人说,要照相?
老祝抱着的孙娃伸出小手,指着照相人胸前挂的相机,咿咿呀呀。老祝说,那不能要,孙娃,那贵着呢。孙娃不管,哭闹起来。照相的人见状,说,这样,大叔,我都走出这么远了,你们还追过来,不管是孩子想玩照相机还是怎么,总之是缘分,我去给你们照一张,那会儿在门口闻到你们锅里蒸煮的香味,想是今天也不同,我可以多送你们几张,这都是缘分。老祝看了眼哭闹的孙娃,说,也好,照一张,也难得,错过了机会想照也照不成了。
照相的人跟着老祝重新回到院子,窑里的妻子听到他们回来,说,这么半天跑哪里去了?老祝放下孙娃,进到窑里,说,老婆子,我们还是照一张吧。妻子看了他一眼,说,不照,要照你去照。老祝走到跟前,低声说,老婆子,照一张吧,我们这年岁、这身体,还能有多久啊,能给孙娃留点念想也是好的。妻子手中的油馍馍面团掉在锅台上,眼泪吧嗒吧嗒掉落。
老祝拉着妻子的手,走出窑洞,照相的人选好地方,去窑里拿两张板凳,放在选好的地方,说,你们看是怎么照?你们两个坐着,抱着孙娃,还是你们两个坐着,孙娃站你们前面中间,身子倚靠着你们?老祝说,都来一张吧。孙娃见他们过来,走到跟前,他们坐下,老祝要抱孙娃,孙娃不要,妻子说,那奶奶来抱孙娃,孙娃也不要。孙娃拨开他们相挨的腿,站进去,两只小手分别放在他们的大腿上。照相的人说,这样也好呢,你们的孙娃一看就照过相。就在照相的人要按快门时,孙娃抬起头看了一眼老祝,用手拍拍老祝的大腿,说,爸爸。然后转过头看了一眼妻子,拍拍妻子的大腿,说,妈妈。
(原载于2023年第2期《创作》)

王闷闷,1993年生,陕西省子洲县人。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百名优秀青年作家扶持计划、西安市委宣传部百名优秀青年文艺人才计划。在《作品》《湖南文学》《延河》《西部》《雨花》《草原》等全国各大刊物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咸的人》《米粒》《日月》,中短篇小说集《零度风景》。现居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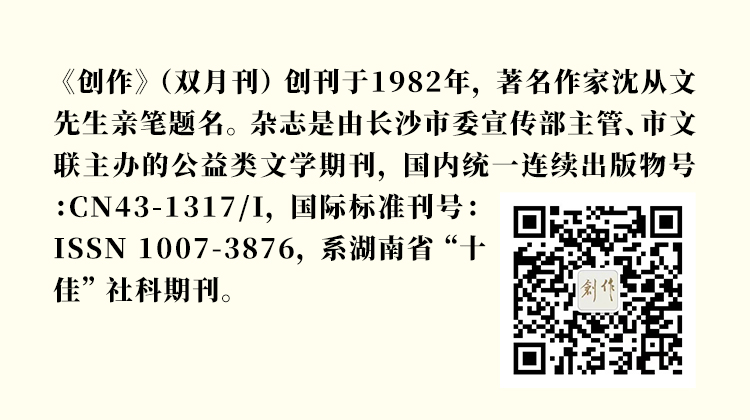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王闷闷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艺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3/66/13075516.html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