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心的痣
文/杨震
一
小杨同志,俺这地方,山好,水好,空气好,风景更好。要在前几年,俺一定带你到处走走。可惜现在腿脚不灵便,不听俺使唤了。
住在山里千般好,也没城里好,不用你说。山里湿气重,风多雾重,你看这天,明明大太阳,林子里却见不到几丝光线。住久了,还落下一身慢性病。光这两只手,没一根手指是好的,你看看,关节全变了形。
你这大老远的,翻山越岭看俺孤老头子,送温暖、送关怀,俺不知怎么感谢才好呢。山里人,不晓得说客气话,但俺说的绝对是心里话。
你刚才说的,句句在理。按理,俺应该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搬下山去享福。但俺现在真不能走,俺要走了,俺儿就找不着家了。自从俺儿找不着后,俺在这里等了足足二十三年,就为等他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俺什么时候搬家,要得不?
你最好别听隔壁那拐子的,他的话听不得,十句有九句是假的,还有一句半真半假。俺不晓得这拐子为啥不走,人家都走了他还赖着不走,他才是真正的“钉子户”。他那鬼脑壳,一天到晚不知想的啥!不满足他的要求,他肯定不会走。
俺不是那样的人,俺从来没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俺一个人,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只要俺儿回来,俺铺盖一卷,二话不说,立马下山。
跟这样的拐子做邻居,俺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老话说,搬不走的是邻居,打不走的是亲戚。俺不这样认为。俺认为,平时连招呼都不打、见面跟仇人似的邻居,绝对不是好邻居。住在一块儿,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俺没想通的是,你们来了这么多次,怎么没把这个祸害劝走,他赖在这里不走,到底想干啥?
俺晓得,俺晓得,你不用再劝了。这一大片林子,俺先替你们守着,不要国家一分钱,就算让俺暂时住在这里的条件,行不?
等哪天国家安排专门的山林巡逻队,哪天俺实在走不动,彻底死心了,一切听你们的,你们不要俺搬,俺也主动搬。
政府的移民政策好,没说的。现在讲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科学发展,讲绿水青山,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些年,这片林子绿得不能再绿,溪水清得不能再清了,连水底下的石头都闪闪发光,俺打心眼里佩服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让俺们全搬走,为的是让树木们好好地长,鸟儿们快活地叫,走兽们自由地跑,俺比哪个都懂。俺在这片林子里住了几十年,闭着眼都数得出林子里有多少条路、多少座岭、多少种野兽,要说没感情,那是假的。如今政府号召俺们搬下山,不就得执行吗?俺不是找借口,俺儿不回来,说一千道一万,俺也不走。
你说猪栏里的小野猪怎么回事?小同志,没白来,看得还挺细致的嘛。难得出回山买仔猪,只能到山里抓只野猪来养,反正野猪多如牛毛,不差这一只。怎么抓的?
用手抓的,你不信?俺现在腿脚不灵便,不代表手不快。哈哈,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难得今日高兴,有人跟俺说话,愿意陪俺说话。是这么回事,前天下午,一大群野猪在番薯地里拱,俺好不容易种的几垄番薯,不能看它们拱吧,便敲起了铜锣,铜锣甩在门槛边呢,就是那面破铜锣,看见没?
没想到,铜锣铛铛铛一响,野猪们箭一般四处乱窜。只有这可怜的小东西吓傻了,慌了神,两条前腿扎在石头缝里出不来。看见俺靠近了,惊声尖叫,挣扎,哪想到,越挣扎,腿扎得越深,把两条前腿都快弄折了,石头上到处沾了血,看着让人心疼。俺走得越近,这野东西叫得越惨。实在挣扎不动了,才哼哼着肯让俺抱回来。俺给它上了点草药,包扎好后放在猪圈里养,反正猪圈空着也是空着,就当养着玩,也算给俺做个伴,没事的时候跟它说说话,给俺解解闷。
等养利索了,再放回去。野兽嘛,终归是野的,养不成器,不如还它自由,让它快活。
跟人不一样,人不管走多远,还是恋自己的窝,是不是?
一只小猪崽,没多少点肉,不够塞牙缝的,没想吃它的肉,真的想吃,你来也见不着它了。养大了也不吃,更不卖,别人也休想吃它的肉。还是那句话,放走。俺从不说假话,自打俺儿不见后,俺就不吃肉,俺儿是俺心头肉。找着俺儿了也不吃,俺在山神面前起过誓的。
小杨同志,你以前来过这儿吗?第一次来?一个人在山里走,不怕吗?现在这山里林深树密,走的人少,草木早遮了路,没人指路,容易迷路,很难找到这山沟沟的。如今的野兽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根本不怕人。前天傍晚,俺还见过山猫子,眨着绿莹莹的两只大眼睛,蹲在树上,老远看,以为是猫头鹰呢。你出山的时候,千万防着点,这家伙看着畏人,绝对是个“投机倒把分子”。
依俺说,你别把心思都花在俺身上,有时间的话,多劝劝隔壁那个拐子。一家的顽固分子,给他们好好上上课,讲讲道理,把他一家说动了,俺给你烧香磕头。一天到晚在俺眼皮底下晃,看见就心烦。
你要实在想帮俺,回去帮俺打听打听俺儿的下落吧,俺相信俺儿一定活着,正找俺,或者,等着俺找他。可你看,俺这身子骨,俺这空荡荡的家。
年轻的时候,俺找过,但凡有点线索,千里万里都找去了。什么?你带俺出山,帮俺找?先去采血?才不去,都是骗人的把戏。先前俺采过几次,血都抽了好几管,抽完后,几个白大褂要俺等,俺就一直等,你看,俺等得胡子都花白了,俺儿呢?再说,这时候下山,万一俺儿这个点回来了,俺不在家,他如何进得了门?
俺要给小花猪喂食去了,不是赶你。那小东西,好像从没吃饱过,从饿牢里放出来似的。玉米棒子、番薯块,见了就啃,嘴没消停过,嘴一停下,就不住地哼。丢了点番薯藤,被它拱到边上当窝睡了,根本不吃,怎么得了,只拣好的下嘴,惯得嘴都刁了,上辈子欠它的。
二
报告领导,这次代表指挥部跟他们谈了,效果还是不好,没达到您的预期。
谈谈我的感受?好吧,第一次进麻布大山,我还是挺好奇、挺激动的,感觉好熟悉、好亲切。小时候就在麻布大山这样的林子里过活,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一家子突然出现在城里了。大了后问爸妈,才晓得这些不连贯的记忆是真的。他们说我是领养的,说我是山里的孩子,他们支持我早点找到亲生爸妈。不知道养父母这么说,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至少是通情达理、为我考虑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
我觉得麻布大山这名字挺有意思。麻布线条一样的小路,密密麻麻,分岔多,人走进去,如同走进迷魂阵。麻布眼似的山头,一座接一座,看着不远,走老半天走不到山脚。一路上,攀岩过溪,到处鸟语花香,树木遮天蔽日,人像在画里穿行,新鲜、有趣,根本不觉得疲倦,跟回自己家一样。在这样的山中走着,竟然没迷过一次路,您说怪不怪。尽管林子里时不时蹿出走兽来,常常吓人一跳。
可气的是,想了一路的话,打了一路腹稿,到了两户人家后,跟他们一说,全被两家户主用相同的话给呛了回来。什么话?那两位老人家絮絮叨叨说了不少话,归根结底一句话:打死不下山。
两个怪老头,一对老冤家。您别怪我这样评价。他们之间好像误会很深,相互间不理睬。我不明白的是,怨恨这么深,他们为啥还一直守着对方为邻。我给两位老人家分别说了,房子早给他们备好了,什么也不用搬,煤气灶具、锅碗瓢盆、床上用品一应俱全,人到了就给钥匙。他们不信,既不看我手机上新房的照片,也不听我的耐心劝告,他们只管说他们的。我说如果不去住,下山参观一下也行。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在山里住了一世,过惯了自由散漫的日子,不想再搬家遭那份罪,反正就是那意思。张进喜还说,修的房子一排排,看着像牢房,没有自留地,没有套牲口的地方,把大家集中关一块儿,想干吗?我哭笑不得,不得不耐心解释,哪是关你们,是请你们在一起居住过日子,集体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指着照片给他们看,周围没有铁丝网,没有站岗放哨的,周围全是花花草草,美着呢。住进去的人,年满六十的,国家负责养老,只管吃,只管住,只管睡,只管玩,什么都不用操心;未满的,国家负责培训好了直接上岗,不用出远门找事做,当然,想要更好的发展,也不拦着;小的,国家送去读书,一直读完高中,不用掏一分钱。比在山里刨食的日子不知好到哪儿去了。最后,张进喜答应来看看。廖老根犟脾气,说不动。
他说岁数大了,走不动了,也不想走了,走一个来回至少两天,出去了,家里的猪和鸡谁来喂?
什么猪这般金贵?野猪,一头小野猪,身上的花纹像椰子皮,棕白色的,见到生人,在猪圈里上蹦下跳,哼哼唧唧。廖老根还在猪栏外跟小野猪尽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什么等你长大了,小冬该回来了;什么我们一起到垭口去接他,等等。一人一猪,有说不完的话。
是的,廖老根有个儿子,叫廖小冬。老人家一说到儿子,跟换了个人似的。他说他儿子小时候特别聪明,胆子特别大,把他儿子一个人放在深山老林,不管多久,都能完好无损地找回家。有一次跟邻居张进喜一家出山赶集,在圩场里走丢了。张进喜找了大半天,没找到,急匆匆赶回家说了情况,廖老根没当回事,认为儿子自个儿会找回来。
结果等了一夜,儿子没回来,他这才着急下山找,没找着,便认为张进喜将他儿子拐卖了。如果没卖,他儿子肯定能回来,廖老根渐渐对张进喜产生了恨意。但他又不甘心,每年农闲的时候出去找几个月,每次都失望而归。后来老伴死了,自己年纪也大了,找不动了,没再继续找,在家痴等儿子回来。
这是他不肯下山的主要原因。还有什么原因?没了。硬邦邦一句话,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什么时候下山。
至于张进喜,只说廖老根什么时候搬,他就什么时候搬,绝不拖延一分钟。如果廖老根不搬,他也不搬,就在那里陪着,陪廖老根陪到死。我认为,所有的根结都在廖老根那里。所以,是不是跟公安部门联系下,先帮忙找到廖小冬,找到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建议我也去采血,早日找到亲生父母?
谢谢,谢谢领导关心,先前真没往这方面想,您提醒了我,我听您的,就去。
三
小杨同志,你能登门,俺很感谢,俺代表全家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有你们这么一群知冷知热、想着俺们老百姓的人。不是俺不想搬,俺跟先前来的领导多次说过,廖老根不走,俺不走,俺要等廖小冬回来了再走。俺要廖小冬当着俺的面,当着他爹廖老根的面亲口说,到底是俺把他拐走的,还是他自己把自己弄丢的。
这么多年来,俺跟廖老根的心情一样,难受,内疚,不安,像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每天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如果有,俺肯定不会带廖小冬出山赶集,哪怕廖小冬抱着俺的后腿。
那天一早,廖小冬在俺家里玩,非要跟俺儿春生一起赶集。他们打小在一起耍,好得跟亲兄弟似的,春生也非要拉着廖小冬一起去,俺就答应了。那时,俺跟廖老根一家关系挺好的,他叫俺喜哥,俺叫他根弟,基本上每天都走动,两家的孩子,只要一家大人外出,另一家就帮着带。出发前,俺觉得带廖小冬出远门,还是要当面跟廖老根说一声稳妥些,免得到时廖老根不晓得廖小冬的去向,到处找。去他家一看,铁将军把门,两口子早早到山里劳动去了。你知道,俺们这里的山地,石头多,不成片,东一小块,西一小块,间隔又远,很难知道他们在哪儿劳动。当时想,或许下山的路上能碰上,赶集赶的是时辰,耽误不得,便拉着廖小冬一起出了门。
下山的路上一直没看见廖老根,在路两边到处找,为此还耽误了些时辰,又不能把廖小冬丢在半路上,只好带到了圩场。两小子正是贪玩的年龄,一到圩场,便变成了飞天蜈蚣,一眨眼工夫,人不晓得飞哪儿去了。俺当时没太在意,想这俩小子在一起,秤不离砣,能飞到哪儿去,等打完货,再去寻他们不迟。
等到背篓里装满货,再去寻他们,怎么也寻不着。俺在圩场来来回回找了五六遍,才在一家牛棚边找到睡着的春生。问廖小冬哪儿去了,春生说在人多的地方跟廖小冬走散了,他也哭着找了小半天,找俺,找廖小冬,谁也没找着,找累了,就在牛棚边睡着了。这时俺才真着急,带着春生发疯似的在圩场上找,一直找到天黑,圩场的人散尽了,还没见人,这才失望地回家。
带着侥幸和不安,俺回来没落自己屋,直接奔去廖老根家,看看廖小冬回来没有。
廖小冬这孩子,平时跟个小野猪似的,不管白天怎么跑,到晚上,总能找到自己的窝。
廖老根在俺面前将廖小冬的能耐夸过不少次,夸上了天,俺还真信。有那么几次,廖小冬不知在哪片林子里野,天黑了不见人,他娘到处寻,去俺家找过问过,结果没过多久,廖小冬自个儿回了家,虚惊一场。
扯野了,小杨同志,你看人一上年纪,啰里啰唆的话就多,但俺还得说。当时,廖老根一人蹲在门口抽闷烟,廖小冬的娘不见人,像往常一样,到处喊山,扯着嗓子喊,十里八乡都能听见。俺告诉廖老根,白天带小冬和春生赶集,小冬跟俺们在圩场上走散了。本以为廖老根会站起来跟俺理论一番,俺做好了挨骂,甚至挨打的准备,没想到廖老根心真宽,蹲在那儿一动不动,猛抽了几口烟才抬起头,瓮声瓮气对俺说,没事,小冬自个儿能找回来。俺说,俺在圩场前前后后找了大半天,没见人,要不要一起再找找?廖老根不以为意,仍在那儿抽闷烟。俺只好不安地回了家,一夜没睡着,张着俩耳朵,希望能听到隔壁屋里的动静。听了一晚,只听到廖小冬的娘不停地号叫,叫声一停,就是一阵怨骂,然后是廖老根短促的吼声。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廖老根站在门口不由分说,狠狠推了俺一把,冲俺吼,怎么没把你家春生弄丢?!
俺真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后来,俺陪着廖老根找了几个月,一起找过,也分开找过,还发动乡亲们找过,廖小冬就像一片飘着的树叶,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这些年,俺一直被廖老根误会。俺三番五次上门解释,廖老根根本不听,以至于到后来,不跟俺说一句多余的话。一开口就骂俺是拐子,还说,有你在边上作祟,俺只怕一辈子找不到俺的儿。俺不怪廖老根,俺只怪俺心软,好心办成坏事,不该带廖小冬赶集。不知哪个人贩子这般歹毒,害了廖老根一家不算,害得俺一家长期抬不起头。
廖小冬的娘,因为一直找不到廖小冬,得了疯病,常常疯言疯语,一见人就问看见廖小冬没有,一个人漫山遍野地找,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地喊,白天喊完,晚上喊,最后一失足,掉下了悬崖。
小杨同志,如果你们帮忙找到那个拐小冬的人,告诉俺,俺一定要会会他,俺只想问一句,他们家有没有孩子,晓不晓得什么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现在搬不搬家不重要了。俺跟廖老根一样,找到廖小冬最重要。俺不是不讲道理,你们一定要俺搬,也行,分两批,要俺婆娘他们先搬,俺不去,哪儿也不去。
四
原先林子里住着二十四户人家,十多个姓,百来号人,有些住在山窝窝里,有些像俺这样,住在山沟沟里,住得比较分散,这边住个三五家,那边住个两三家,看着对面人家里冒炊烟,路上弯弯曲曲的,走到对面少说要个把时辰。有急事的话,一般是一个人在这座山头扯开嗓子喊,两三个字两三个字地喊,另外一个在那座山头回应,那边的山仁义,怕你喊错了,生出重重回音,学你的话,那情景像四个人喊山歌。你以为山歌怎么来的,就是这么生生喊出来的。
住在山里的这些人,不是原住民,全是各个时期因为战争或灾祸逃难,一户一户逃来的。山里人都穷,都没啥亲人,平时互相当亲戚走动,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一家老少齐出动,带着自己家能使的家伙,比如椅子板凳,锅碗瓢盆,当自己家办事。天不亮打着灯笼来,帮完忙,晚上再打着灯笼各回各家。
这山开始时叫癞子山,“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将山刨得跟癞子似的,开了不少梯田,种苞谷,种马铃薯,种番薯,种水稻,以为多开了些地,大家的日子会好过些,结果种啥没啥,当年就饿死了人。后来种橘子,种茶叶,种油茶,东西种出来了,没有大路,销不出去,最后全烂在山里。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年轻人出了山,再也没回来,他们在城里过上了好日子,不愿意回来过苦日子。留下的,全是些老的和小的,山里的活儿干不了,但也得干,收成自然少得可怜。前几年,你们一家接一家上门做工作,要俺们下山,哪有不肯的,只怕下慢了,老老少少欢天喜地的,去了的还接二连三上门动员俺下山,说着山下的许多好处。俺不是不想下山,俺就怕俺儿找回来,俺不在。
小杨同志,你看,你一来,俺就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来,还是动员俺搬家?要是,俺劝你别跑冤枉路了,进山一趟不容易。
不劝俺搬家?你这么远跑来,只是为了看麻布大山的风景?
你想了解下廖小冬的情况,你是说俺儿廖小冬?你想帮俺找,跟公安部门联系了,有线索了就告诉俺?谢谢,太谢谢你了!
你要了解啥情况?行啊,俺这里还有廖小冬小时候穿的鞋子、衣服,给他做的一些木头玩具,小冬的娘全收在大木头箱子里。
这么多年,俺没动过,在那边,你看,锁上都结了蜘蛛网。相片?有一张全家福,小冬三岁的时候,俺们一家下山在照相馆照的,得找找,不知还在不在。小冬有什么能供辨认的印记?有,有,这些印记,小冬自己看不见,俺记得。小冬背心窝有一颗黑痣,左大腿后侧还有块小胎记,像片小叶子。还有啥,你让俺好好想想,哦,手指上全是螺,算不?小冬十个手指头全是。你也有十个?
俺说嘛,这不算特征,有十个螺,不稀奇。
你也是走丢的孩子,不会这么巧吧?先前来怎么没说,你也不晓得你是走丢的,还是被拐的?找到你亲生爹娘没有?还没有?
你为啥丢的,啥时候走丢的,你现在多大年纪?你既然说了,索性让俺验验,看跟俺的小冬对不对得上。快把衣服脱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又没有女的在,怕啥糗。
真是老天有眼啊。小冬,二十三年了,整整二十三年,你真自个儿找回来了。你先别说话,让俺仔细看看,长高了,长壮了,越看越像你那苦命的娘。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在哪里过的,你怎么就没想着早点来找爹娘啊?
俺去把张进喜找来,俺就说了嘛,不管多久,俺儿自个会找回来的,他不信,俺现在就要他信。俺不激动,不激动。小冬,你说,俺听着。
你不是廖小冬,你是小杨?没错,你改姓了。可现在,你是小冬,你哪能不是小冬呢?你今年二十八,还没满,生辰是农历十月初八。早上七点多生的,生你那天,天气有点凉,接生婆准备了一条崭新的大毛巾,你一出生就包裹好了。那条毛巾还在,俺舍不得丢,一直留着,等下拿给你看。再说,刚才俺说的特征,全在你身上应了,虽然你不肯脱衣,俺看不见背心窝的痣。左边大腿没有胎记,兴许俺记错了位置,但右大腿有一条像蚂蟥的胎记,不会假吧。怎么不是,哪里不是,你不是俺的儿,你是谁的儿?你就是俺的儿。小冬,你别嫌俺是山里人,嫌俺又老又穷,俺到中年才有了你。你娘生你的时候难产,差点把命丢了,护你护得跟小牛犊似的,但凡有好吃的好玩的,总会给你留着。一会儿不见你,就开始念叨。你那时贪玩,胆子大,什么地方都敢去,你娘每天都在担惊受怕,生怕把你弄丢了。结果,你还是丢了。
你先别说,听俺说,不管对不对,俺爷俩的血缘关系永远也改不了。小冬,你要不信俺的话,俺拉你一起找张进喜,他可以为俺作证。
张进喜,张进喜,在家吗?应一声。你出来,快点行不行?哪个?你说还有哪个,除了俺,还有哪个,老根。
你快给俺判判。他是谁?别瞪着双牛眼睛装不认得。对,他是上次来给俺们做工作的小杨。也不对,他不是小杨。看把俺欢喜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你看,是不是俺儿小冬,像不像俺儿小冬?这里没别人,你大胆地说,是不是?俺儿小冬怎么丢的,除了俺之外,你最有发言权。
刚才跟小杨,不,跟小冬在家闲聊,他说他也是走丢的孩子。俺想,哪有这么巧的事,这片林子里,二十多户人家,只有俺丢了孩子,而且丢了二十三年。既然小杨,哦,小冬自己找回来了,说明俺这么多年一直信对了。喜哥,你看看,小冬是不是跟他死去的娘长得像,这单眼皮,翘嘴巴,大耳垂,这皱着眉毛的样子,是不是都像?俺是不是跟你说过,俺小冬迟早会自个儿找回来的。现在找回来了,却不认俺,非要等什么结果出来了再说,不知道唱的哪一出。难道俺这么多年烧香拜佛、礼敬山神不够虔诚?
儿可能认错爹,爹不可能认错儿,喜哥,你说是不是?
小冬,好好,俺不激动,俺控制情绪。
俺现在请你进喜伯伯帮着验一遍,如果他还说不是,俺就不死皮赖脸认你了。
哎哟,春生也在。你啥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好好,俺身体还好,这些年你去哪儿发财了?帮俺找小冬去了?春生,在外边办事久了,嘴变乖了,会说话了。你有这份心,根叔心满意足了。春生,你看看,你面前站的小伙子是谁?面熟,当然面熟,怎么不面熟,他是小杨,也是你弟廖小冬。小时候你们天天在一起玩,上山爬树掏鸟窝,下水摸鱼摸螺蛳,形影不离,是不是?你也来帮俺仔细认认,帮小冬一起回忆回忆。小冬说对小时候有记忆,他小时候住在一片林子里,喜欢到处跑,从不迷路。
五
对,廖老根是我亲爹,我是廖老根的亲儿子。我跟我爹相认了,我自己找上山去的。相认时,张进喜伯伯一家都在现场,进喜伯伯一家比我爹还高兴。我爹跟我相认后,没立即跟我下山,而是把我拉到我娘坟前,要我磕了三个头,我爹在坟前还对我娘说:俺给你把儿子找来了,你看,多标致的小子,长得多像你。
我爹说,要我继续姓杨,名字不改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叫我小冬。养父母听说我找到亲爹,高兴得不得了,一起过来看我爹,在新房里住了半个多月,跟我爹认了亲戚。我爹按老礼要给养父母磕头,把我养父母惊吓的,直说折寿。养父母临走的时候,我爹一再保证,不会霸着亲儿子,他已经安排好了,要我每个地方住半个月。养父母很感激,不知说什么好。现在,我跟我爹住一块儿。
乡亲们听说我爹找到我后,纷纷前来祝贺,一家接一家来,热热闹闹了好几天,每天鞭炮声不断,恭贺声不断。乡亲们都夸我爹,固执得好,坚守得好,有福气,到了晚年,还能把亲儿翻出来。
乡亲们围着我,看了又看,像看大熊猫似的,冲我这里捏捏,那里摸摸。长辈们当着我爹的面,亲热地搂着我,逼我叫叔叔伯伯婶子阿姨,挨个地叫,一个不准含糊,一个不许落下。我爹笑呵呵的,在旁边一个个指着给我介绍:这个是你丛叔,你小时候在他家菜园子里屙尿,他还拍过你屁股,记不记得?那个是你兰婶,她家闺女小鼓最喜欢跟在你屁股后面,你一不高兴,就揪人家辫子,小鼓在你娘面前告过不少次状,现在,小鼓的小孩都满地跑了。
我爹现在一有空,就提着酒、提着菜到进喜伯伯家串门。两个人坐在一起喝老酒,有说不完的话,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每次喝高后,都是我上门把他背回来,第二天醒酒后又去,劝都劝不住。我爹说,这些年,让你进喜伯伯背了天大的冤枉,要好好赔罪。
我想,老一辈的人讲究这些,多劝无益,只得反复叮嘱,酒要慢慢喝,毕竟上了岁数,身体又不好,不能一时高兴过了头。我爹跟我保证,只喝这一阵,等进喜伯伯心里稍微好受些,他就不端杯了。
这世上的好人多,我是幸运的。被好心人收养,在健康的环境里快乐地长大,养父母的善良和付出让我懂得,亲情不能忘,养育之恩更不能忘。如今,到了我回报他们的时候。我要在我爹和养父母有生之年,好好在他们跟前尽孝,为他们养老送终。
你们看,这就是个父子相认的故事。没有人贩子,没有谁对不起谁,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更没有什么好采访的。记者同志,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以后别来了,我和我爹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
就这么将记者打发走了。你要我怎么说,这不叫瞒着记者好不好?!我觉得,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比真话更能让人信服。认廖老根当爹,是我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希望你暂时帮我保守秘密。第一次从麻布大山回来时,我就产生了认我爹的想法。第二次,我爹瘸着两条腿,坚持要送我,一直将我送到垭口上,怎么也劝不回,眼泪汪汪的。还一再嘱咐我,鉴定结果出来后,马上告诉他,他就在垭口上望着。我含着泪答应了,一边挥手要他回去,一边快速朝山下跑,跑到山坳的时候,还看见他瘦小的身躯站在垭口,朝我这边张望。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下次去,无论如何要认他当爹。你想,老人家在山里等了亲儿二十三年,等得多煎熬、多辛苦!真不忍心让他一个人在山里继续等下去。只希望他早点结束这种苦苦的等待,早日享受天伦之乐。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爱心人士这么多,我就不信找不到廖小冬,找到廖小冬是迟早的事。找到廖小冬,我不仅多了个爹,还多了个兄弟。如果再找到我亲爹娘,我又多了好多亲人!
当时怎么跟老人家相认的?第二次去,我没敢在我爹面前脱衣服,尽管我爹跟进喜伯伯一再要求。我说鉴定结果没出来,认了也白认。当时那情况,哪敢脱衣服,脱了,开始的一切计划就泡汤了。回来后,我赶紧找人在背心窝里画了颗痣,还认认真真做了份假的鉴定报告。
(原载于2023年第2期《创作》)

杨震,退役军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省市级刊物发表小说二十余万字。作品散见于《湖南文学》《特区文学》《啄木鸟》《短篇小说》等文学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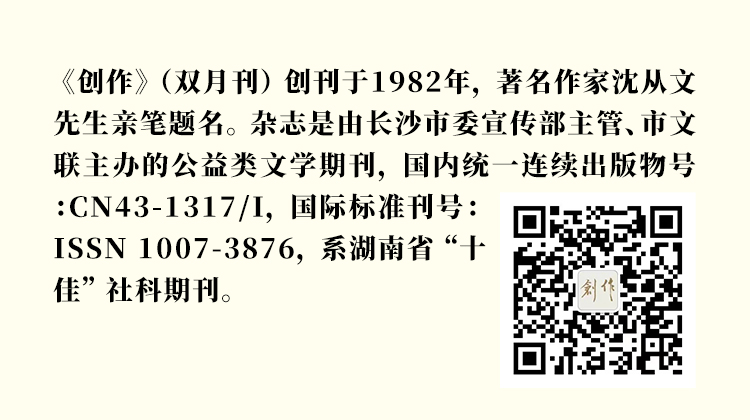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杨震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艺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3/61/13094541.html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