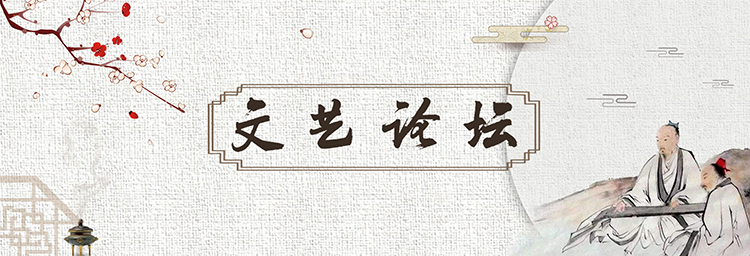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远景
文/刘卫国 李婷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乎都是在“落后焦虑”中进行的。这种“落后焦虑”主要源于中国自19世纪中期之后在现代化发展上全面落后西方的历史形势。一旦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研究者必将祛除“落后焦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发生新的变化,即不再突出审美上的“悲凉感”,不再强调主题上的“反传统”,也许将确立“多元现代性”,告别“西方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将打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过去的认识装置,研究者将在新的认识装置中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落后焦虑;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所谓“发展中”,乃是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作家、作品、文学事件与现象的评价,不断风吹草动,不断翻来覆去。众所周知,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却是主观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对同一历史事实作出不同的评价。评价者的立场,除了受各种思想学说的影响,也受社会形势的影响。接受不同的思想学说,会造就不同的立场。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会改变一个人原有的立场。在思想学说与社会形势之间,归根到底,可能社会形势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思想学说也要接受社会形势的检验,一种思想学说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往往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会被研究者弃如敝履。
中国现代文学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先觉者想用文学来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用文学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启蒙中国人的思想。众所周知,在19至20世纪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是落伍者。1938年,历史学家蒋廷黻如是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1]蒋廷黻所说的“近代化”,其实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洋人,但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追求的是“赶上西洋人”。落后了,人们就会反躬自问: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我们究竟哪里不行?同时还有一些困惑: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我们有没有新的更好的选择?这些问题和困惑纠缠在一起,造成一种心理焦虑。我们将这种焦虑称为“落后焦虑”。
从五四时期起,因为当时中西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差距太大,中国人就产生了这种“落后焦虑”。鲁迅甚至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直到20世纪90年代,即便新中国在追赶现代化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种落后焦虑依然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间。正如谢冕所说:“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3]我们付出了汗水、泪水和血水,我们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到达过,但依然落后,这真是让人痛苦,让人纠结,让人绝望。
这种落后所造成的焦虑,积淀在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灵深处,形成了几代研究者的“认识装置”。几乎文学史上所有被称得上“重要”的问题,都是在这一“认识装置”中被提出、被思考和被解答的。这种“认识装置”形成了一种研究范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取得范式的突破,必然要颠覆过去的认识装置,亦即祛除“落后焦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4],祛除“落后焦虑”,本来极不容易,但社会形势的发展可能会使这一问题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在很多研究者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进入21世纪后突然加速,不断赶超世界列强。到今天,大多数人都坚信中华民族已经越来越接近全面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一旦中国实现现代化,回头再看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心中的“落后焦虑”,可能会啼笑皆非:中国都已经领先了,你怎么还在纠缠中国的落后?
也许,我们是时候考虑一下:当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会出现怎样的远景?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尚无人做出系统论述[5],本文试图抛砖引玉,提出四点预测。
一、“悲凉”感的消失?
“悲凉”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黄子平在1985年提出。他在归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时,一步步提出了这一概念,首先说“一种根源于民族危机感的‘焦灼’,便成为笼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转而说“倘说‘焦灼’是一个不规范的美感术语,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一焦灼的核心部分是一种深刻的‘现代的悲剧感’”,接着说“从鲁迅的《呐喊》《彷徨》,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巴金的《寒夜》,以及新时期文学中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李顺大造屋》《西望茅草地》《黑骏马》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中,你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更是一种‘悲凉’”,最后说“这样一种悲凉之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涵的美感特征”。[6]
黄子平坦承:“论文发表后,争论最大的就是这个‘美感特征的核心是悲凉’,一个世纪的文学现象千差万别,怎能一言以蔽之曰‘悲凉’,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战歌和颂歌的年代,高歌猛进,跟‘悲凉’毫不搭界嘛。所以我对这一部分的论述要负主要的‘文责’。”[7]不过,有关“悲凉”的“争论”并未影响到其传播。正如黄子平所说:“悲凉、焦虑、忧患意识,这些词在八十年代用得相当频繁。”[8]“悲凉”这个词一直流行到1990年代末期。谢冕在《回望百年文学》一文中再度提及“悲凉”:“这是光明与黑暗际会的重要时代。中国作家以敏感的心灵触及了这一时代的真实内容:飘移不定的风,使人难以判定方向;面对一海死水,使人不能不诅咒那肮脏和丑恶的浓重;中国有一个或几个认出了历史书上‘吃人’二字的,那只是有异于众生的‘狂人’;中国的凤凰需自焚以获新生……这一切,都是自近代以至现代的作家所把握到的中国式的悲凉。”[9]
“悲凉”感与“落后焦虑”密切相关。谢冕曾这样描述两者的关系:“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我们,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10]因为落后,人们才感到悲凉。当然,也有一段特殊的时期,当时的国人虽然也有“落后焦虑”,但一则革命成功的激动和喜悦冲淡了这种焦虑,二则国门的封闭使得人们沉浸在乌托邦的幻想之中,因此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不强调“悲凉”这种美感。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之后,人们发现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革命成功的激动和喜悦也淡薄了,人们实在兴奋不起来,即便看到现代文学作品中还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调,也会自动屏蔽掉,甚至觉得这些作品不感时忧国,未免见识浅薄。大家都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种社会氛围,逼得人“不应该感到欢乐,只应该感到悲凉”,你如果不感到悲凉,不仅会被学术共同体排斥,而且似乎也对不起落后的社会现实。
“落后焦虑”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审美感觉,“落后焦虑”下,研究者内心感到悲凉,将这种感觉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11],自然看什么都是悲凉。
一般来说,人们看待世界的心态,可以笼统地分为两种:乐观与悲观。在面对中国长期落后于人的现代化进程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人非常悲观,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错失了无数次机会并且还将再度错失机遇,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与这些人在理论上辩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定型,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也不会信,唯有现实可以纠正他们的看法。所幸,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中国的全面复兴已经不可逆转,不可遏制。当这些人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悲观的看法。
当然,如果现实还不能改变这些人的看法,自然的人事代谢也会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出生和成长的两代人,与前几代有个明显不同的特征,就是没有“落后焦虑”。他们印象中的中国,国势蒸蒸日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落后,甚至还有领先之处。当这些新生代登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并成为大多数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落后焦虑”自然将成为“过去时”。
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特征本就多种多样,并不只有“悲凉”一种。但以前人们只感觉到“悲凉”,对其他审美特征视而不见。正如黄修己在评论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一书时所说:“如果换一个有不同经历的人来写这段历史,他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感受,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团圆的时代,这是王大春回来救出喜儿,与喜儿团圆的时代。在他的作品中不但不会有悲凉之感,反而可能充满着亮色,透露出欢乐的心境。历史客体就这样随着主体的情绪而变换着它的颜色。”[12]其实,钱理群也知道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并不只有“悲凉”风格,他在该书的“楔子”里,描述了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参加新年晚会扭“翻身秧歌”的情景,引述了朱自清日记中“颇愉快”的记述[13],只是他投入了感时忧国的情绪特别是与家人离散的情绪研究1940年代文学,故而忽略了这一时代的“团圆”和“欢乐”。
20世纪的中国,一直落后于西方现代化国家,但同时也在奋力追赶。一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不懈奋斗、艰苦探索,上演了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一幕幕戏剧。观看这一幕幕戏剧,人们心中百感交集,会有多种审美感觉,但到20世纪末的时候,人们还未看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牢骚太盛,故以“悲凉”一言蔽之。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全面起飞,有识之士已能预见美好的前景,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而当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人们必然会祛除“落后焦虑”,心中充满喜悦感、自豪感、成就感。到了那时,历史客体还会随着主体的情绪而变幻着它的颜色,那些以前被忽视的审美特征,如“浪漫”“温暖”“喜悦”“神圣”“崇高”等,都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得以敞开。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俟(鲁迅):《随感录:三十六》,《新青年》5卷5号,
1918年11月15日。
[3]谢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收入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5]《现代中文学刊》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栏目,其中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关的论文,有朱羽《“中国式现代化”与真理—政教—美学机制的转型》(《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卢燕娟《“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空问题》(《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李云雷《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思考》(《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5期)和周展安《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政治维度》(《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6期)。这些论文从各种角度谈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某一侧面的影响,但尚不全面,尚不系统。
[6]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7][8]黄子平、胡红英:《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新文学评论》2017年1期。
[9]谢冕:《回望百年文学》,收入谢冕:《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0]谢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收入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1]王国维:《人间词话》,收入《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页。
[1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13]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JZD0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刘卫国、李婷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远景》)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刘卫国 李婷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