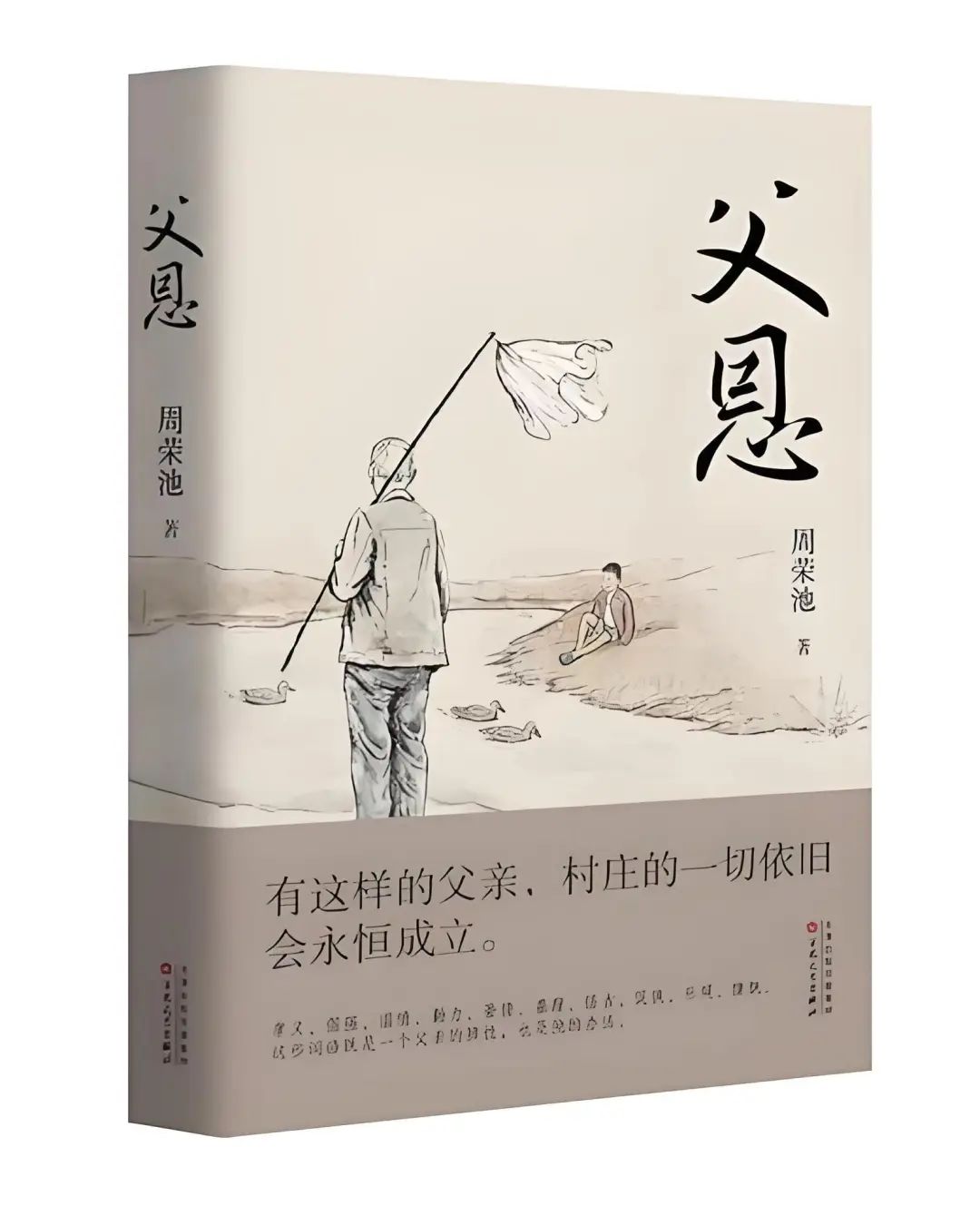
活出自己的样子
——读周荣池长篇散文《父恩》
文丨石绍河
父恩母爱,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从古至今,这类作品可谓灿若星辰,不乏优秀篇什。大家都写的题材,也容易千人一面,虚伪滥情,落入俗套。要想突破,难上加难。我最近读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荣池长篇散文《父恩》,觉得眼前一亮,耳目一新,有话可说。这部作品入选2024年10月文艺联合书单。作者以南角墩村为原点,用生动平实的细节,真挚深情的文字,把一位农民父亲塑造得丰赡饱满,形象鲜活,为我们徐徐呈现了一幅乡土中国真实而又复杂的实景图画。父恩深沉动人,乡土静默丰厚。《父恩》的亲情叙事,乡土表达,路径抵达未来,魅力四射。
植入骨髓的根文化孝文化
孝义是父亲的最大底气和心理防线。他是家中的长子,但早年去离南角墩十多里的三荡口一户本族爷爷辈家承继门户,本族爷爷、奶奶实际上成为他的养父养母,他由此失去长子身份。待养父撒手归天,他带着眼盲的养母回到南角墩,以务农为生,成为南角墩的外来户,与他人格格不入,故养成了倔强、暴躁的性格。他在村庄里受到挤兑、打压,却对家族总是饱含着一种特别的信念,惦记着长眠在地下的养父养母。孝道于他来说,是一种很朴素的意识。他一次半夜醒来,自言自语道:“老家的坟下水了。”过几天去三荡口看,水面真的已经抵达坟边。父亲决定选一个日子,带着兄弟和儿子去三荡口迁坟。他在坟头磕头,口中念念有词:“子孙们来给您二老搬家了。”“你们遭了水淹,受寒了。”最后把二老遗骸迁葬在一处地势更高的圩子。事后,兄弟、妯娌之间为这事有了不同看法,母亲也嘀咕着:“要追究这些规矩做什么?”父亲拍着桌子吐出一句:“这是孝顺。”孝顺在父亲倔强、暴躁的性格之下,有了更深刻的意味。后来,父亲又把二老的骨殖安置在一处公墓。老人最后只剩下一堆骨头,却是父亲挂念了一辈子的岁月。孝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要义,也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父亲不识字,但根文化孝文化融入了他的血脉和骨子里,父亲不懂大道理,却认认真真践行着。
特立独行的生存策略
倔强和固执是父亲突出的个性。他从部队退伍回来,本来安排到省城一家轧花厂工作,需村里盖公章证明其“根正苗红”。可他不肯低头求人,甚至摩挲着手里的一根新扁担说要“敲支书的脑袋”,最后失去到省城就业的机会。直到老年,父亲还在租地与拆迁上固执地不肯让步,成为与工业园区对抗的中坚力量,同前来做工作的村支书发生肢体接触,感叹自己“到底岁数大了,打不过少年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父亲的倔强并非是一个人的脾性,那是一个村庄的情绪遗传,是世代流传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犟种。”
喝酒是父亲最大的生活爱好。“一个男人不愿意大碗喝酒,一个村庄失去了鸡飞狗跳,日子就难有生动的样子。”喝酒是父亲最好的精神安慰剂,酒量好是他逞强的资本。他引以为豪的业绩是一次同黎先生喝了五斤白酒。他靠与先生一起喝酒,竟让“我”在学校享受和先生一桌吃饭的殊荣。“父亲的酒碗里是他自己的主张。”父亲喜欢逞能,当村庄在洪水面前岌岌可危,排涝泵站的闸门是村庄的最后坚守。闸门下已经回水暗涌,如果不及时下水堵漏,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在村人的激将下,朝着翻滚的暗流,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堵住了翻涌的水,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棚子了喝了一口酒,表现出一种淡定和豪情。在乡土社会,喝酒是一种胆量,一种品性,一种豪情。
父亲多年放养鸭子,好喝酒,脾气变得暴躁,且嗓门很大。“他瞪眼睛扯着嗓子在村子里喊,四野的草木似乎都不寒而栗。”因为这种脾性,喝酒经常拍桌子摔酒杯,弄得兄弟失和,村人反目,邻里互不待见。他养的鸭子被人毒死,“这日子,真能把人逼死。”但在关键时刻,父亲却学会了退缩和沉默。暴躁既是送命的脾气,也是在乡土社会生活下去的一种迷人的方法。他的兄妹们说:“要不是他的暴躁脾气,能在这南角墩站得住脚?”
父亲在村子里很“怪古”,也就是乡亲们眼里的“不学好”。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另类”,按时髦的话说是探索和创新。这是父亲具体而有效的生存策略。他不满足于在农田里种粮食,总想鼓捣出一些新玩意,种过一丛甘蔗,栽过两棵桃树,种了一田西瓜,虽有收获,但受当时环境、市场的影响,几乎成为村里的一场笑话。当养虾赚钱时,他又重操旧业放养鸭子,不随大流走,选择动情的坚守。
艰难生活中的强大和柔软
父亲勤劳,但好面子,他不愿别人看见自己的艰难,当他人提到我们家里的困难,父亲就皱起眉头来——他不愿意人们这么看待他。“勤劳也才是村庄和农民应有的样子。”他含辛茹苦,早出晚归,常在月色下干活,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大块吃肥肉,大口喝烈酒,使劲抽土烟,从来不埋怨生活,“不吃苦叫什么庄稼人呢?”一切都靠自己默默承受,咬牙坚持,孤独而不自弃。他最终答应去三荡河边守圩,做护林员,也是想逃离人们的视线,把艰难的日子隐藏起来。父亲是一个内心强大而又脆弱的人。
父亲晚婚,三十四岁娶了一个驼背且精神有些失常的女人,生活过得更加艰难。这个暴躁的人,在自己女人面前却显得温情。当妻子在田里割伤了小腿,他驮着急急地去医疗服务站为其包扎,还杀了鸡给妻子煨汤,“那种耐心比乳白的汤更深情,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暴躁的脾气。”妻子去世后,儿子劝他说这是解脱,哪知他却突然嚎啕大哭:“你不知道,这二十七年里,她在家的每一天,屋子是不用上锁的。”妻子是他生活中的一把锁。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呵护、深爱着女人和孩子,尽管爱的方式有时粗鲁、悲情,不善表达,却用默默承受和付出传播着爱。
乡土社会特有的清醒
因为贫穷、因为饥饿而不能作体面人的人,常常会失去正常的理智,而父亲却异常清醒。在“我”上学的问题上,他咬着牙说:“老子就是勒棍子要饭也要供你上学。”他尊重有文化的人,为过年给家里写过对联的高先生离世黯然神伤。他的长子身份不被兄弟姐妹认可,却想竭尽己力为生身母亲尽孝,在后事处理上忍辱负重。总是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弄点好吃的,生活中不时漏下人性乐观的光亮。
父亲面对艰难的日子,排解和减压的办法是苦中作乐,显示出他幽默的智慧。他喜欢乡土中口口相传的“促狭人物”,津津乐道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把无奈和悲情隐藏在带泪的笑声中。这是困苦中父亲的特有清醒和生活艺术。
晚年的父亲独居多年,习惯自言自语。对城里生活感到迷茫,留恋乡村的日子,眷念过去的人和事。“我要回去了,在南角墩,就是吐口痰也是快活的。”他心里只装着这个村子。他和子侄们比拼酒量,在碗盏中完成村庄的承续和迭代。他一生琢磨出许多简素而深刻的味道,愿意留人吃饭,咂摸有滋有味的生活细节。他在村子里依然独来独往,依旧喜欢出头,活成村庄一道迷人的风景。
父亲一辈子不愿意离开乡土,他和乡土既有对抗,又有回避;既有嫌隙,更有融合。父亲最终活成了自己的样子,他离不开乡土,乡土也不能少了他。有父亲这样的人在,村庄就不会消失。“有这样的父亲,村庄的一切依旧会成立。”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感谢生活和大地于我父亲般的恩情,这是我所爱的现实,也应该成为我的现实主义。”
来源:湖南文联
作者:石绍河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