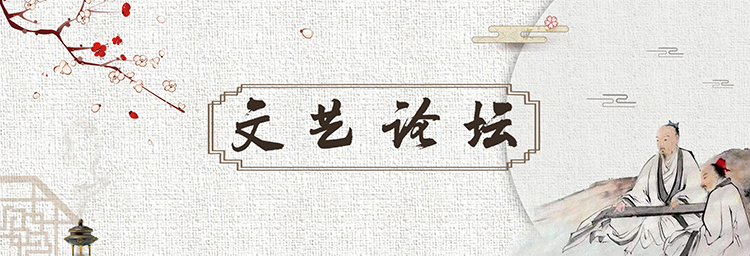

“大地三部曲” 孙未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明的忧患与精神家园的追寻
——对话孙未“大地三部曲”
文/荒林 孙未
荒林:孙未老师您好!北京日报集团高级编辑、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李峥嵘在《北京晚报》发表书评,对您最新出版的“大地三部曲”给予了高度评价,钦佩您“在这广阔未知的世界中一路向前”的勇气。她还说,爱情从来不是您写作的核心。那么,是什么推动您一路向前?又是什么使您绕开了世俗爱情主题?
孙未:人生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世界每时每刻向我们展现着无常,今天静好的生活可能一夜之间就陷入想象不到的困苦。人性本身又是不容易满足的,好日子里也有贪欲不足,遇到糟糕的日子就更加难以忍受了。我观察过很多人,有趣的是,对现状不满的人们有时候能几十年抱怨,却极少有人真的做什么。声称要辞职的,结果一直做到退休。声称要搬家的,结果一直原地不动直到耄耋之年。
人怎么能生活的快乐一点?我觉得这是人生最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一磨叽就是几十年,人生也就差不多过完了。凡事付诸行动才是生活,行动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快乐,更不用说行动之后的改变和成长会让人多么心情开朗了,这也许就是我能“一路向前”的原因吧。
我是一个在上海闹市中心长大的孩子。可是,我除了喜欢上海的人情味、烟火气和理性精神之外,我对摩天大楼和霓虹灯什么的并没有太大热情,反而更喜欢高山大海、星空森林和所有辽阔寂静的远方。于是,我走出城市,去寻找让我内心变得更广阔的地方,寻找让心灵变得宁静的精神家园。不知不觉,这场在中国大地的旅行延续了十年的时间。
“大地三部曲”的《大地尽头》《熊的自白书》和《寻花》是我将近十年行走于中国边地大山之中美好时光的见证,云南西藏的雪山蓝天与古老的故事曾给予我宁静、智慧与喜乐。我旅行,不仅是因为我热爱远方,也是因为我热爱多样化的文化环境,热爱听到不同的声音。我在中国大地漫游的日子里,采撷了不同地方的许多史诗、神话、传说和歌谣。对我而言,这是我人生中积攒的一笔极为庞大的财富。彼时,我在当地做的这些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基础调研,不仅给“大地三部曲”提供了丰富奇幻的素材和理性思想的空间,也给我如今的博士论文课题提供了一部分辅助的理论框架。
因为热爱多样化的文化环境,我又开始了周游世界的计划。这些年,我在欧美各国走来走去,不知不觉已经在十八个国家或长或短地居住过。这个数字让我自己都有些惊讶,如果不是这两年无法旅行,也许我已经去过更多的国家。而写小说让我开心,于是我就每天动手写一点,不知不觉已经出版了二十九本书。旅行与写作,都是因为热爱。
“大地三部曲”写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大都市居民与遥远的田园边地、广袤的大自然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与原本就处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辽阔寂静的远方的关系。
我也非常喜欢很长很长时间宅在家里的日子。曾经有一部长篇小说收尾,我三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而因为外界原因不得不宅在家里的时候,我也可以在自己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生存下来。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我与外面世界貌似隔绝,但因为有了网络,我们的足迹仍可以与这五亿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发生关联。
至于说爱情,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去做,有许多更有趣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聆听、去思考。比如,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身边的许多人正在经历怎样的生存磨难与信仰危机等等。
与爱情相比,我更信仰爱。爱比爱情更持久、更无私、更宽容。比如,把一对夫妇和一个家庭维系在一起大半生的是爱,爱情所占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比如,朋友之间在各自的生活中彼此眺望,在漫长的时光中相互安慰、相互支持,这也是爱。这种爱,远远比爱情靠谱和真诚得多。我觉得,爱的范围更广泛,它甚至包括对陌生人的注视、担忧、帮助。正是这种爱,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我即便在故事中写爱情,我写的大部分也还是爱,这是我的性格与信仰使然。
荒林:《大地尽头》主题是探索人类文明处境,但您对神秘爱情的诗意表达动人心弦。比如,您写安宁与萧岩的性灵之爱,她总是在他熟睡的时候熟睡,而他在她醒来的时候醒来,虽然他们之间隔着大地间漫长的路途,不在同一个空间。比如,您写少年僧人格列有一年非常喜欢一个坝子上的小女孩,她每月上山来还愿,山坡上的草叶子们知道了,就在清晨卷起叶子,把露珠满满地盛在里面,阳光一照就像铺了满山坡的钻石,可惜那女孩一次也没有注意到。女孩走了以后,叶子们失望地垂下来,满山的钻石也消失了。这些描写不同于世俗爱情的人间烟火气式表达,您对神秘爱情的书写起源于何时?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未来有何设想?
孙未:世间万物也许都可以心意相通,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可以的。我去过很多古老的村庄和部落,听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老人跟我讲过一些故事,它们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如果我们脑袋中的念头足够少,我们的内心足够专一与真诚,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与大自然对话,我们也可以彼此传达心意,不需要人类语言。
我还听到过另一个故事,也就是在《大地尽头》这部小说中,村庄里的老人说过的,“如果想要拥有一块石头,它会跑得比一匹好马还要快”。在那个桃花源一般的古老村庄里,河床上有很多美丽的石头,它们只是被送到寺庙作为装饰。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付出了毕生的时间甚至是自己的尊严,用尽了一生的努力,只为了占有更多的石头——那些沉重的、他们并不能带走的石头。
“大地三部曲”《大地尽头》《熊的自白书》和《寻花》都尝试用有趣的方式来讲故事,都有奇幻的元素,但是奇幻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如果按照从《大地尽头》到《熊的自白书》再到《寻花》的顺序来翻看这些故事的话,就像拿着一把小刀,从一幅油画上一点一点把表层的油彩刮掉,然后看到下一层有另一幅画,再刮一次最后看到了底层的那幅最早的画。如果按照从《寻花》到《熊的自白书》再到《大地尽头》的顺序来看,则像是坐在沙发上翻着书页,一公里一公里远离了原来现实世界中的书房,游历忧伤、遗憾与奇迹共存的远方,继而走进幻想世界,见证那些坚固明亮的元素。
我在写作时最感兴趣的是:写作者可以在魔法中走多远?他们又可以让读者跟随他们走多远?这也是我感觉到最困难的地方。身体受困,有一天门打开了,还能重新走出去;心灵受困,有一天即便门打开了也可能永远走不出去了。
德国学者麦克斯·吕蒂曾说:“真正的童话主人公是不会对奇迹和魔法感到吃惊的,他接受奇迹,好像它们是自然而然出现的。”置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还能有多少想象力、相信多少奇迹?我们是否还能像所有纯正的童话中的主人公那样关心远方?
荒林:您的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心灵的寻花。《寻花》讲述了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和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友谊,对于这个作品的心理学价值,您是怎么看待的?
孙未:在我动笔之际,我还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但是我想说,看着近些年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正在变成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人类的问题是心理学根本无法解决的,心理学只是布洛芬。
在谈论爱之前,我觉得首先应该谈论共情能力。《寻花》是一个试图理解他人、理解旅途上许许多多偶遇的陌生人的故事,所以更像是一段心灵的旅程。在故事的旅途中,主人公一路遇到的都是善意以及美好的人们,这也是我所相信的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一些让人痛心的事,有陌生人的恶意引发的冲动型凶杀,也有路人的冷漠造成的绝望与死亡。有很多人问:“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觉得,这种悲剧往往是自我痛苦的转移和转嫁。很多现代人为了身外的某种需要或追求,自己生活得并不快乐,但他们自己并不在乎,反而认为这是一种美德:“我是为了事业而牺牲自己的感受。”“我忽略自己只为家人能生活得更富足。”《礼记》中虽然有“先人而后己”的主张,但我认为,关注和照拂自我的感受其实应该是人生最基本的功课。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感受都不在乎,那他如何能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不少人压抑和忽略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失去共情能力,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初衷。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地呼吸,感受自己,阅读,旅行,这可能并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实际用途,但是肯定能让我们慢慢地快乐起来,慢慢地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善意。
荒林:三部曲中,《熊的自白书》聚焦职场众生相。上海HZ国际通讯公司职员凯文,与横断山脉下原始庶村的牛熊相遇,现代文明与原始生态对话交流使这部小说具有人类学意义,超越了一般职场小说。如果把小说主人公凯文换成一名现代职业女性,您觉得她还能遇到牛熊吗?您的小说引子采用了《搜神后记》里“母熊救人”的传说,但牛熊却不是母熊,这一微妙的性别更换,您是故意为之的吗?
孙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小说中从繁华的上海被流放到遥远的原始村落、与“众熊之神”相撞发生车祸几乎丢掉性命的是一名国际大公司的男性职员,而不是女性职员。因为在小说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在公司内部遭遇的灾难已经足够了。她们是公司饭局中娱悦男性上级以及公司客户的角色,她们是职场酒精暴力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必须要依附男性才能顺利上位。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女性再成功,在与别人的对话中,人们依然会问她是靠哪个男人取得成功的,或者居高临下地建议她最重要的还是赶紧找个好男人。
其实我很偏爱《熊的自白书》中的这个男主人公,他是想保护女同事才得罪上司以致被惩罚流放的,虽然他只是个无用的自封的英雄,而女同事曲折的命运也是许多职场女性真实的经历。
少年时代我一直在上海生活,对女性身份并没有过多的思考。之后在自我经历和对他人的观察中,在多种文化的对照中,我发现女性所遭遇的处境是一种不同文明程度的展现。那些安排饭局中特意计划女性人数、把女性座位刻意分开安排在男性周围的所谓习俗,那些男性上级或者客户对着出色的女性说出“您最需要的就是找个好男人”的猥琐的微表情,说实话,不从艺术和研究的角度来谈,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是挺烦这回事的,所以我自己选择了一个比大多数男性还要短的发型。这种发型在北欧和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公众场合是很常见的女性时尚发型,而在某些国家恐怕就是引人侧目的发型了,会被嘲讽为“女人弄得不像女人”。当男性只看女性脑袋上的头发够不够长,而完全忽视她们的脑袋里面有点什么,我觉得相应的,女性也并不是必须要聆听他们的长篇大论,并且按照他们喜欢的样子一直微笑点头装出崇拜的表情,即便他们是上级或者客户。
所以我把“众熊之神”的牛熊设置为男性,是出于模拟对应人类城市的考虑。其实在真实生活中,熊大多数时候是独居的,因为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食物匮乏,而不是凶残的天敌,所以熊并不需要大规模聚集去抵抗外敌,而大规模聚集去觅食反而会降低觅食的速度,找到的食物也不够吃,这和人类社会有时候不得不“团购”食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至于《搜神记》中救人的是母熊,那是因为只有母熊才会照顾小熊,捎带就把那个幸运的猎人也照顾了。公熊是不照顾小熊的,它们一般在交配时才会和母熊在一起,交配期一过就彻底分开各自觅食,母熊在生小熊的时候还会躲开公熊,因为有时候公熊会杀死小熊。从人类社会的道德来看,公熊们真是妥妥的“渣男”。
荒林:哈哈,现实生活中的“渣男”熊,在您天才的想象力下,变成了文本中的神熊。对神熊现身的神奇描写,魅力无限。谈到现实性别问题,您对女性处境愤愤不平,留短发,周游列国,您用行动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颠覆。不过您文本中的女性像《大地尽头》中的安宁,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温婉深情,女性气质饱满,而男主人公您取名萧岩,形象也突出他的刚毅坚执。您是有意通过《大地尽头》来还原两性气质之美吗?
孙未:这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荒林老师不愧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专家,出的考题都是关键概念。
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性格特别平和的人,我没有过青少年的叛逆期,甚至一直是个痛苦的“老好人”。我承认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女性,我喜欢读书学习,喜欢独处,喜欢不受他人影响地思考问题,喜欢穿舒适的衣裳,不喜欢旁人对我的外形提出要求,所以我无法符合一些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非常有意思的是,以前我在纽约居住的时候,也听到过很多美国年轻女孩谈到美国社会如何期待女性符合他们的“刻板印象”:长发明眸,身材凹凸有致,不能肥胖,微笑聆听,跟芭比娃娃一样,这样就符合标准了。其实,女性必须温柔美丽,男性必须刚毅果敢,这是一种性别偏见。同样的,男女平等就是女性剪掉长发,穿上带肩衬的类似男款西装,说话做事都模仿男人,这也是性别偏见,而且可能是更糟糕的性别歧视。女性不需要假装是个男人来得到尊重。我住在新西兰的时候,新西兰总理是一位年轻女性,她在任期怀孕,挺着大肚子出现在各种场合,后来抱着婴儿出席联合国大会。她长发,衣着自然美丽,治理国家非常靠谱,她并不需要成为“男人样”来赢得肯定。
平等不是让每个人全都变成一种样子,毫无差别,恰恰相反,平等是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不仅是每种性别的独特性,更是每个人的独特性。比如说,让一个温柔的女性保持温柔,尊重这种温柔背后的爱,而不是理所当然视之为软弱可欺,提出种种过分的要求。比如说,不需要让一个家庭主妇去职场取得成功来体现女性价值,但是不要继续顺理成章地把她当成免费的保姆,贬低她的价值,要理解这份劳动比一份八小时的工作更辛苦,尊重她是家庭的灵魂。比如说,对一个热爱自由、不愿意结婚的女性,不要劝说她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每个人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态度、外形和生活方式,并且得到尊重。
《大地尽头》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温婉,男主人公刚毅,然而其实他们两者是一个人,有兴趣的读者也许可以慢慢发现他们之间天生的默契,他们同样真诚与坚定,他们有观察世界的相同的方式,以及对这个世界一致无二的信仰与爱。所以,与其说这是还原了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两性之美,不如说他们原本就是一个人,一枚硬币的两面,我把他们化作了两个注定要相遇的一半,当他们在一起,世界上就再没有孤独这个词了。
说到女性主义文学分析以及性别分析,“大地三部曲”中的《寻花》用的是第一人称女性视角,《熊的自白书》用的是第一人称男性视角,《大地尽头》用的是第三人称多视角。作为女性作者,我也经常使用第一人称男性视角,而且乐在其中。像我另一部长篇小说《岁月有张凶手的脸》也是采用第一人称男性视角的,加上我的名字很中性,没有办法推测男女,所以有的读者读了我的一些小说之后以为我是个男作者,这让我挺高兴的。
我觉得女性和男性的生理特点不同,以及后天环境的观念对他们的要求不同,他们的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会有或多或少的一点差别,而如果女性愿意从男性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男性愿意从女性的视角去理解她们,我觉得这不仅是一种很有爱的尝试,同时也是对智力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对小说作者来说,这则是一项必需的功课。共情对作者尤其重要,作者不仅要试图了解自己,也要试图了解众生。说起来,我觉得小说作者其实是一个很有爱的职业,我们观察、注视万事万物,我们试图理解、共情,站在别人的鞋子里考虑他们的处境,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珍视世间每一个细小生灵的独特性,描写他们的独特性。“刻板印象”是小说大忌,注视个体的独特性才是小说的审美价值。可以说,写作与阅读小说就是爱的行为。
荒林:“大地三部曲”探索的主题宏大,涉及现代社会面对的文明的忧患、精神的困境、职场的竞争,因此被称“为时代作传”。在您未来的写作中,还会关注我们时代哪些主题?您通常会按计划写作还是随性而为?目前有何写作计划?
孙未:其实我不知道“大地三部曲”会有多少人愿意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应该乐观还是悲观。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是关注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为了做正确的事情,可以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甚至遭受一定的后果。一种是关注自己是否在做有用的事情,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并不介意做不正确的事情。如果前者是文明,后者就可以被归入文明的忧患。
这个世界上也有两种人生的心态。一种是首先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想要快乐的有意义的人生,精神上的幸福感是最重要的。一种是只关注提升自我在世俗意义上的价值,即便以自己精神的压抑与苍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这两种心态之间徘徊就是很多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只有拥有第一种观念以及第一种心态的人才会对“大地三部曲”感兴趣,拥有第二种观念和第二种心态的人甚至不会读完“大地三部曲”的这些介绍。所以,如果有朋友已经读到这里了,我和荒林老师都非常感恩遇见您。
文明的忧患与精神家园的追寻一直是我写作的主题,对这一部分主题的探讨,我偏爱用奇幻小说或者软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年我陆续发表这一系列的中篇小说,有上海题材,也有海外题材。同时我也在不断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十几年来陆续成书数本。近年我创作的长篇集中于检察官和律师题材的悬疑故事,背景都是我的家乡上海这个城市,主题是讨论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表达上海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们的追求与心愿。
有时候我会忽然对某个题材或者构思很有热情,这完全是随性的,然而我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我了解自己兴趣过于广泛,热情频发,所以我会制订严格的计划,并且保持自律,否则我就会像熊瞎子掰苞米,没写完这个小说,就掉头去写另一个,结果忘记了前一个小说应该怎样结尾。
我是个很孩子气的人,非常有好奇心,总是喜欢学习一些新的有趣的知识和技能,一直没有停过。我去年出版了第二十六本书以后,遇到了一个可以重返校园的机会,于是我开始在德国念博士。由于研究使用的母语之外的语言种类比较多,同时使用五种语言,我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容量不够大,所以在写博士论文的同时,目前我写小说的进度很缓慢,只能在周末和假期抽时间写,预计接下来的半年内会完成一个中篇,三年内完成一个长篇。
荒林:非常期待您的新作!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市作家协会)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荒林 孙未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