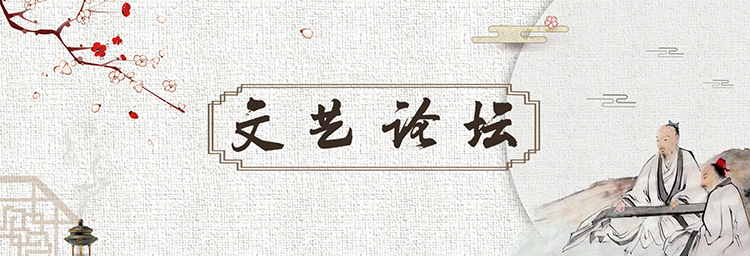

创意写作研究的兴起与创意写作研究新范式探索
文/许道军
摘 要:创意写作兴起一百多年来,经历了“英语写作”“文学写作”和“创意写作”三个阶段,而创意写作研究也随之兴起,经历了自证为新型且有效的写作与教学形式、成为文学领域“非异常”学科和成为独特学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交织且均为最终完成。由于创意写作研究至今没有走出文学研究范畴,它依旧不能充分地阐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预判可能的发展趋势,因此走出创意写作文学研究范式,创建以创意为本位的创意写作研究新范式势在必行。这种范式的逻辑起点是“创意”,中介是“写作”,终点是“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并以此为纲,重建创意写作的发生论、本体论、实践论、方法论和发展论。但正如“创意写作”随着时代变动不居一样,创意写作研究范式也要与时俱进地更新。
关键词:创意写作;创意写作研究;范式;创意本位
随着创意写作在全世界推广以及深度介入社会事务、文化创意产业,它的内涵开始向最初的“创意”回归,而在外延上,越来越溢出“文学写作”形式。与此同时,创意写作的兴起,也极大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写作观念、作家观念、作家培养模式和生存方式,乃至于整体性的文学生态,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创意写作时代。”[1]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有的研究很难准确而深刻地描述当下的写作现象,也更难以科学有效地介入写作现实。因此,深入地考察因为创意写作的兴起而导致世界范围内文学生态的新变,以及根据已经变化的文学现象,革新传统创意写作研究观念,创建一种新型的创意写作研究范式和学术领域,是一项必要而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创意写作研究的兴起及其问题
创意写作的兴起首先从反抗“语文学”“修辞学”以及“作文学”开始,最初几十年里以“英语写作”的形式存在。1922年作为教学实践的“创意写作”首次进入公众视野,1936年创意写作在爱荷华大学成为正式学科。[2]但在爱荷华大学时期以及随后的将近百十年里,创意写作实际上以“文学写作”的身份大行其道。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创意写作在全世界的推广以及时代写作语境与技术条件的变化,它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文学写作”,进入真正的“创意写作”时代。若结合名和实做一个大致划分,以美国为起点的话,创意写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英语写作”“文学写作”和“创意写作”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创意写作的准备时期或过渡阶段,后两个阶段则是“文学写作”和“泛文学写作”之间的拉扯与此长彼消。
创意写作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此时有学者开始关注作为课程形式的创意写作,如简妮·瑟芭(Jane Souba)的《中学里的创意写作》(1925)、弗雷德里克(John T. Frederick)《创意写作在美国校园里的位置》(1933)等,随后开始从创意写作教学问题向其他领域延展,比如有关“创意写作是什么”“创意写作学科定位”“创意写作工作坊教学法”“创意写作的历史”“写作规律与创意方法”“分文体写作技巧”以及“创意写作与社区关系”“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等。[3]其中,有关“创意写作是什么”争议较大且持续至今,各类文体的写作技巧研究成果较多。有学者这么描述:“根据帕特里克·比扎罗的概括,创意写作在美国成为一个理论学科,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1.探索这门课程如何教;2.与英文系的其他学科进行学科互渗,尤其是写作学;3.当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时,创意写作中的高级学位——博士学位应运而生。他预言,未来,由创意写作系统中的博士们展开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新的阶段——这些研究将定义创意写作在知识论方面与其他学科的区别。”[4]但着眼世界创意写作,尤其是纳入作为后发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经验后,我们发现,创意写作研究总体上经历了或者说正在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将创意写作作为新兴写作形式、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来考察,着眼于创意写作的“效能”,比如它在“写作”和“阅读”方面的“创造性”,“写作教学”和“作家培养”上的科学性和成果等,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写作学、语文学、修辞学、作文学等。这个时候的焦点集中在创意写作教学法,创意写作课程的开设,具体文体如小说、诗歌的创作技巧,以及“从作家角度阅读”等,成果也较多,如蒂姆·梅耶斯所言:“‘创意写作研究’中的教学方向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发展完善的。”[5]
第二个阶段,开始争取在英语写作中的合法地位,建构作为“非异常”的创意写作学术科目体系,并尽可能地向传统学术包括多元文化、进步教育、通识教育等领域渗透。用黛安娜·唐纳利的话来说,“创意写作研究的学术目标是能与作文研究、文学研究并肩,成为与其他大学学科平等且独立的专业学科”。[6]而她的《作为学术科目的研究》也“整体上,从学理上确立了创意写作研究作为学科的合法性,让创意写作从文学研究、作文教学分离出来,更把创意写作研究从创意写作领域里独立出来,促进学科成为实践科目的独立性和学科性,破除了有学科无理论,有实践无理论的被动局面”[7]。在这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创意写作“是一种学术异常”。[8]它一方面要借鉴传统学术研究的论证方式,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学科”,虽然不免“羞答答”:“创意写作研究还处于其发展的萌芽阶段,因此对该领域探寻的第一步是定义其学术存在和研究本质。”另一方面,又要证明自己的专业差异性:“毕萨罗和里特明确指出,我们只有从其他英语文学研究学科中区分创意写作特有的方法论,以此来发展新的理论和技能体系。” [9]在这个阶段,创意写作研究反复在作文研究、写作研究、文学研究等之间“游走”,时而是对手,时而是队友,为其他专业服务的现象也是常态,如比扎罗所言:“创意写作被历史化为一个领域,近百年来一直服务于规模更大、地位更高的文学研究学科。”[10]当然,这个阶段重点还是在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辨识度的正常学科,在努力消减自己作为学术“异类”与“特例”形象的同时,也努力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我们在写作中重视教学,从而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学科与英语研究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11]
第三个阶段,创意写作研究开始强调创意写作的“创意”本质,论证创意写作学科作为“独特学科”“新文科”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建构创意写作的新本体论和学术体系,试图完全从传统文学研究中独立。这种趋势在中国更加明显。如葛红兵《新文科视角下的创意写作学科发展》、许道军《新文科为创意写作“正名”》、谭旭东《新文科背景下的创意写作发展》、张永禄《新文科是创意的文科》等论文,试图从创意写作的跨专业、跨学科领域等多个角度,论述创意写作就是“天然的”新文科,创意写作包含文学写作,而不是相反。“创意写作作为一种‘新文科’,不仅强调了创造力的培养,回归到了创意、创造本位,而且也直接以交叉学科、跨学科姿态,打通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社会服务之间的边界,且面向个体、面向大众,也面向社会和国家建设。”[12]但从“什么也不是”到“新文科”,中国创意写作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创意写作研究者以革新者的姿态,对两个方面发起挑战:一是挑战中文学科不培养作家、作家无法培养的传统观念,二是高呼取代现代写作学,要形成文学、语言学和创意写作学三者并驾齐驱的学科格局。”[13]甚至它还展示了更强大的“抱负”:“为了强调自己不是传统中文学科体系的‘一员’,它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另一种中文学科,不愿意自己被那种学科传统收编而‘理论化’‘系统化’,拒绝创意写作的元理论研究……”[14]
这三个阶段事实上都没有最后完成,且始终处于交织状态。第一阶段的某些问题的认知至今尚没有达成共识,比如,作为创意写作学科标致的教学方法创意写作工作坊,缺乏足够的反思;而很多后来入场的创意写作从业者,对创意写作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创意性写作是否可以教学”状态。在第二阶段,创意写作仍旧在努力证明创意写作不是传统文学研究的“特例”“异类”,试图取得后者的“谅解”和“接纳”;在第三个阶段,只有少数创意性写作研究者认识到了创意写作在新的写作语境中的变化,以及它在变化的社会中的地位,但他们的研究仍旧需要重新厘定创意写作的历史、知识、方法,更重要的是,亟须革新传统的研究范式,以新的范式去说明新的事实。
二、创意写作研究的范式革新
“创意写作研究”伴随着“创意写作”实践的进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整体而言,其历程与范式符合“科学革命”的一般结构。“起先,是具有一个范式和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随后,是严重的反常,引发危机;最终,由于新范式的诞生,危机得以平息。”[15]借用“文学研究”范式的“创意写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创意写作“文学写作”时期产生的问题,在这个阶段,由于它的实用性,被默认为“常规科学”,用以解答“创意写作之谜”,即“创意写作这门学术科目的目的之一就是祛除写作的神秘性,而非伪造其复杂性”,[16]也顺利实现了从“修辞学研究”“语文学研究”“作文学研究”到“创意写作(文学写作)研究”的范式转换,但是今天,创意写作研究出现了新的“危机”:“创意写作”事实上已经溢出了“文学写作”的范畴,再也不能用“文学写作”一言以蔽之,“文学研究”范式或者说此时的“创意写作”范式已经无法解决新的问题。
实际上,面对创意写作这个已经不“新”且日趋复杂的现象,创意写作研究也一直在调整自己已有的范式,去努力贴近对象本体。目前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意写作研究”(creative writing research);二是具有探索性和革命性的“作为研究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as research )。前者是创意写作研究的“常规”范式,也就是将创意写作研究当作正常的“学术科目”,纳入(英语)文学研究体系,主要以文学研究以及借用写作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去考察它的学科特征。后者则是“以实践为主导的研究(practice-led research),强调的则是当作者反思和记录他们自己的创意实践时可能出现的洞见、概念化和理论化 ”。[17]这种研究方式更强调创意写作的“实践性”,认为创意写作从事者(主要是创意写作研究生和博士生)同时是“创意写作研究者”,由于其成果是“一份原创性的作品(creative dissertation)和一份内容充实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后者贡献了学科知识)”,而这种工作“从创意写作是文学写作基点出发,认为即使按照现有的评价标准,创意写作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写作即发现’”[18]。按照这种范式的理解,创意写作通过调查(素材搜集、人物采访、“偷听”等)、整理(构思)、写作(创作或编写创意作品)以及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主要是“创作谈”)等,“发现”了新的人物形象、生活认知、语言形式、“主题观点”,创造了同样属于学术研究的“新知识”范畴。
但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建立在对创意写作“文学”本体的原有认识上,面对今天的事实难免捉襟见肘,许多学者开始自行调整,比如在创意写作课堂上,有学者指出:“我认为,学生们想从创意写作中获得的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不是特定的‘文学’,而是没有固定形态的‘创意’。像Jump Associates和其他创意的提供者一样,学生们明白,在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时刻,创意技能和经验具有巨大的价值。当然,创意写作的学生最终会按照要求,在课堂上写诗、写故事、写散文,但他们更看重的是我所说的‘创意素养’,而不是这些作品的文学性。”[19]同样,“我们聚集起来,就是为了探索我们的创造性自我,去为之后将要开始和完成的作品酝酿新的创意”[20]。相对于“文学性”,或者文学写作技巧,“创意”(而不是“文学创作”)与“创意素养”才是创意写作最重要的要素。更有学者指出:“创意写作培训 未来需要在聚焦‘写作’以外,以更开阔跨越文字创作的视野,去涵盖更多的学术范畴和创作元素,培育有别于纯粹文字创作者的‘写作艺术’型人才。”[21]到此时,还真应了一句断言:“也就是说,相比创意写作,文学研究似乎更‘无路可走’。”[22]
“创意”在写作活动中具有第一性价值,它“既是本源(创作的内驱力),又是过程(创意赋形),又是结果(生成性的作品也即产品)”[23],今天尤其如此。“创意能力”或者说“创造力”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起点,“因为我们需要起点,‘创造力’将被暂时定义为创造、行动或成为对他人和我们自己都新颖和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24]在创意大师赖声川那里,“创意”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种跨越界线的能力”,对于创作而言,它也是作品的内在需求,为一种新颖的素材找到合适的结构与形式。类似于游戏文案、文旅策划、短视频脚本、超文本制作、元宇宙世界观的“众筹”、IP的二度创作等新领域的写作,对“创意”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传统“文学性”写作已经力不从心。很大程度上,它们的生成过程,与其说是“写作”,其更像是一种创意活动,或者说,“作为创意活动的创意写作”。[25]从内容上说,“创意”也是作品跨文体、跨业态、跨形态流转的核心要素,二度创意与开发的依据。很多时候,在一个作品向另一个作品形式的转化过程中,它自身的外在形式十分不重要,比如《后宫·甄嬛传》作为网络小说,它文字粗糙、结构拖沓,远谈不上杰作,但是它的故事内核、人物基本设定等这些核心“创意”,却足以支撑电视剧《甄嬛传》大放异彩。短篇小说《潜伏》也是如此,一个极佳的故事核与人物结构,发展出了经典电视剧《潜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它的第一规约是“创造性”,第二规约才是“写作”。[26]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一切创意写作,已经成为创意产业的一个门类和上游环节,对于这些写作,基于摹仿论的社会(文化)本位文学观,基于表现论的作者本位文学观,基于实用论的教益本位文学观,基于客观论的读者本位文学观,以及建立在这些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文学研究范式,局限性显而易见。
创意写作学是以创意为本体论的新型写作学,新型创意写作研究范式以此为依据和出发点,它将创意写作活动,包括教育教学及其他社会服务活动研究放置于“创意”基点上,把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创意写作放到生产者(作者)、产品(作品)、消费者(读者)的结构中加以认识,放在市场机制中加以分析。这种研究范式认为,创意的原创性促生了创意作家的实践,创意的产业化流动及实现导致了包括文学阅读、图像/影像/视频观看、游戏体验、文案采用等内在的消费。而对于创意写作教育而言,新范式同样重申和继承文学/文学写作教育的经验与理念,但此时它的重心已经转向“创意能力可以评估,创意潜能可以激发,创意活动可以控制”[27]等方面,而不仅仅是“文学作家可以培养”“文学写作可以教学与学习”。
三、创意写作研究的新学术领域
新的创意写作研究应从问题出发,直面“今天的创意写作是什么”以及回应“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创意写作”,重构“创意写作知识”和创意写作的新学术领域。当然,我们不能凭空虚构一个抽象的创意写作,割裂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作文、文学写作乃至论文写作的关系,夸大创意写作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从而导致创意写作的孤立。同时,也不必拘泥于名实,只认打上“创意写作”标签的写作形式。众所周知,在英美国家乃至以及在中国,许多创意写作实践是以“反”创意写作之名而存在的,有些学者宣称:“……先纠正一下,我们这儿不叫‘创意写作’,我们的叫作‘文学创作’。……因为‘创意写作’是美国来的一个概念,跟大众文化、实用的、流行的、消费的写作联系可能比较密切。我们强调‘人文’意义上的‘纯文学’的创作,这是概念。”[28]事实上,文学写作与“创意写作”并不是对立关系,我们不必制造人为的对立。
新型创意写作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是“创意”,中介是“写作”,终点是“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起点为终点服务,也就是说,所有的“创意”都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和公共文化事业的提升,其中包括文学写作的繁荣,全民创意能力的提升,人人都能写作的意识和人人成为作家的权利。而事实上,创意写作也的确能够为后者提供巨大支持。比如在历史上,“也正是这样,超过50年的大学创意写作训练让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得到提升”[29]。在更具体的事物方面,创意写作也在应对美国战后专业军人安置、移民浪潮、女权主义的兴起、外来族裔的融合、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问题,着力非凡,而在“文学之都”创建上,更是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在中国也是如此,“南京成为‘世界文学之都’,以创意写作作为原动力的创意产业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支撑作用”。[30]从起点到终点,其中介依旧是“写作”。“写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思路和产品内容,“写作教育”为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提供写作人才、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无论何种面向,“写作”是其基本形式与渠道。
蒂姆·梅耶斯认为:“创意写作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教学、历史和倡导导向三个方向。”[31]新的研究范式同样会考察这些内容,但这个领域显然忽视了创意写作的产业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实践形式与可能性,其外延与内涵远远超过了文学写作、写作教学、作家培养等范畴这一事实。葛红兵这样描述:“创意写作学科是研究创意写作本身的活动规律、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创意产业管理和运作规律的学科。”[32]这种界定大大超越了传统创意写作研究的界限,在目前状况下也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和“倡导导向”特征,但我们认为,它更切近创意写作发展的现状和大势。
新型的创意写作学术领域在逻辑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论:重建创意写作史,但非概念推演,要如实进行历史回溯,同时紧扣问题意识:“创意写作为什么会产生、发展和演变”。实际上,创意写作的产生和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回应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梳理创意写作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还会是什么。要走出校园视野、课程视野、英美视野,纳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创意写作形式和态势,从各种层面、各个地区、国家、时期厘清过去的创意写作、事实的创意写作、理想的创意写作多种形态。我们要在英语写作和文学写作中梳理出“创意写作”,而非在各种创意写作形态中执着于文学写作,最终将创意写作史混同于文学写作史,或者将创意写作史归为文学写作史的一部分。
2.本体论:重新回答创意写作是什么。要重新审视现有的观点和答案,超越“创意写作就是文学写作”“一切写作都是创意写作”两个极端判断,同时也要从二者的模糊地带抽身。在充分考虑创意写作与其他写作之间交织与“跨界”的同时,也要严格界定其发展和动态的内涵与外延,重建创意写作的本体:是什么让写作(文学)具有了创意性,被认同是创意写作。在这个领域,关键是何为“创意”,而有关“创意”的研究在传统创意写作研究那里遭到搁置。“长期以来,对创意本质的看法是,它是一种超出系统思维的东西。……但这种对创意写作‘创造性或创意’评价的标准,许多大学选择回避。”[33]对“创意”研究的不足,严重局限了对“创意写作”本体的认知,以及在实践上影响了对“创意能力评估”“创意潜能激发”“创意素养的培养”等方面研究的展开。经常的替代性方案是,将“文学性”“陌生化”“创新”理解为“创意”,但这样理解,必定将研究拉回文学写作,或限定于文学写作。
3.实践论:创意写作的实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在写作教学、培养作家层面;二是在应对审美性、事务性各种写作需要的层面,比如文学写作、底本写作、文案写作等;三是它在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创意能力提升等层面。在第一个层面,研究集中在创意写作工作坊课堂教学和“创意写作项目”中的作家培养方面,但更多地指向文学写作和文学作家。第二个层面仍旧集中在文学虚构和非虚构写作方面,而非虚构写作中广义的、更具生机的“创意写作”研究又相当匮乏。第三个层面更多指向社区服务。这些实践研究更多是指向“写作”的表层,而在“写作”的底层,也就是“创意”的催生、流转以及“创意能力评估”“创意素养的培养”等方面,却几乎全然交给了创意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或者直接借用文学心理学。“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中的创意写作成果评估实际上是对创意写作者的创意写作能力的评 估路径之一,除结果导向的成果评估外,还存在潜能导向的量表评估、 过程导向的实验评估等方法。”[34]在这方面,青年学者高尔雅进行了新的尝试,“通过对案例进行定性分析,提取出55项创意写作能力因子,将这些因子归为基础能力、专业能力两部分,并进一步提出定量分析研究的方案”。[35]这种通过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考察“创意写作能力”的方法与思路,为“创意”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未来它将为创意写作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4.方法论:方法论对应其实践领域所有的和独特的形式,主要包括教学法、写作论以及相应的工作方法论,但更要涉及个人疗愈、全民写作、自由表达以及服务于“创意城市”/“创意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新实践形式,要深入和延伸到创意产业管理、运作、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提升与方法改进方面,甚至要主动介入国家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决策过程。
5.发展论:这个部分要探讨的是,创意写作未来将如何发展。过去,创意写作更多的是与文字结合,现在则与图像、视频、数字密不可分,并与人工智能、“元宇宙”相互介入;过去它强调生产侧的“创意表达”和接受侧的“创意阅读”,现在鼓励全民创意、人人写作和创意的产品化、产业化,以及作为“创意消费者”和“二度创意者”深度参与作品,“创意/创作”与“创意消费”一体化。这不是预测,而是更深入地研究创意写作的发展规律,从未来的视角考量和监察今天的发展,从而提高理论对现实的介入科学性和力度。
创意写作已经深刻改变了今天的文学生态,它改变了写作的教学方式,改变了作家的培养模式,改变了作家的生成与存在形式,“美国所有的创意写作班都是一半小说家一半诗人,很均匀的”。[36]创意写作因“有利于作家自觉写作言识的养成”“为准作家提供适宜的成长环境”“能够改变我们关于文学写作的观念,促进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作家的传播和文学交流”等,最终会“改变大学,改变作家,改变写作的观念与环境,因此也会改变文学的未来”。[37]它也正在改变传统的文学批评,“创意写作从创作内部入手,更清楚特定文体艺术的本质规定性,更易于进行准确的内部批评……相对宽泛灵活的内容范围,与艺术生产系统的特性密切契合。这也使得创意写作更适合做整体的艺术批评”。未来“若果真如此,则批评生态的构成则或许将呈现专业批评、作家批评及媒介批评三足鼎立的结构,批评王国将更加丰富繁荣”,[38]这些改变是进行时,也是不可逆的趋势,当然,它也会自然而然地改变创意写作的研究。
“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39]因此衡量新范式有效性的标志是:“在每个案例中,一个新理论只有在常规的问题解决活动宣告失败之后才突现出来……新理论好像是对危机的一个直接回答。”[40]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创意写作,因此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创意写作研究范式。创意写作在与时俱进,因而创意写作的研究范式也需要随之更新。
注释:
[1]陈晓辉:《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猜想》,《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许道军:《创意写作的本相及其对立面》,《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19年第1期。
[3]葛红兵、雷勇:《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研究》,《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4]转引自谢彩:《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武汉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5]Tim Mayers. One Simple Word: From Creative Writing to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College English ,2009(3).pp.217-228.
[6][9][14][22]黛安娜·唐纳利著,许道军、汪雨萌译:《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第7—8页、第3页、第150页。
[7]张永禄:《创意写作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建构——评〈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1年第1期。
[8]Allen Tate. What is creative writing. 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64(3).pp.181-184.
[10]Patrick Bizzaro. Research and reflections: The special case of creative writing. College English.2004.p.3.
[11]Ted Lardner. Locating the Boundaries of Composition and Creative Writing.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1999(1):pp.72-77.
[12]谭旭东:《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与探索“新文科”之可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3]宋时磊:《热概念的冷思考: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发展述评(2009—2019)》,《长江学术》2019 年第4期。
[15][39][40]托马斯·塞缪尔·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第20页、第62页。
[16]David Morle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creative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5.
[17]Hazel Smith, Roger T. Dean. Introduction: Practice-led, research-led research-toward the interactive cyclic web. In Hazel Smith & Roger T. Dean. Practice-Led Research, Research-Led Practice in the Creative Arts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p.5.
[18]Jon Cook. Creative Writing as a Research Method. In Gabriele Griffin.Research Methods for English Stud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203.
[19]史蒂夫·希利:《超越文学:为什么创意素养很重要》,选自黛安娜·唐纳利、格雷姆·哈珀主编,范天玉、王岚、雷勇、李枭银译,刘卫东、冯奇审校:《创意写作基础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4页。
[20]杰克·赫佛伦著,雷勇、谢彩译:《作家创意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21]梁慕灵:《创意写作不只是写作:香港都会大学创意艺术学系‘写作艺术’人才培养模式考察》,《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2年第1期。
[23]葛红兵、高尔雅、徐毅成:《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
[24]Rob Pope. Creativity:Theory, History, Practice, London:Routledge,2005.p.xvi.
[25]刘卫东:《创意写作的四种形态:渊源与实践》,《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6]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
[27]葛红兵、高翔:《“创意国家”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文学的“创意化”转型及其当代使命》,《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28]张清华、谭宇婷:《关于文学教育》,《华夏文化论坛》2019年第21辑。
[29]马克·麦克格尔著,葛红兵,郑周明,朱喆译:《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30]叶炜:《作为文学教育共同体的创意写作及其实践品格研究》,《写作》2020年第1期。
[31]Tim Mayers T. One Simple Word: From Creative Writing to Creative Writing Studies. College English ,2009(3).pp.217-228.
[32]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3]Jon Cook. Creative Writing as a Research Method. In Gabriele Griffin. Research Methods for English Stud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200.
[34]赵天琥:《创意写作成果量化评估研究述评(2011-2021)——创意写作能力量化研究方向的确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3年第1期。
[35]高尔雅:《创意写作能力量化理论研究论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6]哈金:《在美国,每一位作家都上创意写作班》,《鸭绿江》2019年第2期。
[37]刁克利:《创意写作改变作家的未来》,《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
[38]夏秀:《批评生态建构与创意写作的空间》,《雨花》2015年第11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创意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项目编号:20BZW1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文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许道军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