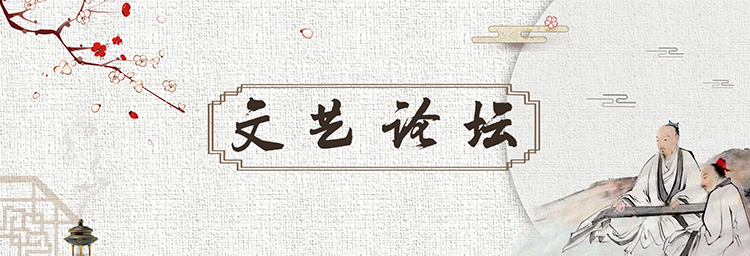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以词学审美惊奇为例
文/张晶 耿心语
一、词学创新之批评标准
“惊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认为“惊奇给人以快感”[2]。此后黑格尔将惊奇引入艺术领域,“艺术观照、宗教观照(毋宁说是二者的统一)乃至于科学研究一般都起于惊奇感”[3]。在中国词学中,惊奇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体验,审美惊奇理论在中国古代隐约可见一条脉络,明代徐文长选诗标准为“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4],后世词论者如清代刘体仁、谢章铤等把诗学之审美惊奇延伸到词学领域,称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历代词论家常不满足于平庸或司空见惯的作品,希望词人能对文本进行创新,给人以惊心动魄之审美感受。审美惊奇理论作为词学创新的评判标准,常用“惊人”“新”“奇”等审美范畴组合进行表述。
首先,词论家认为审美惊奇要以“理”为根据,“新”与“奇”结合。正如清代李渔《窥词管见》第七则所云:“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5]“理”即要求符合理性和逻辑,“理”是“句之惊人”的核心要求,强调新奇的词句要妥而确。李渔还通过具体的例子阐述了“理”在词学中的重要性和具体应用,强调了符合逻辑和理性的词句才能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词学对于创新的追求和对平庸、司空见惯作品的批判态度。这种追求创新的词学精神,不仅体现在单个词句的运用上,也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的始终。
除了“理”之要求,词论家还认为要让读者感受到惊奇,词作还需要达到新奇的审美效果。为了达到这种新奇的审美效果,宋代的杨守斋在“作词五要”中对新奇的标准作了具体要求:“须作不经人道语,或翻前人意,始能惊人。”[6]一方面,“新奇”是指全新、前所未有的不经人道语,得于寻常听睹之外,精彩奇艳。另一方面,“新奇”可以从以往创作经验中汲取营养,翻前人意,词人新意与旧有之句相结合,臻于化境,这也是词论家极为褒赏的境界。虽然极新极奇,却仿佛词中早已存在的佳句,读来流畅自然,宛如穿越时空与古人重逢,此乃词之化境,亦为诗赋古文之化境。德国鲍姆嘉通亦认为,新奇的效果并不仅仅来自对陌生事物的探寻,也在于如何巧妙地将熟知的事物进行创新性的融合。当将熟知与陌生的事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新旧交织、熟悉与生疏共存的境界,能产生更为深沉、浓郁的诗意。它所带来的惊奇感,会深深地触动人的内心,让人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这种惊奇,是深度的艺术体验,也是对美的极致追求。
其次,要达到审美惊奇的效果,不同的风格范式皆可有所作为。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气势雄奇的篇什往往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词作中,那些兼具力量和气魄的豪放风格,同样能引发词论家的审美惊奇,其给人带来的惊奇感丝毫不亚于诗。例如,清代陈廷焯在《云韶集辑评》卷十中评价宋代无名氏的《念奴娇·鲍鱼腥断》一词:“此词魄力雄大,石破天惊,堂堂正正,如大将旗鼓,卓为百代伟作。后来名作虽多,总是另尚新奇,断无此中锋正大、悲壮淋漓也。盖信古人力量之雄厚。”[7]这段评价充分展现了豪放风格词作的震撼力和审美惊奇感。雄大的气魄、强劲的力量、悲壮的情感构成词学审美的豪放风格范式,让读者感到石破天惊。词学中以气、力和情引发惊奇感的例子不在少数,这种风格强调对壮志豪情的抒发,表现出无畏、大胆和激昂的情怀,以及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强烈感慨。通过豪放派的词作,读者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和活力,以及一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词学中引发审美惊奇的不必是雄壮磅礴的豪放风格范式,美人香草、缠绵悱恻的婉约风格也让词论者惊心动魄。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具有与诗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生成原因以及体式特征。词能言诗所不能言处,因而更能引起读者的惊奇感。一方面,士大夫隐晦的婉曲情感,常以美人香草的精彩譬喻展现在词中,这种美人香草式的婉约风格隐含着文人沉郁离忧之情,即便在清平之世,却居安思危,忠爱之情于胸中郁结,但在词中终归于绵惋之句,令人惊叹。另一方面,词体如美人,其艳科本色令词论者惊奇叹绝。词作不仅有艳丽的姿容,更有深厚的内涵和情感,它能够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让词论者为之惊叹不已。
与之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词作产生审美惊奇效果,并不在于词作新奇合理、异于寻常,而是在于妥溜中有奇创。这种观点实质上对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妥溜即要求达到自然纯熟的境界,即清代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所云:“通首之中,用意应有尽有,层次秩然不紊,遣词命笔,无不达之意,安章宅句,磬折铃圆,自然纯熟,而饶有余味,即炉火纯青时候,可以当‘妥溜’二字。”[8]这些词论家崇尚自然而然的境界,故主张求奇要有度,过于求奇,非词家本色。妥溜和奇创的结合使得词作既显得自然纯熟,又充满了创新的元素。这样的词作往往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审美的惊奇感。对于词作的要求不仅仅是达到自然纯熟的境界,还需要在自然中融入奇创的元素,这样词作才能够真正地打动人心,产生持久的审美效果。
词论家为审美惊奇制定了重要的评判标准。对于词人来说,要获得惊奇的审美效果,有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刻意为之、苦吟力索,在词乐、语法和字法上进行精心的雕琢,以创造出奇特的效果。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通过心物交融、情景相生的方式,在主体的情感与外物的偶然感兴中,追求创造性的惊奇发现。这种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震撼和惊喜。
这两种途径虽然不同,但都要求词人在创作中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审美眼光。他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从而达到审美惊奇的效果。
二、创造方式之一:刻意求奇
在西方语境中,笛卡尔把惊奇定义为“对灵魂的突然占有,以至把灵魂提高到对它所认为稀有和异常的事物的一种惊喜若狂的观照”[9]。雅典修辞学家朗吉驽斯也认为,“凡是使人惊心动魄的总是些奇特的东西”[10],这种观点表明,罕见和奇异的事物是审美惊奇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合乐而歌的特殊文体,词在乐曲和文本方面都充满了惊人的奇思。当音乐与词句相配合,再由歌者演唱出来时,它能在审美上给人带来惊奇的体验。这种体验来自词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内容的独特性,它们共同创造出一种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
因此,词的审美惊奇不仅体现在其文本内容上,更体现在其音乐和演唱的表现形式上。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使得词能够深入人心,引发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乐与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古人常依谱填词,善于择腔、择律、押韵,并认为词与乐相结合,才能做到融化文本而无瑕。词乐的重要作用使词人自觉地在乐曲方面下功夫、做文章,以求达到审美惊奇的效果,令味之者一唱三叹,让聆之者动魄惊心。
在乐曲制作中,乐工和词人不断探索新的乐器和技艺,为听者带来审美惊奇。例如,炀帝时期,乐工使用龟兹乐器创制新声,使乐曲独具特色。同时,开皇年间,龟兹乐器大盛,出现了许多善于演奏的乐师。这些新声奇变,不断变换的乐曲形式,给听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此外,词人也常是作曲家,他们秉承着对词乐新奇感的追求,不断自度新曲。如贺铸之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周邦彦之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是奇特。这些新颖的曲调,不仅展现了词人的创新精神,也给听者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享受。无论是乐工还是词人,都在不断地追求词乐的创新和变化,以便给听者带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这种追求新奇的精神,也是审美惊奇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追求审美惊奇的过程中,词人不仅在乐曲制作和曲调创新上有所突破,还将乡野俚俗之调引入词乐中。这种突破雅俗界限的做法,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词人认为这是一种新颖而有趣的尝试。山歌樵唱、里谚童谣等民间音乐元素,被词人采集并融入词乐中,使词乐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这种对词乐审美惊奇的追求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词人为了追求新奇,过度矜持和矫情,甚至于在一调之中巧立多个新题,导致词乐体系出现了混乱。这种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词乐的传承和发展,也使得一些传统的雅正之声逐渐被边缘化。
除了对词乐惊奇的追求,词人每拈一调,务求精警,奇思妙句,总不犹人。为了达到精警的效果,往往在语法上寻求突破,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不因循守旧,而是勇于挑战传统的语法规则,以此来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使词作在整体结构上呈现出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不仅仅是来自词句本身,更是来自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和韵律节奏。通过“精奇”的布局谋篇,词作不仅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更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词人通过精妙的布局,让一些本无甚出奇的词句变得极有层次,用笔有龙跳虎卧之奇。首尾呼应是布局中较为常见的方法。通过在开头和结尾部分使用相似的句子或意象,来强化整首词的主题和情感表达。这种手法不仅能够使词作结构更加紧凑,还可以加深读者对词作的理解和印象。
同时,词人还会运用各种手法来增强词作的层次感和深度。例如,他们可以通过对比、排比、转折等手法,来展现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描绘自然景物、借用典故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得词作更加丰富多彩,还能够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思考,从而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为了达到审美惊奇的效果,词人亦注重于对字词进行锤炼,炼字贵新奇。他们精心挑选每一个字词,注重字词的音韵、意象和内涵,使词作在字里行间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炼字,词人能够更加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也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更加深刻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来自字词本身的美感,也有来自字词所传达的意象和内涵。
经过长时间的经验总结,词人对于炼字出奇的方法颇有心得,通过引入一些在词作中不常见到的字词,以达到审美惊奇的效果。具体方法表现为五方面:其一,以毛诗字入词,这可以赋予词作更深的诗意和文化底蕴。例如,使用毛诗中的典故或字眼,能够使词的表达更加含蓄且意味深长。其二,以经史百家之言入词,通过引入经典文献中的字词或思想,使得词作更具哲理性和思想深度。其三,以方言入词,使用方言中的特殊字词,可以为词作增添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其四,以民间歌谣入词,借鉴民间歌谣中的表达方式和字词,使得词作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更具艺术感染力。最后,以佛、道等诸家语入词,引入其他宗教或学派的特殊字词或思想,可以为词作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
通过这些方法,词人能够锤炼出独特的字词,为词作增添新的审美元素。这些字词不仅具有独特的美感,还能够传达出深刻的意象和内涵。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到词作的美感,还能够深入思考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哲理。
三、创造方式之二:偶然感兴
除了处心积虑地刻意寻求文本创作之奇,审美惊奇的获得还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词学审美惊奇的客观基础在于审美文本本身之“奇”,但惊奇感属于审美心理的范畴。“感兴”即感于物而兴,是创作主体在客观环境偶然触发下产生惊奇的审美心理,从而进行创造性的写作,所谓“感兴”就是审美惊奇,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发现,张世英认为“诗人在这里超越了平常以‘散文式的态度’所看待的事物,而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一样,这就是创造”[11]。
“感兴”的基础在于感物而起情,它注重心物之间的偶然触发,正如明代顾胤光《秋水庵花影集序》所云,“词不难繁音之噪耳,而难柔致之感物”[12],触物是词学感兴的起始。词人对于所触之物的选择是带有目的性的,他们以审美惊奇作为标准来选择和感知事物。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与环境一同发展,因此在自然界中,最能引起词人惊奇感的莫过于节序风物的变化。节序风物的变化能够深刻地感动人心,因此词人在创作时,贵在能够真实地描绘出他们此时此刻的所见、所感和所悟,这样才能避免落入俗套。
词人所惊奇的“物”也包含着人为主观因素,一些人为创造出来的物品,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意义,能够感荡心灵。这些物品可能是一件旧物、一件纪念品或者是一件工艺品,它们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成为词人创作的灵感来源。例如,一件曾经陪伴词人度过美好时光的旧物,能够引发词人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成为词作中的情感寄托。又如,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其独特的造型和工艺能够引发词人的审美愉悦和创作灵感,成为词作中的独特意象。
这些人为创造的物品,在词人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它们不仅仅是物品,更是词人情感的载体和审美的体现。通过这些物品,词人能够更加深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也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加深刻的审美体验。
触物过后,情感的兴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触物生情”,词人本身并没有情感,而是通过接触外物而产生情感。由于人的感觉是因为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词人在触物的过程中,会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和感悟融入对自然界的感知中。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界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与词人的内心世界相互交融,成为词人情感的触发点和灵感源泉。词人通过对外物的观察和感知,将自己的情感投射于自然景物,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这种情感的兴发是自然而然的,也是词人创作的重要动力。通过对外物的感知和情感的投射,词人能够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界相互交融,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和审美价值的词作。
第二阶段是“感于情而物”。在第一阶段触物生情之后,情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形成对于“物”的感悟和理解。词人通过将情感投射到自然景物之中,使自然景物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浓缩的情感寄寓在文本中又再次以自然景物的形态出现。在这一阶段,“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而是寄寓着词人的情感和思想。词人通过对于“物”的描绘和表达,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传递给读者,使读者在欣赏词作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词人内心的情感世界。这种情感的寄寓和表达方式,使得词作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通过对于“物”的描绘和情感的表达,词人能够创作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让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审美体验并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西方诗学认为诗歌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艺术,而形象则是诗歌情感的外化形式。在中国古代词论中,这种形象被称为“意象”。朱光潜先生将意象和情趣的融合过程概括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情趣逐渐征服意象,中间是征服的完成,后来意象蔚起,几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境界,自引起一种情趣。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意象逐渐被纳入审美范畴,并具备了独立表情达意的功能。这种功能使得意象成为词人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也是读者理解和感受词作的重要途径。
经过创作主体与客体之感兴,文本中的情景关系最终呈现为分离或相融的状态,在古典词论中可分为三种情况,即前景后情、前情后景、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大多数词论家认为,在词的创作中,情与景是密不可分的。词人需要深入表达情感,同时也要善于描绘景物。情景双绘,才能够写出好的词句。他们主张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表达方式,使情景相互融合,从而达到情景交炼的效果。例如,宋词中的一些佳句将情感融入景物之中,情系于景也,才能融情景于一家,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可称好词。由此词论家对情景相融提出要求,一方面以有意有味者为佳,在情景交集处,得言外意;另一方面要求情真景真。只有当创作者心目中有一个真实的情景或情感,倾尽其才情和努力去表达,才能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正如清代郑文焯《致朱祖谋书》所云:“即着一意、下一语必有真情景在心目中,而后倾其才力以赴之,方能令人歌泣出地,若有感触于境之适然,如吾胸中所欲言者。”[13]
词学之感兴把创作主体与客观事物的关系视为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情与物交融、主客观感通,进而推动词作从主客关系走向超主客关系,情与景的分合,各显其妙,景物还是原来的景物,但词人通过“感兴”而见到其中的美。感兴论使中国词学审美意识沿着主客观相互感通的方向发展,没有情景遇合的感兴论的不断发展,便不会有意象论、意境论的盛行于词坛,在某种程度上感兴论决定了中国古典词学的前进道路。
四、审美惊奇之生成因素
审美惊奇来源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状态,它与主体的情感、想象和理解等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国古典词学中,审美惊奇的主体通常包括创作者(即词人)和接受者(即词论家)。词人可以同时具备接受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他们能够先作为接受者感受到审美惊奇,然后再作为创作者创作出具有审美惊奇的作品。
审美惊奇的生成受到词人和词论家的文化素养、审美追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不同的词人和词论家对于同一作品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惊奇感受,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词学的独特魅力之一。
首先,审美惊奇的生成要求词人和词论家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养。这不仅涉及创作者的思维、知识、文化修养和艺术训练,还需要他们不断学习、思考和实践,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海德格尔亦认为“艺术家是艺术品的根源”[14],词人无论是使用方法技巧人为构建具备审美惊奇的词作,还是在偶然的外在契机触发下获得审美惊奇,都需要一定的创作能力和审美水平。例如,清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五记录了陈孟周《忆秦娥》词的撰写过程,表明词人的才情是让作品具备审美惊奇的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词论家是词作重要的阐释者和传播者。词作之审美惊奇需要具备一定鉴赏水平的词论家来发现与品味,清代周雪客认为“文章不遇赏鉴家,宁落咸阳一劫,甚为士人之恨”[15]。这是因为审美惊奇往往隐藏在作品的深层内涵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的读者才能够领悟。在这个过程中,词论家通过深入挖掘和品味词作,感受到了审美惊奇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和快感。例如,南宋吴文英的《瑞鹤仙·泪荷抛碎璧》一词,于秋景中怀人,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清代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认为,此词最惊心动魄之处在于“暮砧催、银屏翦尺”这一句。通过分析这一句,可以体会到词人深深的思念和无奈之情,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词作的艺术魅力。又如周邦彦的《四园竹·浮云护月》一词,写羁旅之情,陈洵评价下阕“犹在纸”一语惊人,认为这一句表达了词人深深的思乡之情和对过去的回忆。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表达方式朴拙而不做作,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其次,从词文体自身的发展来看,词在宋代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词人极尽铺陈之能事,运用丰富的意象和华丽的辞藻来表达情感和描绘景象。这种发展使得后来的词人不得不刻意求奇,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和创意,清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亦认为“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16]。这说明,随着词文体的发展和成熟,后来的词人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超越前人的成就。这种探索和创新也是审美惊奇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引发读者的审美惊奇,词论家认为词作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方面,词作需要在表达方式和意象上有所创新,打破传统的模式和框架,以独特的手法展现词人的情感和思考。另一方面,词作更要在主题和思想上展现独特的见解,突破传统的限制,对主题进行深入挖掘和重新诠释。只有这样,词作才能真正地引发读者的审美惊奇,使读者在欣赏作品时感受到新的意境和思考。
词论家强调,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求新求变,更在于对传统主题和思想的深入挖掘与重新诠释。这种创新需要词人在创作时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特的审美视角,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通过创新的手法,词人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和意境,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新的体验和思考。例如,明代俞仲茅在《爰园词话》中认为“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袭”[17],即词人在立意时要避免平庸、浅陋和抄袭,词意要新颖独特,不能仅仅是在寻常所见之外寻找新的题材和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和创新的手法,词作才能真正地引发读者的审美惊奇,成为具有独特魅力和价值的艺术品。
最后,虽然诗与词为两种不同的文体,但词是在诗达到成熟后产生的,那么作为一种新生的文体,词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诗的因袭与借鉴,杜甫诗歌中的新变因素,如表现手法的创新、主题的拓展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深度剖析等,对词体的内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表现手法上,杜甫的诗歌语言、意象影响了词的创作。词人们借鉴了杜诗的精髓,运用丰富的意象和细腻的笔触,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杜甫诗歌中的新变因素为词体的内质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其在表现手法、主题内涵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词学中审美惊奇的生成与杜甫诗学“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审美风尚有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词人在词作中借鉴杜甫诗意,追求惊奇的文本效果。这种借鉴不仅体现在词作的构思和意境上,还体现在语言和表达方式上。通过借鉴杜甫的诗作,词人不仅拓宽了自己的创作视野,还让自己的词作更具有深度和内涵。同时,这种借鉴也使词作在表达惊奇效果的同时,更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如清代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认为吴文英《霜花腴·翠微路窄》“次句乃翻杜子美《宴蓝田庄》诗意,言若翠微路窄,则谁为整冠乎。翻腾而起,掷笔空际,使人惊绝”[18];另一方面,词论家评价作品经常以杜甫诗学审美为标准。杜甫作为唐代诗歌的集大成者,其诗学审美观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词论家认为,以杜甫的诗学审美为标准,能够更准确地评价作品的优劣,更能引导创作者向着更高的艺术境界迈进。此外,借鉴杜甫的诗学思想,对于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以及拓宽创作者的视野和思路,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虽然中西方的文化不同,但有着共通的审美心理。在中国古典词学中,审美惊奇显然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审美惊奇被表述为“动魄惊心”“惊动千古”“石破天惊”等审美范畴,作为审美主体的词人和词论家在创作和鉴赏过程中把审美惊奇作为重要标准,有意使作品出新出奇,这对词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词学中的审美惊奇理论,虽然在古代词论家的论述中较为零散,但其深厚的根基是深深扎根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之中。这种理论不仅来源于众多词人和词论家的艺术创作实践,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审美惊奇理论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这种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特性,它既能够产生新的内涵,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延续和变异。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源于对不同时代众多作家创作体验的总结,具有生生不息的绵延性和实践性。除了审美惊奇理论外,中国古典词学中还有许多其他富有创新力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审美惊奇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审美体验,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脑海中的“集体无意识”。它影响着作者的创作构想和鉴赏者的审美意识,使人们不自觉地期待文艺作品能够有所创新,带来惊奇的审美体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一种体现。
注释: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9页。
[3](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页。
[4]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2页。
[5]李渔:《窥词管见》,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6]王又华:《古今词论》,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
[7]陈廷焯:《云韶集辑评》,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页。
[8]张炎:《山中白云词笺证》,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09页。
[9]方汉文:《西方文艺心理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10]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页。
[11]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3页。
[12]邓子勉:《明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3359页。
[13]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50—251页。
[14](德)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5]沈雄:《古今词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86页。
[1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443—444页。
[17]江顺诒:《词学集成》,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84页。
[18]马志嘉、章心绰:《吴文英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1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有删减。原载于2024年第1期《文艺论坛》)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张晶 耿心语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