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上迁陵
文/张远文
一
去大秦的迁陵,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但,还是去了,大着胆子。
天刚麻麻亮,谷雨的雨,如期而至,酥酥的,如芒,如线,据说,可生百谷。车站,年轻的女售票员问,去哪儿?我脱口说,迁陵。她愣了愣,甩过一声脆响:没这个地儿。我也愣了愣,半晌,才恍然,瑟瑟地说:里耶。
实实在在的,我要去的,并非里耶,而是迁陵。
一岭岭的山,一脉脉的水,纠缠,撞击,拦截着朝晖夕阴的时间。
路,转山,转水,一寸寸地高,又一寸寸地矮,盘盘绕绕中,车上的人大都开始有点晕晕乎乎,埋首在前座的椅背。黄昏时分,终于到了里耶。
下得车来,我发了好大一会儿呆,辨不出何处是东西,哪里是南北。雨,倒是并未被惊扰到,从从容容,仿佛从千年前下过来,落在砖墙、屋檐、青石板上,许多往事的轮廓,模糊了又清晰,清晰了又模糊。歇脚在里耶公馆,土家木楼古色古香,细雨敲窗时,一些过于陈旧遥远的风吹过来,听得见八面山上与酉水河边许多湿漉漉的心事。雨帘,素纱般倾来斜去。缓步走廊,木板微响,咯吱咯吱的,我探头看看两边,左边是秦城壹号客栈,右边是水木年华KTV,一左一右,离得很近,却隔了很久,咫尺间,便是两千余年。
大堂里,一位姑娘,眉清目秀,白色蕾丝边衬衫,休闲牛仔七分裤,一双小白鞋,挑染了的长发,随意斜在胸前,清纯、飘逸、时尚。我问姑娘,从何处来?姑娘莞尔:咸阳。我说,咸阳,八百里秦川腹地,大秦帝都,今来此,算是怀想当年的郡城县治了。姑娘嫣然,说,只是想看看迁陵,看看当年的高里户人大女子杜衡、南阳户人大女子媅,抑或是东成户人大女子沙。我遽然一惊,您与她们有渊源?姑娘眼里掠过一抹烟云:有,也没有。我垂下眼帘,原本生性木讷,加之是与异性对话,更加口拙,很快,不再说话。只是,在心底,隐隐觉得,每一朵云都不再陌生,每一丛草都很善良,而姑娘所说的大秦迁陵女子,似乎正于桑间濮上缦立远视,从城阙郊野迤逦而来。
起身,朝着屋外走去。许多暮色中的事物,想必经得起端详。里耶,是个好听的名字,有着“开拓这片土地”的意思。它更为久远的名字,是土家人世代相称的“梅茶里耶”,意为“开天辟地”。后来,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六王毕,四海一”,于是,楚地的梅茶里耶,成了大秦的迁陵。
现在的里耶,与王村、浦市、茶峒并称为湘西四大名镇,大概建成于明清,繁盛于民国,整饬于当下。夜色渐浓,踟蹰在里耶街头,触摸一缕缕年老的时光,尘世的跫音,显得寂寥而又安静。马头墙上,每一缕席卷天下的风,都历历可数。老屋庭院,泛出状如兰花的光芒,曾经妆满青春与红颜的窗棂,端庄、简约、明媚,像是画框,框住了一阕橘黄的小令,在暗夜里楚楚动人。
匿于武陵山腹地,居酉水中游的咽喉地带,“上接巴蜀通天府,下入洞庭抵长江”,里耶,既是峥嵘天堑,又山大物丰。明清时期,凭借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成为“楚蜀通津”的货物集散中心。湘鄂川黔赣等地的大批客商云集,贸易经商,修街建房,七街、八巷、五行、三码头,绿窗朱户,酒旗斜矗,往来商贾,络绎不绝。蹀躞在固执的乡音之外,我想得更多的是,两千多年前,那场秦楚争霸之战。秦将司马错浮江伐楚,里耶楚军绝地反击,在反复争夺的拉锯之中,八面山下战马嘶鸣,酉水河中浪花飞溅,流血漂橹,这块无法预订春天的膏腴之地,时而属楚,时而属秦,甚至“朝秦暮楚”,那该是怎样壮阔的沙场烽火,怎样激昂的战士悲歌?
二
清晨,薄雾不紧不慢地升起来,酉水河里,几叶闲闲的小舟,若隐若现。近水人家的吊脚楼,线条参差柔软,多半水灵灵的,值得反复描摹。春蓼还没到开花的时候,滩涂上的酢浆草、鸢尾、窃衣、婆婆纳,倒是拼了老命似的绽放,粉、紫、蓝、白,一股脑儿,没有章法地铺陈,用自己一瓣瓣的色彩,给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村庄晕染季节的味道与气息。或许,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它们就一直隐伏在那儿。两千多年后,它们依旧择了吉日,飘然摇曳,迎风怒放。
我用手机小心翼翼地拍了几张,设想,它们是我前往两千二百年前的迁陵,能够持有的信物与凭证。
东阡西陌,惴惴然,递上身份证,跨过井字形古城遗址大门,又在门禁处扫脸、眨眼,确认自己的身份。天高云淡,远吠空旷。我突然感觉,当年进入这座城池的那个男人——故邯郸韩审里,大男子吴骚,为人黄皙色,隋面,长七尺三寸,也需要如此这般地验明正身,方能入城。一枚小小的竹简,始终记得他当初的样子。
毋庸置疑,我,终于进入大秦的迁陵。
护城河边,我久久地伫立、凝望、遐想,一个人,一条路,一座城池,一处远方,追亡逐北的金戈铁马,烽烟四起的折戟沉沙,在夯土与大卵石垒砌筑就的城墙内外比权量力,喧嚣扰攘,在筒瓦、古井、竹简与木牍之间随俗雅化,快意当前。荒寂的城中,有残存着两千多年前的车辙的路,一条横贯东西,一条纵通南北,二者在古城中部交会,仿佛一场醒自千年的大寐,引渡着大秦直道、驰道,乃至五尺道的方向,携带着尘世烟火不灭的余温。占地两万平方米的考古遗址,东西连接城池与酉水,南北贯通古城内外,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城墙,沧桑厚重,敦实深沉,似乎还能窥见当年防敌御寇时的凛凛威风。县署、兵营、武库,排水设施、手工作坊、民居古宅,板瓦、铜器、水井,皆在一派阒寂中眉目栩栩。
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里耶秦简牍。帝国的时间,没有终点,一部分行走在骊山脚下的坑穴隧道,一部分蛰伏于里耶的四方古井。2002年仲夏,里耶古井出土了38000余枚秦简,总计20余万字,数量之大,是此前全国秦简出土总数的十倍,学术价值足以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媲美。
井,是枯井,木框套榫,井壁暗黑,方方正正,普普通通,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却因为积攒下了一个帝国的如烟往事,成为惊艳世人的中华第一井。井中竹简,火烧过,水泡过,细细的,薄薄的,并不规整,然而,光阴辞中,并未远走他乡的墨色犹在,杳不可考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原始古朴的刀耕火种与日升月落,都在笃定的方寸之间,扯地连天,一笔是春秋,一画是流年。
三万八千多枚秦简,三万八千多个无法想象的从前,三万八千多个扑朔迷离的瞬间,无数个曾经被焚毁的事实,无数个无法被看见的小日子,都在简牍版“清明上河图”中慢慢清晰,直到太阳热烈、水波温柔。
棘枝上的交交黄鸟,鸣叫在光阴的深处;有条有梅的终南山,孤月高悬;长空雁叫,西风猎猎,岂曰无衣的士兵,正在修我戈矛;六辔在手的小戎,驾长车勇往直前,他的妻子,在其板屋,言念君子,辗转反侧,载寝载兴,温其如玉;西北往北,东南偏南,家国天下,布衣高冠,一会儿是秦风,一会儿是楚韵,九歌天问、惜誓卜居、痛我生民、国殇礼魂,官吏任免、公文传递、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灾害防治、物资运输、户籍统计、司法诉讼、债务追讨、贸易往来、祭祀先农、教育医药……很久很远的秦人、秦事,披着依稀的光芒,在无法虚构的某一天,相遇于轻薄的竹简,现身于停云落月的尺牍,这个样子,那种情形,纷至沓来,既端庄严肃,又活灵活现。
坐忘,恍惚间。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从古老的竹简中浮现出来,蘸着秦时明月的辉光。
大男子吴骚,从千里之外的故邯郸韩审里,到偏远的洞庭郡迁陵县服役,已有好几个年头。始皇三十二年春日的一个早晨,他蹲在酉水河边,满面尘灰,让人无法看出他确切的年纪。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丁男被甲,丁女转输。面前的河水,白浪翻滚,船来船往,身后蓬牖茅椽,连天接地。他来到城门口,守城官兵对着竹简所记载的样子细细查验一番,方才允许他进城。在城里,他看见许多头上梳着发髻、身着粗麻褐衣的人,都在小心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细心注视着他人的生活。因为,所有人都被编了户籍,以户为单位,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捆绑”在一起,如果有人犯错被包庇,所有“捆绑”在一起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此时的吴骚,心里有点怯怯的,生怕被别人注视、盘问,如果回答不全,或是档案丢失,等待自己的很可能会是“将阳”(游荡)、“阑亡”(逃亡出关)、“邦亡”(偷渡出境)等罪名,被罚为刑徒。快到傍晚,饥肠辘辘的他,想起当年母亲准备饭食的时光。绳床瓦灶,瘦弱的母亲,把黍、菽和蔬菜混合,放在鬲中煮成羹,把韭菜、卷耳,以及一些野菜,做成齑或菹,偶尔还会做一种名叫“醢”的肉酱。他这样想时,舌头禁不住舔了舔嘴唇,肚子愈发咕咕地叫,于是,他到了南阳户人郑不宝的家门前。郑不宝享有爵位“不更”,妻子名叫“有”,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虒”。他向郑讨了碗水喝,想到自己千里服役,举目无亲,徭役不断,禁不住满心伤悲,泪水涟涟。
县署里,一个叫“昌”的人,是这里的县丞。依照秦律,大小事务,须“无宿治”,即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他都要处理大量公文。这些公文,有的是给直属上司洞庭郡的请示报告;有的是与苍梧郡、桂林郡、巴郡、象郡、巫郡等郡公务来往的文件;还有的是与同级的酉阳县、沅陵县、益阳县、弋阳县、临沅县的事务交往文件。从县一级“令、守、丞、尉、少内、司空、狱史、主户、田官、仓主”等,到乡一级“啬夫、乡守、乡主、邮人”等,按秦制,凡在此地处理过的文件,官吏们都要仔细抄写备份,建立档案,以便查验,若有丢失,都要受到“赀一甲”或“赀一盾”的处罚。大清早,鸟鸣啁啾,隶属迁陵县启陵乡的乡守“夫”正在给“昌”写信,说乡里缺少一个里长和一名邮差。这封信在正月戊寅朔甲午送往县城,负责送信的人,被发现竟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四天后,夫收到了县丞昌的回信,请求被驳回,且斥责的口气十分严厉。贰春乡的啬夫“㭯”把乡里的遭灾记录“水火败亡者课”交送给县丞昌,昌收到后,立即派令史“感”送达洞庭郡。阡陌交通,草色青青,傩祭先农后,仓吏将祭祀剩下的一斗半酒卖给了一个叫“城”的人,这,足以让很多个白天之后的黑夜酒气熏天。
在这个帝国的小城,黔首们要么耕,要么战。所有的人“奸邪不容,皆务贞良”,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从上至下,“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耕种得遵循《田律》撒种子、交税;饲养牲畜要遵照《厩苑律》;储存粮食需按照《仓律》操作;从军的要按《军爵律》赏罚;经商的有《金布律》《关市律》制约;做匠人的有《工律》《工人程》规范;吏员要按《置吏律》《除吏律》慎遵职守。孟春之月,桃红李白,禁止伐木;仲春之月,黄鹂婉转,不能涸竭川泽。依据《田律》,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毋毒鱼鳖,禁止采摘刚发芽的植物,禁止设置陷阱,捕捉幼兽及掏鸟蛋等,不从令者有罪。成千上万的刑徒被驱使着从事各种各样的劳作,除农耕之外,作园、捕羽、为席、牧畜、库工、取薪、输马、买徒衣、徒养、吏养、治传舍、治邸,乃至担任狱卒或信差,行书、与吏上计或守囚、执城旦……
各样的小吏与平民,有的弯腰屈膝,有的满面尘灰,有的行色匆匆,有的只留下一个个忙碌的背影……
三
迷失在大秦的迁陵,我多少有点中心摇摇,如醉如噎,行迈靡靡。
秦国,自非子公元前770年建国,止于始皇,历经三十几代君主,前后五百余年,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由西戎小国最终横扫六国,终结春秋以来五百年诸侯割据之局面,缔造了华夏第一个大一统的泱泱帝国,废封国,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其万千烽火与硝烟,诸多雄心与荣耀,皆在万物丛生的时光深处起伏、沉潜、磨损、消耗,最后,彼黍离离,盛极而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何其悲哉。
一个王朝,赢得那么彻底,却又输得那么决绝。乌云压城时,最后的迁陵,同样免不了城破墙毁,烈焰腾空,付之一炬。我不知道,那个叫“昌”的县令,将未能焚烧殆尽的竹简,悉数倾倒在井里,最后去了何方。那个叫“吴骚”的大男子,是否最终回到了邯郸,与母亲相聚。还有那万千的农夫、刑徒,他们的背影,是否会被完好无损地剪辑到后来的某个时光卷轴里。
雨,终于停了。我低着头,不知怎的,心生几许沉郁与顿挫,为苍生没有选择的选择、无法回避的回避,以及诸多无法期许的未来。
倏然,一个声音仿若天籁:嗨,你也在这儿?
我哆嗦了一下,愕然相觑,缓缓回过神来,只见昨日大堂相遇的那个咸阳姑娘,此时一袭天青色长裙,妆容素淡,像是水墨丹青中的女子,从《诗经》中款款走出,与之前的休闲、时尚判若两人。
我凝了凝神,讷讷地说:呵,真是巧了,您也在这儿。
我忽然想起,她来到这儿,就是想看看杜衡、媅和沙等大秦迁陵女子,于是问:您看到她们了吗?
姑娘嫣然含笑:似乎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
我蹙了蹙眉:此话怎讲?
姑娘螓首轻点:这些编户齐民的迁陵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细,平常养蚕、缫丝、湅丝、穿梭、纺织,战时传输粮草,甚至铁甲红妆,骑着心爱的桃花马所向披靡,感觉她们天生就是女汉子。当听到“南山有鸟,北山置罗。念思公子,毋奈远道何”时,才知原来她们也有裙幅飘闪、环佩叮当、移柱调弦的时候,一脉江南妹子的温婉动人。
我默默颔首:斯文在野,雅源于俗,迁陵女子,如精灵小兽,想来,您是见着了,像是一种命,找到了命运,一个人,找到了人生,只可惜,我们都无法知道,后来的她们到底会怎么样。
姑娘将目光略抬了抬,沉默半晌,幽幽地说:谁知道呢?只是,明天,我得回咸阳了。
我看了看姑娘,姑娘也看了看我,没有亲近,也没有疏离,彼此似乎还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雨后的阳光,照在两千多年前潮湿的城池上,遗址上各样的草,葳蕤葱绿,只是,风一起,它们就晃,就乱。一只白鸟,突然从草丛飞了出来,斜掠过天空,像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去处。我眼巴巴站在井边,像块被野风驯服了的石头,攥紧大把大把寂静的光阴,一动不动。恰到好处的风吹过来,一缕吹着她,一缕吹着我,还有一缕,吹着苍茫的尘世。在风中,我们交换着方向,一个往北,一个向南。
天青色姑娘走了。风拂过她的长发,衣袂飘飘,莲步生辉,逆光中的背影是天青色的,剩下的事物与心绪也是天青色的。许多人,可能,一辈子只记住了那个大秦的皇帝,以及几个被车裂、被腰斩弃市的大臣,更多的人,更多的事,大都下落不明。这个姑娘,却牵挂并探望了那个朝代的大女子小民,并试图用云端的数据,在微信朋友圈,帮她们伺机逃出自己的一生。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两千多年前的杜衡、媅和沙,她们在片片竹简里谈论或早或晚的桑麻,絮语不咸不淡的人生,仿佛一直活着,从未死去。而这个远道而来的姑娘,或许,就是千年之后的她们,一颦一笑,即可润了心间的半亩花田。
四
从众多迁陵往事中撤退出来,回到烟火漫卷的庸常,遥远的迁陵,已然成了一种不容篡改的符号。
缭乱的世事,把最后剩的一点白天黑夜用完,天下大溃之前,往往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会提前疏散并穿过人间,预约下一个轮回。而我,只是碰巧在某个沉重的时刻,路过万物。万物皆许我以缄默。一阵风从双肩掠过。顺风细听,似有高亢悠扬的酉水船工号子从河边传来,“撑着篙,拽着纤,一身精光一身汗。冲急流,闯险滩,飙那要命的陡坎坎啊!摇一橹,荡一桨,一盘号子喊千年”,轻一声,重一声,急一声,缓一声,腔调里有生死、有光阴、有蛮力、有挣扎,也有渴望、思念与牵挂。说实在的,我需要听到一些声音,伐木丁丁,采石咚咚,花开花落,号角长鸣,经上古、先秦、两汉,泾水、渭水、灞水,一路向东、向南,过洞庭,入沅酉,直到迁陵,每一粒声音都是万物的呓语,每一次呓语都是生命鲜活的胎记。
很久的迁陵,很近的里耶,既不想占有过去,也无法占有未来,只是,尘世每一场无法隐姓埋名的风雨,都与之息息相关。或许,千年万年过去,每座城池,每个人,都会是最初的里耶,最后的迁陵,谁也无法一声不吭,走到自己的前面、后边。
雪峰苍苍,江水泱泱,两千两百年前的夯土泥墙依旧,两千两百年后的绿树青山愈加朴茂。断壁、残垣、铁血、老酒,牛羊缓行、舟楫往来、战旗猎猎、人喧马嘶。许多来过的人,都已早早离去。许多迟迟不肯现身的事,隐藏在尺牍里,一再地出发,一再地返回。
在迁陵,这座远离大秦帝都的城池,人们可以看到《史记》之外的大秦,一个偏远县城的烟火人间。在这里,有“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火光,有“销锋镝,以弱天下之民”的酷令,有“践华为城,因河为池”的固守,有“繁法严刑,亲疏皆危”的恐怖,有“暴虐不仁,赋敛无度”的残暴,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悲凄。在这里,也有“男女礼顺,慎遵职事”的法度,有“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的休养生息,有“普施明法,经纬天下”的壮志雄心,有“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的制度建设,有“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职责分明。
从迁陵回到老家沅陵,我坐在酉水河的终点——溪子口老码头上,点燃一支烟,看山在、水在、大地在、岁月在,身在万物之中,心在万物之上,禁不住默神良久。江流、郡邑、山色、燕群,似乎正从遥远处而来,又欲回到遥远处去。抬头,眼见烟云散尽,剩下的天空,一派苍茫、寥廓。
(原载于2023年第2期《创作》)

张远文,中学高级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教师报》《湖南日报》《中国报告文学》《湖南文学》《湘江文艺》《文艺生活》《文学风》《诗歌世界》等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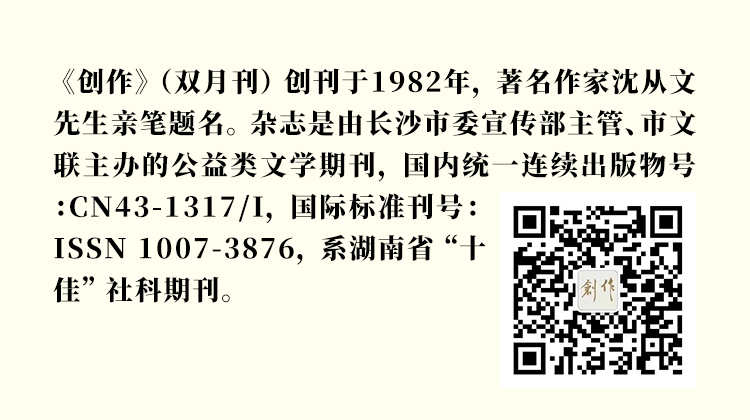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张远文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艺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3/61/13094560.html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