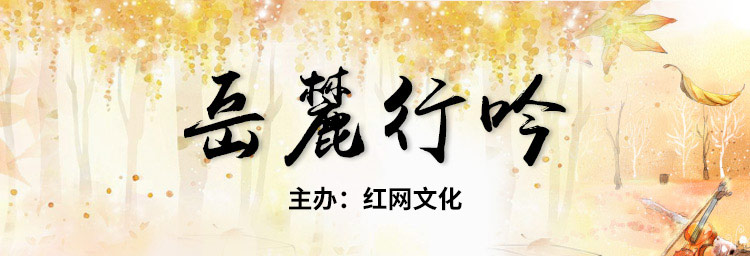

田文国/摄
故乡的老物件
文/严柏洪
前些年到宁乡道林江湾拜会老师五一先生,在老师的艺术馆里,我看到了老师精心收藏的很多农耕时代老物件。有犁、耙、蒲滚、水车、风谷车、扮桶、箢箕、畚箕、箩筐、连枷、扁担等老农具,也有竹铺子、柴耙、擂槌、煤油灯、双喜瓷坛、蓑衣、斗笠、摇井、石磨、烘篮子等日常生活旧用具。那些老物件,都是我小时候见过或使用过的,如今大多消失不见了。它们安安静静地陈列在那里,诉说着往日弥足珍贵又不可复制的乡村故事。见物怀乡,睹物思人,一下子唤起了我心中沉寂了许多年的美好记忆。
在进门的显眼位置,摆放的是一整套犁、耙、蒲滚等耕田农具。看到它们,我仿佛看见了面带憨笑、心地善良的爷爷。
我的童年时代,爷爷正值壮年。爷爷是生产队里耕田的顶尖好手,为人称道,那是爷爷一生的荣耀和骄傲。犁、耙、蒲滚,在爷爷手中,那就是爷爷施展精湛武艺的拿手兵器。
早春三月,春寒依然料峭,油菜花、紫云英迎着春风疯长,蜜蜂“嗡嗡嗡”不停飞舞忙碌。爷爷脱去冬装,打着赤脚,扛起犁,牵上养得膘肥体壮的大水牛,去犁开那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肥沃泥土。
爷爷一手扶着犁把手,一手牵着牛绳,掌控着大水牛前进的方向。泥土在爷爷的脚下翻飞,像一页一页的书整齐翻过,赏心悦目。紫云英作为肥料被纷纷埋在泥土下,只在两垅泥土之间还露出一些花朵和绿叶来,用它们最后的芬芳,装饰着这本充满收获希望的大地春耕之书。
田犁完了,泥坯要在春水中浸泡两天,泡软浸烂,同时让紫云英充分腐烂发酵,增强土地肥力。待到稻田里的水微微发黄,就可以开始耙田了。爷爷肩起耙,牵上他的老伙计大水牛,再次走进他无比热爱与熟悉的田野。
耙是个长着一排铁齿有点吓人的农具,把铁齿深深插入泥土,爷爷扶着耙的扶手,指挥着大水牛奋力前行,来来回回将泥坯一次一次耙碎。
随着气温的上升和淅淅沥沥的春雨洒落,水田里游进来了好多鲫鱼。爷爷耙田的时候,我就提个桶子跟在后面,在浑浊的泥水中捉鱼。不消半个时辰,就能抓到一小桶子。
爷爷是个做事追求精细和完美的人,他耙过的田,都在一个水平面上,如镜子般平整,绝不允许这边高那边低。这点很重要,耕田后插下去的禾苗才能均衡灌溉、均衡受肥。这也是爷爷受人赞誉的关键功夫,别人夸赞他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只是很享受地眯眯笑着。
最后是打蒲滚。纯木质的蒲滚结构略为复杂,滚筒装在一个木架子中间,跨滚筒两边制作安装了类似一个高脚凳子样的物件,人可以站着或坐在上面操作。用蒲滚再打一遍,能把草根和禾根打得更细碎,把泥巴打出泥浆来,秧苗插下去后能快速生根。
我觉得打蒲滚好玩,爷爷偶尔会叫我站在蒲滚上,韵韵味。爷爷在左后方“嗬嗤嗬嗤”赶着牛,蒲滚在泥水中翻滚,不断发出“扑噜扑噜”的响声,一路滔滔向前,我感觉自己无比的快意和飒爽。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快又省事的柴油耕田机大量投入使用,这一套历经千年风雨、立下过不朽功勋的传统农具就彻底下岗,退出了历史舞台和我们的视线。爷爷也失去了他施展技艺的舞台,靠做些零星的木工、泥工活,给人配狂犬病药方,打发时间,安度晚年。
犁耙的位置过去,老师摆放了好几架水车和风谷车。水车和风谷车是农具家族中的大个子,制作工艺讲究,结构颇为繁复。看到它们,我感觉格外激动,我摸摸水车,又摇摇风谷车,童年往事浮现眼前。
水车,又叫翻车,2000多年来,一直是农耕文明时代最著名的抗旱灌溉神器。由车身、链轮、矩形长槽、龙骨刮水板组成。龙骨叶板用作链条,由铰关依次连接,首尾衔接成环状,卧于矩形长槽中。操作时,将车身斜置在池塘边,下链轮和一部分长槽没入水中,驱动链轮,叶板就沿着长槽刮水上升,到长槽上端将水送出,流入稻田。可手摇,可脚踏。我老家的水车是脚踏的,三个大人坐在车身上,双脚飞快顺溜地踩踏着链轮,抽着喇叭筒烟,开心地聊着天、讲着笑话,水汩汩地流进田里,滋润着干喝的土地,看似十分地悠闲轻松。农忙时节,劳力紧张,两个人也能操作应付。
我喜欢看大人车水,常在旁边玩,也很渴望上去试一试。赶上只有两个大人车水时,他们会喊我:洪妹几,上来帮我们车水啰。在老家,习惯把男孩子叫妹几,女孩子叫伢几,大概是为了好养活吧。
听到他们的喊声,我很兴奋,终于可以一试身手了。我麻利地爬上水车。他们帮我调好坐板,坐板是可以前后移动的,我正好够得着链轮上的脚踏坨。他们慢悠悠踏着,我勉强能跟上节奏。正在得意之际,谁知他们突然发力,把链轮踩得呼呼生风,我一下子不知所措,步步踏空,失去控制,脚背频频被链轮打得生痛。幸亏水车前面有一根当扶手和趴着休息用的横杠,我双手死死吊在横杠上,脚蜷曲着,悬挂在空中,吓得大叫:快停下来,快停下来。两个大人哈哈大笑,原来他们是故意捉弄我的。我惊魂未定从水车上下来,再不敢轻易上水车了。直到分田到户后,和父母一起为自家的责任田车水,顶着炎炎烈日,脚踏着沉重的链轮,汗水不停流淌,才知道车水并不好玩。
后来,有了柴油抽水机,水车由于需要的人力多,效率又远不及抽水机,就成了摆设。责任包干制后,生产队的水车折价分给了社员。可是水车占地方,需要一间杂屋存放,灌溉的作用也逐渐失去,不少水车被劈了当柴火,少数留下来的成了旧物古董,被有心人收藏陈列起来。
稻谷收回来晒干进粮仓前,就要用到风谷车。风谷车是用来去除稻谷中的杂质、瘪粒、秸秆灰屑的木制农具,由风箱、摇手、漏粮斗、出风口等部件组成。风谷车扬去稻谷中的秕谷和草屑杂物,剩下饱满、干净的谷子,担进粮仓储藏,或卖给国家粮站。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生产队的晒谷坪上,一堆堆晒好的稻谷在夕阳的映照下,如金子般闪着金黄的光。十几架风谷车一字摆开,一人用撮箕往漏粮斗中添谷子,一人摇车,一人把车干净的谷子担进粮仓。我们一群小孩子在晒谷坪追打玩耍,帮忙赶着偷吃谷子的麻雀和鸡鸭,那劳动的场面十分地壮观热闹。
摇风谷车看似简单,其实也有技巧。摇手摇动的速度和漏粮斗下方搁条的位置都必须控制好。摇手摇得太快,风力过大,会把饱满的谷粒也一起吹出去,浪费粮食。摇得太慢,风力微弱,秕谷和杂物就无法完全车出来。还有风谷车摆放的方向要与风向一致,顺风车谷,灰尘和杂屑才不会吹向操作的人。
承包到户后,我家没有分到风谷车,每次早、晚稻车谷子,都找邻居家借用。我和父亲从邻居家抬回风谷车,母亲摇车,我负责添加谷子,父亲挑谷子进仓。谷子进了仓,除一部分上缴送粮站外,剩下的就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了。
后来收割机出现了,收割、去屑、烘干、打包,一气呵成,省事省力省工,就没有风谷车的事了,风谷车就这样被无声地淘汰了。不过,前几年,我去雪峰山驻村扶贫,看到有老乡还在使用风谷车,很是亲切,赶紧上去帮忙,拍了照片作留念。
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我看到了三个棒槌,用的时间久了,棒槌的底部光滑如玉,摸起来很温润。看到棒槌,让我想起了母亲。童年的时候,洗衣服连搓衣板都还没有,更别说洗衣机了,靠的是母亲的双手搓洗和棒槌来回的敲打。棒槌,我们老家也叫擂槌。擂槌大都是整块杂木做的,结实耐用。
我家老屋前面有一口月牙形池塘,塘基长着高大茂密的樟树和柳树,我们捉鱼摸虾,游泳洗澡,爬树捕蝉,那是儿时的乐土。一块长长的青石跳板伸向池塘,母亲在跳板上挑水洗菜,用棒槌“梆梆梆”有节奏地捣洗着一家人的粗布衣裳,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棒槌声声,很远就能听到。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支枕怯空房,且拭清砧就月光。”古诗词里,那月下捣衣的棒槌声,一声声敲打着诗人的思念与凄凉,敲打着诗人的乡愁。也可见棒槌漫长悠久的历史。可是,棒槌实在太不起眼了,没人在意它是什么时候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见的。感谢老师有心,让我记起了它,记起了母亲池塘边捣衣的身影。
挨着棒槌的,是十多盏各式煤油灯。在没有电灯的年代,煤油灯是我家里唯一的照明工具。吃了晚饭,我在煤油灯下伏案写作业,母亲缝补衣服,一灯如豆,时间长了,灯芯结花,光线暗下来,母亲取下玻璃罩,用针头挑去灯花,又拿块布条把玻璃罩擦干净,屋子里重新亮堂起来。那时煤油又叫洋油,很精贵的,好多人家用不起,吃过晚饭,早早就上床睡觉了。母亲为了能让我读书跳出农门,她是从不吝啬煤油的。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映照出母亲那坚定深远的目光。
在一排博古架上,老师收藏陈列了上百个瓷坛,这些瓷坛皆出自民窑,有青花的,有釉下五彩的,虽说胎质和釉彩一般,但如此多保存完好的瓷坛摆在一起,很是震撼。在我小的时候,这样的瓷坛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用来装糕点或茶叶。
我家也有两个,青花双喜的,是母亲出嫁时外婆家打发的嫁妆。母亲用来存放用纸封着的胡椒饼、雪枣糕,下面放了一层石灰,防潮。双喜瓷坛藏在衣柜里,衣柜上了一把老式锁。那胡椒饼、雪枣糕对我有无穷的诱惑力。母亲外出干农活时,我想方设法找到钥匙,打开柜子,揭开双喜瓷坛的盖子,轻轻把封纸掏出一个小洞,用食指和中指小心翼翼夹出两块胡椒饼、一块雪枣糕,然后将洞口尽量恢复原状,锁上柜子,躲到屋后,心“怦怦”地乱跳着,独自享受这人世间最美味的零食。后来那两个双喜瓷坛烂了一个,另一个完好,我保存在我书房里,也是对母亲的一种念想。
在展厅的拐弯处,老师码放了好几张竹床。那竹床浸润了岁月的汗渍,经历了时光的打磨,泛着沉着的幽光。不禁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夏夜,吃完饭,抬出竹床,出来纳凉的场景。月光如水,蟋蟀轻鸣,萤火点点,蛙声一片。长辈陈七嗲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着吓人的各类鬼故事,我们听得入神,大气都不敢出。夜深了,陈七嗲留下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回家去了,我们也恋恋不舍地收拾竹床,回屋睡觉。
老师收藏的这些农耕时代的农具和生活用具,大多流传了上千年,散发着最质朴而不失厚重的乡土气息,它们是父辈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们也陪伴我度过了少年。而今,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覆盖着尘埃,寂寞无语。在我的眼中,它们依旧那么珍贵,那是我对家乡最真切深情的记忆。

严柏洪,号墨禅,宁乡人。现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湖南金融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文汇报》《新民晚报》《辽宁青年》《金融文坛》《中国金融文学》《湖南散文》《武汉文学》《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全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多万字。发表国画作品100多幅,多次参加画展并获奖。2018年3月至2021年5月,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工作队长,荣获湖南省“最美扶贫人物”称号。出版有个人散文随笔集《岁月留痕》。
来源:红网
作者:严柏洪
编辑:施文
本文为文艺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3/61/13093917.html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