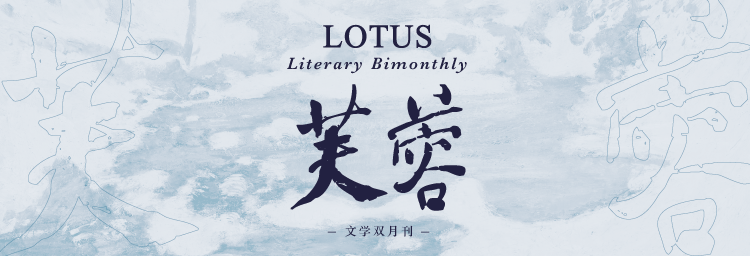

穿上他的鞋(中篇小说)
文/杨映川
他站在河中,他站在雨里。
他看往上游,雨雾迷茫的树林之间如野马蹿出的河水奔向他,冲撞他。如果他的双脚没有用力地扎根踩地,他会像漂浮在水上的木头、树叶、塑料袋、烂拖鞋、死鱼,随波逐流,或是被淹没。他突然放弃对抗,身子向后一倒,河水迅速把一个失去根基的人往下游推送。水灌进耳道、鼻孔,他呛咳,挣扎,大口喝水。他似乎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水已没顶,恐惧竟然不是黑色,是黄色的,偏绿的黄。身子越来越沉,往前漂移又沉沉浮浮。失去方向感的身体被一条硬物拦住,他停止了漂移,死不了了,他有一点点欣喜,老天爷还是留他的。当然,他早就做好准备,如果他不被飞云渡的木头卡住,那便死吧,死在这条令他爱恨交加的河里。他睁开水涩的眼睛,面朝下游的方向,再往前十来米有一个陡然滑落的小峡谷,落差十米左右。如果刚才他不被木头拦住,他便会掉下去,多半再无浮头的可能。以往来漂流的游客随着皮筏往下坠时,无不发出高分贝的惊叫,将树林里的猴子惊得一只只蹿往高处。此处是一个缓冲带,就像一只葫芦颈,宽度七八米,中间修有分隔桩,将皮筏左右分流减少碰撞,当初他亲自取名为飞云渡。洪水泛滥之前,老万借着分隔桩的支撑横上几条长木,目的是拦截那些从上游冲下来的木材,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刚才那一声惊呼便是老万发出来的。老万追着他一路沿河往下跑,看他在飞云渡被木头拦住,老万冲他挥挥手,气喘吁吁地蹲下来。
老万跟袁布林吹牛他曾经在飞云渡拦下过一头牛,那头牛没敢留,第二天就转手卖了,收入九百。他还拦下过一个女人,不过是个死人,怕影响景区生意,没有报警,而是用竹竿捅了捅,让那个女人继续往下漂流。老万拦下来的木材,齐整一些的能卖钱,一根能卖几十,小的送人当柴烧。每年靠洪水赚外快是一件令老万兴奋的事。袁布林是最近在景区收拾残局才有空来听老万吹牛的,以前他根本没留意过这个蓬头垢面身材短小的老光棍儿。在他还没有接手猴子涧之时老万就是景区的员工,平时负责整个漂流河段的清洁和皮筏救生衣的收集,人就住在收放杂物的仓房里。景区已经半年发不出工资,员工们陆续离开,只有老万不走。老万从不催袁布林发工资,他说他在猴子涧待了将近十年,经历了三个老板,袁布林心最善,反正他也没有地方可去,待在这儿看风景蛮好。老万在远处的半坡上种了几畦菜,偶尔也在下河段宽展处撒网,捞上来的大小鱼儿一律煮汤,说是省油又能做到见者有份。他告诉袁布林他连米都不用买,种的红薯吃不完,有时就拿去跟附近的村民换米。清明前是旅游淡季,他抽空帮人种田插秧,说好不要工钱,收成时送米。
袁布林羡慕老万,这个一无所有的老光棍日子过得比他潇洒。他前年初接盘猴子涧,前任老板说是要出国忍痛转手,如果他早一点认识老万,听老万吹牛,他就不会那么盲目了。他考察景区是在十月间,正是旅游旺季,客房全部住满,漂流项目从白日扩展到夜间,一整天山清水秀的猴子涧人声鼎沸。袁布林悄悄用手机计算,这一天下来的收入上十万。而且,猴子涧的自然风光是迷人的,青翠的山谷,淙淙的河水,每一口吸进肺里的空气都是甜的。他认定撞上好项目捡了大便宜,手上的钱不够,便四处筹钱把整个景区盘了下来。
猴子涧上游河段每年五六月间都会发洪水,洪水有大有小,前年就是小洪水,五六月间景区还能营业,只有漂流项目被暂停。大的洪水去年上演了一次,把他沿河新建的茶座全部冲塌,花圃全部冲垮。他重建时把建筑物往里挪了几米,没想到今年的洪水更加肆虐,几乎蔓延进景区的所有建筑物里,茶楼、药浴馆、商店统统被水泡了,存放皮筏的仓库也被冲塌,要不是老万抢救及时,皮筏剩不下几只。偌大一个景区,每年来一次洗劫,终究是撑不下去了。
老万拿着一只橙色的救生圈跳下河,他游到袁布林身边,把救生圈套到袁布林脖子上。两人回到岸上,袁布林被老万搀着进入小商场,小商场门没锁,地上全是黄色的泥浆,货架上的商品早被员工瓜分了。袁布林随老万上了二楼。二楼是干爽的,有一桌一椅,桌上放着两只没洗的碗,床垫直接铺在地上,还有一罐煤气和一个灶台,这儿现在是老万的暂住地。老万让袁布林坐下休息,把一只黑乎乎的水壶架到灶上烧水。两人一开始都无话,袁布林全身上下淋水,很是尴尬,他刚才那一出叫寻死吗?更像是一场闹剧,唯一的目击人是老万。老万看他兴许就像看一个全身赤裸的人游街吧,癫狂撒泼,颜面扫地。
“袁总,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拧一拧,烤一烤。”
袁布林摇了摇头。
“这洪水过得一两天就退了,我们收拾收拾可以开门营业。”
“什么都没有了,营什么业?”袁布林嘘出一口凉气。
老万拿刀削了两片姜递给袁布林,袁布林把姜片含在嘴里,辛辣蹿上鼻腔,他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
“吴老板带你参观猴子涧那年,他已经亏了好几百万,那阵子他是借钱装门面,景区搞打折活动把游客吸引过来,你看到的全是热闹。”
袁布林脸上浮出一丝苦笑,吴金治还是妻子的表兄呢,这杀熟便利快捷,他这接盘侠当得不冤。
“要不,你也学学吴老板,等洪水过后花些钱装装门面,找人接手?吴老板之前是从一个叫黄智海的手上把这儿盘下来的,黄智海那家伙才是流氓咧,拿到钱就开溜,欠员工的工资一分不补,让吴老板当背锅侠被人追了好久的债。”
“吴金治也被坑过?”
“是呀!这就是一个骗一个,轮到谁头上算谁倒霉了。”
想到吴金治这样精明的角色也吃过大亏,袁布林心里好受了一些。还有,刚才老万说的话让他动心了。“能找到接手的人吗?”
“猴子涧山清水秀,交通便利,如果不在洪水期,谁来了都会看上。”
水壶嘴发出嘘嘘声。老万倒了一杯水递给袁布林。袁布林把杯子压在他的膝盖上。隔着湿漉漉的裤子,杯底的温度传到骨头上,他的膝盖泡了冷水隐隐作痛。袁布林没有喝水,一肚子的河水在他嗓子眼里摇晃,不小心控制能吐出来。他把杯子放到桌上起身说:“老万,洪水退了,你帮我收拾收拾。”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能收拾好的。”
袁布林独自下楼,摆手阻止了老万的送行。他回到车上,车子没锁,手机和钱包都放在副驾驶座上。大概是在两个小时前,他驾车在景区逛了一圈,空无一人的景区,鸟叫声比平日更欢乐,空气清凉湿润,山林青翠欲滴,如果没有一屁股要命的债务,这儿就是桃源,眼下却是他濒临破产被人追债的荒凉底板。他怅然下车,无比绝望地步入雨中,走向那条正在发疯的河流。他又回来了,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顿悟,更没有时空的穿越转换,除了湿漉漉的身体,鼓胀的肠腹,什么都没有改变。他拿起手机,有好些未接电话,大部分来自债主。他先回拨妻子的电话。唐百合说她的行程改了,明天往凯里去,还得三四天返程。他让她好好玩,说家里都好 ,她那头就挂了电话。唐百合有自己的工作室,设计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像蜡染布、绣花鞋之类的。这些年,袁布林没看她做出什么作品,她似乎更热衷于旅游,东南西北跑,碰到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就说要实地考察,要搜集资料,每次出门十天半月回不来,儿子袁昇基本上由姥姥姥爷看管。袁昇马上就要中考了,按平时的成绩,重点高中基本无望。
有一个陌生电话拨打了三次,又给他发了信息。“布林好!我是谢康。多年不联系,好不容易找到你的手机号码。胡白玉老师现在南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患了肾功能衰竭,如果你有时间,希望你能去看一看,胡老师一直记着你。”
胡白玉是袁布林高中时代的班主任,袁布林是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高考前父亲锒铛入狱,要不是胡老师一直给他鼓劲打气,他根本支撑不下来。高中毕业至今二十年,袁布林从不和以前的同学和老师联系,胡老师已经是个疾病缠身的老太太了,那一头浓密自然卷曲的长发怕是都白了吧?他鼻子一酸,想回拨谢康的电话,谢康是原来的班长,最后他还是没打出这个电话,信息也没有回复。
袁布林驱车四个多小时回到南安市,身上的湿衣服干透了。他洗了个热水澡,喝了一杯板蓝根,把自己放倒在大床上,一觉睡得昏天黑地。要不是岳父上门,他能睡到对日。岳父面对呵欠连天的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一般到周末岳父母才会领着袁昇回家。“爸,是袁昇出事了?”“这孩子闯祸了,他给同班一个女同学写情书,女孩把情书交给老师,老师批评他不好好学习,思想有问题,他很生气,回教室把那女生的书包扔下楼了。”“书包砸到人了?”“那倒没有,可那女孩哭着跑回家不上学了,老师说袁昇有暴力倾向,让我们把孩子领回家好好教育,还说在袁昇完全认识到错误之前,先在家反省。”“胆大包天!这臭小子是有暴力倾向,这么无耻的事都能干得出来,也不嫌丢人。”“我倒不觉得有啥,孩子青春期,这是正常现象,我让他好好跟老师同学道歉,他偏不,说不想上学了,你看这怎么弄?”“都是你们惯的,还不觉得有啥?他不想上就不上,随他,以后当流氓不用读这么多书。”气话说完袁布林还是到岳父母家去了。
袁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漫画书,听父亲来了,老大不情愿地挎着一张脸走出来。袁布林压下心头的怒火说:“马上就要中考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不想回学校了,妈妈已经帮我申请英国的高中了。”“哦,把国外当避风港了,难道人家国外录取就不看成绩?”“妈说了,有平时成绩就行,我钢琴过了八级,围棋比赛又拿过奖,这些都有加分。”“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赶紧把检讨书写好,明天交给老师,再弄什么幺蛾子出来,我抽不死你。”儿子用刀一样的目光剜他,他的手想抽过去,忍着捏成了拳头。他从来没打过孩子,不想破例。裤兜里的手机振动,他掏出来看,又是一个债主的来电,这个债主是他以前一块儿创业的好友,电话他不敢不接,又没有和对方直接对话的勇气。他答应昨天把钱还人家,又一次失信了。在电话铃声停止之后,他编了一条信息发过去,先是道歉,再说明愿意拿猴子涧景区的股份做抵押,希望对方能再借五十万助他渡过难关。朋友的回复很快过来,两个字“无耻”。他也觉得自己很无耻。
从岳父家出来,袁布林下到车库感到一阵眩晕,从昨天到现在他肚子里就没进过一粒米,不过,还真没觉出饿来。车子开到大街上,他目光在两边搜索,看到一家快餐店,进出的人好像不少。他把车子停好,进店点了一份梅菜扣肉,掏钱付账才发现钱包里只有一张五元票子。拿出手机扫码付账,看到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说本月店里搞活动,一次吃完一斤老友米粉可以不用买单。他环顾了一下周围,果然看到一张长桌边上围了一些观众,两个吃客面前堆着几只碗,前头还有一个服务员双目炯炯地盯着。
“免费吃粉的活动是真的?”“真的啊,在二十分钟内吃完一斤就可以。”“吃不完呢?”“吃了多少就交多少钱呗。”听起来没啥可亏的,袁布林暗忖他平时吃三两刚好,这吃一斤不过是额外发挥一下,有什么难的。于是,他跟服务员说他要参加比赛。服务员面无表情地冲着长桌那边喊:“这里有人要参加活动。”
等五碗米粉一字排开在袁布林面前,他有点后悔了。他这是怎么了?人家是借酒浇愁,他是要借粉浇愁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拿起筷子开干。吃的时候思维大半不在粉上,他想着吃饱了得赶紧想办法借钱,再借七八十万让猴子涧重新开业,维持着顺利转手。可能正是因为思绪的游移,降低了难度系数,五碗米粉在二十分钟内被他消灭了。服务员面带微笑恭喜他获得大奖,一千元的消费卡。他接过一张红色的卡片在众人钦佩的目光洗礼中步出店外。车子开了几公里,他的肚子突然如刀割般剧痛,眼睛发黑,手连握方向盘的力气都没了。难道把肠子撑爆了?他咬牙坚持,驱车前往南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车一停稳直奔急诊室。诊室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他直接冲进诊室,将自己放倒到病床上。
“医生,快救救我,我肚子快破了。”
一个护士走过来问是什么问题,他艰难地说吃撑了。
护士狐疑地看着他说:“你吃了什么?”
“一斤米粉。”
话音未落,他的嘴大大地张开,向外“鲸喷”,护士惊叫退后。几分钟后,他把身体内多余的内容全排空了,他知道他不药而愈,全身上下无病无灾。医生护士如临大敌站在一旁,他从床上爬起来说自己去补挂号,然后快速地逃离现场。
他上下检查,衣服竟然没有沾上秽物,刚才他只是把急诊室的病床和地板弄脏了。他怀疑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应该是了,所以才会干出不正常的事,才会如此丢人现眼。他在挂号口徘徊,想需不需要看一下精神科。他深吸一口气,给自己鼓了一下劲,说都会好起来的,没那么容易被打倒,口号喊了几句,他想起多年前天天给他鼓劲的胡白玉,泪如泉涌。当他把车子拐进这家医院,潜意识就是知道胡老师住在这家医院。就算是要发疯,要破产,老师是要看的。
袁布林走向住院部,在护士站查到胡老师的病房号。要等一个多小时才到探视时间,他到医院外头的取款机想取点钱给老师,只有一张卡余额三千多,信用卡全透支了。这三千多块还要支撑他借到钱为止呢。他最后取了五百块,买了一篮水果两箱牛奶。站在病房门口,他一眼认出胡老师,胡老师人枯黄清瘦,坐在靠窗边的一张椅子上,头发剪短了,也全白了。房里还有其他人,看样子是一对夫妻,还带着孩子。
“胡老师,我是袁布林,您还记得我吗?”
胡老师一惊,站起来说:“布林啊,你这孩子,有二十年不见了吧?惦记你啊。”
“胡老师,对不起,我来迟了。”袁布林放下手中的东西,走上前握住胡老师的手。胡老师的手冰凉,他把老师扶回椅子上坐下。
“袁布林,看看我是谁?”说话的是那对夫妻中的女士。
袁布林仔细盯着那张化了浓妆的脸,脸蛋虽然圆润,但看得出早年是瓜子脸,眼睛又大又圆,没有层叠的眼袋之前肯定也是清亮水汪的。
“冯燕如!”
“算你有良心,还记得起来。”
“班花,不,校花,谁敢不记得。”
冯燕如得意地扫了旁边的男人一眼,介绍说:“这是我老公,高宇明。高宇明,这是我同学袁布林,大圩林场唯一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个男人握手分别坐下。冯燕如又让那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叫袁布林叔叔,说孩子一直是胡老师帮补习数学。袁布林想起当年胡老师也给自己开过小灶,讲解了很多数学题。他问老师病情如何,胡老师笑着说这种病一下死不了,就是拖着,把人拖到人财两空为止。袁布林听着心上一片悲凉,他后悔刚才小气了,怎么都该给老师取点钱。
“袁布林,有个好消息,你还记得陶庆霞吧,她跟你一样和我们大家都没联系,今年刚回南安发展,她听说老师病了,张罗着给老师找肾源做移植,费用她全包。”
陶庆霞这个名字对袁布林来说确实是久违了,如果没有人重提,这个人和名字很难从记忆沟里翻腾上来,但这一翻腾上来竟然鲜活无比,如奔跑而至,将大圩林场那一片山林间的气息撞入他的胸口。他一点也不奇怪陶庆霞能做出这么伟大的事,他还为她感到自豪。
“太好了,真是个好消息,胡老师您要安心养病,都会好起来的。”
“多亏了你们这些孩子,我真有福气。”
“袁布林,听说你也是富豪级别了,帮衬一下我们这些老同学呀。”
冯燕如拍了一下高宇明的肩膀,高宇明马上掏出手机要加袁布林的微信,并自我介绍说是做花木生意的。
袁布林说:“现在生意难做,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你们就只管谦虚吧,陶庆霞我给她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估计是怕我们沾她的光吧。”
胡老师说:“燕如,别这么说庆霞,她性子是有些孤僻,但心好着呢。我到她新买的办公楼去看过,能俯瞰整个南湖公园,可气派了。她又没什么背景,全靠自己打拼,真不容易。”
冯燕如说:“我早听说她资产好几千万,看来还不止呢。”
高宇明说:“你还说跟人家是好朋友,到现在面都没碰上。”
“那可不怪我,问问袁布林就知道了,袁布林,你和陶庆霞有联系吗?”
袁布林摇了摇头。
“我一直觉得她暗恋你,想不到她和你也没联系,不理我们就不奇怪了。”
(节选自2023年第3期《芙蓉》杨映川的中篇小说《穿上他的鞋》)

杨映川,女,1972年生,文学硕士,一级作家,现供职于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在《花城》《人民文学》《作家》《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数百万字,有《魔术师》《淑女学堂》《我记仇》《狩猎季》等十余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出版。曾获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广西独秀文学奖、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杨映川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