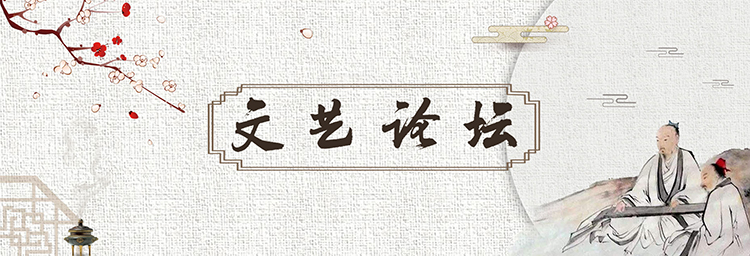

《理想照耀中国》剧照。
百年理想的影像表达
——《理想照耀中国》丛论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意义上的“理想”进行传承,从而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何在40集的短剧中尝试40种不同的讲述艺术?可以说,《理想照耀中国》无论从其主题的开掘还是其“复调表达”“新主流”剧、“轻”叙事等方面的艺术创新,都具有难得的开创性的意义。
何庆平:
轻逸、精确与多样
——《理想照耀中国》的美学特征
作家卡尔维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讲稿{1} 中,论述了新千年后文学的几个重要特性,即“轻逸”“速度”“精确”“形象鲜明”和“内容多样”。虽然卡尔维诺的论述是从文学角度出发,但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具有相通性,若将这些思考拓展到影视领域,会发现不少新世纪的影视作品也有类似特性,如《理想照耀中国》就具备了“轻逸”“精确”和“多样”等美学特征。
一是轻逸。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减轻词语的重量;叙述一种细微的思维或心理过程;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形象。作为影视作品,《理想照耀中国》的“轻逸”体现在三个方面:形式上的轻盈、叙述上的轻快与意象上的轻细。
形式上的轻盈。与其他电视剧一集45分钟不同,该剧一集30分钟,除去片头片尾才25分钟。每集故事和人物独立,相当于一个电影短片。正如汪曾祺先生认为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是短{2},现代影视作品中短片、短剧也越来越多。短片形式轻盈多变,给予了主创更大创作空间,在切入角度和故事结构上可以更加灵活。排播也可以随机应变,如高考首日6月7日播出的《远方不远》,主人公是参加了1978年高考的林鸣。
叙述上的轻快。剧集常略写人物的重大时刻,而将重心放在侧面时刻、理想酝酿时刻。如《从头再来》讲述杰出民营企业家薛荣的创业,戏份集中在薛荣跟姐妹们的散伙饭和重聚饭两场大戏上。《我送亲人过大江》没有把重点放在颜红英撑船渡过长江天险的宏大场面上,而是聚焦在颜红英能否参加渡江的戏剧冲突上。
意象上的轻细。剧集的象征性物品都比较具体而微。比如《纽扣》把改革开放的宏大、个体工商业的艰辛,凝聚到一颗小小的纽扣上面;《第五十五封信》从一张老照片入手,用照片修复来引出烈士陈毅安的故事;《冰糖》把两弹一星伟业的厚重感,蕴藏在小小的冰糖上。从轻的角度切入,传递出重的分量。
二是精确。“精确”是《理想照耀中国》的又一个美学特征,既包含艺术上的精致和精巧,也包含制作上的细致与细腻。
从艺术上的精巧来说,《真理的味道》长镜头营造的镜头跟进效果,电影感十足。《歌唱祖国》的黑白画面营造了五十年代的时代感,长镜头调度体现了艺术技巧的娴熟。《磊磊的勋章》几处场景采用“留白”手法,可谓“无声胜有声”,回味悠长。《雪国的篝火》的雪景都是实地拍摄,质感铺面而来。《秀才遇到兵》两个人物的性格冲突设计得非常巧妙,故事节奏感极佳。
从制作的精致来说,这可以体现在配乐上。主题曲《理想》旋律优美流畅,歌词深邃隽永,令人过耳难忘;《真理的味道》开头悲壮配乐,立即把观众拉入凄风苦雨的时代情境;《八妹》片尾合唱曲目感人至深,还融入了闽西客家红歌乐调。配乐最为突出的是《173米》,活泼多变的三弦伴奏和黑管配乐传递了人物斗志昂扬、充满干劲的状态,接地气的唢呐伴奏与工头老陈闹离开的欢乐片段相映成趣,多种乐器交响合奏适配了铁路施工时的协作配合与热火朝天,低沉悲伤的钢琴片段表达了遭遇塌方之后主人公的沮丧和绝望心情……多种配乐完美贴合了剧情走向和人物心境。
该剧道具使用也很用心,几乎每集都有独到细节。如讲述1994年薛荣创业故事的《从头再来》这一集,就使用了多个属于九十年代甚至独属于河南当地的道具。比如当时非常火爆的万利达VCD,非常时髦的摩托罗拉汉字寻呼机,在河南当地成为龙头企业的“金星”啤酒,在牌照变革之前的老式牌照车辆等,共同构建了浓厚的时代风味。
三是多样。如果说现代小说可能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包含更多信息的“内容多样”,那么身处“视觉文化”时代{3}的影视剧,携带的信息量自然更为庞大和丰富。《理想照耀中国》具备的第三个美学特征是“多样”,包含内容的多样和风格的多样。
内容的多样。主要体现在人物选择和故事题材上。剧集讲述的四十个人物,涵盖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个时代,既有陈望道、邓稼先这样较为著名的人物,又有只在某个领域内闻名的人物,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人物所在领域不同,使得故事题材也很多样,可能涉及战争(《烈性》),可能涉及音乐(《歌唱祖国》),可能涉及教育(《秀才遇到兵》),可能涉及环保(《你的眼神》),可能涉及《体育》(《磊磊的勋章》)。
艺术风格的多样。有严肃端庄的风格,如《真理的味道》《天河》,有感动催泪的风格,如《天河》《雪国的篝火》,有轻松幽默的风格,如《173米》《秀才遇到兵》,有平实却回味悠长的风格,如《磊磊的勋章》《从头再来》,还有偏艺术偏诗意的风格,如《歌唱祖国》《八妹》等。丰富多样的风格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
作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重点剧目,《理想照耀中国》却具备了卡尔维诺预言的新世纪文学的美学特征。这是一种巧合,因为主创首先是从故事和人物出发,不可能参照着先框定其美学特征再创作;这又不是一种巧合,因为若要创作符合人们审美旨趣的作品,必然会包含相应美学特征。可见,《理想照耀中国》在艺术上具有探索性和先锋性,树立了可供将来的主旋律作品及其他影视作品借鉴的美学范式。
张静雅:
复调表达:以叙事结构增殖故事
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横跨百年时间,抓取具有集中表现力的历史片段,编织各自独立又彼此勾连的四十则单元故事,并通过叙事结构实现故事增殖,进而以点带面,复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在各行各业的奋斗历程,极具震撼力与感召力。
作为一部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播出的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秉持现实主义审美原则,在深入的历史考察中营构真实的时代环境和丰富的视听形象系统,篇幅虽短,意蕴悠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所实现的复调表达效果,既在有限的篇幅内扩增了故事的体量,又实现了与观众的对话与交互,以精彩的中国故事参与当下中国文化自信的巩固。
复调表达,首先表现为通过多声部的叙事,更充分还原历史场景,凸显核心人物的抉择。“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历史”{4},这些具体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物做出决定的动因。《理想照耀中国》以凝练的笔法展示了同一时代不同人物之所以为之的心理机制:首集《真理的味道》,陈望道见证了所谓“底层人”生活的酸楚,为谋求社会变革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而其童年密友江流,虽也渴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却屡屡受挫于文化惯性带来的现实遭际,几近一蹶不振;第七集《你的眼神》,龙勇诚有感于滇金丝猴数量的减少,决定将一生奉献给动物保护,他的学生也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希望回到都市;第九集《劳工万岁》,律师施洋脱掉西装,换上粗布长衫,弃绝自己的阶层优待为劳苦大众发声,其故友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法庭上成了施洋的被告;第十六集《希望的田野》,女大学生雷金玉放弃在厦门待遇优渥的工作,毅然回到故乡福建福安坂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带领与感召全村人民共同建设家乡,她的同事、家人甚至当地乡民最初都不理解、不配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剧集中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成立的逻辑,都有其之所以为之的因由。所有角色都提供了自己的立场与视角,诉说自己的故事,或曰“对生活的比喻”{5}。在理解人物的同时,故事自然实现了增殖,历史的景貌也依托这些迥异的抉择方式得到了多层次的叙述。众声喧哗中,主人公的声量不曾削减,却更为昭彰,那正是理想的光芒,在纷杂的社会中将人的生命照亮。
复调表达,更意味着穿越时代,实现深沉的召唤。在有限的篇幅中,总有不少镜头是人物的背影,结合大量考究的历史细节,使得观众的代入感大大增强。无论是《173米》和《冰糖》中的标语,还是《雪国的篝火》和《我是小方》中惨烈的场景,都是在陌生化的氛围中传递了跨越时空的坚定精神。正如美术史上,弗里德里希以《雾海里的漫游者》开了背面画的先河,模糊主人公的面容使观众直接转换立场浸入其面临之情景,《理想照耀中国》也通过自然的背面镜头丰富了观众的感受,通过与前辈的一致视角实现心理穿越。经由此,四十个章节呈现的是与观众有一定距离的故事,观众却可以在观剧过程中建立深度的共情。伴随着人物的抉择而情绪起伏,更在每一个关隘,明了之所以我们能看到前行者的背影,是因为与前辈们方向相同。因而,故事就在剧中人的时代性剖白外,又共时性补充了观众的此时性剖白,形成照应。剧中人物的剖白,也就有了更为清晰的引导性,导向当下语境中对庸俗的抵抗,更指引着中国文化的建构。“文化的进化离不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6},《理想照耀中国》的四十个单元提供了海量具有感召力与真实性的历史样本,以更有代入感的年轻态话语实现了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更达成了跨时代的民族性共情。
复调表达,实质是在剧集的内外交互中实现当下与未来的文化建构。历史剧对具体故事的选择中即隐含着信息,而这种筛选指向对集体记忆的搭建。百年之际,影视剧集的社会责任更加清晰。“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7}如果说回顾所来径,清理历史的脉络构成了《理想照耀中国》的第一层叙事目的,其与当下现实的照应就是故事之外又必定涵盖的一份平行结构,这二者交织与共,构成我国文化道路的砖石。正因为“是观众(而不是电影)建构了这样一个‘叙事综合体’”{8},《理想照耀中国》在考究表达之外,也注重与观众的交互。选取有生活感的片段推进亲近感,启用“流量明星”增强整体的新鲜感,在整体的考量下也就成了必然。片头的引入与片尾的简介,包括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对剧集的阐发与讨论,正体现了观众意识与影视剧的使命感。
《理想照耀中国》,通过复调表达,在内外交互中增殖故事。这种增殖,与剧集的内容高度适配,是对内容感召力与表达力的增强:历史,正是对复调表达的清理,中华民族不灭的理想光芒,将照亮那份独特的中国表达。每个人都可以是这份理想之火的传递者,特别是今日的你我。
陈雪莹:
“新主流”剧《理想照耀中国》艺术创新之处
“新主流”剧{9}由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在2021年《中国电视/网络剧产业报告2021》中提出,报告中将“新主流”剧的特征概括为“主流价值+主流市场”,即既符合主流价值观、又符合市场诉求,并给予了“新主流将更主流”的高度评价和殷切展望。
《理想照耀中国》作为献礼建党一百周年的主旋律剧,采用了“诗选剧”的形式,通过“散点透视”书写百年历史,从而在“有意义的瞬间 ”{10}里构建出壮阔史诗,并通过中心人物的“陌生化”和边缘人物的“核心化”的手法,在艺术性和真实性的结合中完成了“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书写。
一是百年历史的“散点”书写。《理想照耀中国》采用“诗选剧”的形式,选取中国建党一百年来不同时期的40组人物故事,浓缩在每集25分钟左右,共40集的剧情里。“诗选剧”为英文anthology series的翻译,也称“独立单元剧”, Anthology源自古希腊语·νθολογ·α,以“鲜花采集”的意蕴引申为诗歌的集合。诗选剧每一集都有不同的角色和故事,相对独立,又有统一主题,较有代表的有英剧《黑镜》《9号秘事》等。国内电视剧创作中,连续剧为主要形式。2019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采用多编剧、多导演编写和拍摄独立单元的方法,其艺术性的呈现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新突破。2020年,抗疫报告剧《在一起》同样采用多个编剧、导演合作的方式,由单元故事组成全剧,使每集剧集得到了更精心的打磨,实现了“主旋律”与“艺术性”的结合。
作为建党一百年的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展现了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梦”,从贫穷落后到走向伟大复兴,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的历史前进之路。在如此大的时间和历史跨度中,《理想照耀中国》采用了“诗选剧”的形式,很好地处理好了主题与内容的关系。在已播的二十余剧集中,有写建党伊始的《真理的味道》,红军长征时期的《雪国的篝火》,实行市场经济的《纽扣》,现代农村发展的《希望的田野》,2020年抗击疫情的《一家人》……从建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再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建设性成就,《理想照耀中国》选取了40个时间节点中的小故事,将其中或温情或坚毅,或崇高或朴素的理想内核,细微而深入地呈现出来,从而用这样一种“散点透视”的方式,汇集出了多维度、立体化的百年党史。如总编剧梁振华所说:“《理想照耀中国》像是在写一个个盛大宴会的回音,或者故事的关键转折点,抑或是一首歌曲最唯美的变奏。40个故事40种风格,仿佛一首歌,它并非单一的调性,既有表现主义,也有诗歌般的象征主义,是非常浪漫的创作态度。”{11}全剧犹如一首组诗,通过每一小节的抒情,合力完成了壮阔的情感表达和内容表达。
二是人物的“陌生化”与“核心化”。总体来说,《理想照耀中国》的人物塑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知名人物;一类是在历史或现实中较为“边缘”、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前者的人物塑造主要采用了“陌生化”的手法,即选取该人物不太为人所知的特点,或者不常关注的角度,以此为切入点来塑造人物。例如《真理的味道》,讲述陈望道的故事。但其并没有从陈望道的留学经历、归国经历等人生经历来展开,而是将人物放置在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中,引入“江流”这一人物进行对照,在自然的叙事推进中,诗意地展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极具匠心。《冰糖》则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研究工作,与妻子为低血糖的他积攒冰糖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给故事增添了温情色彩,又带来了新的观剧体验。
而在四十集的剧集中,在历史或现实中较为“边缘”、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占了更大的比重。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上,则采用了“核心化”的手法,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人物自身经历上,从而展现人物精神。例如《守护》讲述共产党员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对重要材料的守护,《磊磊的勋章》的主人公是女子柔道队的陪练员,《纽扣》书写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章华妹这一个体户的经历作为主线,《雪国的篝火》的主人公甚至未在历史中留下姓名……作为主旋律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未只着眼于历史中“英雄人物”的“高光时刻”,而是将视点更多聚焦于“历史的角落”,在角落中发掘人物身上理想的光芒和信念的力量,从而达到“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
三是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作为“主旋律”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保证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能从侧面反映历史。而作为“新主流”剧,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性,从而在市场中获得好评。如《天河》以红旗渠的修建为背景,在时代环境、地理条件和修建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但其中因打翻水而自尽的妇人、多次出现的“红旗”意象以及对吴祖太回忆中妻子的镜头表达,皆有艺术加工和艺术处理的成分。又如《八妹》中,将八妹唱歌进行革命的故事与当代一所学校合唱团学习唱歌的故事两条线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两个时空的并置中实现了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总而言之,《理想照耀中国》在时间和历史的处理上,采用“散点”书写的“诗选剧”形式,在人物的处理上采用“陌生化”和“核心化”的方式,将真实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在书写百年党史的过程中完成了“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表达,既符合主流价值观、又符合市场诉求,是“新主流”剧创作的代表。
王璇:
瞬间·情感·记忆
——《理想照耀中国》中的理想传承
文化记忆借助不同媒介载体,选择、储存以及重塑社会框架及文化体系中的共同记忆,进而建构共同文化心理,共同文化心理是形成文化认同与集体归属感的关键因素。在读图时代环境下,影视等传播媒介以其强大的视听效果逐渐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影视作品的制作传播过程也就是文化记忆的传播过程,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情感被唤起,存储在影视中的文化记忆形成社会共同文化心理,进而将信仰火炬传承下去。
媒介:理想力量的影像载体。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做出的延伸,“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12}因此,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否关系到群体是否能够形成共有的文化心理,而是否能够形成社会共有的文化心理则对文化身份的建构产生影响。文化记忆的传承对社会群体的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
影视作品将抽象文化经验具象化,其以图像、声音的呈现形式给予观众直接冲击。《理想照耀中国》通过闪回、画外音、长镜头、黑白摄影、蒙太奇等多种拍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观赏性与冲击力,真正做到了艺术性、真实性以及可看性的多重结合,用不尽相同却又恰如其分的表现手法将熟悉或陌生的故事带到屏幕中,带入情境中,将理想力量传递至观众身上。
路径:历史瞬间的创意表达。主旋律作品往往存在内容与观众审美差异较大的问题,作品中蕴含的力量难以传达到观众身上。部分观众能够轻易共情,是因为其拥有与作品讲述的故事相似甚至相同的经验,如此仅形成了个体记忆而非共同文化记忆。随着经历者的离世,记忆如果没有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那么记忆力量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因此,为吸引青年观众,主旋律与青春化的结合势在必行。
四十集,意味着四十个瞬间,但刻画瞬间并不意味着情怀缩水。作品以诗选剧的形态与非线性的播出方式带来了时空穿越和思维跳跃感,将历史瞬间与个人经验“正面相撞”,情感在此刻被唤醒。
《歌唱祖国》中梦境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交错中实现记忆永恒;杜富佳在走廊哭泣的瞬间、章华妹成为第一个个体户的瞬间、刘磊磊心甘情愿被摔284万次的记忆……这些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平凡又不简单的瞬间与青年的情感形成共振。
年轻观众从来都不是与主流对立的存在,从《觉醒年代》到《理想照耀中国》,从参演人员到观众,年轻人已经成为主流作品的主力军。四十个原型故事中大多都是年轻人的故事,而正是同龄人的事迹易为另一群同龄人所接受,并为之而感动,在高浓度情感力量的感染下,自然而然强化归属感。
《理想照耀中国》在筹备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青春化倾向,表现出与青年观众对话的诉求。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确定选题,每一个参与到投票的网友都是“制作人”,以参与感带来责任感,由责任感催生好奇心。当青年人的情感经由重点突出的故事情节和创新性表达方式唤醒,自然而然地就会进入剧情,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思考,在此过程中,文化记忆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距离较远的青年人身上复现,由此形成了文化和情感上的双重认同。
功能:文化记忆的留存与延续。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影视、新闻等具备视觉冲击力的传播媒介对记忆的保存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文化记忆成为影像媒介的内容构成时,影像也成为文化记忆的内在构成。
在现代生活背景下,形成高度文化认同和群体归属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理想精神与信仰力量的传承则是个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主流作品的创作过程也是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传承过程。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以墨水味为“真理的味道”,到“音乐疯子”王莘创作《歌唱祖国》的经历,再到邓稼先为了研究原子弹远离家人长达28年……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在历史课本中出现过,但电视剧更多讲述的是小方、刘磊磊、祁建华等相对平凡和陌生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理想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感与美好,又是一种不简单的信仰力量,持续影响着今天的观众。当观众为“小切口,大情怀,正能量,青春态”的作品所吸引,电视剧中储存的文化记忆得以延续,得以形成更加稳固的群体。
理想与信仰不是某些人特有的,它们潜藏在每个人的身上,被某个特殊的瞬间击中,唤起情感认同。《理想照耀中国》以影像的形式承载了四十个故事,这些故事展现出的理想力量犹如黏合剂,将被唤起记忆和经验的国人凝聚在一起,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理想”,理想与信仰的力量之火传承至今,又将借助记忆的力量延续下去。
孙小淅:
“风吹树叶,自成波浪”
——《理想照耀中国》的“轻”叙事
《理想照耀中国》作为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剧,以具有首创性的序列剧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电视剧“一剧一中心”的规范。这种多维散点的形式,除了以短小而完整的方式嵌入当代碎片化的影视观看需求外,还力求以“全景化”取代“神圣化”,将理想落于实地,在平凡的生活情境中追求伟大。这种“消解”无疑更加符合日趋强烈的以“主体性”取代“集体性”的主流价值观,但却在“主体性”确立的过程中增加了个体对于集体的认同感。
在形式创新的基础上,不磨损单个剧集的美感和韵味,在大体量的创作要求下,保持自身对纯艺术的追求。既不拖沓、又不呆板,以合乎时代的方式让历史“复活”,熔铸一个时代的“理想”,烛照新时代下的中国,这或许就是《理想照耀中国》在新形式下所深深埋藏的匠心。
生活视角下的“轻叙事”。《理想照耀中国》的总编剧梁振华曾经谈道:“所谓‘轻叙事’,首先在题材上偏爱日常生活或者野史轶闻的断面,在表现形式上崇尚去繁从简,不追求大篇幅、大场面、大制作,同时在内涵表达上,‘轻叙事’全力挣脱现实和历史的负重,并不致力于探求现象背后恒常的真理与规律;此外,在审美意趣上排斥严肃端庄,尤其钟爱幽默与调侃。”{13}相对于以死亡和牺牲作为途径,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终点,追求悲剧和救赎意味的宏大叙事,《理想照耀中国》通过完成叙述视角由历史向生活的转换,将叙述重心“向内转”这一方式完成了一种生活化的“轻”叙事的构建。
如在《守护》中,剧集并不着眼于守护的艰辛,而是以“父爱”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注入灵魂,相对于牺牲和热血,正是那些被掩埋在地表之下的温情瞬间给了我们跨越时间的感动与力量。
又如《冰糖》中,以“冰糖”这个小道具贯穿了家人的爱、战友共患难的情谊、邓稼先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等情感需求,正是这些脉络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历史瞬间背后的,更加具有永恒意味的生活层面上的“真实”。
以情感需求将“英雄”打下神坛,还原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知觉,在保留以“移情”“共情”等传统方式与观众进行情感共振的基础上,以人物的贡献和功绩构建了“第四堵墙”,给观众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与其说“轻”是一种对于“历史感”的抛弃,不如说是在历史的表层下,寻找生活中的暗流,在静水流深的意义上,在克制、沉默的镜头语言下,追求更为极致的情感张力。
具有独立意义的景观叙事。相对于将视角集中于人物、故事的传统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则力图通过有意味的场景和道具来增加剧集的层次。这种试图在情节之外,开拓出单纯的审美维度,无疑是一种对于纯艺术的匠心。
如《第五十五封信》中,原本游离于故事之外的,由旗袍、信件、捣衣杵等构成的“景观”也在故事之外不断激活着我们的“民国”想象。在具有“望夫石”意味的“思妇”主题之外,由“自行车铃”“捣衣声”所构成的故事节奏也无时无刻不在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通过对叙事角度的开拓,破除传统剧集中对于“人物”“情节”的聚焦,在审美意义上开拓叙事空间,也是《理想照耀中国》这一剧集在叙述之外的美学追求所在。以客观他物来构建一个“平淡而山高水长”的参照,无疑又是冲淡情感浓度,从而达到叙事之“轻”的又一重要手段。
但这种“冲淡”,实则是一种积蓄,有着“厚积薄发”的力量,借以营造“似淡而实美”的审美体验。
多元统一结构下的“新历史”叙事。以一组事件来勾勒时代的历史风貌并不是《理想照耀中国》的首创,而是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国庆献礼电影中就已初见端倪。但受制于电视剧的体量所带来的创意难度,始终没有编剧将这一形式移植于电视剧的创作中。而《理想照耀中国》作为这一形式的开山之作,在创新之外还用自己的匠心确立了多个维度的标准。
首先体现在人物塑造的多元统一上。《理想照耀中国》不将视线拘泥于党的建设,而是在现实成果的立场上,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既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的陈望道,又有冲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章华妹”;既有成功背后默默付出的刘磊磊,也有冲在建设祖国一线的邓稼先……将职业的特殊性统一于国家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百川东到海”式的景观。
此外还体现在艺术风格的多元统一之中。这一方面体现在题材的多元性中,体育、音乐、商业等元素的加入无疑增加了艺术统一的难度,当一切熔铸于努力拼搏的中心主旨之上时就显得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表现手法的多元性之中,当庄严与诙谐相遇、纪实与浪漫相交,从而达到了一种“真理可以笑着表达,不见得那么沉重。笑是认真,它的另一面不是哭,它的对立面是严肃”的艺术效果。{14}《理想照耀中国》以博采众长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具有生活实感的艺术真实。
《理想照耀中国》以碎片化的形式,通过个体和历史的边缘景观来构造和呈现了中国从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一步步走来的文化肌理。通过历史场景的拼贴法、以丰富的边缘事件来构建通往主流的修辞手段。这种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劳顿·牛顿所说的“交叉文化蒙太奇”式的创作,一方面以形式革新的方式积极推动着主流创作,另一方面则是以新历史主义的思想来反推时代认知水平的进步。《理想照耀中国》在思想和内容之外,还坚持对纯艺术的追求,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艺术效果。以创新推动艺术进步,以情感作为连接和共鸣,《理想照耀中国》在“轻叙事”的姿态中,不磨损现实主义的质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注释:
{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萧天佑译:《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②汪曾祺在《说短》一文中指出:“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的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见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③[美]丹尼尔·贝尔、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④马原:《电影密码》,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⑤[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⑥[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⑦[挪威]雅各布·卢特著,徐强译,申丹校:《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⑧杨文山:《“新主流”的前世今生》,影与灯,https://mp.weixin.qq.com/s/l-ryb6J65IIrRTja1g_fLA。
⑨张颐武:《〈理想照耀中国〉:“有意义的瞬间”凝缩建党百年》,《中关村》2021年第5期。
⑩林芳:《〈理想照耀中国〉首映,笑泪交织,以平凡见不凡》,广州日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528101504084003&wfr=spider&for=pc。
{11}童庆炳:《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简·奥斯曼、陶东风:《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文化研究》2011年第00期。
{13}梁振华:《“轻叙事”:当代中国文艺的美学新征候》,《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8期。
{14}劳马、梁鸿:《“笑”的文学传统与轻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03期。
(何庆平、张静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陈雪莹、王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硕士,孙小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硕士)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何庆平 张静雅 陈雪莹 王璇 孙小淅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