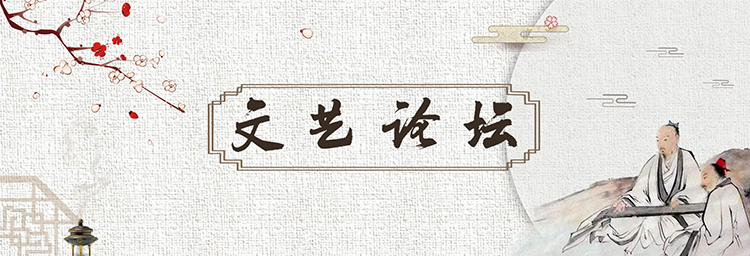

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海报。
国产动画电影的文化表征与叙事美学
——以《白蛇:缘起》为例
文/金文恺 张虹
摘 要:伴随国产动画电影类型在电影市场的崛起,越来越多民族的、传统的、民间的文化故事被搬上荧幕,经影像语言的重新阐释,开辟出新的审美空间。作为近年来成功的案例之一,《白蛇:缘起》以“白蛇”故事为蓝本,通过故事线的前溯,以动画中国学派的风格为影像表征,丰富了以白蛇传说为文化源点的故事世界;通过重塑叙事时间线、重构文本空间,串联了德勒兹意义上“运动与时间的晶体”叙事美学,进而在民族和现代之间,形成了文化价值的深层表征与平衡,为思考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影视传播的更新,提供了影像实践的出口。
关键词:《白蛇:缘起》;故事世界;气韵生动;德勒兹—晶体;叙事美学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凭借传统的文化内核和全新的影像表达,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期许。作为其中较为成功的案例,《白蛇:缘起》将“白蛇”的故事重新延展,借助声像表达和叙事结构的创新,打开了动画电影发展的新思路,兼具影视研究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立足于电影本身,从故事、影像等多维文本出发,分析《白蛇:缘起》对于同类型电影的借鉴价值。
一、文化源点:“白蛇”的IP“故事世界”
从“白蛇传说”到《白蛇:缘起》,文本维度的拓展正在彰显着中国动画电影对于“故事世界”的追寻与塑造。
(一)“白蛇”故事的历史迭代
在文化的历史流变中,白蛇故事也不断随时代进化,出现了口头传播、民间评话、弹词、戏剧表演、小说等多种形式。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禅宗故事中就出现了其源头,经过宋代的《李黄》和《李琯》两个版本,白蛇故事以小说的形式被收录于《太平广记》。在卷458中,讲述了公子哥李琯被白蛇妖怪所吸引的故事,将白蛇塑造成邪恶的化身,借故事本身告诫世人不要贪恋美色。随后的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增加了旁线人物,使得人妖恋情和警世教育意义更为突出,公子奚宣、白蛇精白娘娘、乌鸦精白卯奴、獭精黑衣老妪、奚真人等人物构成了“人妖恋爱—陷入危险—收服镇压”的故事全貌。真正成型的故事出现在明代冯梦龙纂辑的《警示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许宣、法海等人物在故事中出现,最为重要的是,在降妖除魔的逻辑之外,扭转了白蛇原本面目可憎的妖性形象,注入了渴望真情、勇于寻爱的成分。到了清代,戏曲家方成培的改编作品《雷峰塔传奇》基本勾勒了我们熟知的“白蛇传”故事,降妖除魔的主题进一步弱化,对跨越种族的旷世爱恋重点着墨,兼具对传统文化意义以及世界意义上的平权意识和种族议题的思考。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后,白蛇则更加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意识,成为宣扬现代爱情观念、批判封建礼教的良好示例。
《白蛇:缘起》的故事脱胎于这样的故事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现实观照整合到故事的改编之中。电影以前溯时间线的方式,选择以唐代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捕蛇者说》为故事背景,在湖南永州设置了故事展开的空间,借用明代冯梦龙小说里主角的名字许宣,以“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的主旨丰富了原有故事聚焦于人蛇之恋的主题,进而揭示了晚唐年间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赋敛之毒有甚于蛇的黑暗现实,也呼应了电影中借男主人公之口传达的电影关切——“人间多得是长了两只脚的恶人,长了条尾巴又怎么样”。可以说,在故事层面,《白蛇:缘起》汲取了古代不同故事版本中的要素,从前世的角度,来探寻女主“小白”平权意识、爱恋所起的原因,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对善恶道德、人间正义、种族差异的价值讨论。
(二)“白蛇”影视的跨媒介呈现
现代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白蛇”故事的阐释空间。民国之后,在原有小说、戏剧之外,歌剧、歌仔戏、漫画等方式开始出现,现代舞、电影、电视剧等方式,则进一步拓宽了“白蛇”IP在坊间的流传度,让其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
从影视媒介的改编来看,“白蛇”故事流变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新中国成立前阶段。主要包括《义妖白蛇传》(1926)、《仕林祭塔》(1927)、《白蛇传·荒塔沉冤》(1939)。这些故事深化了对白蛇精神的渲染、宣扬了人间大义和真情,基本承袭了之前纸质版媒介的故事蓝本。第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阶段。主要包括《白娘娘借尸还魂》(1953)、《白蛇传·白夫人的妖恋》(1956)、《白蛇传》(1962)、《白蛇大闹天宫》(1975)、《真白蛇传》(1978)等。这些影视剧进一步丰富了白蛇的形象,赋予了白蛇更加具有反叛、平权精神的内涵。第三,改革开放到新世纪。主要有《白蛇传》(1980)、《白蛇传》(1982)、《奇幻人世间》(1990)、《新白娘子传奇》(1992)、《青蛇》(1993)、《白蛇后传之人间有爱》(1995)等。影视市场的扩大激发了对于支线故事的着墨以及故事时间线的延展,以“青蛇”为主的影视剧开始出现,而赵雅芝版的《新白娘子传说》凭借饱满的叙事,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集体记忆。第四,新世纪以后。影视媒介的发展将更多的技术美学注入到故事之中,这个阶段的影视剧包括《青蛇外传·青蛇与白蛇》(2001)、《白蛇传》(2006)、《白蛇传说》(2011)、《白蛇外传》(2013)、《天乩之白蛇传说》(2018)、《白蛇:缘起》(2019)、《新白娘子传奇》(2019)、《白蛇传·情》(2021)等。创作者们通过外传故事、玄幻元素、动画改编、戏曲影视化等形式开拓着白蛇IP更为多元的跨媒介呈现。
《白蛇:缘起》在媒介形式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动画电影的形式扩大了观众对于已有熟悉题材的想象空间。一方面,选用“前传”的形式展现人物前世的勾连;另一方面,中国画风的影像表达,在保留传统文化神韵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融合了现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美学偏好。无论是神似“李逍遥”的许宣、具备传统中国美丽女性特征的“小白”,还是“A气十足”的“青蛇”,二次元气质的“双面狐妖”,萌宠设定的“肚兜”,都在动画电影的媒介呈现中实现了故事与审美的结合。
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动画中国学派中“气韵生动”的美学表达,通过多媒介语言的整合和民族文化元素的融汇,形成了对于故事内容的补充。该片不仅抓住了传统文化题材、文化符号等要素,也将社会关系、精神价值、民俗文化等文化内核贯通其中,在保有传统基因的同时,也展现了现代审美旨趣。观众可以在风景灵韵的捕蛇村、风波平静的湖水,河上的一叶扁舟、共赏的一场日落,氤氲的水雾、秋日的红枫,星空下的互诉衷肠、风雪中的矢志不渝等场景中,体会如同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气韵生动”。这种中国学派的动画风格,在意境之外留白,在风度之外留意,构成了一种“韵外之致”“境生象外”{1}的影像表征,将故事内容引入了更深更广的跨媒介美学体验之中。
(三)“白蛇”故事世界的文化内核
经历了故事的流变与跨媒介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白蛇”IP愈发成为一个极具传统文化内核和审美旨趣的故事世界。
故事世界的概念在叙事学、传播学、文学领域兴起,试图以IP为核心,通过故事在跨媒介载体上的建构,不断生成一个新的叙事学意义上的世界形态。诚如亨利·詹金斯所指出的,跨媒介叙事的原则包括建构世界,它强调了故事横跨多媒介平台实现的融合,每一种媒介可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2},进而形成了以电影、电视、小说、连环画乃至其他周边所构成的新的感知世界。从国产电影市场来看,光线传媒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开端,串联《姜子牙》《凤凰》《杨戬》等人物故事,并通过故事之间的创意联结,“彩蛋”设计的联动,以及情感价值观层面的呼应,在中国神话的IP影像改编基础上,建立一个“封神宇宙”的故事世界。
《白蛇:缘起》也试图进行这样的努力,动漫电影的新的类型学正在丰富一个围绕“白蛇”的故事世界。在戴维·赫尔曼看来,媒介文本是“故事世界”的基本蓝图,而不同的叙述者会围绕蓝图本身开始重构故事的时空背景、人物关系和行为模式,进而在时代语境下复现并复活一个“故事世界”{3}。《白蛇:缘起》在故事世界上的尝试,围绕的文化内核是“白蛇”故事本身,故事世界搭建在这个内核的基础上,并展开了叙事学和美学层面的努力:在叙事学层面,故事世界的生产和建立,不仅包含了之前众多版本的“白蛇”故事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白蛇”题材,还借鉴了跨媒介载体对于故事的演绎,进而重塑一个新的故事表征;在美学层面,《白蛇·缘起》通过声像美学的塑造,传达对文化的、情感的、道德的讨论,勾连起虚拟故事世界于现实世界的互动,形成了对现实的回应和折射。无论是读者还是观众,在《白蛇:缘起》中可以期待即将到来的新的故事线索和空间,如玲珑的双面狐妖、小青的情感线、蛰伏在西湖的妖怪身份,这些尚未延展的故事,也为打造基于“白蛇”的故事世界奠定了生产基础,形成了受众进一步的心理期待。
二、叙事美学:电影内外的“德勒兹—晶体”
从叙事美学上,《白蛇:缘起》以白娘子和许仙的“前世”故事为切入,改变了我们所熟悉的“白蛇故事”的叙事常态,通过陌生化的叙事手段,在继承旧有模式的基础上创新,体现传统化与时代感的交融。在时间和空间运动上,为受众营造出一种“德勒兹—晶体”{4}意义上的“内外”交织的体验,让观影者在电影时空中,不自觉地进行叙事的联想,形成对于人物、故事、时代、价值等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前世与今生:冲破叙事时间线
新的开始、复兴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它们意欲如何开辟将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5}。《白蛇:缘起》在叙事时间上的巧妙,也体现在这种对“过去”的挖掘之上。纵观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现状,会发现创作者大多借助于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进行时间线上的追溯、颠覆、逆转等多种方式的再创作,力图将前史、后史与观众熟知的“今世”联结起来。
《白蛇:缘起》利用的也是这样的方式。在尊重白蛇传说原型故事的基础上,延伸了白蛇与许仙的前世故事,从而激发观众对于原版故事在时间线上的好奇心:第一,白蛇的报恩报的是什么恩?第二,许仙和白蛇之间的情缘是如何发生的?前者从白蛇的视角出发来解释“恩义”的产生,后者从许仙的视角出发来解释“情缘”的产生。在充分利用这两点好奇心的基础上,《白蛇:缘起》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这两个原因之上,将主体故事的发生前置到500年前。
在“报恩”的故事线上,塑造了女主小白“失忆—被救—反抗—重生”的故事主线,使得这份“恩义”的缘起有了充足的理由。在“情缘”的故事线上,捕蛇者许宣不捕蛇的善意、与小白相处过程中对于人与妖界限的理解,以及在生死面前毅然决然的爱的选择,都充分诠释了这份人妖殊途却双向奔赴的爱情的起因。就这样,“报恩”与“情缘”的双重起因都被统合到“缘起”的探讨之中。借此,电影在前世故事中,对人和妖的“一见钟情”进行了合理而大胆的想象,将“缘起何时,缘起因何”置于叙事的核心,不仅迎合了观影者的心理期待,也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因果循环的持守。
值得一提的是,《白蛇:缘起》的再创作很好地遵循了观影体验的可追溯性。这一点体现在——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是唐朝,为了体现叙事逻辑的完整和真实,电影以柳宗元《捕蛇者说》的地点永州作为故事的空间坐标,为故事的发生奠定了一个可以折射现实的历史语境,补充了故事前溯的真实性。沉重的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以蛇抵税的政策驱使人们以捕蛇为生,捕蛇村、国师、蛇族的现实利益冲突在此背景下展开,阿宣与小白的“缘起”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这种叙事结构的营造,不仅使得原有的故事线得以延展,更重要的是,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时空从而与观众所熟知的白蛇故事进行对话,在观众认知共识的基础上,体现出了新的审美况味和价值认同。
《白蛇:缘起》对于前作的“颠覆性创新”也借此搭建了自身的叙事结构和话语体系,使得其试图想要构建的故事世界有了更为广阔的叙事时间,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联通,形成了国产动画电影对于“旧故事”的“新叙事”。
(二)文字与影像:重构文本空间感
《白蛇:缘起》将之前故事的多种文本进行了融合、拼贴和再创作,创新性地采用动画电影的表达方式以展示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通过将文字与影像融汇到新的叙事空间,原本熟悉的对象开始陌生化,新的艺术审美开始在这样的空间里建立起来。
第一,建立全新的叙事空间。一方面,以动画中国学派的形式,为故事发生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实体空间和时代感知。观众可以从小白、小青的唐代服饰、建筑、道具中加深这种空间印象,在民族式的审美中,体会从动作设计到配乐,从人物到场景的空间塑造。另一方面,在细节空间上,宝青坊的奇观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极为宽广的想象空间,用充满奇门遁甲的东方美学和西方魔幻色彩的表征,打造了极为关键的空间,很多重要的线索、故事的推动力都在这个节点出现。这种“陌生化”的空间处理,与前作的任何一个版本都不相同,它在白蛇故事内部,生成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的叙事空间,为观众探索电影本身的叙事提供了切口。
第二,人与物的空间塑造。其一,人物是空间的重要元素。《白蛇:缘起》中出现的道士、国师、蛇母,不仅形成了叙事上的戏剧性冲突,也在人物所处的不同空间中,建立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国师的“鹤”和“纸片兵阵”、蛇母的蛇兵阵、捕蛇村的山清水秀都暗含了人物性格、故事张力和价值导向。其二,以物牵引的空间。白蛇所持有的“发簪”不仅实现叙事转折,还折射出精神世界,使物象成为意象。它连接了白蛇故事的前世今生,形成了“缘起”的定情之物,同时也作为小白与小道士、国师抗衡的“反抗武器”,还作为小白寻找记忆、转世寻情的关键所在。这样一个由物体构成的空间,穿过了时间本身,推动了电影叙事功能的实现,展示了白蛇身上的平权意识、反抗精神和对美好爱情的追寻。
《白蛇:缘起》正是借助动画电影的表达方式,通过对人、事、物、场景构成的空间挪移,形成了叙事情节的迁移,进而重构了文本的叙事空间,为影像与历史、现实、未来的联动,提供了方法,使得影像不仅是一种文本、语言和符号,更是一种与影片人物、创作者、现实世界的关系载体,折射着贯穿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流动和价值变迁。
(三)影像叙事的“晶体”循环
德勒兹意义上,电影影像建立在先验和经验的双重维度上。影像不仅是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运动,而且还深刻关乎政治、市场、创作者等实践面向。影像是作为电影的影像,同时也是作为作者的、政治的、历史的影像。这构成了对影像“内外”的理解向度:从内向度来看,影像与文化符号、叙事时间、镜头语言密切相关;从外向度来看,影像是一种“泛文本”,影像延伸到了影像之外,使得时空在“作者—人物—世界”之间穿梭,拓展了叙事线程,打造了新的主客体关系{6},形成了兼容内外、超越先验与经验的叙事结构。因此,诚如在德勒兹的《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中所秉持的叙事策略和方式,我们将这种在影像内外循环、映射的状态称为“德勒兹—晶体”,用以指代在电影叙事中,将影像的实在面与潜在面{7}打通,形成了一种回环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回环的关系,包括了世界影像、生命影像、电影影像的回环,以及媒介的影像、影像的内容与内容的影像的回环{8}。
对于《白蛇:缘起》而言,影像的晶体在“白蛇故事的前世与今生对于时间线的打破”与“白蛇不同媒介载体的文本类型对空间感的重构”之中循环。在时空交错的影像叙事里,《白蛇:缘起》实现了实在面与潜在面、内向度与外向度的打通:第一层,影像呈现的是前世故事,这个故事构成了实实在在的人物关系,捕蛇者许宣、蛇妖小白、小青、蛇母、太阴真人等人物形成了新的故事的实在面,在观众脑海中建构了新的时间和空间,进而生成对影像语言和符号的内向度感知,即影像与文化符号、叙事时间、镜头语言所形成的叙事结构。第二层,尽管《白蛇:缘起》重新前溯了新的故事,但在观众的脑海里,故事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却在外向度地与观众的经验和记忆产生关联,加之创作者对故事历史性和时代感的借用,使得影像冲出叙事内部抵达一个新的时空,在“作者—人物—世界”之间拥有了重新嫁接影像迁移的可能性。各种媒介的白蛇故事,开始在新的语境里达成新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对外在现实世界的新的理解。
三、国产动画电影的未来:在传统和现代的平衡间寻找落点
发展至今,白蛇故事的改编从未停止,成为广受各类诠释者青睐的经典IP。从经典的意义上,经典是具有特定的开创性,能够提供特定的意义范式、叙事或抒情范式乃至生产制作模式,并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艺术审美影响、思想影响与现实影响的文本{9}。白蛇故事的历史迭代映射了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思潮变迁,无论是人物、故事、审美、文化均体现着文本建构者通过故事传达精神内核的美学追求。也正因此,《白蛇:缘起》的成功并非偶然。对故事文化内核的尊重、叙事结构的拓维、声像表征的神韵都在很大程度上再造了对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的价值表述。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文化产业的洗礼,内在观照的电影作品必将成为电影市场“物竞天择”的价值趋向。一方面,在市场驱动造成的价值浅表化背景下,如何回归动画电影对于民族文化的真正体悟,不仅是创作者、叙述者的责任,也对观影者的价值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从文化艺术的承载来看,如何探索动画电影的中国风格,通过多元化的跨媒介叙事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也成为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综合而言,当国产动画电影面临受众口味、市场体量、文化表达的三重考验之时,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平衡间寻找价值落点,在故事的完整性、创新性、艺术性上继续延续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形成兼具历史与现代的叙事美学,让我们的时代的电影作品,能够充分折射出文化在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心灵追求,充分抒写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集体记忆,充分调动文化自信的自觉意识,这需要倾注更长足的耐心和努力。
注释:
{1}杨 漪:《气韵生动审美心理与高峰体验对比研究》,《牡丹》2021年第8期。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7页。
{3}Herman D. Stories, Media, and the Mind: Narrative Worldmaking through Word and Imag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10.32(04).
{4}应雄:《德勒兹〈电影2〉读解:时间影像与结晶》,《电影艺术》2010年第6期。
{5}[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6} [法]吉尔·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7}周冬莹:《论德勒兹的“潜在影像”》,《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8}孙 澄:《时间的景深:德勒兹电影理论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6月。
{9}任灵秀:《〈白蛇:缘起〉——中国文学经典的叙事重构》,《艺海》2020年第7期。
*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动画片民族性认知与呈现的历史变迁”(项目编号:20YJA760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金文恺 张虹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