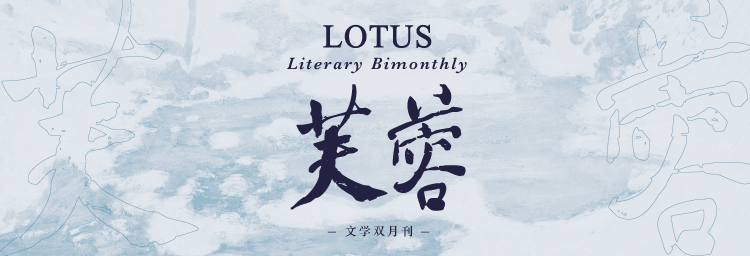

山窗
文/傅菲
窗外
我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除了窗外的森林。我不去森林了,便坐在饭厅看着窗外。窗是大玻璃窗,有一个外伸的窗台,窗台之下是两棵桂花树。楼略高,我看不到桂花树,看不到近物,远眺尖帽形北山。松杉遍野,四季不动声色,始终默然如静物。起床了,见松杉林;喝茶了,抬眼见松杉林;看天色了,还是见松杉林。有时,我在饭厅坐一个下午,对着松杉林,北山在眼际虚化,一切不见了踪影。玻璃上蒙着豆粒大的水珠,我用手抹了抹,水珠还在。水珠在玻璃的另一面,轻轻的细雨遮住了北山。
可以独坐一个下午的人,其实和一棵桂花树没什么区别。我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带到了这扇窗下,又将被什么带去何处。“何处”,让人困顿和迷惑。我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去了很多地方,或暂居,或孤行,最后还是在这扇窗前安安静静坐了下来。“何处”似乎是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似乎,我放弃了路途,放弃了路途中的那些人。
窗台上,摞着水杯、镜子、饭盒、书籍。那十几本书随我辗转了好第几个地方,但我很少翻动过,甚至有几本还没拆封。那些书和药丸差不多,病没发作,药丸是无效的,一旦突然发作,药丸可以给心肺提供动力。
一日,我在静坐,对着北山发呆。发呆可以让自己松懈下来。我听到窗外有三五个妇人在叽叽喳喳。这个院子,很少有人来。我拉开窗户,见她们在院子里种法国冬青作篱笆。我下了楼,在屋角见两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在挖洞种树。我问种树的师傅:大热天的,种树成活率太低了,可惜了这么多树。
树是竹柏、山矾、樟树、垂丝海棠、枸骨树、紫荆、桂花。一个老汉用铁锹挖洞,另一个老汉用洋铲铲土。洞挖得浅,树根栽不深,土也堆得松。我天天看他们栽树浇水。我知道,那些树存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我说:树洞掏得深,水浇透,再栽树下去,土压实,再浇水,树才容易生根,水分可以多保持一些时间。
一个老汉说:栽下去了,是死是活,由它们吧。
暑天栽树,得清晨浇水,天天浇,树才有存活的可能。可栽树人不讲究,每天下午浇水,拿着水管,嘟嘟嘟地喷射。暴日之下浇水,树死得更快。
大地蒸腾热浪。我哪里也去不了。我约朋友去梨花堂,朋友也懒得搭理我,说:这么热的天,烤蚂蚁一样,跑去梨花堂干什么?
梨花堂是一个废弃的高山小村,很多年无人居住了。那里有原始森林和大片的茶园,我很想去看看。但我终究没去。
树栽种下去了,篱笆栽完了,院子再也没人来。每天临近傍晚,灰胸竹鸡在山边叫得很凶:嘘呱呱——嘘呱呱——嘘呱呱——嘘呱呱——嘘呱呱。我讨厌它的叫声,歇斯底里,根本不顾及我在静坐。它就像一个隐居深山的敲钟人。
我端了一个碗下楼,给葱浇水。在山矾树下,我种了三个葱蔸,全活了。我每天给葱浇水,一棵浇一碗。葱长到半寸高,山矾树的叶子全黄了。我折一根细枝,啪一声,脆断,火柴杆一样脆。山矾树死了。叶黄,不卷不落。三棵竹柏也死了,树叶深绛,不卷不落。竹柏修了冠盖,看起来像一朵巨大的雀斑蘑菇。
山矾树有5米多高,树杈分层向上生,渐渐收拢成一个树冠。在它没有死的时候,树叶繁茂,树冠如一股喷泉。长尾山雀很喜欢在树上嬉戏,嘁嘁欢叫。但它慢慢黄了下去。叶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不容易被发觉。厚实的绿叶遮住了树杈,主叶脉却泛起金线似的黄丝。叶脉的金黄之色,慢慢向通向叶缘的支叶脉扩散,如荒火在野地蔓延。叶子半青半黄,叶绿色素日复一日消退,最终杳无影迹,叶子黄如一片金箔。不注意叶色的人,在某一天突然发现树叶黄得让人震颤,才猛然知道,这棵树还没活过一个季节。
我是每天都要注意叶色的人。叶色即生命之色,也即时间之色。时间是有气味的,也是有颜色的。树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气味和颜色。如山矾,在暮春初夏之时,树皮、树叶都会生发一种淡雅的清香,叶色则是凝重的新绿;暑气来临,清香消失,继而是涩香,叶色则是淳厚的深绿;入秋之后则是芳油香,叶色则是油油的墨青绿。
山矾是我喜欢的树。窗外的这棵山矾树,是我唯一见过的死树。它的树叶一直黄着。我每天打开窗户,看满树的黄叶,叶就那么黄着,黄着,黄到我心里。
看一个人,是这样的:不厌其烦地看,这个人便住进了心里。心里有一个神庙,供奉着诸神,不厌其烦去看的人,成了诸神之一。看星空也是这样:无数的繁星,密集而疏朗,只有风、水流、眼神得以流过其间,高古而亲切,神秘而透明。星空便倒映在心里,成了湖泊。看一棵树也是这样:树被镂刻进身体,自己是树的替身,或者说,树是自己的替身。
万物皆为我们镜像。在万物中,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自己,一个隐藏很深的自己,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自己。
窗外,北山既遥且近。可以目视的地方,都很近。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山体森林分布的状况、山梁的走向、山巅的形状。甚至可以看清主要分布的树种:湿地松、黄山松、杉树、枫香树、朴树、乌桕树、黄檫树、梓树、油桐、泡桐。在傍晚,我沿着山边小路,抄过一道矮山梁,便进入了鱼篓形的山坞。这个山坞,我走了无数遍,很适合一个人走,很适合我这样一个异乡人走——越走越深,直至不见身后的村子,我也因此不必问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树林茂密,再无任何人声。高高的苦槠树独自成林。我开阔自己的,是在不可目视之外。
当然,窗外不仅仅有北山,还有夜空。夜空是一团黑,不见山不见星云。夜吟虫嘘嘘嘘叫,窗外仅仅是窗外,无物可视,世界是虚拟的,让我无法确定还有真实的事物存在。窗玻璃上扑着眉纹天蚕蛾、姬透目天蚕蛾、中带白苔蛾、黄群夜蛾、变色夜蛾。它们蹁跹,它们群舞,它们扑打。有那么一些时间(9月中下旬),我每天出门,看见门口、楼道,死了很多蛾。我清扫了它们,堆在桂花树下。它们成了鸟雀的食物。蛾的生命以小时计算。所居之地,在森林边,虫蛾之多,无法想象。我便把饭厅的灯,亮至深夜12点,让它们尽可能长时间见到光亮。它们热爱光,理应给它们更多的光。它们见不到光,会非常痛苦——假如它们可以感知痛苦的话。
蛾在飞舞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它们的口器张开,如绿豆破壳。在晚上9点之前,蛾聚集,一群群。光在感召它们。10点以后,蛾非常少,有时只剩下一只两只。它们去了哪里呢。
乌鸫来窗台下的小阳台(安放空调外机)吃食,有那么些时日了。乌鸫来一只,来两只,来三只。最多的时候,来过十几只,挤挨在窄小的空间里,甩着喙嘴,吃蛾。死了的蛾掉在小阳台上。平时,院子很少看到乌鸫,死蛾的气息招引了它们。我也会捡拾几只蛾,夹在书页中,当作书签。
夜不仅仅是黑的,也有白的。白如清霜。星辰浩繁。窗户是星空的缩写,玻璃缀满了珍珠。熠熠生辉的珍珠。窗外的大野明净,北山朗朗,黑魆魆的山影也是朗朗的。窗户于我,是弥足珍贵的。没有窗户,我兴许忘记了,我的头顶之上还有一条亘古不息的银河。我所向往的人,都居住在那条凝固的河里。河水泻进了我的窗户,慢慢上涨,淹没我。
山雨也会飘进窗户。有一次外出,我忘记关玻璃了。我去看洎水河。洎水河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去,河面宽阔。我喜欢看河水流淌,喜欢在红山桥头看鸟在树林觅食嬉戏。桥头有一片樟树、杜英、刺槐、喜树构成的树林,有成群成群的画眉鸟、树鹊、乌鸫。林侧是滔滔的洎水河。芒草、刺藤覆盖了河岸。画眉鸟的鸣叫之声,让我觉得人间是多么让人留恋。仅凭画眉鸟的鸣唱,人就该好好活下去,哪怕世事多艰,枯寂如野草。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唧哩唧哩,卡唧唧卡唧唧,呱啦唧唧。滑音如波浪,转音如飞瀑,婉转悠扬。我常去洎水河边。鸟一直叫着,我舍不得走。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子也来倾听鸟鸣,也来观流水,那么我会爱上她。她必是一个与我同样心涌热爱的人。雨来了,不疾不徐。我抱头跑回。雨浇透了窗台,十几本书也浸透了水。山雨凛冽,卷起来,一团团涌进窗户。我望着白茫茫的雨,心一点点敞亮了起来。天干旱太久了,万物倦怠,我内心也荫蔽。雨,绿雨,坚硬的泥土在软化。
雨落完了,满地落叶。我连忙跑下楼,看山矾树和竹柏。出乎我意料的是,山矾树和竹柏依然满树叶。树死了,留着枯叶也是好的。
入冬了,种树的两个老汉又来了。他们在挖死树,替换新树苗。挖上来的垂丝海棠、紫荆、樟树,树根发黑了,泥团也发黑。他们抬着树,堆在一起。死了的树,任由日晒雨淋,任由霉烂。他们挖竹柏、山矾,被我制止了。我说:等树叶落尽了,你们再替换吧。
留着死树干什么,占地方。一个老汉说。
有叶子的树,都不算是死树。我说。他们被我说得笑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残忍的人。因为满树的枯叶,我留下了竹柏、山矾。或者说,我在审美它们死亡的品相。死亡是有品相的。
大多数植物死亡是垂败之相。如垂序商陆枯死,干茎腐烂,萎谢一下去,发出一种酸臭的味道。酸模、紫堇、射干,也是如此。初冬的旷野,满目都是荒凉的垂败之相,让人心慌。但有些植物死亡,却显出无比的高贵、壮丽、尊严,如黄山松、竹柏、翠竹、山矾、枫香树、榕树。它们迟迟不落枯叶,在山野突兀而出,即使死了,仍然独具生命气质。
辛丑年丁酉月,我在广东阳江市大澳村“渔家博物馆”,看到了鳁鲸的骨骼标本。鳁鲸体长12.8米,骨骼被支架撑了起来。每一根骨骼,都如象牙。我不忍凝神目睹,我甚至不忍看鳁鲸的头骨。海洋最大体量的个体生命,最为一个符号而存在。当时,我就想起了死去的竹柏、山矾。
入冬后,下了两场小雨。雨无声无息。第一场雨下了半个下午,第二场雨下了半夜。雨,带来了草木集体的枯萎。窗外,矮山坡上,一片枯黄。雨前,它们还是半青半黄的。雨腐化了草茎。雨抽走了草本最后的脉息。山矾的枯叶由黄蜕变为苍白,麻一样的苍白。竹柏的枯叶则变成深绛红。
冬风来一次,枯叶落一地。山矾从冠顶往下落叶,落了十几天,冠顶空空落落,仅剩光秃秃的青白色枝条。竹柏则是风吹哪儿,哪儿落叶。一个月下来,竹柏和山矾,一叶不剩。我站在窗前,看着它们落叶,慢慢旋飞下来,像垂死的蛾蝶落下来。昨日下午,下了一场大雨,冲刷着落叶。我去清扫院子,落叶被雨水冲烂了,我把落叶堆在桂花树下,盖上土作肥料。叶耗尽了生命历程中的每一种颜色,叶落即腐。腐烂的叶不是叶,是腐殖物。
窗外再也没什么可看的,苍山依旧是苍山,孤月依旧是孤月。我清理了窗台杂物,栽了一钵野山茶。有野山茶,也是好的。人总得安慰自己。
晒酱记
黄豆一日胜一日褐黄。豆是矮秆豆,秆上挂满褐麻的豆荚,枯败的豆叶却迟迟不掉落。我去松树林,往右边走,在山梁口便经过这片黄豆地。其实也不算是地,是一栋孤零零的旧民宅,因常年无人居住,日晒雨淋,屋梁霉变腐朽,木头被天牛蛀空,屋顶坍塌了下来,雨水剥蚀了墙泥,夯土墙的上截便倒了下来。倒下的墙回归泥,没有倒下的墙成了篱笆墙——长了蔷薇科的野刺梨、络石藤、野山茶,以及白茅、狗尾巴草、五节芒、野稗。有人在废墟上挖地,种上了黄豆。种豆人心细,把挖出的石块垒在路边,旧瓦在石墙上叠出一条瓦垄。冬瓜藤攀爬在瓦垄上,粗壮的白毛冬瓜垂下来。我经过黄豆地,摘三五个豆荚下来,一边走路一边剥豆子吃。
豆子是小黄豆,也叫土黄豆,豆粒圆小饱满,脆口微甜,水浆多。豆子还没黄熟,豆肉青黄,嚼起来带劲。一日早晨,我去爬山梁,见一个穿黑秋衣的妇人扎一条黄头巾,在拔黄豆,我问她:这块地,可以打多少豆子?
三十来斤吧,打不了多。妇人说。
我把水壶摆在瓦垄上,下地,和她一起拔黄豆。我双手抄紧豆秆往上拔,脚蹬地,豆秆岿然不动。妇人笑了,说:哪有这样拔豆的。她手握着豆根,摇一下根土,往上拽,连根带土拔出来。豆根在石块上敲敲,碎泥落了。6根豆秆扎一捆,两捆扎一个“人”字形捆,堆在簸箕上。我拔了十几株,拔不了啦,手掌辣热,火烧一样辣痛。这些豆都是她种的,豆种也是她一年年留下来的。她老公在竹编厂当保安,月工资2200元。我说:嫂子,能不能卖5斤黄豆给我?单价可以贵2块。
就这些黄豆,哪舍得卖呢?做不了几次豆腐,便没了。妇人说。
你的黄豆好,下了心思种。我说。
土黄豆产量低,村里人种高秆豆。妇人说。
你不舍得卖,那我用一个新电饭煲给你换吧。我说。
黄豆再值钱,也换不上一个电饭煲。妇人被我说笑了起来。
电饭煲不能吃,黄豆可以吃。我说。
我的黄豆磨豆浆好吃,豆浆一冷,起一层豆皮。妇人说。
我去抱电饭煲来,现在就换。我说。
就这样,我换了她一担带秆黄豆。我把黄豆挂在竹竿上,天天日晒。朋友来做客,见我晒黄豆,问我:你还种了黄豆?
我笑而不答。朋友说:你真是个不嫌烦的人。
晒了半个月,黄豆熟透了,豆荚噼啪响,零星地嘣嘣。像是太阳在炸响,也像是牙齿咯嘣。桂花幽静地散着花香。我想,凭豆荚爆裂的声响,就值一个电饭煲。我借来连枷,打黄豆。连枷咿呀咿呀,啪嗒啪嗒,打在豆秆上,豆子沙啦沙啦,滚落出来。
过了一下秤,豆子足足有8斤之多。豆子倒在圆匾上,搁在小方桌,在太阳下挑拣豆子。我把干瘪的豆子,挑拣出来,装在玻璃罐里。挑拣豆子需要一颗安静细致的心。豆子是另一种钟摆,在无声地摆动。豆子挑拣完了,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我又过秤,称出5斤,泡在水缸里。清水是山泉水,我走了3里路,从石泉井打来的。翌日,我打开缸盖,豆子沉在缸底,胀鼓鼓,黄得诱人,捞一把上来,磨豆浆。
出缸的豆子倒在筲箕上沥水,水晶莹剔透。我烧起灶膛。灶膛还是在正月烧过,冷冷的,灶膛灰焉扑扑,是木柴死亡的气息。灶砖是木炭色,冰冷僵硬。第一把木柴烧进去,火焰也是冷冷的,灶口吐出冷风。灶口像山垛口,冷风从山巅往下跑,被收集起来,往山垛口涌。冷灶风让人伤感——久久没有烧的灶膛是人间之一种颓败之像。在我们生活的屋子里,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冷的:被窝不可以冷,灶膛不可以冷,饭桌不可以冷,眼神不可以冷。
三把木柴扠进去,灶膛火映着脸。脸红扑扑,手热扑扑。锅底烈火漫卷。灶膛灰忽闪忽闪,焰苗(像红绸缎)包住了铁锅。锅里的水翻起水泡,如小鱼群聚在锅里吐气。白白的气翻出来,成了蒸气。蒸气往饭甑吸,往上吸,消失在饭甑板。饭甑板一副饥渴难耐的样子,贪婪地吸蒸气。手捂在饭甑盖上,仍然是冷冷的。灶台热烘烘,在表达热情,一种永远渴望填满火的热情。火来自高山,来自砍柴人的胸腔。灶膛口呼呼地叫着,滚出的空气焦鼻。木柴烧了满满一簸箕,饭甑盖热乎乎,烫手。豆子的香气随蒸气萦绕。掀开饭甑盖,豆子软塌塌绽开了肉皮。
饭甑放在地面竹席上,等豆子慢慢凉下来。泥是个好东西。泥吸走了柴火的燥热气,吸走杂味。豆子仅仅是豆子。凉了豆子,摊在圆匾,盖上牡荆新枝,隔在阳台上晒。牡荆捂蒸熟了的黄豆,晒七八个大太阳,滋生豆毛花(一种霉菌),青绿色,粉状。豆毛花像檵木籽,粗糙,结壳,有一股昆虫的臭味和霉豆的香味。
豆子在发酵,豆皮皱巴巴。我去小镇菜场买新鲜红辣椒,去了三次,也没买回半斤。红辣椒是有,却是大棚辣椒,易烂易变质。卖菜人说,5月份下了半个月的雨,辣椒烂根,死了大半,8月旱到现在,有110多天了,谁还有那个天天浇水的闲工夫。确实,自9月底,镇菜场便没土辣椒卖了。一日,朋友约我去一家山庄吃晚饭。我不愿去,太远了。朋友说,山庄菜蔬都是自己种的,在藕塘养了鱼,再不去,最后一季荷花看不到了。我心一下子动了。深秋的荷花多难得一见。山庄墙上,挂了很多红辣椒干、黄玉米棒、高粱穗、豆秆,作装饰。这些装饰物都是今年新收的,颜色鲜艳,很有田园感。我也顾不上去看荷花,找老板买了2斤辣椒干。辣椒是朝天椒,又辣又香。
实际上,过了霜降,地里的辣椒秆大部分枯萎了。山垄有一片菜园,村人都在那儿种菜。辣椒、茄子、南瓜、丝瓜、白玉豆,大多枯了藤或秆,根部的土蓬松,脚一踢,秆子脆断。种菜人把藤或秆收了,捂在菜地。唯一没死的,是架上的扁豆。扁豆从初夏一直开花到初冬,越严寒,花越开得繁盛。甚至冬雪来了,它还在开花。我去山垄收集山胡椒籽。
山胡椒是樟科植物,3~4月开花,7~8月结果籽,花朵细腻淡黄淡白,果皮青蓝。秋分后,果皮转黄转黑。果籽味辛辣,是大热之物,去腥去腐去虫。此时已是晚秋,山胡椒尚未落叶,树叶蜕变为麻黄。果籽零星结在树丫上。我用剪刀把果籽剪下来,收进布袋里。山垄有一条很小的溪流,入夏时候,溪流无水,长竹节草和紫堇。溪流边沙地,有七八棵山胡椒树,约3米高,冠盖披散。我注意到有霜期来临,山胡椒树落叶非常快,风吹树摇,满地黄叶。我曾在自己院子里种植过山胡椒树,3年长得比人高。
我也收山胡椒叶,收的叶肥阔,一张一张叠起来,用麻线穿起来,挂在阳台上。我也收木姜子叶。在我眼里,作为调味品,它们比陈皮好。我把两种树叶和山胡椒籽、辣椒干,磨碎成粉末,一并装在大玻璃瓶里。
豆子出一团团的豆毛花了,牡荆也晒干了。把霉豆子收进圆腰缸,与藠、大蒜、老生姜、葱头、黑芝麻末等碎末一起搅拌,晒在阳台上。晒了七八日,我浇上一斤熟山茶油,油慢慢往下渗。
这一斤山茶油,耗费了我半天时间。我把那罐粉末,泡在热熟油里,香味和辛辣味刺鼻,粉末一圈圈散开,深褐变得油黄。
豆毛花消失了,霉豆变得深紫。我煮了小浅锅水,倒进圆腰缸,搅拌霉豆,调匀,继续晒。说是水,其实不是,是酸橙汁。山垄有一个矮山冈,竖了一根高压线电杆,平日无人去矮山冈。我不知道是架电杆的人,还是村人,在电杆侧边种了一棵橙树。橙是酸橙,树上挂了40多个果,无人采摘。我背扁篮,去摘了大半,背了回来,连皮带肉榨汁,连同半斤老冰糖,放在锅里煮。
晒了几天,霉豆化为酱汁。圆腰缸蒙着纱布放在木架上,晒在太阳。
一日,我收到一包干燥花。花是桂花,丹红色。干燥花是一个远方朋友寄来的。朋友写一手好诗。每次读朋友的诗,我都有些伤感。我熟悉字里行间分泌出来的气息。荷尔蒙气息。荷叶田田的气息。忽而南风忽而北风的气息。朋友每年收丹桂花,晒干,装入巴掌大的布袋寄给我。每次收到桂花,我在阳台坐半个下午,手上握着桂花。作为干燥花,没有比丹桂花更好的花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是神的。我没有见过神。在我收到干燥花那一刹那,神降临了。其实,我收了多年的干燥花,一次也没泡茶喝过,我挂在书房上。
干燥花散发浓郁的香气。我把干燥花调进了酱缸。
每天傍晚,我取竹棒子,调酱。酱越晒越浓,但不能板结,须天天搅动。
晒酱的时候,我都不敢出远门。我必须在日落前赶回来,酱不搅动就会霉腐出来。汁水全收入酱里了,早晨,我舀一碟出来,佐以馒头或面包。一个来看望我的朋友,还没上楼,站在楼下喊:晒酱,我要吃晒酱。
我的孩童时代,乡人是家家户户晒豆瓣酱的。乡人不买酱油也不买味精,费冤枉钱。晒酱是费神费时的事,防雨防露防虫。我有一个奶娘,晒豆瓣酱晒得特别好。我喜欢跟着奶娘,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嘴巴馋了,她用筷子蘸酱,送进我嘴巴里。吃了酱,隔不了一会儿,我又嘟起嘴吧,翘着,等她蘸酱。奶娘是我邻居,带了我两年。1983年,她迁回老家沙溪镇东风村。我每年去她家。她很瘦弱。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显得很苍老,说话有气无力,走路拖着脚。我15岁了,她还抱着我睡觉。我最后一次去东风村,是8年前,她的老公去世。我一直叫她娘,但我不叫她老公“爸”,叫“老余”。“老余”代指什么,我也不清楚。“老余”姓王,奶娘姓什么,我不知道。奶娘还是那副病恹恹的样子。去年(2020年)正月,我邻居宗森叔对我说:你奶娘去年冬走了。我说:她不可能走的,她一直是即将病倒却始终不生病的人。
我打电话给她儿子世明,世明说:是走了。
你怎么不通知我呢?你应该通知我的。我说。
我没吃过比奶娘的晒酱更好吃的酱了。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人不晒酱了。在我入居山里,见了那一块豆地,剥吃了豆子,我便起意晒酱。做一件事,需要缘分,与结识人一样。好土豆子,不晒酱,可惜了。无论何种吃法,除了晒酱,都是委屈了豆子。每餐,我都蘸点酱下饭。我也想,我若以惜物之心,去惜人,我的一生又会怎样?
我装了一瓶酱,送给那个种豆人。她的家住在罗家墩河边。她老公钓鱼回来。她老公不上班的时候(包括晚上),就去钓鱼。她老公说:上班工资养不了家,钓鱼卖,补贴家用。他去20里外的永乐河钓小溪鱼,一斤卖17块钱。他在剖小鱼,指甲抠出鱼丁点儿内脏。我说:买了你家豆子,晒了豆酱,给你尝尝。
他连忙站起来,说:怎么当得起呢?带点鱼去吃吃。
我说:明年,你家还得种土黄豆,我还得晒酱。
他说:我多种一块地,不收你豆钱。
在他家坐了一会儿,天下起了雨。雨细细的,下得静悄悄。转眼就要到小雪了,一年将尽,冬寒袭袭。我看了看天色,晚上可能有大雨。
霜露来信
露的寒,是塌进肌肤的寒。在清晨,一滴露落在额头上,便陷下去,长出了毛细血管般的根须,深入到五脏六腑。植物就是这样衰老的。在雷打坞,林缘地带的荒草在快速结籽,草叶泛黄。荒草以狗尾巴草、鬼针草、一枝黄花、垂序商陆、钻叶紫菀、一年蓬、青葙居多。在干燥、贫瘠、生硬的黄土地,它们最先来到这里,成为“原住民”。一枝黄花一蓬蓬地生长,金黄金黄的花密集,寒露给了它灿烂时刻。它的叶子打焉,叶尖蜷缩,死亡之兆是一副垂丧的样子。它以花照见了自己的模样。
狗尾巴草垂着穗,两叶斜对生,分茎而上,叶青翠而有弹性。在清晨,露水悬在叶尖上,闪射白光。穗饱满而圆实,芒针茸茸,籽壳青青。金头扇尾莺抓住弧弯下来的草茎,摇摇摆摆而不坠,翅膀张起欲飞,嘘哩哩嘘哩哩鸣叫,像个踩风火轮的杂技演员。狗尾巴草是南方最普通的草,长于菜地边、田埂、荒地、鱼塘堤坝、墙垛、瓦楞、水泥缝。它是一种性格倔强的草,顽固、偏执。3月,它已返青,草芽从枯烂的茬探出,芽根裹着黑草衣。从它的叶脉里,看到了大地旺盛、贪婪、永不满足的欲望:凡是死去的,必给予新生。当它穗头下垂,暮秋已经来了。枫香树的叶片边缘,慢慢焦黑。
寒露是慢火,在悄悄地煨烤,煨烤万物。画眉鸟很早就在我窗外叫了:“叽呱哩,叽呱哩,呱哩呱……”我睡得迷迷糊糊,但鸟声真切。我下床,烧水煮茶。画眉在窗外的某一棵树上,听到了天亮的声音——天亮不光光是色彩在迅速变化,也是声音在交替。鱼开始穿梭,跳出塘面,啪嗒啪嗒。珠颈斑鸠是叫早的更夫,打着一面破锣:咕咕咕——咕。种菜人用长柄木勺从水坑里搲水。我只有这个时辰,才听得到画眉鸟在叫。茶叶在热水里翻滚,腾腾的蒸气从壶嘴噗噗噗冒出。一壶茶喝完了,画眉鸟也停止了鸣叫。继而是麻雀、白鹡鸰、黄山雀、黑枕王鹟、金头缝叶莺在“登台演唱”。听惯了画眉鸟的叫声,我对其他的鸟叫声暂时没有兴趣。画眉鸟啼唱得太热烈太持久,歌声圆润饱满,转音和滑音交替出现,如涧水出岫。喝罢茶,我去雷打坞。
唯有清晨,山林是湿漉漉的。巨石澹澹,裸露的地衣有了眼睛(露水多像水汪汪的眼睛)。钻叶紫菀焦缩的叶子暂时舒张,一束花籽被一泡露水裹着。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的裤脚衣袖。山坞有一块斜长狭小的地,被竹鸡林人垦了出来种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选地种菜。我认识他。我帮他挖过地下过菜籽。我叫他余师傅,他叫我上饶客。我第一次去雷打坞,是大暑之前。他在挖地。人热得像地面的蚯蚓。他戴一顶脱了帽檐的草帽,光着上身,仇恨似的对着手上的锄头发力。我从一丛枫香树林下去,见他扒山皮开荒。我说:挖出地种些什么呢?
种些白菜、萝卜、菠菜。他说。
我转过山脚,见一块地种满了辣椒、茄子、丝瓜。辣椒挂满了枝丫,半红半青。茄子干瘪,很小,有很多的虫斑。余师傅说:这些菜种得还可以吧?
太可以了。我说。我拿起他的锄头,扒山皮。扒出的草根、矮灌木,堆在地头,开始烧荒。我浑身湿透了,汗如雨下。我说,在这里种菜,要去半华里外挑水浇菜,很费力气。
力气总是要用的,不用会作废。余师傅说。
看得出,余师傅是个乐观的人。他给新垦的地浇水,我施菜籽。菜籽拌上灰土沫,匀细地撒下去。菜籽比芝麻还小,黑褐色,落下了地,它们有了愿望:发芽吧,必要就此死去。余师傅给撒菜籽的地面,铺上稀稀的干芒草,预防鸟啄食。
每次在傍晚去雷打坞,我多数时候,可以碰上余师傅。他热情地下摩托车陪我走一段路。他去给菜浇水。
寒露过后,我去看枫香树林,见辣椒、茄子、丝瓜全死了。死了的辣椒秆还挂着辣椒。辣椒白白的,空瘪瘪的,阳光生成的水嫩色泽被露水抽走抽空,只剩下纤维。白菜被移栽了,行距齐整。路边一棵大拇指粗的黄檫树,叶脱落。我举头望望四周山坡,清幽的杉树林有十余棵高大树木,完全脱了叶子。我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树,还是晚秋,就失去了生机。
一场细雨,山里完全寒凉了。细雨是傍晚来的。我在看《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纪录片,窗玻璃在沙啦沙啦响。我拉开玻璃,雨飘到我脸上。我关了电脑,去院子,地面湿湿的黑黑的,泛着一层油亮的光。夜吟虫在嘁嘁嘁叫。天边翻滚着黑云,黑魆魆的山峦生出神秘的尊严。
翌日,我顾不上聆听画眉鸟鸣叫,早早去了雷打坞。鬼针草结了一包包的果籽,盖住了枝头。在一座山民储藏肥料的简易木屋旁,有十余棵白背叶野桐,我发现许多叶面聚集着一堆甲虫。聚在一起的昆虫,有三个种类:一种是瓜片形,两支长长的触须,四肢(肢脚分三节)可以弹起身体,凌空而飞,甲壳桨形,拇指甲大,壳色是熟透了的番茄色,带有形状不一的黄斑纹;一种是椭圆片形,小指甲大,壳色如熟枣,头如黑豆;一种是个头、形状、壳色均如菝葜。我抖了抖叶子,虫散开了,但并不飞走。黑头虫趴着不动,我扒开它,虫腹之下是黏黏的液体——一只刚死的虫,被其他虫吸了肉液。其实是一种叫椿象的变态性昆虫,体大的是成虫,体小的是幼虫,黑头虫是幼虫在发育。这时,我才看清,树叶上粘着许多虫卵,鹅黄色,粟米一般大。这些虫卵,随着树叶凋零,进入地面冬眠,来年开春破蛹。死去的虫被分解,进入生命循环,它的肉液成了美食。我这样理解昆虫时,我觉得死亡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可怕。
千金子单独一丛生长,一个根兜长9根茎出来,叶子不剩,开出了棉白的穗花。它在风中轻轻地摆动,悠然而立。它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别名,叫看园老。这是一个既温暖又悲伤的别名。千年的荒园废墟,它不疾不徐地长,千百年一个模样,挺拔摇曳,一岁一枯黄。一棵草,守着故园,守着寸土,守着四季的荒老。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千金药解,是治蛇毒的良药。其实,棉白的不是穗花,穗粒早已脱落,被风送往风歇之处,穗毛散开,一身素白。在有霜的早晨,肉眼分不清素白的是穗毛还是白霜。从下往上看,千金子比最高的山梁还高。
其实,雷打坞很少见到千金子,蔓延而生的是沿阶草和败酱。沿阶草还是青郁葱茏,在碎石堆、黄土堆,大蓬大蓬地长。败酱则盛开着白花,一茎一簇,花团满枝。看到败酱花,我知道,霜降已经来了。霜降是消失与洇散,是熟稔与繁盛。霜是大地的色笔,在每一株植物上洋洋洒洒地精雕细刻。
霜来了,酸浆红透了。没有见过酸浆的人,不足以谈论晚秋。酸浆是一种耐旱、耐寒、耐热的茄科植物,茎直立,不分枝,茎节膨大。酸浆果在7月,便挂了出来,像野梨。一场白霜蒙下来,酸浆透红,灶膛火一样炽烈。一棵酸浆草挂几十个“红灯笼”。它虽是常见低海拔植物,但我已有十余年没见过它。在孩童时代,我去摘过酸浆果,漫山遍野地找。它通常在山中番薯地生长,和扛板归一起,长得疯狂野性。我把酸浆果塞在大玻璃罐里挤压,压榨出“红颜料”,涂在脸上,涂在手臂上。
在福建荣华山,我特意寻找过酸浆,找了几次,都空手而归。在雷打坞,我在一处被人开挖了的山体,遇见了它。山体被挖出了一块平地,因雨水的常年冲刷,表层泥浆被洗去,成了一块片石嶙峋的石片地。这样的地方,长楤木、白背叶野桐、盐麸木、苎麻、垂序商陆、芒,以及刚竹。刚竹还没长过来,它是统领林缘、路缘和荒地的最强大植物,一旦被它占领,寸草不生。我去石片地,是想看看地面是否有鸟巢。很多林鸟,在地面筑巢,如环颈雉、短耳鸮、云雀、红胁蓝尾鸲、歌鸲、棕扇尾莺。冬季即将来临,鸟过暖冬,已开始营巢。荒僻、人迹罕至的开阔地,是鸟营巢的首选之地。一棵苎麻紧挨着一棵酸浆。酸浆高过了我的腰部,茎冠斜出了一节节的细茎,我数了一下,挂了27个酸浆果。酸浆果褪去了果皮,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果衣,一个个细格呈网状。果衣残留着浆红,网状纤维麻白麻黄。果囊里,是酸浆籽——浆水干涸,籽积淀了下来。在赣东的方言里,酸浆果被称作“灯笼泡”。酸浆是阳台或庭院的至美园艺植物,从挂果到红果,是一个漫长熬熟的过程。人生也是如此,需要很有耐性地熬,由霜催化,熬出自己绚美之色。
早霜很稀薄,远望而去,早霜还谈不上是一种物质,仅仅是一种颜色。厚实浑厚的山野,这个时候,变得纯粹。霜是月光白,白得迷蒙。我没有准确记录过早霜在草叶停留的时间。白露为霜。霜是露的晶体。我从雷打坞路口进去,霜铺满了荒草,走到野塘(约一刻钟),太阳上山,霜消失了。我很细致地观察过霜消失的过程:白菜叶上的霜,晶体变小,圆缩,白色变淡,菜叶有了水渍,水渍洇开,往叶心洇,有了第一滴露,霜消失了。霜还原了露水。对植物而言,这是一个渗透、激发、催化、摧残的过程。草茎软化,耷拉下去,萎谢。荒路边,狗尾巴草倒伏下去,垂序商陆拦腰折断,一枝黄花成堆枯黄。枫香树林纷扬着稀稀拉拉的残叶。我们看到的秋境,是何等的残忍:暴露着惨败之相的草木,其实是一种本真的面目,与春夏之葱郁,是一种妥帖的对应。霜仅仅是一面幻镜,让万物照见自己衰败的一面。
野塘边的山矾树上,麻雀在育雏。它外出觅食,不慌不忙,在收割了的芝麻地啄食芝麻。我刚来山里,芝麻在收花,结荚壳。我还和收芝麻的人一起,割芝麻,用稻草扎捆。芝麻在荚壳里叫: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麻雀在食源丰富之地,一年可抱窝3次,一窝5~7只。我见过最多的一窝,有9只。晚秋是草籽最兴盛之时,颗粒饱满,油脂丰沛。鸟在尽情地吃,吃绝皇膳(方言,皇膳指皇帝的盛宴)一样,止不住嘴巴。山斑鸠窝扎草丛,一天不露头。鸟把吃下去的草籽、果核,带到了每一个适合种子发芽的地方。很多鸟都会在秋冬交替之际育雏,如白鹡鸰、野鸽。在寒冬,一部分鸟会被冻死,它们唯有旺盛地繁殖,才能抵消死亡。
画眉鸟有好几日不叫了。也可能它去别的地方安家落户了。人建房,是为了安家,安生才可安心。鸟营巢,是为了繁衍。人眠于榻,是安睡。鸟憩于树,是过夜。画眉鸟去了哪里,我不关心,虽然我有很多失落感,虽然我煮茶时还怀念一阵阵悠扬的鸣唱。
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枯败:酸模一节节烂下去,垂序商陆从根部开始往上死,溪涧断流,山樱裸了枝条,野芝麻萎缩得只剩下一团根,乌桕叶上盆结着死虫。这是自然的一环,也是原本的面目。枯败之相,让我们生出诸多的希冀。没有希冀,我们不堪忍受眼前一切。无法忍受,便无法度过更深的严寒。于是,我们盼着,望眼欲穿地盼着,盼到白发爬上双鬓。
霜露垂降,大地沉重,万物轻盈。

傅菲,江西上饶人,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出版散文集《元灯长歌》《深山已晚》《河边生起炊烟》《鸟的盟约》等20余部,曾获三毛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江西省文学艺术奖等,及多家刊物年度奖。
来源:《芙蓉》
作者:傅菲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