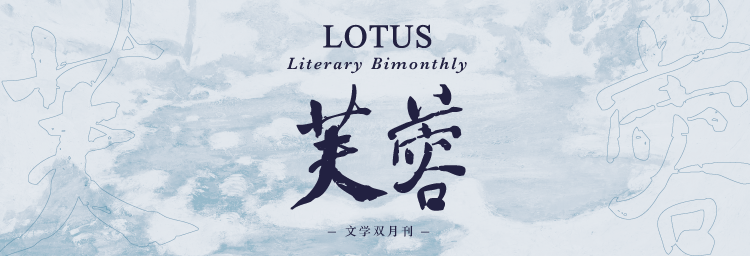

在中国的蝉声里
文/耿立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诗经·七月》
小引
这个暑假,从岭南回到中原腹地的老家,朋友款待,当把一盘炸金蝉端上来的时候,我说,谁愿意吃谁吃,我不吃。
我站起来,走掉。
大家一时惊愕。
在现实生活里,中原腹地的百姓,有吃蝉的习惯,或油炸,或煎爆,大街饭店的招牌菜必有一道美食:炸金蝉。围绕人们的口福,就形成一个产业,在夜幕低垂或黎明之时,在村头树下,在河堤树林,有手电、马灯、矿灯,寻觅刚出土的蝉;在白日,又有人用现代的工具粘树枝上的蝉。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交界地带,蝉的交易,以数十吨数百吨计,对一个小小的蝉来说,那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多么恐怖的杀戮。
吃野味,是某些人的不良癖好。我想到画家韩美林,有一次,他到南方采风,当地干部盛情款待,宴席中有野味火锅。天性珍爱动物的美林先生看到秃鹫的头在沸汤里滚动,心中不忍,甚是愤怒。待到招待者过来献殷勤,问美林先生“吃得高兴吗?”,率直的美林先生直接爆了粗口。
我没有骂人,我从吃金蝉的酒席走掉,把尴尬留给了朋友,把内心的羞耻留给了自己。我只能阻止自己不吃,但阻止不了别人。
这个夏天,我从岭南回中原腹地的故乡,归家伊始,顿觉故乡的异样与不适,也总说不出是哪里出了毛病,心里只是压抑,只是空落,手足无处安放,陷入惊恐与心慌,觉得有巨大的静寂带来的难受。静寂吗?汽车声、工地的打桩声、空调昼夜的滴水声,各种工业美学带来的噪声,扰我思绪,使我彻夜不眠。这个夏天,在故乡,似乎比往昔多了什么,又好像少了什么。一天,我终于觉察到,所谓的心慌,所谓的难受,不就是中原腹地的这个夏天没有了蝉鸣吗?从我的童年,从我们民族的童年,那历史深处回响了几千年的蝉鸣声,它们一下子隐遁了,失落了,我一时慌张地惊问:它们去哪了?
是季节的变乱,让蝉声消失了吗?是人们的杀戮,还是别的?
我一时接受不了,在文化心理和精神上,我觉得,没有了蝉声,往大了说,就如被掘了祖坟。华夏的夏,夏朝的夏,这夏字的来源,或者图腾,就是一只蝉呢,没有了蝉声,从《诗经》开始那些塑造我们心灵的审美,到唐诗宋词里的意象,就这样,无声了吗?就这样在自然里,一下隐遁消失了吗?
没有了蝉鸣,我的耳朵好像陷入了一种别样的耳聋,犹如戈雅在一次与女儿谈论绘画时,戈雅告诉女儿的一个秘密。戈雅告诉女儿,他46岁耳聋以后,“现在听到的,比以前更多”。
女儿不相信,摇摇了头。
“因为,现在我用自己体内的耳朵(内部的听力)在听。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愿意吗?”
女儿闭上眼睛聆听。
“听见了什么?孩子?”
“什么也听不见吗?”
女儿说:“能听见,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我听到一些遥远的声音……有一个小孩在哭……”
“那不是!那些不是!”戈雅厉声斥责。他突然滔滔问道:
“你没听见一种嘈杂在逼近——”
“它沉默、恐怖,若数百头公牛践踏大地?”
“你没听见一个女人的哀号,她嘶吼大哭,为着她的儿子被杀?”
“你没听见她痛苦的喊声?”
“没听见一个魔鬼的号叫?!”
“你听!”
“你听!!!”
戈雅虽然耳聋了,他依然能听到人类遭受一切之后灵魂的叹息。耳聋而心不盲。
我现在也觉得自己不如耳聋了,我现在所处的充满噪声的世界,也折磨得我近乎耳聋,耳聋反而内心的听觉更丰富,好像那远古的蝉声、魏晋的蝉声、唐宋的蝉声迢递而至,汹涌澎湃。
(节选自2024年第6期《芙蓉》耿立的散文《在中国的蝉声里》)

耿立,本名石耿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诗人,教授。散文集《向泥土敬礼》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遮蔽与记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前十,《悲哉,上将军》入选“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缅想的灵地》入选“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第六届老舍文学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广东省第十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大奖、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
来源:《芙蓉》
作者:耿立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