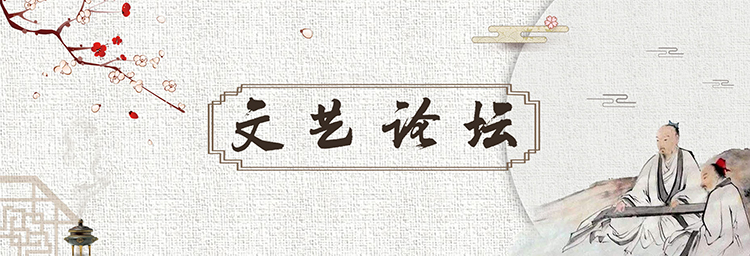

独异性:理解文学事件的理论基点
文/李明彦 王一州
摘 要:文学事件的独异性,即主体主动地尝试捕获主体与他者相遇时的“溢出”,它源于语言能指与所指的根本性断裂。这使得文学的独异性本身成为一个事件,它总是在发生着,且不是固定的。在文学与事件的联结中,独异性指向事件的生成,文学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被视为事件。在逻辑上,事件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文学,因此只有从文学事件的独异性入手才能理解文学事件。独异性理论尽管内斥着含混性和矛盾性,但依然是理解文学与事件深层联系的理论基点。
关键词:文学事件;独异性;主体;他者
“文学事件”已经成为文学理论与事件哲学融合后的专业名词,但这个概念在文学理论的视野内仍然有待辨证。对于“文学事件”究竟是什么,“文学事件”内涵、外延及其限度,“文学事件”的形态,学界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证。在事件哲学的视野中,将“事件”与“文学”直接关联并以文学为基点做阐释的学者,只有刘阳等寥寥数位。文学理论家寻求“事件”与“文学”的耦合点往往是根据事件哲学对作为一种语言活动的“文学”的提及,“文学事件”论在事件哲学的谱系中还未建立起充分的学理根基。此外,中文的“文学事件”与英文的“the literary event”都侧重于“作为文学形态的事件”或“文学意义上的事件”,未能将这一理论本应具有的内涵完整表述出来,因为“事件”与“文学”的联系必须同时包含两个维度:事件的文学位和文学的事件位。因此,对“事件”与“文学”的关系的考查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事件如何进入文学?
国内学界对于西方文学事件理论的接受直接受到了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著作《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的影响。这部著作尽管以“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为题,却并没有阐明“文学”与“事件”的关系。事实上,伊格尔顿并非“文学事件”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英国学者德里克·阿特里奇在2003年出版的《文学的独异性》(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中以文学为基点,明确地将“文学”与“事件”联系起来,探究文学的事件性,是“文学事件”理论最早的学理出处。在该书第四章的第三节,阿特里奇对“文学事件”(the literary event)的概念做出了学理性阐述:
因此,并非所有需要重新表述现有规范的语言创新都是一种文学的创新。事实上,大多数并非如此。人们可以通过编程使计算机产生数百万种偏离英语规则的语言项,而没有一种语言项能被理解为一件文学作品。只有当这个偏离性事件被读者(在第一种情况下,作者在文字出现时阅读或表达)“作为一个事件”经历,作为一个打开了意义与感觉(被理解为动词)的新的可能性的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这种打开的”事件,我们才能谈论文学。
……
这就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本质”:一种行为、一个事件、一种阅读,决不能完全与写作的行为-事件(或复数行为-复数事件)相分离,那使其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可读文本,决不能完全与它投射于其上,并在其中得到阅读的历史事件所隔离。[1]
这段论述实际上揭示了文学成为事件的两种逻辑:其一,文学在被读者体验时开启了新的意义,这种生成性在阿特里奇看来是“他者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the other)[2]。其二,文学作品只有在阅读的意义上才能成为其所是,即文学作品就是文学阅读,否则就只是一系列语言符号。这两种逻辑存在着时间先后的关系。后者是一种总体性视角,是对事件已然显现的概括,而前者则具有事件如何在文学中发生的理路,这种发生就是“他者的创造”。
在《文学的独异性》中,“他者的创造”经阿特里奇表述,可以从两个层次理解:第一个层次为创造出完全不同于既存之物的事物,这强调了创造的过程;第二个层次强调主体的被动性,主体无法清楚地说明新事物是如何被创造的,主体没有实现对创造物的完全掌控,因此,创造物与创造行动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因果关系。在对文学事件性的理解上,阿特里奇更加侧重于第二个层次。基于这种被动性,他者的创造结果是无法用逻辑推论简单得出的。在事件哲学的视域中,事件天然地具有突变性、反自明性和非因果性。经由阿特里奇的分析,“他者”是一个事件,并且是文学成为事件的原因。那么,“他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者”(the other),阿特里奇也将其表述为“他异性”(alterity),“制造了一个特定的时刻,提供文化界限之外的思考、理解、想象、感觉和感知”,能够“对个体心理世界的现有框架产生一定影响”[3]。可见,“他者”仍然是一种知觉活动,作用于主体的心理结构而具有事件性。关于“他者”更深层次的存在原理,阿特里奇并没有论述,这与许多事件思想的论证状态相似,都停留在事件的表现状态上,停留在人们对它追认的过程中。
在阿特里奇的理论中,“他者”作为一个事件只能在阅读中产生,而这首先以作为事件的语言为基础。文学文本由段落组成,段落由句子组成,句子又能被分割为词,最终能追溯到语素。“读者或听者会在对较小单位的识别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较大单位的意义做出判断”[4],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其中包含着不同等级的排列,其边界是互相渗透的。写作、言说、阅读会对这些事件的确认进行重复和修正,文学作为一种语言创造活动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原有规则进行重组并创造新的可能性,并生发出对事件的体验。这一思路在日本当代文学批评家小森阳一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他将这种阅读理解为“源源不断的邂逅”[5],阅读的事件性就在于“通过文本的语言,同时对他我及自我进行组织,并一次性地展开相互之间的作用运用”[6]。更进一步,在《作为事件的阅读》中,小森阳一探究了知觉感觉式体验与语言的关系,这一问题是阅读事件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语言不能完全表述出知觉感觉式体验,为此引入了数学中微积分的理念,将知觉感觉体验在时间序列上不断切割、微分,唤起各部分对应的语言,对暂时僵化的对象进行重构,使得知觉感觉体验的叙述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微分的重构使得原本不可表达的语言向知觉感觉体验生成,揭示了语言与体验之间的裂隙,而这裂隙正是事件之所在。从阿特里奇的“他者”事件到小森阳一的微分法,有两条清晰的脉络凸显出来:一是文学事件只能在阅读中产生;二是阅读事件的发生根本上是作为知觉感觉的“他者”事件的产生,而这“他者”是知觉感觉的溢出促使语言向不可能表达之处位移的表征。因此,事件在文学中的发生根本上是由于感性较之语言的溢出,这种溢出制造了一个断裂性空间,事件从中产生。
与以上观点相似的思路,还在德里达那里得到体现。德里达事件思想的核心是“可重复性”(iterability),这一概念有极其丰富的含义。J.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区分了两种重复,一种是柏拉图式的,将重复视为对本质的同一性的复制;另一种是尼采式的,将相似甚至是同一视为本质差异的重复。前者实质是绝对的同一,后者实质是绝对的差异。德里达的“可重复性”理念则不同于二者,是一种差异的重复,但不是绝对的差异,而是重复形式的差异类型学。在《签名 事件 语境》中,德里达指出,文字发挥功能的源头就在于“可重复性”,他以引用为例,说明这种可重复性能够打破任何既定的语境,以不可饱和的方式生产出无限的新语境。在写作事件中,德里达的差异重复就表现为,在语言符号的书写过程中,下一个符号以之前若干符号为基础,不断完成对既有意义的承接,并产生新的意义,而之前的若干符号又在后续生成的新符号的影响下不断调整、改变和丰富,生成新的可能性。在这种差异的重复中,每一位读者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似乎都是唯一的,同一读者在不同时间阅读所获得的意义都是有差异的,而不同的读者获取的意义差异更大。阿特里奇在《文学作品》中援引了德里达的“可重复性”理论来说明文学作品的这种无限变化的现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两个人阅读过同一部作品。”[7]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两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意识去阅读同一部文学作品。符号不断向新语境开放,这也使得作品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阿特里奇的“他异性”观点已经涉及他对于文学独异性的看法。在《文学作品》中,他表达出了从各个方面确证文学独异性的困难和无力,认为只有将文学视为事件,并从阅读的角度才能确定文学的独异性。在这个视角下,文学的独异性正源于可重复性带来的无限变化,这使得文学的独异性本身成为一个事件,它总是在发生着,且不是固定的。但是德里达的“可重复性”只说明了文学事件生成的表现和状态,并没有揭示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理,阿特里奇的语焉不详也会将文学的独异性简单地导向意义生成和变化之“新”,独异性就没有了具体内容,而只是流于能指。因此,无论是阿特里奇还是德里达,都没有真正揭示出文学独异性的深层原理。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文学的独异性已经显现,那就是“他者”的产生和主体性经验回应,这也是事件独异性的一种体现。由此,“文学”与“事件”由这种独异性事件联系了起来。但是,“文学”如何成为“文学事件”,仍然是一个需要怀疑的问题。“文学”与“事件”是否完全兼容,是否存在矛盾,需要进一步考察。
(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李明彦、王一州的《独异性:理解文学事件的理论基点》)
注释:
[1]ATTRIDGE D.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pp.58-59. 译文参照了刘阳《事件思想史》第八章“事件的英美面向——伊格尔顿与阿特里奇事件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的译文。下同。
[2]作者在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第二章“Creation and the other”第三节“The creation of the other”中提到的概念。
[3][4][8]ATTRIDGE D.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
tledge, 2004,p19、p57、pp63-64.
[5][6]〔日〕小森阳一著,王奕红、贺晓星译:《作为事件的阅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7]ATTRIDGE D. The Work of Literatur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3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中的人民主体性阐释研究”(项目编号:23&ZD27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李明彦 王一州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56/98/145200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