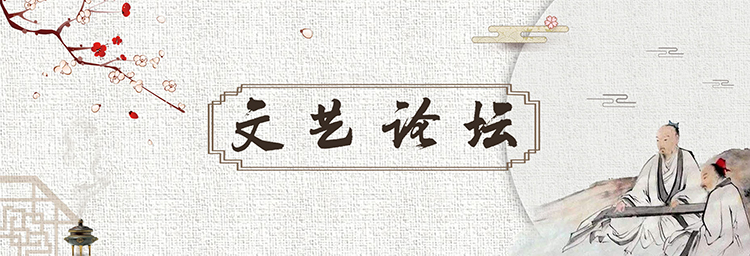

作为事件的文学记忆的三重性
文/刘兮颖
摘 要:事件充满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且不断生成,并由此产生差异,意义亦显现其中。记忆与事件之间的共通之处,正在于由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差异感。在索尔·贝娄的经典之作《洪堡的礼物》中,洪堡与西特林对于二战所产生的个体记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记忆作为差异事件的流动性与不一致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洪堡的创伤记忆强化了他的受害者身份,而西特林对于记忆的无视与忽略使得他未能产生相似的身份认同感。他们曾经签订的契约也随之遭到毁坏。另一方面,记忆作为相遇事件而现身,查理·西特林从各个角度,还原了关于洪堡的死亡及其与精神共同体的分离乃至重构之路。而作为意义事件出现的家庭记忆,则显示出血缘共同体聚合的强大作用。作为犹太移民后裔的洪堡和西特林,在对抗以实用主义价值为导向的主流社会中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留给世人最后的生命之书拯救了深陷精神困境的西特林,证实了作为事件的文学记忆的三重性。
关键词:记忆;事件;文学;三重性;《洪堡的礼物》
美国重要小说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年-2005年)最杰出的代表作《洪堡的礼物》,自诞生之日(1975年)开始就赢得了无数赞誉,作家本人也因此荣膺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从事件的角度切入研究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可以发现记忆一方面作为差异事件,展示了洪堡的创伤记忆,一方面作为相遇事件,展示了查理·西特林关于洪堡的死亡记忆及其与精神共同体的分离乃至重构之路,另一方面作为意义事件,揭示了家庭记忆和血缘共同体聚合的强大作用。从这三个方面,可窥探到虽然洪堡和西特林在对抗以实用主义价值为导向的主流社会中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艺术家的洪堡留给世人最后的生命之书,却拯救了深陷精神困境的西特林。这提出了从“事件”角度深入理解和研究文学记忆的重要课题。
一、记忆作为差异事件
事件是连续性差异产生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什么事情正在进行,便会有事件发生。”[1]换而言之,事件充满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并由此产生差异。事件理论关注的是事件作为时间和空间中的基本单位,强调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瞬时性。事件是连续性差异的表现,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本单位。在这种框架下,事件不仅是独立发生的事实,它们还具有过程性和关系性,即事件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和影响。记忆中包含的事件不仅被保存下来,还被个人和社会的框架所影响和重塑。
记忆与事件之间的共通之处正在于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差异感。记忆作为差异事件,意味着即使是相同的经历,不同个体的记忆和解释也可能大相径庭。这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视角和情感,也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事件的差异性是世界变化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记忆——每一次记忆的重构都是对事件的一次再创造和再解释。在《洪堡的礼物》中,事件理论可用于理解角色之间的记忆差异如何重塑了他们各自的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记忆作为差异事件不仅塑造了他们的个体经历,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看法。显而易见之处在于洪堡与西特林对于二战中的历史事件所产生的个体记忆存在极大差异,他们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情感体悟与身份认同。记忆作为差异事件的流动性与不一致性,被展示得淋漓尽致。洪堡的创伤记忆强化了他的受害者身份,而西特林对于相关记忆的无视与忽略,使他未能对彼时的精神导师兼挚友洪堡的遭遇感同身受,更未能产生相似的受害者身份认同意识。他们曾经签订的契约也随之遭到毁坏。
虽然洪堡的创伤记忆不直接来自个人的亲身经历,但这些记忆却深深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他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是对一系列社会历史事件的回应,这些事件在他的记忆中被强化和重构,内化成为他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他作为幸存者和受难者,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为恐惧感、不安全感和梦魇。洪堡与基督徒凯瑟琳缔结了婚约,然而在美满婚姻的表象之下深藏着不稳定因素,宗教与族裔身份的差异令洪堡无法产生安全感和幸福感。婚后洪堡夫妇由都市空间移居到了民风封闭保守饶有田园风光的乡村空间,后者非但没有成为他们的伊甸乐园和庇护所,相反犹如难以挣脱的牢笼和藩篱,让洪堡产生深切的恐怖情绪,甚至患有被迫害妄想症。“暴力在真实生活情境中表现为人类恐惧、愤怒、激动等情感等交织,其方式往往与正常情境中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2]洪堡并未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暴力袭击,而是在梦魇中,他梦见自己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非人道的迫害。所有的悲剧性事件如私有财产被侵犯、身体被暴力伤害、人格被无情羞辱等并没有在洪堡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梦魇显然是他心底恐惧心理的投射。洪堡不仅“在别克车的车篷下搜索,看是否有人设下机关暗算他”[3],表面上看起来,洪堡一切匪夷所思的言语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举止似乎显得荒诞可笑,然而究其缘由,这是可怕的情感记忆带给他的条件反射,一旦外界存在产生恐惧不安心理的环境,它就有可能不断被强化。虽然“每个人都有可能对自身的某个经历过度敏感并在情感上夸大其感受”[4],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洪堡的担心和畏惧心理与此密切相关。他在乡村生活中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恐惧,认为自己因身份差异而受到潜在威胁,这体现了他对周围世界的不信任和高度敏感性。
创伤记忆以差异事件的形式凸显出来,令洪堡作为受难者的身份意识根深蒂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逾越了其他身份如学者、诗人、丈夫等,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身份之间,个人必须就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做出选择,不管是自觉地还是隐含地。”[5]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身居高位还是取得世俗意义上令人羡慕的荣光,洪堡依然囿于无法摆脱的受害者身份。作为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洪堡根本无法专注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洪堡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言语和行动上的抗争。他炮轰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塞威尔,认为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存在明显的阶层鸿沟。尽管洪堡已凭借卓越的才华与毋庸置疑的实力,为自己赢得常青藤高校里的一席之地,却始终对被区别对待而耿耿于怀。综上,洪堡的反抗意识是激烈的,行为是卓绝的,尽管并未取得他渴望获得的任何成效。洪堡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话语权的不对等,深感遗憾与郁闷,他被迫放弃了诸多荣誉和讲学机会,这正是他悲剧性命运之所在。可以看出,洪堡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成为心无桎梏身无藩篱具有自由开放精神的知识分子,洪堡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根本不可能获得痊愈,这早已成为了他人格乃至无意识深处最阴暗隐秘的组成部分,印证了所经历的苦难与沧桑。创伤记忆令洪堡再也无法体验到共同体的归属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剧作家西特林,记忆作为差异事件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与洪堡结成忘年挚交,彼此因身份的一致性而生发出更多的认同感,然而同样作为非亲历者,西特林对此的态度显得极为冷漠淡然处之,仿若与己毫无干系。他对事件的反应却更为冷静和理性。这种差异反映了记忆在个体间如何形成独特的身份认同。西特林的冷静态度可能源于他在记忆中对这些事件毫无情感投入,这使他能够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事物,而不被情感左右。
事件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何同一事件会在不同个体中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差异性,还因为每一个个体的记忆和经历与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事件是连续性的表达,是变化和过程的集中表现。在洪堡和西特林的案例中,这些变化和过程在他们的记忆中被重组和再现,从而影响到他们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选择。
通过深入分析事件理论与记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记忆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简单回顾,更是对这些事件的再现和重构。它们共同塑造了个体的身份和行动。由是观之,记忆作为差异事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并且时刻表现出不确定性和独异性。事实上,个体记忆本身就具有难以言喻的差异化表达,千差万别不断生成的记忆之流会掩盖甚至抹杀最初的记忆,而因情感的流动性使得记忆作为差异事件存在本身更显突出。不同记忆铸就了完全不一样的身份认同感,身份的浮动、变迁以及被建构与此息息相关。
注释:
[1]White head, Alfred. The Concept of Nature, New York: Prome the us Books, 2014, p.78.
[2]Collins, Randall. Violence: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2009, p.4.
[3][15][17][23][26]〔美〕索尔·贝娄著,蒲隆译:《洪堡的礼物》,摘自《索尔·贝娄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第151页、第496-497页、第313页、第485页。
[4][16][20][25]〔德〕汉娜·莫妮耶、马丁·盖斯曼著,常晅译:《忆见未来:记忆如何影响你的一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第168页、第159页、第203页。
[5]Sen, Amartya.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W.W.Norton, 2006, p.19.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
(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刘兮颖的《作为事件的文学记忆的三重性》)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刘兮颖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56/54/1452907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