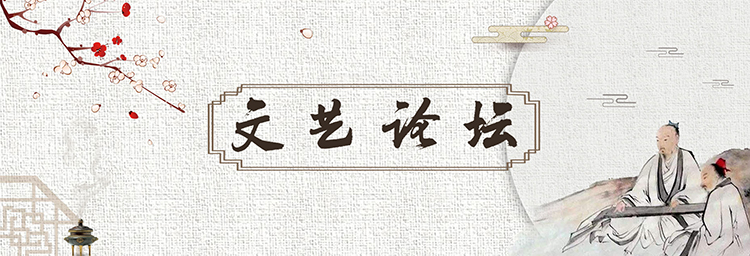

批评如何面对文本
——关于文学批评的对话
文/谢有顺 陈培浩
一、批评的初印象:确立边界与精通对象
陈培浩: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批评如何面对文本”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批评”,二是“文本”。如今,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最明显的表征是文学批评的过度知识化、理论化,这往往导致它与文本脱节。您的文学批评始终与文本结伴而行,照亮文本、阐发文本。您是从福建师范大学走出去的知名批评家,师大应该是您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您是如何开始写作文学批评的呢?对于您的第一次文学批评,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谢有顺:你的话让我开始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我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我所有的文学储备、文学理想都源自长安山,这里的一草一木、老师们的一言一行都我对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尽管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电子设备可以查询资料,甚至阅读条件也有限,想要读到最新的期刊,只能在阅览室看,有时一本喜欢的杂志别人在看,你只能守在边上,等他不看了,赶紧占位阅读。写文章也多半是在图书馆,宿舍太嘈杂了,拿着一沓稿纸在阅览室写,自己都能听到钢笔在纸上滑动的声音,现在用电脑写,这种声音也听不到了。那个年代,写文章也基本上是想到哪写到哪,没有今天这么多学术规范。我至今记得,我发表在《文学评论》杂志的文章,很多注释要素都是不齐全的,不少还是转引,编辑也没介意。可见,写作和研究确实受一个时代的风气所影响,你经历过,就能获得一种历史感,也能在一种变化的过程中辨析问题。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历史感的获得是很重要的,但尼采也说,获得历史感与摆脱历史的束缚同等重要,这也意味着,文学研究要有超越时代的东西。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尤其是做当代文学研究,既要熟悉当代文学的现场,但也不能完全跟着热点走,现象、热点太多了,贴得太紧,太时髦,也很快就会被时间所冲刷。时代滚滚的洪流中,有浮在面上的泡沫、树枝,有沉下去的石头,我们还是要在洪流中抱住石头。我很庆幸,我最早阅读和研究的当代作家是那些先锋小说家,当时苏童、格非、北村等人也才二十多岁,余华也才三十出头,但他们的写作才华和变革勇气,让人觉得他们可以走得很远。一个自觉的批评家,总是会选择一批作家与自己一同成长的,比如陈思和、程德培、南帆他们特别熟悉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等人,陈晓明、吴义勤他们特别熟悉余华、苏童、格非等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当然,批评总是小众的、孤寂的,如果要问我何以对文学批评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想它只能是来自热爱。没有热爱,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坚持下去。斯坦纳说,“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这也对,每次读到好作品,心里都有一种感动和感激之情,觉得要说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所读的作品。很多时候,写作的冲动都来源于此。
我发表第一篇评论时,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用的是笔名,内容是评苏童的小说,尤其是评他的新长篇小说《米》,发表在一本有名的刊物上。《米》是1991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被称为是先锋作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非常多人性中堕落、溃败、黑暗、凶狠的东西,向我们展示了那些令人震撼、不忍直视的一面,这对我的冲击很大。这篇评论文笔稚嫩,但包含了我读一部长篇小说的直接感受。后来以真实姓名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是在《福建文学》上,探讨先锋小说如何讲故事这个话题。这篇文章未收到我的集子里,毕竟是初学者的作品,不太好,但那时我已开始确立自己的批评领地,开始知道自己喜欢读哪类小说,喜欢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它也让我意识到,一个人选择做学问、做文学批评,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边界。你不可能喜欢所有作品,也不可能喜欢所有作家,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然后与之一同成长。我写评论的时候,先锋作家比较受关注,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这就要求批评者也要有一些新的知识储备,比如了解现代哲学、现代小说、现代叙事学等。若能用新的理论来解读这些新的小说,就能体现出一个人比较新锐的思想,也表明他有肯定新质文学的胆识和勇气。熟悉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最基本的准备。我到现在都能基本记得,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小说发表在哪本刊物的哪一期。这种因熟悉而有的常识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局限性,尤其在做出判断的时候,参考的东西比较全面,不容易流于偏颇。沈从文说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我们经常讲写作要有根据地,学术也要有专攻。你如果想研究某个问题、某个领域,就要去了解、钻研、调查、分析,把它琢磨透。写作与研究一样,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题材、领域,然后持续地钻探和挖掘。你要成为一个茶叶专家,就要喝过很多茶,了解很多茶的知识,能够辨析不同茶的味道。茶冲泡出来,你一喝,就大致知道是什么茶,品质如何。写文章也是如此。有些人的文章写得好,是因为他很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有自己依凭的一些思想资源,还有自己喜欢的作者,建立起思想和文体方面的标高之后,他就不会失去方向。我早期莽撞地确立先锋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多少就有了在一个领域持续研究钻探下去的意识,有没有这个意识,差别是很大的。当然,一个人能力有限,不可能研究一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择其重点,也是一种便捷的思路。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做学问的原理大致都相似吧,抓住大问题、大方向,很多枝节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二、批评如何发现文本:生命的学问与艺术感觉
陈培浩:您刚刚讲的批评经验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说,天才并不比常人拥有更多的光,但是天才有一个特殊的透镜,可以把一切光线聚焦至燃点。很多人认为您是天才,今天的对话或许能让我们了解您有什么样的透镜,可以把工作推到燃点。大家从事批评,首先是热爱,其次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这个先精后通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有读者朋友问我“去哪找好作品”,我告诉他到谢有顺老师的书中看他引用的文本,谢老师非常善于选择文本,通常被他选出来分析的文本,读者即使没有读过全文,也能看得明白,明白它所阐述的道理,也明白被阐释文本在上下文中的位置。这涉及到批评与文本的关系问题。您曾从鲁迅笔下的阿Q如何把圆画得圆的细节中,读出一个普通人无声无止的尊严。您有很强的发现文本、照亮文本的能力,文学批评怎样发现文本是一个症候性问题,您认为文学批评如何发现文本呢?
谢有顺:首先,我肯定不是天才,我的局限性太明显了,我生在农村,少年时代的阅读基础太差了,外语不好,学术训练也不够,对下苦功才能有所得的问题涉猎太少,当然,也不够勤奋,但我对自己没有过高的期许,更没有什么学术雄心,安于现状,进一分有进一分的欢喜,这也很好。至于你谈到批评对文本的发现,我们福建师大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孙绍振教授以及他的文本解读法。他的文本细读能力是公认的,而且他的解读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当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听过孙老师讲课的作家,比如莫言、麦家、赵琪,还有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老师的朱向前等人都曾和我说过,他们听过的很多课都忘记了,但孙绍振老师的课他们仍然记得。这不仅是因为孙老师讲得好,还因为孙老师讲的一些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莫言和我说,孙老师当年讲感觉的变异,对他写《透明的红萝卜》很有启发。《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把人的感觉推到一个特殊境遇下,让感觉发生变异,从而产生幻觉、梦境,这就有了文学性。孙老师经常讲,要把人放到各种极端环境和压力下,才能把一些人性深处的东西逼出来。为什么要三打白骨精?打一次是打不出原型的,要在盐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才能逼视出内在的人性。当然,科林伍德也说:“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人性也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所以雅斯贝尔斯才会认为,“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了”,但即便如此,“历史”仍然是一个试验场,人性在其中实验的时候,如果没有极限施压,真实就不会敞露出来。孙绍振老师长于自我驳难式的追问和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他对一些语文名篇的文本分析,得到了中学语文教研组的极大认同,对于教学,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福建师范大学在文学批评领域有这么好的传统,有孙老师所贡献的解读文本的经典方法,应该发挥好这方面的优势。
我们经常讲,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是生命的学问。既然文学是生命的学问,就意味着它是活泼的、动态的。要把握住文学这个动态的生命体,首先要有艺术感觉,要对作品有感觉、对作品中的人有感觉、对作品的语言有感觉。没有感觉,就意味着你看什么都是僵死的。陈嘉映有一篇文章叫《从感觉开始》,我们探讨问题、研究问题,都要从感觉开始,有感而发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原始起点,并非有材料和知识就能做好研究的。陈寅恪讲到材料也说,“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这就表明,我们在征引资料、札记、日记等材料时,不能见之便信以为真,而忽略了“一时偶然兴会”这些可能性因素,否则做出的结论就会容易流于武断。那如何辨析这些材料?除了知识的助力,对材料有一种感觉也是必要的。现代学术不仅要求实,也要求真,不仅要求同,也要见异,要用系统、贯通的眼光来安放材料和感受,如蒙文通所说,点、线、面、体兼具,又如钱穆所言,“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而要贯通这些,就意味着要有对所研究问题的直觉,感觉敏锐了,才能找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文学作品就更是如此,它是对人心、人性的考证,感觉更是基础。陈嘉映说,“自然理解才是本然的因此也是最深厚的理解”,我很喜欢这句话,自然的、本然的,就是带着个体的感觉、经验、省悟,它也可能包含深刻的理解,那些直指本心、一语中的的观点,许多时候正是一些直觉和碎片。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尤其不能轻视感觉,很多故事、很多观念都是从一团混沌的感觉开始的。先感知到一点什么,然后让这种感觉明朗化、形象化,继而通过想象、虚构或论证让感觉壮大、蓬勃,所谓的写作,大抵就是循着这个路线进行的。文学作品的结构,也多是细节加联想,一个细节勾连另一个细节,一个场面带出另一个场面,一个灵魂席卷着另一个灵魂,中间的黏合剂正是生机勃勃的对人和世界的那份感觉。
关于这个问题,我很喜欢举《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的例子。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诗写得好,对诗词她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是一个心气高、才气足的奇女子。以前读《红楼梦》,读到这里,总是有点不明白,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初看起来,对仗很是工整,但林黛玉说“断不可学这样的诗”,至于为何不可学,她没有做进一步解释。这个疑问,直到读了钱穆的《谈诗》一文,才算有了答案。钱穆是这样解释的:“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 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寥寥几句,令人豁然开朗。陆放翁这句诗的问题,就出在 “背后没有人”。修辞是精到的,可假若一种文字里,看不到一个人的胸襟和旨趣,这样的文字,如何感染人?又如何不俗?文学的背后要有人,要有一个人独有的感受,这才是文学的感受。王维有些诗没有写人,但诗的后面其实是有人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看起来是写景,没有写人,但背后有人的情趣。这样的人,一定是内心平静的人,否则他怎么能听到山果落下、草虫鸣叫的声音?当香菱读完王维的诗,黛玉问她有什么感受,香菱说:有些诗看起来无理,想过去却是合情合理的。这句话很有见地。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烟如何直?似乎不可能,而落日本来就是圆的,这个形容又显得有点俗,可“直”与“圆”两个字合起来就很有特点,好像找不到别的字眼代替它,画面感很强,这就是文学的感觉。
因此,文学的情理常常是一种感觉、一种生命的逻辑。为什么一些很奇谲的情节,你会觉得它仍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某一种想象的情理。所有对文本的解读、对人物的理解,都来自对经验、情感、思想、人物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阅读大量作品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一种关于文学的知识、感觉和判断。当然,面对文本,也不能完全依靠感觉,还要有思想的穿透力才能做出判断。但是,说千道万,感觉是基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谢有顺、陈培浩的《批评如何面对文本——关于文学批评的对话》)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谢有顺 陈培浩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55/66/1448018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