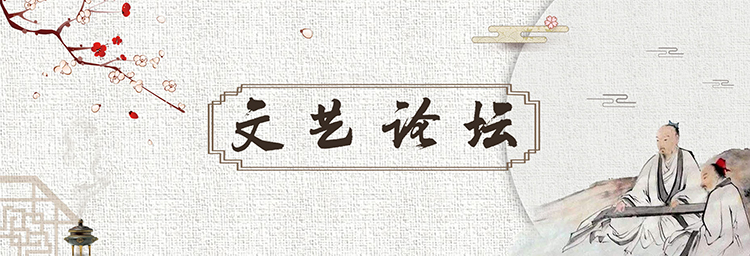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世界与生命世界
——论谢有顺的批评观及其写作伦理
文/陈劲松
摘 要:重理论、轻文本是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的痼疾,针对这种现象,强调重新回到文本,恢复文本细读,提倡一种“在场”的文本批评,既合时宜,又有必要。以批评家谢有顺为例,通过对其批评观和写作伦理的深入解读,不难发现他的批评写作始终将文本与历史、时代、社会、个人生命高度融合,充分展示出他对文本具有独特的批评眼光与鉴赏能力。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以文采与思想见长,却也须臾不忘文本细读,在文本细读中张扬文采,在细读文本中彰显思想。他的文本批评观念和创作实践,或可为当下理论界提供一条与众不同但有导向价值的路径。
关键词:文学世界;生命世界;谢有顺;批评观;写作伦理
重读谢有顺《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对其关于当下文学研究重理论、轻文本现象的忧思深有同感。今天,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文学自身的面目却越来越混沌,“这个背景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倾向,那就是不怎么注重对文学文本解读的有效性……尤其是这些年来,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出现了许多脱离文学文本的理论迷思”[1]。“理论中心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即是典型例子。就理论界而言,这种现象实乃痼疾。学者於可训曾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出现了‘失语’现象,文学批评家也频繁‘缺席’。这种‘失语’和‘缺席’,不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无所作为,而是其中的许多作为背离了文本又疏远了读者”[2]。直到现在,这样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依然屡见不鲜。
故而,重新回到文本,恢复文本细读,提倡一种“在场”的文本批评,既是繁荣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手段,也是焕发文学批评生命力的根本方法。学者孙绍振认为,“任何一个文学理论家,必须有两种功夫。第一当然是对理论文本的理解力,第二就是对文学文本的悟性。我觉得,前者虽然经常在发挥作用,可是后者却更加重要”[3]。这让我再次想起了谢有顺。尽管他从不以文学理论家自诩,但他对理论文本的理解力,以及对文学文本的悟性,彰显了一个批评家精神中极其出色的双重面相。谢有顺认为,“批评首先是介入文学现场,出示对作家作品的直觉判断,厘清当下的文学面貌。其次是由作品通到历史,通到时代,为当下的文学找寻坐标,同时也确证它在何种历史脉络之中,与时代又是如何同构或错位的。再次是由作品通到人,通及作者,也通及批评家自身,最终使批评不仅阐释别人,也自我阐释,成为个人生命的表达。三者合一,就是批评的使命和价值”。[4]这段表达严谨的批评自述,将文本与历史、时代、社会、个人生命高度融合,精炼概述了谢有顺的批评观及其写作伦理。他的批评与研究,多半围绕以上几个维度展开。从中,我们不难知晓什么是好的文学,亦能更好理解什么是值得珍视的生命。
一、所有文本都与“我”有关
谢有顺出道很早。他虽然是“70后”,却和“60后”这代批评家一起成名,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是中国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在本科期间写作的论述先锋小说的长篇论文,就发表在《文学评论》杂志,至今仍是该刊办刊史上的一个特例。同为“70后”的诗人朵渔论及谢有顺时说:“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一代里的先觉者,他的文字在一代人里亦可谓独步。想想看,直到读大学之前,除了田园和大山,他没有一本书可读,而一入大学即妙笔生花,如乃师(孙绍振)所言,是‘一个奇迹’。他有不同一般的理解力和陈述力,诚正,勤奋,贯注细节,眼光直接,用词恳切,没有那种少年成名者的作张作致的世故犬儒姿态。他的性格里似乎有一种谦恭忍让和敏锐独立的巧妙结合。”[5]谢有顺的批评成就与时代流变、自身机遇确乎密不可分,但更关键的,是他独特的人生经历、独到的文学悟性和独有的写作禀赋。作为“今日批评家”样本,谢有顺的成长乃至成名之路难以复制,不过,其批评写作中传达出对文本的探索与观察技巧、阅读和写作经验,值得借鉴与研究。
1992年9月,尚读大学二年级的谢有顺,在《福建文学》发表了谈论先锋小说的处女作《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由此踏入批评之路。短短两三年,其文章频繁刊载于《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等杂志,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一时广受关注。自1995年第5期开始,至2000年第6期结束,谢有顺在《小说评论》开设了长达6年的个人专栏,写下了“小说的可能性”“阅读与沉思”等主题文章32篇,提出小说要回到当代、回到存在、回到抒情性、回到精神性、回到冲突、回到勇气、回到真实、回到朴素等文学主张,探讨写作的恐惧与难度、写作与存在的尊严、批评的智慧、文学与什么相关、批评焦虑的缓解等重要问题,揭示写作不是养病的方式,而是信心的事业。借助这些文字,谢有顺开启了早期文本批评实践,批评对象涉及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北村、孙甘露、吕新、张炜、莫言、王朔、刘震云、贾平凹、王安忆等国内作家,国外作家则有卡夫卡、加缪、海明威、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萨特等。现在看来,这些文章虽属少作,但辨识度颇高,奠定了谢有顺整个文本批评的知识谱系、理论视野、话语精神和写作伦理。譬如《小说:回到精神性》是关于“对当下人类精神境遇的洞察与表现”“良知的向度”,《小说:回到存在》是关于“写作要回到存在”,《小说:回到勇气》是关于“存在的勇气”,《小说:回到真实》是关于“真实的斗争”,这些闪烁着才情与思想光芒的关键词,其后的批评文章不断出现,并持续得以深化。
在此阶段,谢有顺还专文论述了余华《呼喊与细雨》(作者后将其改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北村《施洗的河》、格非《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旗帜》、张炜《柏慧》等作家作品,对发展转型中的先锋小说及迟子建早期小说进行了综论,以“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总括迟子建小说特征,充分展示谢有顺对文本具有独特的批评眼光与鉴赏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谢有顺早期的批评写作,以印象批评为主,他坦言自己“不喜欢那种只对作品喋喋不休而从不出示自己的心灵价值与道德勇气的批评”[6]。他崇尚的是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以及哲学家牟宗三评《红楼梦》《水浒传》,国学大师钱穆评中国散文和诗歌,当代学者朱学勤评王朔小说这类批评,他不赞成把批评当作一门僵化的学问来做,而是注重文本背后的精神价值与思想内核。因此,他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文章,既是文学批评,也像是文化随笔,字里行间透着思辨色彩,可视为他本人“流动的生命形式”。
彼时的谢有顺,为何如此注重透过文本追求精神自由与思想独立?一方面,与他当年的阅读和他对文本的理解有关:“我不仅读文学和文学理论,更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像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的著作,雅斯贝尔斯、波普尔,甚至维特根斯坦那么难啃的书,我也读得津津有味。”[7]同时,《圣经》,卡夫卡、加缪、曹雪芹、鲁迅、钱穆、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通过这些思想性著作的阅读,谢有顺发现,那些作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并非僵化、枯燥的,而是有很多个人生命的投入,表达上也往往独树一帜”[8]。这段庞杂而纯粹的阅读经历,对谢有顺的批评观及其写作伦理的影响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则是时代因素使然。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众声喧哗,大家关注的焦点却已转向文化和思想,文艺理论研究日趋衰落,文学批评写作暮气沉沉。诸多新变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深思以下问题:批评的使命究竟只是纯粹的文本分析,还是一种既包含文本分析,又融合社会批判和精神探查的思想表述?在《批评焦虑的缓解》一文中,谢有顺坦率地说:“文学批评只对文本负责的界限迟早是会打破的……并不存在一种完全客观的文本分析,所有的文本都是‘我’所理解的文本,与‘我’有关的文本。况且,当许多作家都用无所事事的作品来搪塞我们的时候,批评家为何非得从这种作品里再去寻找它有什么技术上的精彩之处呢?这多么无趣。”[9]因此,谢有顺十分看重批评品质,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文学批评的标准:“在技术的尺度之外,还应有心灵与存在的尺度。”[10]言外之意,批评“不仅包含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理解,也包含批评家对现实和对‘我’的存在的理解”。[11]他以批评家尹昌龙的专著《重返自身的文学》为例,详细阐述自己的批评观,他从中得到的启示,亦让笔者深受启发——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要做冷漠的工匠,也不要让手中的笔成为医生的手术刀,批评除了对文本进行精细的技术分析之外,还应包含心灵的热情与温度,因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12]他还非常推崇思想在批评中的力量,认为“没有思想,批评很可能会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浪费过多的时间,无法把批评从作品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13]。谢有顺“从心灵出发,而非迷信知识和形式的推演”的批评标准,以及“出色的批评家也应是一个思想家”的批评理念,主观上缘于个人思考与选择,客观上对当时剑走偏锋的批评现状,有着极强的警醒作用,仿佛“一条有力的鞭子,抽打着昏睡和垂死的文学,叫它从中醒来”[14]。那时的他,只想做一个面对存在的思想者,而不是仅仅面对知识的学者。
2001年,年仅29岁的谢有顺荣膺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授奖辞精准洞悉了他当时的写作状态:“他的写作保持着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品格,以鲜明的立论和泼辣的论辩介入纷繁的文学现状,表现了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他以犀利的思想评论见长,直面现代人的灵魂冲突,以批判的立场探讨当下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矛盾,使批评呈现为一种激越、敏捷、具有冲击力的思想交锋。但同时,他也相对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文本感受和艺术分析。”[15]他在获奖前后出版的《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等著作,即是如此,“相对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文本感受和艺术分析”,其中缘由,前文已作大致分析。批评家孟繁华认为,这不是那时谢有顺一个人的问题,至今可能在很多批评家那里仍然没有解决。[16]2005年,《此时的事物》出版,谢有顺开始重视并努力实践“深入、细致的文本感受和艺术分析”。在他看来,“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就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作家作品研究这一基础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定论都是可疑的”[17]。他据此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转移到作家作品上来。多研究一些作品,少空谈一些理论,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出路所在”[18]。他后来出版的《从密室到旷野》《文学如何立心》《小说中的心事》《诗歌中的心事》《散文中的心事》《文学及其所创造的》《当代小说十论》《成为小说家》《文学的通见》等著作,确实更加注重以作家作品为基础,针对这些作家作品开展的文本批评,让谢有顺见证并参与了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性建构。
探析恩师孙绍振的思想核仁时,谢有顺从其研究中清晰地看到,“文本是文学研究的肌理和血肉,解析文本的能力,越细微,越见学养”[19]。而我在阅读谢有顺近期文章《现代学术视野里的陈晓明》后,发现他对文本重要性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当代文学批评,很多的解读都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事先设定或套用的理论话语中作出的,很多的批评是把文本当作理论的试验场,并不能贴身理解文学文本自身的艺术价值……所以,文学研究要警觉两种趋向,一是迷信研究的客观化,只重历史和知识史料的考辨,而无力进行心灵的考证——心灵的考证有时比材料的考证难度更大;二是迷信理论的自我演绎,从概念到概念,对文学作品并无贴身的理解,从而使文学研究成了一种理论的空转。”[20]唯有摒弃这两种迷信,文学研究才能真正回归文学,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把握文本。
注释:
[1][22][46]谢有顺:《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2]於可训:《回到文本 面向读者——关于当下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光明日报》2021年6月9日,第16版。
[3]孙绍振:《我的桥和我的墙——从康德到拉康》,《山花》2000年第1期。
[4]谢有顺:《重寻一种言之有物、文采沛然的表达》,《文学报》2015年11月5日,第4版。
[5]朵渔:《这一代的先觉者》,见谢有顺:《文学及其所创造的》,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04页。
[6]谢有顺:《我们批评什么》,《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
[7][8][34]谢有顺、高旭:《学术研究是一种自我觉悟的方式——谢有顺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
[9][10][11][12][13][14]谢有顺:《批评焦虑的缓解》,《小说评论》2000年第6期。
[15]《第二届冯牧文学奖评语》,《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16][33]孟繁华:《文章:是追求,是方法,也是生命状态——谢有顺文学批评的新变》,《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6期。
[17][18][21][31]谢有顺:《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第252页、第333页、第332页。
[19][45]谢有顺:《孙绍振的思想核仁》,《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
[20]谢有顺:《现代学术视野里的陈晓明》,《文艺争鸣》2024年第1期。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23XZW18)、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人文与创新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
(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陈劲松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世界与生命世界——论谢有顺的批评观及其写作伦理》)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陈劲松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55/60/144896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