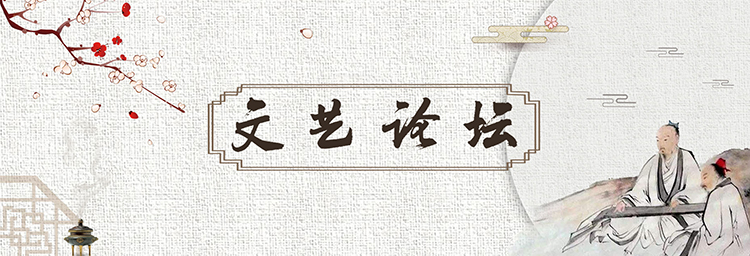

生命本位、个体记忆与家国意识
——《喝汤的声音》与当代民族文学的景观塑造
文/顾津荣
摘 要:迟子建《喝汤的声音》以北方跨境少数民族族裔哈喇泊家庭的故事为核心,采用复调叙事,描绘了国家百年进程中民族代际变迁的历史景观;另一方面也传递出了民间守护家族生命、国家历史和国境国土的真实意愿。小说围绕着“生命”这一文学主题,进一步从个体记忆、家国意识等方面展现出当代民族文学中景观塑造的可能性,并在少数民族文学、地域文学等方面为当代文学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启示。这部作品也再次表明作家迟子建对当代民族文学议题的深刻关切与探索。
关键词:迟子建;《喝汤的声音》;生命主题;民族文学景观
新世纪以后,迟子建在文学创作中频频去回溯童年记忆中出现的“天外来客”及其所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并试图以全新的民族文学视角聚焦东北边境历史。这些作品多以“碎片历史”的视角切入民族历史叙事,通过对当代文学内涵的探索塑造出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生命景观,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文学景观上的转变彰显了其对民族文学议题的关注。2021年发表在《作家》上的《喝汤的声音》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表明了迟子建在新世纪后的创作思想倾向。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中俄边境地带,以一个赫哲族祖孙三代的家庭为起点,透过家族“喝汤”的行为揭示了民族历史创伤和生命个体之间的紧密关联。一方面,该作品通过中国人民在“庚子俄难”中所经历的惨痛经历,描绘了国家百年进程中民族代际变迁的历史景观;另一方面,“喝汤”的故事传递出了民间守护家族生命、国家历史和国境国土的真实意愿。更为可贵的是,《喝汤的声音》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历史叙事的层面,而是进一步从生命本位、个体记忆、家国意识等方面展现出当代民族文学中景观塑造的可能性,同时也在少数民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作等方面为当代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启示。
一、回到生命本身的文学
作为一位在东北地区出生的作家,迟子建一直对故乡边陲的人文景观有着细致的观察。在这个过程中,她以真实的生命经历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将故乡人物生命的本真样态投射到笔下的文学世界,为当代文坛提供了许多“野性的、原生态的生命意象”[1]。而在《喝汤的声音》之前,《额尔古纳河右岸》《别雅山谷的父子》等作品已经透露出迟子建对边陲少数民族生活的关注,透露出作家试图将当代文学的审美回归到生命本身的思想迹象,而《喝汤的声音》更是对这一创作转向的再次印证,展示了她对当代民族文学景观的新探索。
《喝汤的声音》中独特的“复调叙事”是小说人物之间建立情感交流的纽带,故而也是本文进行叙事分析的一个基础视点。这个结构里嵌套了三重故事和两个“讲故事的人”,其中第一层故事是以“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在饶河市下乡调研的经历。调研结束后,“我”在江鲜小馆儿独酌回忆起与亡妻之间的温馨往事时,低声自语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位穿绛紫色麻布长袍的神秘女“摆渡人”。而与这个摆渡人的对话也带来了小说的第二层故事:“哈喇泊”家族“喝汤”的历史。小说的情节开始以描绘“我”和摆渡人的对话以及展现哈喇泊家族的生活为重点。在描写两人的交流中,迟子建将复调思维的对话性、多样性以及未完成性等元素融入到“我”与摆渡人的酒桌时空。巴赫金曾提出,作为结构形式的对话并不只局限于小说人物在情节中的实际交谈,还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力量和不同的时空之间的共存,“是消亡、生存、诞生间的对话”[2]。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了边陲小镇的建筑景观、自然风光等特征,写出了人物在江鲜小馆儿中对声音、气味等的真实感受。而在对话性的情节中,迟子建通过“我”的语言塑造了摆渡人或神秘、或真实的生命形象,并以摆渡人的话语塑造了哈喇泊家族身上的民族魂灵特质。由此可见,摆渡人和“我”这两个角色的叙述功能代表着迟子建的多重话语,展示了她对少数民族的多方面情感。
小说中最神秘的情节是:次日酒醒后,“我”去追问酒馆老板竟得知无人见过这个摆渡人,这意味着前夜的那场对话并非真实发生过。酒馆老板笑“我”是发生了梦魇,“我”却认出他是第二层故事中哈喇泊前妻张雪的儿子,并真实地听到了哈喇泊在喝汤的声音。迟子建充分发挥了这种复调叙事的艺术魅力,运用这种虚实交融的叙事方式,在弥漫烟火气息的沿江小酒馆中营构了一场梦幻的交流情境。在人物设置方面,摆渡人对“我”来说是哈喇泊家族历史故事的一个陌生讲述者。在主题和寓意上,她又代表了那些依靠这条母亲河世代生存的少数民族魂灵。但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她是由“我”对亡妻“麦小牙”情感凝结出的一个极具梦幻性的心灵意象,反射出“我”生命中因失去“麦小牙”而落寞寂寥的心境。这一点体现在摆渡人能够说出属于“我”与亡妻之间的吸烟暗语——“熏个腊肉”。摆渡人作为民族的神性意象,在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交汇处应运而生,象征着少数民族灵性生命与都市社会的生活融合,使历史得以在现实中延续。她将“我”领入一个由“海兰泡惨案”所带来的民间故事,“我”也因此成为这个故事的现实见证者。人物在倾听与讲述的交流之际,小说通过两个人的对话作为全篇的基础结构形式,以一种偶然和神秘的故事语境来演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迟子建采用这种交织的场景,以不同的讲述视角再现了平凡个体在不同历史中的遭遇,揭示出生命、历史、现实和国土之间深刻的联系。小说使读者跟随“我”的视角共同去感知这片土地的过去,表达出迟子建对边陲生命怀抱着深深的民族情感。毫无疑问,这种写作视野通过将民间文化与国家历史联系在一起,发掘不同的人生经历所承载的丰富历史元素。
哈喇泊家族故事是小说的第二个叙事环节及核心内容,重点描写了近代沙俄给中国人带来的生命迫害以及延续性的情感伤痛。主人公哈喇泊是中国北方跨境少数民族赫哲族的后裔,其祖辈在“海兰泡惨案”中罹难。祖辈遗留下来的家庭记忆成为他背负民族创伤的起点。哈喇泊的名字取蒙古语“海兰泡”之意,是祖母用来“纪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岁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儿”[3]。这种寓意注定了他的牙齿也要在家族故事里殉葬,化为齑粉。小说中曾这样描述哈喇泊一家:“没有一个好牙齿,都是满嘴的残垣断壁”。他们一家因为牙齿残缺,无法咀嚼坚硬食物,因而只能喝汤。这种生活方式在全镇广为人知。残缺的牙齿是由对沙俄士兵的仇恨造成的,成为这个家族创伤的核心象征。这种象征作为一种后天遗传性的生命特征,寄托了家族经历“国难”后的复杂情感。迟子建在哈喇泊家族的故事中对残缺牙齿的人物形象塑造,使生命意识逐渐在创伤中浮现,为摆渡人的讲述增添了传奇和荒诞的色彩。
牙齿残缺这一情感象征元素,一方面表明了家族成员曾在国难现场拼命挣扎的生命经历;另一方面,又代表了家人们对历史遭遇的悲愤回忆的传承。通过祖母的回忆可以得知,祖父目睹了女儿被俄军残忍杀害的过程,他在进行反击时也被枪杀身亡。祖父临死之前用残留的意志向妻子高呼:“快游过哈拉穆河”。他相信赫哲族的妻子是“可以搏击激流的鱼”,能游到对岸的中国。最终,祖母侥幸逃出,抱着浮尸游过了乌苏里江。上岸后发现牙齿“多半化为乌有”的祖母在万吉镇落脚并生下了哈喇泊的父亲“火磨”。而火磨常常会在重温父亲的故事中嘎吱嘎吱咬碎牙齿,成为镇上远近闻名的没有牙齿的男人。受到这个惨痛故事的影响,火磨年轻时就认为世事难料,害怕遭遇不幸时无法保护亲人,因此对生命繁衍和夫妻情感的建立产生了抗拒。这种不愿接受情爱的恐惧也给火磨的内心带来了长久的孤独。另一边,祖母却希望将苦难的记忆深深铭刻在家族后代的心中,所以对儿子早日成家延续家族血脉的事显得急迫。最终,四十岁的火磨在母亲的催促下成婚,并在东北光复后有了哈喇泊。迟子建以细腻且严肃的写作态度,表现了东北边境的人们脆弱而坚毅的一面。这种生活景观也成为民族文学中的文化元素,承担重述、丰富民族历史的文艺使命。
迟子建认为“无论历史怎么样去流动,但还是有生活的一个底”[4]。因此,迟子建重点描绘那些被大历史忽视的小人物的命运,借他们述说民间历史的细处、底处,并以此反映民众在承担历史责任中的主体意识。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喝汤的声音》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而诞生。迟子建以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文学素材,将悲壮的“海兰泡惨案”国难史折射到对哈喇泊家族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等叙述中。哈喇泊家族的仇恨情感源自于沙俄士兵对家人生命的残忍剥夺,以及外族对家园生活的侵犯。当个体生命承受着巨大的苦痛时,对于苦难的忍耐并非是历史的惰性,并没有对历史或社会进程造成阻碍、延缓的影响。这种个体生命实则携带着坚韧精神和反抗的基因,构成了民族历史的核心。这也是迟子建在小说中呈现出哈喇泊三代人珍视生命和守护边境的原因之一。祖母对丈夫女儿的追思、火磨对妻儿的抵触,以及哈喇泊对生育和国境线航标的执着追求,都强烈地显示出他们生命中坚韧不屈的情感意志。
迟子建对近现代东北地域的描绘是理解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审美变迁的一个重要途径。《喝汤的声音》将个体命运与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使民族的生命主体融入历史叙事中。由此,个人生命发展的“历史性”与社会变迁的历程产生融合,成为表述民族公共历史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通过哈喇泊家族生命中这种“历史性”的情感故事来影响读者的感性审美经验,进而引导当代民族文学叙事的景观变迁,同时也以生命美学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探索。感性生命的审美意识是作为对启蒙理性的反射作用而产生,构成对启蒙现代性的一种镜像反思[5],并通过生命使“审美与艺术成为解除理性束缚并且指向自由生存路径”[6]。从个体生命的视角,迟子建以少数民族文化的视野体现了回归生命本位的文学审美倾向。因此,迟子建文学的生命美学也在对历史和现代文化的反思浪潮中应运而生。这种生命本位的文学思想倾向作为当代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之一,也践行着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省和超越。
注释:
[1][10]孙郁:《文字后的历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第99页。
[2]〔俄〕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第344页。
[3]迟子建:《喝汤的声音》,《作家》2021年第7期。以下引自该作品的均不再注明出处。
[4][7]郭力、迟子建:《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方文坛》2008年第1 期。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8页。
[6]潘知常:《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节选自2024年第2期《文艺论坛》顾津荣的《生命本位、个体记忆与家国意识——《喝汤的声音》与当代民族文学的景观塑造》)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顾津荣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54/74/144067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