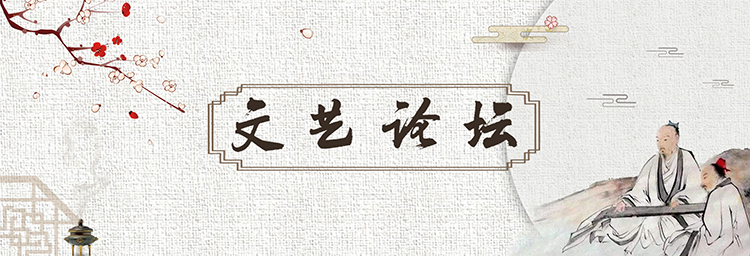

西部青年批评家成长的困境
——以云南青年批评家群体为例
文/周明全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馆自2011年至2022年,十一年十届一百人,入选客座研究员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文学大省。《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每年推介六位批评家,也主要集中在以上文学较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青年批评家群体,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和《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的较少。当然,进入《文艺论坛》《名作欣赏》《芳草》等推介的也很少。在整个青年批评家快速成长的十余年间,西部的青年批评家却始终默默无闻。另外,相较于西部青年批评家的落寂,西部的文学创作却始终有较好的创作成就,涌现了如阿来、雷平阳、刘亮程等著名的作家。文学要健康发展,创作和评论都应得到相应的关照,故重视西部青年批评家的成长,迫在眉睫。
关键词:客座研究员;“今日批评家”;西部;青年批评家;成长困境
2012年5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与会者“惊呼”80后批评家在文学评论界缺席,遂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在报纸、网络的推波助澜下,80后迎来改变“边缘”处境的时代机遇。202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5位80后批评家——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被聘任为客座研究员(80后批评家杨庆祥2011年进入首届客座研究员队伍);2023年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集中研讨了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六位批评家;2013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收录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徐刚、何同彬、傅逸尘等8人的批评文集。《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亦开始大量推介80后批评家,在2008年推介了杨庆祥、金理,2011年推介了黄平,2013年后相继推介了何同彬、傅逸尘、岳雯、李德南、丛治辰等多位80后批评家。
此外,湖南的《创作与评论》(评论版)开设了“新锐批评家”栏目,2018年改刊为《文艺论坛》,持续开设“起点批评”,大力推介青年批评家;湖北的《长江文艺评论》杂志开设“轻骑士”栏目多年;《名作欣赏》多年来开设多个推介青年批评家的专栏;湖北的《芳草》杂志近年开设了“批评家档案”栏目推介青年批评家……
然而,在近十年来80后、70后批评家的崛起背后,我们可能忽视了中西部地区的青年批评家群体的艰难成长。整体来说,中西部批评家几乎被淹没在声势浩大的青年批评家崛起的轰鸣声中,即便发声,声音也显得廖寂和微弱。
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等地域性文学概念受到了高度关注。张晓琴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感慨道:“文学界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讨论越来越多,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也举行过相关的研讨,而有关新西部文学的讨论并不多,能够看到的文献也只是偶尔有论者在论述西部文学时提到过,如杨庆祥在《西行悟道》的研讨会发言、杨天豪在研究《西行悟道》的文章中,曾先后提出过‘新西部’的概念。”[1]无论是西部写作还是“新西部”,它的美学,都有其独特性,要对西部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关注西部地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使批评和创作的发展更为协调,刻不容缓。
一、西部青年批评家现状
衡量一个区域的文学生态,除了看写作者群体的数量、创作状况、重要作品的影响力,批评家群体的数量和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评价批评家的现状中,指标众多,但从对西部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来说,笔者选取在业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选取的批评家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自2011年至2022年选聘的十届一百人所涵盖的地域为例。从这两个重要的入选者区域分布,可以从一个侧面看清整个年青一代批评家受教育的状况、分布状况等,从而看出西部地区青年批评家的现状。
作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的《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是国内理论刊物中最早设立专栏推介批评家的刊物,在理论界有重要的影响力,自1998年开设至2023年年底(2003年、2004年两年停办),先后推介了南帆、陈晓明、李敬泽、吴义勤、谢有顺、张清华、郜元宝、张新颖、吴俊、黄发有、贺桂梅、赵勇等144位当下国内最重要的一批批评家。批评界赞誉“今日批评家”栏目“催生了批评家的成熟”。2001年年底,近30名批评家相聚广西。会上,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认为“今日批评家”栏目“年龄从南帆到李洁非往下挪,已经挪到年纪比较轻的一批批评家,他们正是我们九十年代—— —个正值文坛变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很优秀的年轻批评家。‘今日批评家’实际上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道路、规则的清楚展现。它集结起一支如此有生气的批评力量,这不是一个一般栏目的问题”。[2]
张燕玲曾撰文《〈南方文坛〉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重点谈论了“今日批评家”推介的批评家与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关系,《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专门就“今日批评家”栏目撰写了《“今日批评家”与当代中国文学》,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高度讨论了“今日批评家”栏目的重要性。学界都在反思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忽视了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这轮挑战,正好落在了70后、80后以及后来者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对70后批评家、80后批评家的推介,对当下文学批评生态的建构和健康发展意义重大。2022年,本人对当下重要的70后批评家、80后批评家展开对话,其中有个相对固定的问题,就是在自己成长道路上,“今日批评家”起到的推动作用,几乎大多接受访谈的青年批评家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了“今日批评家”栏目对自己成长的重要意义。
武汉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李遇春说:“我在2010年有幸进入《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阵营,这于我是一次重要的‘出场’,我不仅公开表明了自己《从阐释到实证》的批评观,而且著名作家刘醒龙老师、同门周新民教授也为我写了推介文章,如此这般以一组专栏文章的形式推介我,如今想来真是受之有愧!记得2010年底,我还应邀参加了《南方文坛》在上海与上海市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在上海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好多70后批评家,以前但知其名、不见其人,这次终于有缘在会上各抒己见。因为我长期在武汉求学和工作,此前从未进入上海和北京的学术圈,颇有外省人进巴黎的感觉。记得大家探讨的是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问题,随后以一组文章集束发表在《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其中就包括我根据发言写的短论《被媒体绑缚的文学批评》。所以我要感谢《南方文坛》,感谢张燕玲主编,2010年对于我个人确实具有纪念意义。岁月飘忽,人事倥偬,至今想来仍倍觉温暖,无限感念。”[3]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金理自2005年硕士时第一次在《南方文坛》上发表文章, 2008年被“今日批评家”栏目推介;2012年和庆祥、黄平一起开设“三人谈”专栏。金理称“张燕玲老师是批评界的‘养成系教母’,当她看准年轻人的潜力后,会持续地给予提携,陪伴成长,而不只是等待果实成熟之后去采摘现成。唯有兢兢业业才能不辜负张燕玲老师和《南方文坛》的栽培”[4]。海南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李音说:“我相信更多的青年批评家是像我一样,深深体会到,张燕玲老师‘催生了中国新生代批评家的成长与成熟’,这才是这个栏目最宝贵的品质。”[5]
李遇春、金理、李音对《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及主编张燕玲的感激之情,基本代表了年青一代批评家的心声。至今,本人已经访谈了近50位70后批评家、80后批评家,与以上三位的言说也基本一致。从陈思和到自己的学生金理辈——几代人对《南方文坛》的赞誉,这在刊物界是非常少见的现象,足见《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对当代批评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人将《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自2011年至2023年的入选者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各省区占比情况分别是:北京23人,上海19人,江苏7人,广东7人,广西6人,山东、海南、甘肃、辽宁、吉林、湖北、陕西、福建、浙江各占2人;新疆、贵州、山西、河北、天津、云南、安徽各占1人。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及自治区,即西南五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年轻批评家占比情况为:广西6人、陕西2人、甘肃2人、新疆1人、云南1人、贵州1人。西部共13人,西部地区青年批评家占比16.7%。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为加快青年批评家的培养和成长速度,努力打造一个新的青年批评家群体而设立。自2011年至2022年,十届一百人。“在国内各大学论资排辈严重、年轻学者和批评家很难从大学体制中走出来的情况相比,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建构的‘客座研究员’体制,显然迅速催生了大多出自于各大学中文系、知识结构新颖、批评眼光敏锐的新一代批评家。”[6]
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得者张莉在谈到客座研究员制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2011年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对她而言是极幸运的事。“一方面,客座研究员制度为我打开了一个空间,让我有机会和更多的同行认识、切磋;另一方面也逼迫我去迅速了解当代文学现场,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回过头看,从2011年到2015年也是我创作、思考最为旺盛的时期,我的很多问题意识都源自那时候,而且,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惶惑,这样的交流使我开始客观看待自己,事实上,每次交流和研讨,我都会发现自己身上的诸多不足,怎么办呢,只能回家刻苦阅读,刻苦写作。”[7]《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坦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积十年之功,缔造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传统,我个人忝列其中,与有荣焉。当然这个所谓的‘批评传统’内部既单纯又复杂,并非完全是一个褒奖的正面的范畴。所谓‘单纯’即批评的学院化、大学化,所谓‘复杂’就一言难尽了,诸如圈子化、精英化、功利性、话语权的垄断、资源的优先权等等。大概从客座研究员制度以后,文坛方才聚焦所谓‘青批’,这十年‘青批’既广受关注和赞誉,也不乏尖锐但真诚的批评,我个人更关注那些‘质疑的声音’。”[8]
无论“批评传统”内部既单纯又复杂,还是有“质疑的声音”,年轻批评家开始受到大量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第十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所言:“十一年十届过去,最早的那群‘青批’已经成为‘中批’,新的‘青批’也在不断涌现。我们可以说,我们当初的设想已经成功实现。一大批中青年批评家在新时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一支曾经期待的队伍。”[9]
从2011年第一届到2022年第十届客座研究的基本情况如下:
地域分布统计:北京26人,上海19人,江苏9人,广东5人,山东5人,天津3人,浙江3人,甘肃2人,陕西2人,四川2人,广西2人,山西2人,福建2人,湖南2人,辽宁、新疆、安徽、河北、云南、贵州、海南、重庆、内蒙古各占1人。
中国西部地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十届客座研究员中的占比情况:陕西2人、甘肃2人、广西2人、四川2人、云南1人、贵州1人、重庆1人,共11人,占客座研究员总数的11%。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兼《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一共48人,分别是房伟、何同彬、刘涛、刘大先、傅逸尘、张立群、郭冰茹、黄平、张定浩、丛治辰、张晓琴、徐刚、饶翔、陈思、夏烈、王晴飞、李振、项静、黄德海、杨晓帆、马兵、方岩、王鹏程、王迅、周明全、韩松刚、李德南、刘波、颜水生、杨辉、张涛、徐勇、李丹、李伟长、金春平、木叶、李音、李松睿、张光昕、程旸、陈培浩、来颖燕、李章斌、汪雨萌、陈舒劼、曾攀、康凌、李浴洋。
在这个重叠名单中,西部有5人,占比10.4%,但张晓琴、王迅分别调入北京、浙江,使得目前西部在这个名单中只有3人,占比6.25%。
无论是《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整个西部地区的年轻批评家占比是非常小的。这一方面是名校博士毕业后,大多留在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中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少有名校博士后到西部地区高校工作的,或者说,即便有,比率也相当小。以云南为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名校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回云南工作的就非常少。另一方面,地域的限制对批评而言,还是非常明显的。西部地区的年轻批评家,很难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批评家一样,享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以云南大学文学院为例,据《2020年中文简讯》《2021年中文简讯》《2022年中文简讯》三年的统计,2020年,文学院教师外出交流15人次,举办国际学会会议一次——2020年1月8日至11日,韩国中国语文学研究会、中国云南大学文学院、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暨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举行。2021年,文学院教师外出交流13人次,举办国际学会会议一次——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国云南大学与韩国延世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东亚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论坛“东亚各国文化多样性的社区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线上会议方式顺利召开。2022年位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举办国际学会会议一次——2022年5月28日至29日,由云南大学文学院主办,世界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南亚文学研究中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印尼华文写作者协会、文莱华文作家协会联办的“第一届东南亚南亚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腾讯会议线上召开。整体来说,对外交流相对偏少,文学会议也极少。学术重在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学术,举办文学会议,积极走出去参与学术活动,是青年学者成长必不可少的要素。
二、云南青年批评家现状及其问题
2015年10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课题组撰写了《云南文艺评论现状、问题、对策和措施研究》一文,其中对当代云南文艺评论历史简要回顾:
当时云南文艺评论队伍主要集中在省文联(作协)、部分高校的文学系、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等单位。文艺评论作品的发表园地主要集中在《边疆文艺》《云南日报》等报刊开设的评论栏目中。基本没有专职文艺评论家,没有专门的文艺评论阵地。在当时文艺评论队伍中发生过重要作用、如今健在的晓雪,在全国一直以诗名世,但他最早成名之作《生活的牧歌》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艾青的诗学论著。周良沛也以诗歌创作著名,后半生却以研究和整理出版中国现代诗歌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那些评论写作起步于 1960年代的云南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如今还有评论新作发表者已经不多,且已影响式微。从1980年代开始发表评论作品,并坚持至今的评论写作者,早已成为当下云南文艺评论的中坚力量。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相较于诗歌、儿童文学等题材的创作在全国取得的成绩来说,云南的文艺批评无论从人才队伍构成、影响力还是平台建设来说,都处于相当不乐观的状态。
现在谈起云南文学,无论是文坛还是云南人自己,都觉得云南文学太羸弱,其实,云南文学自五四以来,并不弱,只是评论太弱,没有及时将云南文学推介宣传出去,或者,云南的文学评论没能和创作取得同样的成就。
早在1920年10月25日,云南第一份新文化期刊《滇潮》就由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创办,该刊开宗明义地表明要“做云南新文化的导管”。[10]1929年至1933年,云南现代文学的先驱李乔、马曜、马子华、罗铁鹰等先后抵达文化中心上海,接受新思潮,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云南的文学先辈,积极参与其中,正如1935年马子华出版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后,茅盾评价说:“显示了云南虽然边远,到底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11] 抗战期间,云南籍作家徐嘉瑞、楚图南、马子华、罗铁鹰、雷溅波、张天虚等陆续返回云南。同时,中法大学、东方语专、国立艺专内迁到昆明办学,中山大学前往澄江办学等。特别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办学,为云南的文学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沈从文、穆木天、施蛰存、朱自清、曹禺、闻一多、李何林、李广田、田汉等“外来户”培养了大量的云南青年作家。
正如《云南文艺评论现状、问题、对策和措施研究》提到的,对云南“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却开展甚少,即便当时出现过一些评介文章,其中多数也并非由云南本土评论家所完成”,如最早提出“认识云南,表现云南”的是穆木天。张光年1943年6月,在《新地文丛》提出“描写云南”的口号,1944年2月,又在《高原文丛》上发表《云南生活——地方色彩和地方性格》 一文,说“地方色彩是通过了对于主题和形象的完满表现以后所自然放射出来的光彩”“所谓云南性格,是指的复杂多变的云南生活的总和”。[12]即便当下,对云南文学研究有理论高度的,依旧是省外批评家,如张直心对五四以来云南文学的整体把握,其专著《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对研究云南现代以来的文学具有启发意义。再如对抗战期间云南文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的亦是早年在云南工作,后离开云南到西南民族大学工作的李光荣教授,其专著《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西南联大艺术历程》等,是研究西南联大文学艺术发展的扛鼎之作。
从批评家的视角看,老一代中有晓雪、周良沛、余斌等曾在全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1980 年代开始发表评论作品,并坚持至今的评论写作者,早已成为当下云南文艺评论的中坚力量”的主要是蔡毅、李骞、冉隆中、胡彦、李森、宋家宏、黄玲、张永刚等,他们大多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或在社科联、文联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本土文学,对云南文学整体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一代人中,蔡毅先后出版了专著《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渴盼辉煌——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等五部专著。先后有《不是生活直接决定文学》《从生活到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导师》等五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起蔡毅致力于探索创造之秘,研究文学创作的发生过程,这在国内外皆属首创。他曾深入探索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将两者作了详细的比较研究,被全国同行所重视。国内研究宗教理论方面的最高学术刊物《世界宗教研究》杂志1993年第4期用很大篇幅评价介绍,说明蔡毅在此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和成就。李森既写诗又做文学批评,阅读广泛,视野开阔,文笔洒脱,他首创的“语言漂移说”,阐释了诗和诗意生发的问题,在文艺理论普遍疲软之时,为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阐释元素并拓展了诗歌的阐释空间。冉隆中对“底层文学真相的调查”产生过广泛影响,由此在2010年第6期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推介,冉隆中成为云南首位被关注的批评家。李骞小说、诗歌、评论,三面出击,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现当代诗歌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群,也是云南这代批评家中,刊发理论文章最多的批评家。宋家宏早年研究张爱玲,之后转入对云南文学的深耕,多年来主持“云大评刊”,对云南文学的研究颇为深入。黄玲对云南的女性作家、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族别研究,对进一步研究云南文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青年批评家较活跃的马绍玺、李海英、于昊燕、一行(王凌云)、李濛濛、农为平、朱彩梅、蔡丽、方婷、邱健、孙金燕、李直飞、谢轶群、杨荣昌等,这代批评家和上几代批评家最大的差别是,几乎全是文学博士,起点高,学养较好。如马绍玺在北京语言大学跟随李玲完成博士学习,李海英在河南大学跟随著名学者耿占春完成博士学业,等等。其他如一行(王凌云)、李濛濛、朱彩梅、方婷都是在省内完成了博士学业。
整体观之,云南高校中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青年批评家,毕业于名校,师从著名学者的相对较少。大量的本土博士,带来一个隐性问题,没能在国内一流高校接受系统训练,没有接受过国内一线名师指导。纵观国内最优秀的70后、80后批评家,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高校,不是说毕业于一流高校就代表了自身的素养,但国内最好的批评家几乎集中在这些高校,站在巨人肩膀上,接受最前沿的批评训练,对从事文学批评肯定是有利的。从本土培养来说,目前云南有现当代博士点的高校只有云南大学一家,博导有李森、张志平、杨绍军三人,外加几位校外导师。有现当代硕士点的高校也只有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昆明学院四所高校。这导致云南在本土批评人才的培养上,也和省外有很大差距。
文学的地方性,是文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属性。批评家关注本土创作,也是题中之义,但正如南京大学著名教授丁帆评介青年批评家金春平时所言(关注山西文学):“无疑,这是一个从地域作家作品研究为学术发端的格局,也是许多学者的必经之路,但是,倘若走不出这个怪圈,他只能是一个格局狭窄的三流评论家,好在金春平像许许多多的批评家一样,很快就走出了山西的大山,放眼全国,指点整个中国当代的作家作品了,这是他的第一次飞跃。许多评论家就会停留在这个位置上耗费毕生精力,满足于成为一个二流的批评家。聪敏的学者是决不会在这停留很久的,他们一定是会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升到新的境界,在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研究中,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学术能量来,也许这就是朝着一流学者迈进的标志,虽然这个过程是十分艰难的攀登,然而,能够朝着这个目标前行的人,总是拥有不一样的格局,他的眼光是与一般学者不同的,因为他的视野是开阔的、胸襟是博大的。当然,要想登上光明顶是不易的,必须还得有世界文学格局的眼力劲,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的,这种大师风范应该是每一个学者都要追求的目标,虽不能至,然必心向往之矣!”[13]
丁帆对自己弟子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从地域作家作品研究为学术发端的格局,也是许多学者的必经之路,但是,倘若走不出这个怪圈,他只能是一个格局狭窄的三流评论家。”大多进入云南高校的在省外完成硕士、博士教育的青年学者,进入云南后,为评职称,申报国家社科课题或省哲社课题时,大多又只能申报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内容。这导致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搞田野调查、完成课题。更为让人感到可惜的是,部分高校年轻老师,为了现实利益,花费大量时间从事几乎无人问津的县市级文学和大量没有写作成绩的作家的研究。我近来关注过云南一所地方高校的文学院,它大量年轻教师是在省外完成博士教育的,学养非常好,其中几位的文章、研究也做得很有特点。但为了现实利益或不得不为之的理由,一年内至少两次去研究县、乡作家,而这些作家,连生活在云南、从事文学刊物编辑和研究的笔者自己,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笔者看他们的文章,大多只能发在市批评家协会的微信公号上,点击量在两三百次。不是不可以去研究底层作家,要看你的研究方式,冉隆中多年研究底层文学,不就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吗?另外,对县乡作家的研究,不能成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若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县乡、自己生活的地域内,完全忽视、放弃前沿问题的研究,那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云南有非常优秀的诗人,如于坚、雷平阳、海男、祝立根、王单单等,小说家如夏天敏、范稳、胡性能、张庆国、潘灵、雷杰龙、陈鹏、段爱松、包倬等,恰恰很少有云南年轻批评家去做系统研究。
我们云南有不错的批评家,文章好、观念新,但他们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在业内没有任何影响,印数太少,无法被更多的人看到。不是说文章一定要发表在这些刊物才有价值,而是在当下,文学研究者、高校从事文学批评的老师、学生,他们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些杂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长时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刊物之外,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
笔者对云南青年批评家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整体发文的质和量都不太理想。但从抽样中也可以发现,马绍玺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的研究以及小凉山诗歌群体的研究,研究方向明确而专注。李海英主要集中在欧美主流诗人的翻译、研究以及对昌耀的研究上,心无旁骛,申报的国家社科合格专著也主要集中在这两块上。于昊燕博士做的是老舍研究,多年来持续在老舍研究上着力,近年亦开始对云南直过民族展开研究,成绩突出。邱健本科学的是艺术专业,自身在音乐上有极高的天赋,跨学科研究优势非常明显。李濛濛是云南少有的文二代,为李骞之女,博士做的是萧红研究,今年对王蒙、铁凝等重要作家作品下过硬功夫,文本细读和理论功底兼备,假以时日,必将成为云南重要的批评家。
另一个问题是云南批评家没有与云南的作家形成相互成长的共同进步模式。批评和创作是同构的关系,是相互砥砺、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关系。但目前云南的批评和创作并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云南的诗歌创作在全国都成为了“云南现象”,近年又涌现出“云南青年诗歌群体”,但云南的诗歌研究并没有完全跟上,对云南重要诗人的研究中,研究得有水准的还是省外的批评家。云南有一批很优秀的中青年小说家,但也很少看到云南批评家对他们进行系统研究。不是说云南批评家就一定要花更多的心思来研究云南作家,没有哪个批评家是为某一个地域的写作者服务的,但是,作为云南批评家,我们不仅对他们的作品熟悉,对他们的人我们也很熟悉,这样再研究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在云南文艺批评本身就很弱的情况下,和作家形成互相成长的氛围,对彼此都是有利的。
除了人才匮乏,还有阵地建设,这也是制约云南青年批评家成长的一个致命因素。从平台来说,云南这么一个大省,至今连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文艺评论刊物都没有。有一本自己的评论刊物,对聚结全国最有影响的批评家队伍、培养自己的批评家队伍,都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以广西为例,1997年底,《南方文坛》联手中国作协创研部,邀请了国内一线批评家到广西,召开了东西、鬼子、李冯的研讨会,并在《南方文坛》专题讨论三位的创作,从此,“广西三剑客”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专有名词。2015年底,《南方文坛》再次联手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在京召开“广西后三剑客作品研讨会”。田耳、朱山坡、光盘三位被誉为 “广西后三剑客”,等等。广西诸多对作家的推介,都有《南方文坛》的身影,这说明一个刊物对地方文学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作为广西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期刊,《南方文坛》自创刊以来始终把推介广西文艺作为办刊宗旨之一,特别是改版后突破以前单纯的地域性界限,它以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关怀和在宏观的全国背景上来关注广西文学、推介广西文学,把广西的创作让一些本身就在思考当代文学整体性、具备整体性把握能力的著名批评家去研究和推介。” “《南方文坛》努力在批评和创作间、在广西与全国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染。尽可能把广西文艺纳入所有栏目中推介……不仅让青年作家言说,还组织批评家进行评说。尤其把广西实力派作家与外省知名作家并置参照,其同处于中国文坛的大背景之下,境界阔大。”[14]近年来,曾攀主持桂学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项目,担任首席专家,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主持“文学桂军点将台”栏目;在《贺州学院学报》主持“桂派批评英雄谱”栏目,率先提出“桂派批评”概念,并进行深入论析和阐释;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丛书的《短篇小说卷》(上、下)与《中篇小说卷》(上、中、下),并撰写这两卷的导言。广西文学创作和研究彼此联动、相互促进,这也让广西文学在西部独放光芒。
2022年4月,《西部文艺研究》杂志在甘肃兰州创刊,从它近一年多刊发的文章和办刊理念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西部文艺研究》一定会像甘肃当年主办的《当代文艺思潮》一样,影响全国文艺批评界。
目前云南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文艺评论刊物。2009年《边疆文学·文艺评论》创刊,对培养云南批评家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办刊过程中,连续五届都获评《边疆文学·文艺评论》年度奖,该奖项每两年评一次。但因诸多客观原因,《边疆文学·文艺评论》停办。没有自己公开、独立的理论刊物,是制约云南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边疆文学·文艺评论》停办,由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负责编辑出版的《云南文艺评论》图书,以书代刊集中展示文艺评论学术成果,但每年一本,不仅容量较小,且影响力难以展示出来。
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平台建设,这些短板都制约云南文学批评事业的发展。
三、西部或云南青年批评家培养方式及路径
《南方文坛》副主编、青年批评家曾攀在谈《南方文坛》时讲道:“边缘与中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圜甚至逆变。”[15]边缘与中心,在时空上往往会发生逆转。从地域上,处于广西的《南方文坛》属于边地,但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看,《南方文坛》何尝不是中心?
从《南方文坛》成功的办刊经验上,西部地区12省市及自治区联动起来,在批评家协会、高校间搭建广泛的交流平台,组建西部青年批评家联盟,定期开展西部青年批评家论坛。早在2015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大西南文学论坛便在成都举行,并挂牌成立了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同时,编辑出版《大西南文学论坛》,至今已经出版至第5辑。只需在大西南文学论坛的基础上,将“西南”扩大地域范围至整个西部地区,在现有论坛的基础上加大对青年批评家的研讨和培养,便可结成更广意义上的西部青年批评家联盟。
创办新的理论刊物,难度较大,但可以依托西部各省目前已有的文学刊物,开设相应栏目培养青年批评家。可以借鉴的例子是《芳草》杂志。《芳草》本身是一本综合性文学刊物,但近年来开设的“批评家档案”栏目,每期用五万字的篇幅推荐青年批评家,整组文章由於可训老师的主持人语(实为对推介的青年批评家的评论,每期主持人语在两三千字),学术自传、评介文章、访谈、学术年谱组成,全方位推介青年批评家,开设以来,备受关注。2024年起《大家》将开设“同步成长”专栏,遴选六位云南青年批评家,对云南六位重要作家进行作家论,形成云南作家和云南青年批评家共同成长,创作与评论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云南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另外,在昆明市文联的签约批评家制度的推进中,《大家》与昆明市文联携手合作,开设与签约批评家相应的栏目,增加云南青年批评家的曝光度。
刊物创办难,依托出版推介青年批评家亦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以云南为例,云南人民出版社自2013年开始,陆续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大型批评丛书。《80后批评家文丛》出版后,被称为中国80后批评家成长的“北馆南社”事件之一。青年批评家张元珂兄在《80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一文中认为, “一个批评家群体的形成,至少拥有以下几个必要条件:(1)有一位或几位领军人物,以其为中心联系一定数量的优秀批评家;(2)有固定的学术平台或期刊媒介,使其拥有表达该群体愿景的话语权力。这个平台对他们的支持是长期的,而非一时的。(3)他们的批评深度介入下文学现场,特别是对同代作家的成长与创作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4)这个群体具有同仁团体的凝聚力、发展力,既表现出了集团作战的优势,又有个体独特的批评个性。(5)批评家主要成员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前瞻性的批评视野,其在场方式引人瞩目” [16]。出版,以丛书的形式推出青年批评家文丛,能将这五个因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推动青年批评家成长。
云南可以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已经在批评类丛书出版得到认可的情况下,由高校、科研机构共同打造云南的《滇籍诗学批评丛书》,从熊秉明、姜亮夫等到张文勋、蔡毅、李骞、李森等,一直沿袭到马绍玺、李海英、于昊燕、孙金燕、李濛濛、符二等,包括云南籍在外工作的批评家杨晓帆、颜炼军等,全部纳入其中,通过召开高峰论坛、出版丛书的方式,推动云南文艺批评事业的发展。
当然,除了平台外,西部青年批评家自身素养的提升才是最为关键的。这需要西部地区的青年批评家更加用功、用心地阅读,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
注释:
[1]张晓琴:《新的西部美学原则在崛起》,《文艺报》2023年9月21日。
[2]张燕玲:《〈南方文坛〉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373页。
[3]李遇春、周明全:《怀中国文学复兴之志》,《名作欣赏》2022年第6期。
[4]金理、周明全:《金理:“困得睡着”又“睁开眼睛”,感受辽阔的江面和风》,《名作欣赏》2022年第7期。
[5]李音、周明全:《我想做一个慢教授,去理解世界的变化》,《名作欣赏》2023年第6期。
[6]程光炜:《“80后”批评家的崛起》,中国作家网2020年9月13日。
[7]张莉、周明全:《做学问的魅力在于与世界上最有趣、最有生命能量的人对话》,《名作欣赏》2022年第2期。
[8]何同彬、周明全:《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少了》,《名作欣赏》2022年第10期。
[9]《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十届百人”了》,澎湃新闻2022-08-1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0954741028615234&wfr=spider&for=pc.
[10][11]张直心:《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第5页。
[12]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13]丁帆:《朝乾夕惕 钩深致远——金春平印象记》,《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14]张燕玲:《〈南方文坛〉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社2020年,第368—369页。
[15]曾攀:《“今日批评家”与当代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16]张元珂:《80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大家》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云南出版集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周明全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48/74/138525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