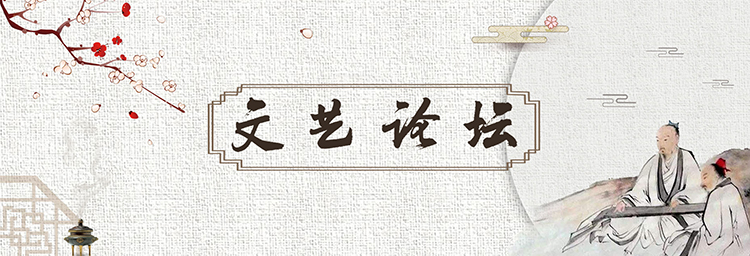

《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国科幻电影的“逆向式”探索
文/贺潇雨
摘 要:世界科幻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从向外探索外太空与外星他者到以宇宙为镜子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这一“向内转”的过程。《宇宙探索编辑部》抓住了世界的非理性一面,融合了意识流小说的诗意叙事与超现实主义电影的碎片化镜头语言,并结合伪纪录片这样一种具有元叙事性的拍摄形式,使得观众也参与了这样一次探索内心的宇宙之旅,无疑是中国科幻电影“向内转”的一个成功范例。
关键词:《宇宙探索编辑部》;科幻电影;“向内转”;意识流
“向内转”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是指文学从表现外在客观世界转向对人内在世界深层意识的探索,文学创作的焦点也从人物的行为转变成人物的精神世界。吴晓东称之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地心说的神话,将人从宇宙中心的位置上驱逐出去了,人成为了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微尘,“而普鲁斯特的小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新发掘,使人的精神重新置于天地的中心,这是与哥白尼革命相逆相悖的”[1]。纵观世界科幻电影史,科幻电影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科幻电影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大约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作为一项电影类别被人们广泛认识。早期科幻电影多以太空旅行与外星探险为主题,或是书写人类与机器人、外星人等他者之间的对抗或交流。此时的科幻电影探索大多是向外扩张式的,如好莱坞早期科幻片基本都像西部片一样,对开疆拓土的主题深深着迷。还有另一类乌托邦或反乌托邦题材的科幻片,这类影片的背后则是巴尔扎克式的社会全景设想。影片将整个社会视作人物的领地,仍是“向外”的整体性思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让-吕克·戈达尔、阿伦·雷乃等法国新浪潮导演创作出一批回归人类大脑的科幻之作,在他们看来人类所寻求的未来实际上是对人类自己精神的溯源,宇宙并不是大脑的外在,“向内转”的趋势渐渐在科幻电影界显现出来。
中国科幻电影起步相对较晚。2019年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硬科幻片有了全新发展。但软科幻片佳作的出现要稍迟一些,《疯狂的外星人》《独行月球》《外太空的莫扎特》等都未能深入挖掘软科幻片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或哲学维度,仍然停留在商业喜剧片的水平,并未成为科幻电影真正“向内转”的佳作。2023年4月上映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无疑是让人惊喜的。从对人类生离死别之精神创伤的关注到对人类终极存在的追问,《宇宙探索编辑部》抛弃了科幻电影自身严谨理性的科学外壳和传统叙事的统一性与连贯性,有着浓厚的诗意和深刻的哲学思索。
一、从“疯狂科学家”到堂吉诃德:非理性与相似性的英雄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向内转”首先体现在影片对非理性的关注上。传统意义上的科幻片往往建构在科学与理性的权威之上,常依托一些科学理论或科学猜想作为故事背景进行叙事。《宇宙探索编辑部》则几乎抛弃了理性崇拜,转而走入非理性的诗意之中。
被导演孔大山戏称为“民间科幻片”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最初灵感源自孔大山2017年看到的一则新闻:山东某村一位农民声称自己电死了一个外星人,并将其遗体藏在自家冰柜之中,记者赶到农民家时发现冰柜里放的不过是一个劣质的硅胶玩偶。孔大山发现新闻里这位农民讲述这个荒唐的故事时态度极其认真,这让他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荒诞感,于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故事雏形诞生了。影片的主人公《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唐志军是一个离婚丧女的颓废中年男人。三十年来他深信有更高等的外星文明存在,并认为找到外星人是人类文明再次进化的唯一办法,到了那时候人类的一切隔阂、战争、人性所有丑陋的东西都会消失。在某天发现所谓“外星文明发来的强烈信号”后,唐志军带着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去往西南部的“鸟烧窝村”寻找外星人。可见无论是导演最初的灵光一现亦或是主人公唐志军踏上旅途的契机似乎都是非理性的。
过往许多科幻电影中的主人公或重要角色常是科学家或科学研究者。在日常认知里,这类人物往往拥有着超前的科学智慧,最终似乎也都会找到有关宇宙或人类的真相或真理,他们与非理性一词似乎毫无关系。早期科幻电影里也出现过一些误入歧途的科学狂魔甚至是恶魔式的疯狂科学家,这或许是由于二十世纪初人们认为科学迅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这些电影里的疯狂科学家并不是非理性的存在,而是过分热衷于一种工具理性走火入魔,期望对世界进行彻底的改造。而《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主人公唐志军则显示出一种浓厚的非理性情结。作为宇宙外星文明的研究者,唐志军在寻找外星文明的旅途中所依赖的都是一些玄学巧合或非科学的猜测。比如他认为鸟烧窝村的孤儿孙一通时常突然晕倒的本质原因并非是脑部疾病,而是因为接收太多宇宙信息,头脑信息过载所致。影片经常刻意描写唐志军这个人物身上科学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打破科学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在日常对话中,唐志军常常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以科学式语言说着荒诞的话。当家里的电视机坏了时,唐志军立刻打电话找气象站的朋友那日苏询问NASA官网是否发布最新突发事件:“不排除是某两个星系的汇合,或者是半人马座的某一颗恒星它坍缩了,散发出的宇宙射线过于强烈,导致我这个电视机现在过载。我个人觉得更有可能是某种外星文明它突然发来了某种强烈的信号……”[2]他的日常话语具有明显的书面化气质,专业名词信手拈来,这使得他整个人学术气质浓厚,可他所说的内容却与严密的逻辑理性毫无关系。唐志军对疯癫的态度也十分有趣。在精神病院病房外等待做讲座时,他面对镜头这样谈到自己对精神病的看法:“精神病是人类为了区隔少数特殊人群的一个标签……所谓的精神病人脑部结构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异常的,(他们)大脑里面的神经细胞的交流电是异于常人的,所以这个人群他可能会拾取到我们普通人类没有办法读取的外星信号。所以精神病也是我们研究人类与地外文明连接的一个突破口。”在他看来疯癫不意味着比所谓的正常人少了些什么,反而是多了些什么。因为精神病人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所以他们才不被普通人理解。通常意义上,科学似乎总是与严谨、理性这类词紧密联系,电影却展现了科学与理性之对应关系的某种断裂,同时呈现了科学与疯癫之间的一种诗意连结。科学真的一定只能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吗?智利小说家本哈明·拉巴图特在短篇小说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就讲述了多位科学家在临近科学真理时所处的癫狂状态,那一刻这些科学家们完全是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中。而《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唐志军也正是吃了毒蘑菇之后,在幻梦一般的场景中去认识宇宙真相的。
唐志军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堂吉诃德式人物。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堂吉诃德处于文艺复兴知识型与古典知识型之间的断裂之中。堂吉诃德混淆了文艺复兴知识型的相似性与古典时期知识型的同一性,因此将风车当作巨人,视羊群为军队。如果说他是一位处在信仰同一性的古典时代却执着寻找相似性的英雄,唐志军则是一个处在理性时代却致力于寻找非理性真理的英雄。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文学转向的同时,二十世纪欧洲大陆的哲学也有回归寻找“相似性”的趋势,它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视为一种相似性关系,而非传统逻辑中的演绎关系或归纳关系。可见“向内转”本身就与寻找相似性有着共通之处。二十世纪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哲学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就时常描写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相似性。不同于十九世纪小说家喜欢将故事情节建立在稳定的因果关系之上,排除临时或即兴的成分,二十世纪的作家重视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写作,回避逻辑判断的确定性,而相似性的诗意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凸显出来。唐志军就是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去追寻人类终极问题的答案的,因此他时常将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解读为重要的因果关系,并将之视为发现外星文明的重要线索。他所抓住的因果关系都未建立在理性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出于一种“向内转”的、诗意的非理性。比如家里的老式电视机坏了,他认为是宇宙出现了问题,将人类工业文明的造物电视机视为与更高等宇宙文明沟通的工具。他也会将电视机上出现的雪花视作“宇宙诞生时的余晖”,如此诗意而浪漫。影片中与外星人沟通的孤儿孙一通同样暗示着相似性的诗意与非理性真理之间的重要联系。能接收外星人信号的孙一通喜欢写诗,他将宇宙传给他的秘密都通过诗句表达出来。当唐志军问他有关外星人的问题时,他会说不知道怎么表达,但看完整个影片我们会发现其实答案都在那些朦胧的诗句里。聊到写诗时,孙一通也表达了对确定性的某种质疑,他说:“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数学老师经常来占我们语文课。他说诗歌只是人类感情沟通的工具,但是数学是整个宇宙都通用的语言。我问他你确定不。他说你举手了没有。我就把手举起来,他说他确定。所以数学就是太确定了,我学不好。”诗意往往与非理性的世界相通,也正是诗意让非理性与理性处在了同等位置,而非福柯所说的疯癫与正常的权力关系之中。
写出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相对真理,所以人所拥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3]。二十世纪文学“向内转”一定程度上受物理学中吉布斯革命的影响。诺伯特·维纳将吉布斯与弗洛伊德联系起来,他指出:“承认世界中有着一个非完全决定论的几乎是非理性的要素,这在某一方面讲来,和弗洛伊德之承认人类行为和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理性成分,是并行不悖的。”[4]可见,文学之“向内转”并非只是对人类内在世界的重视,更是对客观世界理性之绝对权威的反思,而从科学理论与科学想象中发展起来的科幻电影之转向也是如此。(节选自2024年第2期《文艺论坛》贺潇雨《<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国科幻电影的“逆向式”探索》)
注释:
[1]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4页。
[2]出自《宇宙探索编辑部》台词,后文不再标注。
[3]〔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4]〔美〕诺伯特·维纳著,陈步译:《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贺潇雨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40/62/140439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