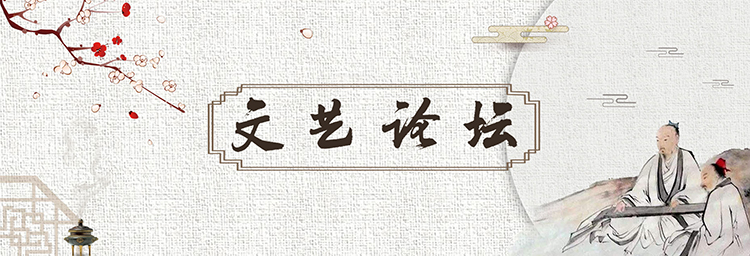

未竟的形式与远方
——从《去洞庭》到《南方巴赫》
文/赵晨
摘 要:郑小驴的《去洞庭》与《南方巴赫》极富个人风格,在形式追求与内容表达层面皆展现出了积极的探索意识,暴力、情欲、出逃姿态成为其南方系列小说的重要标识,这与作家本人的代际、经历、认识息息相关。从集缀形式入手分析故事便于发现两部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挖掘中国传统小说形式在当代的流变脉络与意义变形,借此可探析青年作者这一阶段的写作沉淀,展现其创作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去洞庭》;《南方巴赫》;“故事集缀”;郑小驴;青年写作
一、未竟的“故事集缀”
学者顾明栋分析中国传统小说在实践中展现出的诸多特点时,曾指出其中一个特点便是:“一部长篇小说可以由不同的片段连缀而成,而这些片段之间时常缺乏明显的关联。”[1]连缀之法,丰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形貌,是中国传统小说笔法之一种。“故事集缀”则是对顾这一判断的学理性提炼,学者张蕾基于鲁迅和胡适两位先生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儒林外史》之评价提炼出此概念用以表征现代小说的结构形式,依照其定义:“‘故事集缀’型小说是一种现代小说,它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故事,和古代小说的故事传统一脉相承。”[2]其故事构成类型分为并联与串联两种,并联型的集缀故事彼此之间可以相互穿插,齐头并进,《去洞庭》正属此类,小耿、张舸、史谦、岳廉等人的故事相互平等,各自区别,在小说中保持着自身故事的相对完整性。已有论者指出《去洞庭》“看上去具备‘好看’的故事外壳”[3],不妨沿此话题继续,所谓的“好看”来自于小说五个人物之间相互关联为小说带来的叙事密度,而这一阅读效果得益于小说形式,即“故事集缀”。
《去洞庭》最为典型的特征便是:“去”这一愿景统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相互关联,关联之处的情节总体上连贯成大故事,旁逸出的小故事之间则相互平等。如果将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稍加分组,可以得到:小耿与张舸、小耿与史谦、史谦与顾烨、顾烨与岳廉四组主线关系,分别构成犯罪、雇佣、夫妻、情人关系。在此之外,还有史谦与汪灵、张舸与图门两组旁支线索,用以对小说中的婚姻、恋爱主题加以补充,在丰富小说人物前身的同时扩展了故事的容量。而这些关系最终都被“洞庭”这一终点所囊括。一切破碎,一切成灰,既已看到现实的底色,那么小说也要从这里开始着墨,拼联碎片,赋予形状与色彩,洞庭,恰好是一个合适的表达。开篇第一章名为“北归”,饶有意味,既提纲挈领,又表全书主旨。北与南相对,小说中出现的东北老工业区、北京等地作为洞庭这一意象的反面,分别表征着衰败与冷漠这两种不同的城市形态促使城市中的人们做出不同的抉择,而所有的抉择最终都被“归”统摄,归于洞庭,归于理想桃源。在以洞庭为终点,并以“归”之意为动力的小说叙事中,作者放弃了“可悲的第一人称”,上帝视角带来的第三人称叙述使得小说事件种种如浮世绘般呈现,保持独立,相互连缀。
两车相撞将这组典型的集缀故事归拢,“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车祸,这一作者人为设置的意外将缀联的子故事集结一处,集于一部长篇内的故事以不同的面向展现了这场车祸所引出的“中国现实”,爆破出一个关乎时代的宏大母题。两车相撞,一场车祸,一首一尾,在暴烈中开始,在爆裂中终结。两场车祸关涉的五个人物相互关联,可将此视为“人与现实的关系正在转变为碎片与系统的关系”[5],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管窥小说所牵涉的时代,也可将此视为“故事集缀”这一形式带给小说的动力。
叙事技艺的自觉是写作者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郑小驴展现出的便是这一种自觉。
在郑小驴另一小说《消失的女儿》里,一开篇作者便引了远藤周作《沉默》一书中的句子:“所谓罪,是指一个人穿越另一个人的人生,却忘了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6]此篇推进仰赖于叙事焦点的转移,焦点转移依托于人物的变化,受限视角带来讲故事的神秘性与新鲜感,一九九四与二零零八两个明确的年份时间有效联结了故事间的罅隙。人物的集缀还原了解密的过程,消失事件通过人物的转换来搭建故事的全貌,《去洞庭》则是通过故事的集缀来搭建车祸事件的全貌,是为集缀的扩容与升级,几人命运或明或暗的交织,恰是雪泥鸿爪的再次显形。这一形式的选用有其现实因素,清末民初新章回小说的兴起与彼时报刊行业的蓬勃发展不无关联,连载的形式反过来要求小说创作在形式上作出改变,因而集缀小说能以复古姿态冲击章回之规范,遂成现代小说新变一种。而当代小说《去洞庭》依旧展现出此般形式特征,一方面是传统效应的现形,另一方面则是以文学形式回应“碎片化”时代。集缀之形式不仅在现代,在当代亦有生存之道,传统形式与当代生活的弥合亦属借复古以求解放,或许并非有意复古,而是当代小说文体创新过程中无心插柳反而映照出现代小说变迁之样貌。
《去洞庭》中,车祸的出现其实不无刻意,刻意背后恰是作者之表意,戏剧矛盾增添了小说叙事的复杂性,强化了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失控,促进了小说张力的重叠与增殖。此外,以集缀的形式来展开两场车祸的前因、后果、旁支细节,打碎了线性的叙事时间,让记忆的碎片作为时间的表形方式,交错纵横,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可以说,车祸,是集结小说各人物的事件线索;洞庭,是集结小说各事件的精神线索。在小说后记中,作者提到“制造迷雾的人”,将这一身份的主谓宾打散、重组,会得到这样一则动宾关系:人制造迷雾。将其扩展开来,便是写小说之人通过“故事集缀”这一形式制造了小说中氤氲的迷雾,清晰的形式所呈现的恰恰是时代的混乱,并借此映照时代中人的迷惘无措。事无虚设,层叠重组。
郑小驴有一篇散文名为《写作的三个关键词》[7],三个词分别是:媚俗、公共空间、中国现实。这篇短文拥有一个颇像课堂教案的标题,与其说这篇表达了作者传道授业之心,不如说此篇是写作者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提炼与总结。媚俗,这并非对其小说整体风貌的概括,而是作者挥舞起小说长剑意欲斩伐的首要对象。昆德拉的逝世及其逝世所引发的媒体狂欢再次给予读者一个直观反思“媚俗”的契机,作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艳照、游行、出轨等元素亦属直观反思媚俗,反思后通过一场车祸将这些元素都撕裂为碎片,犹如荒原之上的雷霆烈火,焚烧罪恶,消除孽债。“公共空间”与“中国现实”,委实是一组过于宏大、艰深的词汇,但将其放置在小说创作的语境中似乎更易把握其指向。“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叙述的人物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活动。”[8]当我们讨论“湖南”“乡村”“公众”时,不妨将目光拉回到1931年。那年二月,胡也频遇害;三月,丁玲在沈从文的陪伴下送蒋祖林返回湖南常德;九月,丁玲开始在《北斗》创刊号连载小说《水》。遍布多省的洪灾是小说诞生的主要背景,也是作家本人与工农靠近的积极尝试。何以是“水”?一来与现实洪灾直接相关,二来水与群众之间存在一层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暧昧关系。洞庭多水,水是一个潜藏在小说中的巧妙意象,郑小驴以此营构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缠,集缀之形式正符此意,水波荡漾,弥合了私人意象与集体经验之间的缝隙。
集缀,在原子化时代的分散中致力构建一种新的关联与秩序。集缀类属文学形式的表达,如果借用音乐来进一步具象化其文体特征便是《南方巴赫》一篇中提到的《哥德堡变奏曲》。变奏曲乐章包含三十个变奏,主题反复,每三个变奏是一组,每一组的最后一曲都是卡农曲。变奏的重组,主题的反复,正是集缀给予当代小说的形式收获。集缀未竟,个人与社会之关联未竟,南方文学的卡农组曲未竟。
二、未竟的南方
“去”意味着尚未抵达,而这一状态的延伸版本即“远方”。因此,小说的结构整体建立在一种缩小距离的强烈意愿之上,并在此意愿中召唤出一组区别于“去”之过程的别样秩序。于是“去”成为小说的基本动力与外部框架,形成对小说内失落秩序的一种积极补偿。相较于一路向南的小耿,雪夜狂奔的小金似乎逃得更远。洞庭,尚且算是一个经纬度明晰的地理坐标;南方,则更为阔大与含混,弥漫着更多未知。“她说,湘江汇入洞庭,再入长江,最终流向大海。”[9]小说中的这句话也可用以揭示作者从《去洞庭》到《南方巴赫》创作历程中的异与同、变迁与坚持。
在郑小驴笔下,同南方相伴相生的文学元素,一者是暴力,另一者是情欲。
《南方巴赫》开头的关键是十八岁的“我”将要进城,不妨参照一下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暴力是迫使青少年成人的重要一环,郑小驴的做法类同,在其作品中,大有将暴力场景描写设定为“仪式”之感,以此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去洞庭》中,旁人眼中内向纤弱的小耿打砸平和堂商场的日系车;《南方巴赫》中小金砸碎茶几上的玻璃杯、挥舞螺丝刀。两组场景都展现着青年行径的幼稚冲动以及随之相生的危险阴影,暴力的身后潜伏着时代气候与个体成长危机。文字构建的残酷血腥画面背后是浓郁的恐惧情绪。小耿的恐惧在于害怕自己真的犯罪,文明的光照将从本已黑暗的人生中决绝退场;小金的恐惧在于害怕自诩正义的攻击乃属虚假幻想。悲惨境遇与绝望心理在小说中相继浮现,由此构筑了“幽黯”。“我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一群现实中灰头土脸的失败者,在社会规则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他们活在时代的夹缝之中,唯一能伤害的人就是自身。刀子扎得越深,意味着越痛,他们反抗的力度也越大。”[10]而在社会的固化和板结之中,反抗之力往往走向法制规范之外,由此暴力是为个体面向现实的冲锋形式,一种在绝望之中展现出的破坏力,粗蛮,却偶显闪烁的希望光斑。
在南方荡漾开的情欲表露则更为直白,《去洞庭》小说始于一桩强暴案件,中段的落笔重点是中年男女的出轨事迹,事件主人公虽不同,但一部长篇小说的关键词在叙述过程中逐渐清晰浮现,即情欲,而且其叙述偏向分明,欲才是表达的重点。《蚁王》所收录的八篇小说中,“情人”是一个便利的身份,无论是沈齐还是秋红,作者都在用这些人物去耕耘“欲”这一字,为压抑忙碌的都市生活增添一丝游移的暧昧,为溢满暴力的小说增加大众阅读看点。情,从来不是郑小驴小说中的落点,而欲,往往才是其小说中的一股重要推力。《南方巴赫》亦不例外,无论是道貌岸然的表哥精心用密码封锁起来的电脑文件,还是“我”在入伍前的奔波周折,如此经历种种皆是到“欲”为止,而当小金为了她想要探求一个真相,寻找一个回答时,此时的小说生出了一点情意。欲,用以超克青年虚无状态的工具;情,带领青年奔向更为广阔的南方。两者都是郑小驴作品里无限溃败的混乱中所展现出的相对恒定,以至成为其写作的一则重要标识。
暴力与情欲,糅合出郑小驴小说的“黑色气质”。黑色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类型片,往往通过血腥、暴力、情色来刺激观众的视觉体验,“犯罪”是这一类型电影中的重要元素。“这类电影充满了黑夜、暴力、负罪感和非法的激情,没有哪个类型比她更诱人了。”[11]这不仅可用以表现郑小驴创作的一大倾向,也可揭示其如此创作的成因。血腥与暴力显然是作者在开头便扔出的噱头,但却并不能仅仅以此概括小说样貌。哲学家韩炳哲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启发下提出当代文学的“爱欲之死”,并指出“生命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有积极面的生命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消极对于保持生命力至关重要……”[12]郑小驴小说之中的“黑”,正是以消极之法寻觅生命力,以黑寻光。“一篇成功的小说总是兼具多重属性,如同特殊暗物质,置身黑暗,不断发光。”[13]显然,作为一个积蓄了不少阅读、写作经验的作者,郑小驴已然具备了自己的审美判断,但创作最有趣之处往往在于创作实践与审美判断之间的分离或落差。的确,光是黑色电影塑造影响风格的重要影视技巧,也是郑小驴执意在小说中展现的写作技艺,但反复通过犯罪这一极端形式以抵达黑色路径,刻板对立,重复颇多,人性探索欠缺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潜文本的存在是郑小驴小说写作的另一标识,便利之处在于引用减轻了直写的负担,委婉表意,不便之处则在于给读者的阅读过程立起一座名为经典的大山,要想越过经典的意义实属不小的挑战。《去洞庭》中潜隐着两部当代文学史的“大书”,“大”在于其影响,《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的共性不仅在于其在当代文学史中所获得的高评价还在于其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受欢迎程度。这两部书在小说中的出现都与主线人物小耿有关,前者在小耿高考之后、家中父亲患病无钱医治的情境中出现,后者则在小耿打工谋生的场景中出现,暗中串联出小耿进城打工这条事件线索背后的精神旨归。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高中毕业之后外出务工,先后在建筑工地与煤矿工区打工,与选择驻留双水村开办砖瓦厂的孙少安形成对照,高加林总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纠结困局在对照的人物设定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兄与弟,乡村与城市,两种选择,两种青年面对时代的方式。饶有趣味的是,孙少平的心灵成长史仰赖于《创业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类书籍唤起了他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而《平凡的世界》之于小耿,所彰显的更多是消极的迷惘,艰难痛苦的日子不仅在村内也在城内。可以说,路遥在小说中刻意用理想、美好愿景所抹平的阶级差异与矛盾在《去洞庭》中被不断突出强化,这种强化的根源正是时代的变迁,八十年代的纯真逐渐被新教伦理掩埋,个人奋斗的效力不断被压缩。《去洞庭》中小耿化名张小华在各个工地流窜的经历也可视为对孙少平那段黄原城经历的致敬,虽在人群中,却如在荒野。《平凡的世界》仍未结束,在黄原城中无限孤独的孙少平后来在大牙湾找到了某种情感依托。如果说《去洞庭》中小耿在工地打零工的经历回应了孙少平的黄原城经历,那么《南方巴赫》中小金通过QQ漂流瓶获悉的矿厂事件与其后续闯进矿厂主家中便是回应了孙少平的大牙湾经历。因为煤矿之重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孙少平通过这份工作获得了人生认同感,而小金的行径再次解构了这份认同背后的美好理想。狂乱挥舞螺丝刀,这样一个富有攻击性、对抗性的画面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这仅仅成为一个出逃的动机,事已至此,不得不逃。由此,不难看到80后作家在致敬八十年代经典书籍时的反叛心理,也可由此看出时代与文学的变迁脉络。高加林之路,是一条无法通往美好的路,孙少平凭借理想与劳动奋斗克服苦难,沿着高加林之路往前大跨一步。而《去洞庭》虽言“去”,实则在“退”与“逃”,洞庭之路依然是一条无法通向美好的路,涂自强的危机在小耿的生活中延续,青年病症成为笼罩小说的一道障网。
《白鹿原》的出现其实稍显突兀,小说所背负的“新历史”标签很大程度上来自白、鹿两家所共同呈现出的乡土社会宗法底色,但是如果拿掉标签进而回归到文本自身,小说所展现的乡土伦理在现代发展进程中的溃败缩影实则再次映照出小耿悲剧的时代因素,没有“乡约”的现代生活迫使一个青年逃离乡村、在都市犯罪,没有“乡约”的小说也无法再挥舞起民族秘史的旗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野聚焦于白鹿原里的青年,那么其作为《去洞庭》潜文本的意义指向性会更为清晰。首先,青年们身后的白鹿原与洞庭都是地理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复合表征,维系着小说中人的记忆脉络和情感线索。其次,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白嘉轩在白鹿原所表征的“仁义”是为正统,田小娥的情欲翻涌与白灵的革命精神则是对绝对正统的调适抑或反叛。尤其是白灵,多次离开乡土,其出走姿态照亮了郑小驴小说中“逃”的主题,同时,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白灵获得了重生,而郑小驴笔下出逃的人群大都陷入了孤独的死寂之中,两相对照,再次显现时代变迁与困境,青年出走已不再能够作为医治时代病态的良方。
《南方巴赫》里出现的另一部“大书”是《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这部“大书”出现的意义首先在于混淆读者对“南方”这一概念的判断,威廉.福克纳身后的南方是美国内战后的分野之一,艾米莉小姐正是根植于传统南方土壤的一朵贵族玫瑰,她的死亡既宣告了南方历史的终结,也表明了传统与现代两股力量相撞之后的精神荒原图景。近年来,关乎“南方”的诸番“新”论断层出不穷,洞庭身后的湖南按照地理维度标识来看自然也可算其中一支,将“南方”堂而皇之地放置于小说标题之中,更是一次作者对自我写作身份以及小说气质归类的强调。其次,借福克纳的笔法来勾描另一位艾米莉,《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以死亡为小说起点,也以死亡为小说的终点,在死亡之间慢慢呈现出的不仅是南方淑女悲凄的一生,还有南方社会旧秩序的失落与新秩序的重组。此外,福克纳小说中充满留白,在有限的信息表达中,艾米莉小姐与尸身长期相拥而卧,这样诡异的情形使小说被贴上了“哥特”的标签。《南方巴赫》中封死的矿洞里出现的拿着书的女玩具人偶、诡异颓败的别墅以及不可靠的凶杀叙述都呈现出浓郁的哥特风格,而这一风格凭借其悬疑感再次强化了郑小驴小说的“黑色气质”。同时,致敬经典的弊端在此全面显露,致敬对象的光环会不遗余力地照亮新文本的瑕疵。福克纳面对南方的态度百般复杂纠结,对待南方象征的艾米莉小姐亦如此,因而这一女性形象具备丰富的阐释空间,而郑小驴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沦为男性人物凝视中的色情客体,刻板单薄,工具性大于人性,玫瑰无人可献。
从洞庭到远方,从经典到当下,通过空间挖掘青年道路、探索写作道路,南方未竟。
三、未竟的八十年代
“一九八八年,永远过去了,人类最后一个纯真年代。”[14]这是作者临近小说尾声时的感慨,既是追忆又含批判。《去洞庭》着力处理的一大问题是“八十年代”,处理的方式则是通过“80后”个体去反观时代。反观时代有两种指向,一种是通过当前的时代回顾往昔,将八十年代作为怀念的终点;另一种则是以八十年代镜鉴当下,将八十年代作为批判的起点。郑小驴,生于一九八六年,八十年代当然会在这样无限追忆的氛围中具备某种类乎起源性质的神话,同时,也很容易落入煽情的窠臼。八十年代之瑰丽,其中一个侧面是新知识与新方法的喷涌,而隔着时距的重审则会发现知识已过时且方法已失效。越是瑰丽,越易煽情,失效之幻灭越强,郑小驴的小说便由此开始,在失效的庞大幻灭中不断探索生活的边界与生存的可能,可能的表征可以是洞庭也可以是八十年代,在此意义上“洞庭”与“八十年代”是从空间到时间的一组文学转喻,其表意基本一致。
“去”,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根本动力;“洞庭”,是小说人物归宿的终极指向,在小说中有着两重表征。首先意指故乡,开篇章节为“北归”,归字暗示起源与重返。小说诸人皆是离乡远行客,无根漂泊,因此他们无法凭借自己暧昧的身份占有“回”这一行为及其背后属性。洞庭乡土与田园世界,意指朴素的幸福,无风亦无波,与小说中种种事件发生之地的冒险、刺激、混乱形成对比。“洞庭”还表征着终结,如果说小耿的故事是小说的明线,那么史谦的故事便是小说的暗线,这是去往洞庭、回溯八十年代的一组对照结构。一方面,史谦比小耿年岁更长,其存在以中年生活的失败映照青年们的失败,强调失败之必然性。另一方面史谦生意失败,家庭破碎,过往商业之成功与如今之破败两相对比,表明“阶级”并非逃避人生苦难底色的药方。最终,史谦义无反顾冲向洞庭,是为小说的暴力终结。
类乎《去洞庭》,《南方巴赫》中亦设置了一组基于年龄层的对照结构,即小金与表哥,年龄的差别与社会地位的差距使“表哥”在父亲的话语中成为一个理想的参照系。离开家意味着拒绝成为下一个父亲,而驾车夜奔则意味着拒绝成为下一个表哥,两次拒绝不仅是拒绝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复杂,也是拒绝父辈话语的可信度,探索再次成为一个积极的青年姿态跃上纸面,虽然仍未在都市生活中寻索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已经无需承受“父”的规训。在雪夜,小金握住了方向盘,而表哥放下了方向盘,对照关系再次通过“车”这一意象延伸到人生境遇中。
“疲惫夹杂着焦躁,他狠狠地拍着方向盘,诅咒着糟糕的天气,诅咒着头顶的厄运,诅咒无情的老天爷。”[18]在开篇的暴烈呈现之后,作者迫不及待地为小说主线人物按下了这样的判词。其实,“疲惫夹杂着焦躁”,既可以用以描述通往洞庭的途中,也可用以描述雪夜狂奔的小金,更可以描述作者近期以来的写作状态。当作者本人亦无法处理时代的困局时,其写作便不可抑制地弥散出焦虑气息。时至今日,现代性的焦虑几乎成为悬在每一个人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有坠落并击垮人生的危险,关乎时代与社会的宏大外部议题早已随风潜入个体的精神困境之中。《去洞庭》应对困境的方案是悬置洞庭之意义,迫使人物出逃。而《南方巴赫》的出现则让“洞庭”这一终极幻觉失去效力,南方浪潮抑或生活的洪流会剥夺“去”的可能,于是“在路上”成为必然,“驾驶我的车”成为必然中的慰藉与向往。这展现了青年作家认识的变迁,彼时“洞庭”作为意义架设在小说的起始、终结之处,而《南方巴赫》奏响的是意义消散的组曲,重构外部秩序已沦为幻想,下一步则是在消散中寻觅个体内心的安宁。由此不难看出两部小说中暗藏的成长之伏线,小耿的可能是消极抵抗,不断逃离,终致犯罪。小金的可能则是主动反抗,踩下油门的那个瞬间,所表征的不仅仅是逃离的可能,还是成长的可能,在对洞庭的否认中抵达更远的远方。但是逃向何方依然迷茫,雪夜出逃的小金不似林冲,并无梁山可上,只能握紧方向盘,重演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八十年代的未竟之路上,重续八十年代的探索精神。
水波荡漾,南方的故事不绝,八十年代的精神不绝,来自南方的青年写作者还在积极探索南方,从《去洞庭》到《南方巴赫》,其中所奏响的人生变奏正是属于郑小驴的“在路上”。
注释:
[1]顾明栋:《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体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2]张蕾:《“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4—5页。
[3]参见金理:《“在之间”:〈去洞庭〉中的关系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选自《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5]参见黄平:《系统与碎片——以郑小驴〈去洞庭〉为例》,《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
[6]郑小驴:《消失的女儿》,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7]郑小驴:《写作的三个关键词》,选自郑小驴:《你知道的太多了》,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197页。
[8]张蕾:《论“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9][17]郑小驴:《南方巴赫》,《十月》2022年11月号,总第377期。
[10]走走:《非写不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页。
[11]〔美〕罗杰·伊伯特著,殷宴、周博群译:《伟大的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12]〔德〕韩炳哲著,宋娀译:《爱欲之死》,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13]郑小驴:《南方巴赫》创作谈,微信专稿,见https://mp.weixin.qq.com/s/W1GVrl-Gbgd2QM3EQfDZAA.
[14][18] 郑小驴:《去洞庭》,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页、第15页。
[15]〔法〕芭芭拉·卡森著,唐珍译:《乡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16]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选自郑小驴:《蚁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赵晨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840/58/139992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