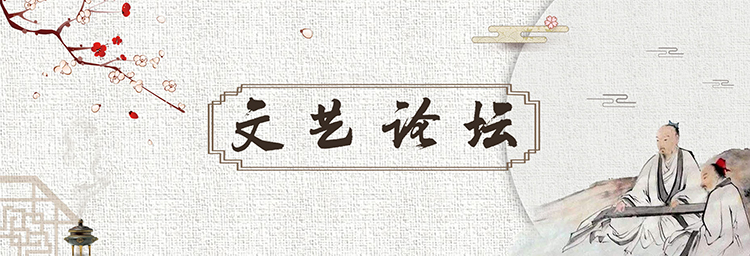

勃兰兑斯的地理批评实践及当代启示
文/杜雪琴
摘 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研究方法与文学观点对世界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文学地理学视为一种科学的批评方法,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革新。第一,以个案研究作为地理批评实践的基础,将文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渗透于对文学规律的探索中。第二,以文学的自然环境作为地理批评实践的对象,认为一种文学形态的构成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以世界文学作为地理批评实践的视野,将西欧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厘清各个国家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将文学地理学作为批评方法进行实践操作,着眼于实证研究,二是各学科因素的融入使文学地理学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三是已经从个案研究转向理论建构以及学科体系建设,为中国文学理论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可以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许多新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文学地理学;传承与革新
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西方资源中,除了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丹纳《艺术哲学》、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等经典著作之外,19世纪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也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著作。此书的作者被誉为“泰纳以后欧洲最大的批评家”。①有学者评价:“他是唯一一个完全认同整个欧洲文化和整个时代精神的评论家。批评家的名字对他而言实在太狭隘,应该称他为‘文化使者’。”②他通过一系列的演讲以及论著,为斯堪的纳维亚作家打开了通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大门,他让外面的世界第一次了解丹麦作家雅各布森,为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铺平走向世界的道路,③他还发掘了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的天才,并向全世界宣布这一重大发现。他的著作中有一种源源不断的新鲜意识、一种哥伦布和十字军战士的精神、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大的创造性。戏剧大师易卜生早就认识到了这本著作的价值:“迥异于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作品”。④这部著作主要概述了19世纪初欧洲国家(法国部分到30年代止,英国、德国部分到20年代和1848年止)的文学发展状况,阐释了浪漫主义的盛衰消长以及现实主义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此著“以科学的批评方法代替了狭隘的传统的价值观”,⑤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是西方最早在文学研究领域系统实践文学地理学理论方法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学者正在从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出发,对斯达尔夫人、丹纳、勃兰兑斯等人的地理批评实践进行知识整合与理论重构,努力建构属于新时代语境下的、具有中国气象的文艺思想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勃兰兑斯的多卷本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本文主要讨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及其对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一、个案研究是其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方式
文学批评首先是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文学研究也首先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这是以勃兰兑斯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批评家及其批评所证明了的。然而,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着重于对个案的研究转向为对宏观文学现象的研究,似乎一切都是可以靠感觉把握的,一切都成了一种理论的形态。勃兰兑斯著作的最大特点,首先就是注重对个案的观照,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既有对文学的理论性建构,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作者总是对作家与作品进行解析与评论,都是一种具体、生动与形象的存在。他对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也同样是如此,并且在此方面做得特别出色。
首先,作者以“流亡文学”作为主线将个案相互串联起来。将《流亡文学》作为第一分册,意义深远。“有理由将《流亡文学》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对于流亡状态的文学家的认同与赞美,以及由此透露出来的对流亡文学的深深的理解,视为整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写作之纲,或者是精神品质。”⑥在卢梭文学思想的启蒙下,众多作家夏多布里昂、维特、勒奈、奥勃曼、诺迪埃、贡斯当、斯达尔夫人、巴朗特等逃离本国,到国外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诸多文学家的流亡、放逐以及旅行几乎成为常态,而他们文学创作正是在“流亡”的生存环境之下进行的。“流亡”首先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同时更具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上的含义,与“越界”“失重”“寻根”“失语”“家庭史”“民族记忆”⑦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流亡”的书写几近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题以及时代的心灵表现。作者指出:“世纪初的法国文学自然受到德国的影响,这尤其是因为各国间这时开始进行持续的思想交流。大动荡、共和国和帝国引起的战事,把欧洲各民族推到一起,使他们互相熟悉起来。而受外国环境影响最深的,是那些由于这些事件遭到流放甚至终生流亡的人。”⑧处于“流亡”环境中的作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及文化视野,即所谓的“双世界视景”,⑨在分离与组合中,容易产生新的生命形态,随之产生出文化的新选择、新组接与新融合,而在这样的关联变动之中,通过接纳、批判、选择、融合文化资源,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在这样的历史性过程中,不同国度的作家相互之间熟悉起来,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因而有了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与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与德国文学、德国文学与挪威文学、挪威文学与俄国文学等不同文化间的影响、交融、碰撞与吸收,并在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环境之中产生新的质素与新的差异。这就是“双世界效应”。⑩
“流亡文学”的渊源来自卢梭,“在十九世纪初,卢梭对欧洲所有主要国家巨大文艺运动影响程度之深是惊人的”⑪。卢梭文学思想影响力的广度,显示出了那个时代欧洲文学与流亡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8世纪时期,法国的圣皮埃、狄德罗和罗伯斯庇尔,德国作家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雅各比、歌德、席勒和让保尔等,都是他的精神传承者。19世纪时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乔治·桑,德国的蒂克,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无一不受到他的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是持久而广泛的,涉及很多国家与民族。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学,包括法国、德国、英国、俄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的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作家之间也在进行着不同文化的较量、冲突与对话。作家与作品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往往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彼此间互通往来、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因此,各国家与各民族的作家与作品之间所产生的关系,则成为极其重要而典型的个案。千差万别的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成为勃兰兑斯文学论著中不可缺少的个案,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个案,其所做的研究或许无法进行下去,并且其本身也许就不存在。而人与地理存在一种因缘关系,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地理基因的生成、传递与迁移等,还有一个作家群体的会合、形成、发展与最后的集散地等,都是他在文学地理学批评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多种多样的文学个案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而作家与作品是最为生动、具体与形象的个案,也是进行相关理论论证不可多得的材料。作者将大量的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作家作品趣闻逸事等材料融会贯通,认为作品中人物亦是作家的自我写照,强调作家、艺术家的“宝贵的个性”。许许多多作家作品就这样成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典型个案,又以“流亡文学”作为主线串联起来,各国家、各民族的个案又集结形成不同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等,如法国的浪漫派、德国的浪漫派、英国的自然主义思潮等,而所谓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与文学流派等,又形成另外一种不同的案例。作者通过大量诸如此类的大小不一的个案研究,将文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渗透于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对文学历程的追溯中,勾勒出19世纪上半叶西欧文学的历史、文化、地理轮廓,正是其宏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视野之体现。
二、以自然环境作为地理批评的主要对象
勃兰兑斯在文学地理学理论中,特别强调自然环境对作家和作品所发生的作用。在《英国的自然主义》(第四分册)中谈论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他认为自然环境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司各特、济慈、穆尔、坎贝尔、兰多、拜伦、雪莱等的生活和创作,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作家和作品,但并不是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评,而是对作家身上的地理要素进行讨论,对作品里所存在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并以此把握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地理因素中,自然地理因素所发生的意义是基础性的,正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制约着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作家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很重要,但没有自然地理的支撑作家就是不存在的,没有自然地理的渗透作品就是另外的样态。因此,勃兰兑斯特别注重自然地理因素的文学意义,这是符合逻辑的,也体现了他的文学地理学基本观念与主要思想。
首先,英国诗人体现着“强烈而真挚的对自然之爱”,⑫他们 “全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⑬华兹华斯“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然’这个名词,描绘了一幅幅英国北部的山川湖泊和乡村居民的图画”。⑭司各特对大自然细致入微地观察,“以致使一个植物学家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关于被描绘地区的植被的正确观念”。⑮济慈以“最敏锐、最广阔和最细腻的感受能力”“看见、听见、感觉、尝到和吸入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灿烂的色彩、歌声、丝一样的质地、水果的香甜和花的芬芳”。⑯穆尔“仿佛生活在大自然一切最珍奇、最美丽的环境之中;他以阳光使我们目荡神迷,以夜莺的歌声使我们如醉如痴,把我们的心灵沉浸在甜美之中”⑰。而拜伦与雪莱的诗歌有着“最强烈的倾向”。⑱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⑲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⑳。大自然的景物及风格总是浸透于作家的血液中而影响其后的文学创作,并且不同环境影响下的创作风格也会有很大差异。在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中,对于卢梭与蒂克的创作风格为什么存在明显的差异,他指出:“卢梭生活在天堂般美丽的风景中间——在日内瓦和勃朗峰附近——直接从感情上受到大自然的熏陶,而蒂克生活在一个无自然可言的地区,便染上了都市人对于森林和山岳的病态的憧憬,这种憧憬便产生了对于自然的幻想。寒冷的亮如白昼的柏林,及其现代的北德意志的理性主义,唤起了对于原始森林的憧憬和一种对于原始森林的诗意的偏爱。”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是西方最早主张文学要回归自然的倡导者,他常在自然美丽的风景包围之中,而这些自然的景观又赋予他思想的方式、想象的方式,有一种返璞归真、复归生命的原始,都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而蒂克生于柏林,柏林在所有的大都市中是最缺少自然美感的,特别是那些砂原上的又高又瘦的松树,他没有见过比这更贫瘠的风景。因此,他认为生活环境的差异也就决定了蒂克的作品只能叙述“森林间的孤寂”“月色皎洁的魔夜”的风景。
勃兰兑斯在肯定自然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也相当重视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英国诗人的自然之爱,是因为骨子里潜藏着一种“英国气质”,来自一个“明显的本源”,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这种“英国气质”首先源于“英国人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其次源于“诗人们对高级动物的喜爱以及他们对一般动物世界的熟悉”,最后源于“一种更深刻民族感情”,且英国作家拥有强烈的“个人的独立性”,这是“纯粹的英国特性的产物”。由此可见,勃兰兑斯所言的“英国气质”,并不是单指自然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同时也包括英国民族的心理、性格、习俗与风尚等。那么,一种文学形态的构成,不能以单一自然环境影响而论,而是整体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文因素如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美学的影响。斯达尔夫人也认为西欧的文化与文学被分割为南方和北方,是受到莱茵河自然流向的影响而成的:“德、法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证明了这一分歧;莱茵河的永久疆界分开了两个文化地区,它们和两个国家一样是互不相干的。”其在《论文学》中开篇即言:“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又言:“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比作家的个人性格留下更多的痕迹。”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谈到希腊人雕塑时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深刻,乡土的痕迹越深刻。”勃兰兑斯与斯达尔夫人、丹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包括了地方宗教与风尚、时间与空间、文本等诸多因素,而形成一个复杂的、精细的且流动的复合体。勃兰兑斯用大量的文学事实进行文本阐释,在世界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深度阐发,从而将斯达尔夫人和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文学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理论上的发现是重要的,但只有选对了研究的对象,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文学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学与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来是文学地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自然环境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是地理批评绕不过去的问题。文学地理学所谓的“地理”,就是“天地之物”,也就是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一切事物,勃兰兑斯虽然还没有提出这样的文学地理学观念,但他对作家身上与作品中的自然地理因素的重视与挖掘,却与此种观念是完全相通的。
(节选自2023年第3期《文艺论坛》杜雪琴的《勃兰兑斯的地理批评实践及当代启示》)
注释:
①①⑤⑧[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前言”第1页、“修订版说明”第4页、第3页、第3页、“引言”第3页、“引言”第2页、第181页。
②Moritzen, Julius. Georg Brandes in life and letters[M].?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rofessor Robert H. Fife.?Newark, N. J. D. S. Colyer, 1922.
③勃兰兑斯从早年对易卜生作品的鼓励和敏锐的批评,一直到这位剧作家生命的尽头,都对易卜生的思想产生显著影响。尽管在1886—1896年十年间,两人之间的联系很少,但勃兰兑斯持续将其新作寄给易卜生,值得重点关注。1886年11月,易卜生写下他对勃兰兑斯在华沙巡回演讲的感想,并感谢他再次寄来最新关于波兰和路德的文章。1888年10月,易卜生再次确认收到勃兰兑斯关于左拉的文章和专著《波兰的印象》;在几天后的附言中,易卜生感谢勃兰兑斯写了一本关于俄罗斯的书,这本书是其系列讲座的部分内容。参见Kaufman, Michael W.Nietzsche, George Brandes, and Ibsen's The Master Builder[J]. Comparative Drama.?1972, Vol.?6, No.3, pp.169-186.
④Kaufman, Michael W. Nietzsche, George Brandes, and Ibsen's The Master Builder[J]. Comparative Drama. 1972, Vol.6,No.3, pp.173.
⑥朱寿桐:《〈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第185页。
⑦张德明:《流浪的缪斯——20世纪流亡文学初探》,《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⑨⑩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第36页、“序言”第1页、第55页。
⑪[丹麦]勃兰兑斯著,高中甫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第411页、第411页、第411页。
⑫[丹麦]勃兰兑斯著,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第1页、第1页、第1页、第1页、第7页、第7页、第7页、第6页、第6页、第7页、第9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36页、“引言”第1页、第414页。
⑬[丹麦]勃兰兑斯著,刘半九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第127页。
⑭[法]斯达尔夫人著,徐继曾译:《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第152页。
⑮[法]丹纳著,傅雷译,傅敏编:《艺术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⑯据相关资料,鲁迅于1926年7月5日购得东京新潮社出版的《文豪评传丛书》,其一为勃兰兑斯撰写的评传《亨利·易卜生》,写有1867年、1882年、1898年三次印象。1933年8月19日、9月21日、10月7日,又分别购进当年东京春秋社出版的《春秋文库》第3部之一: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2、4、6册,即《移民文学》、《德国浪漫派》、《英国的自然主义》和《青年德意志》。1939年,鲁迅购读了新出版的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流》日译本的1、2、4、6册,同年12月20日致信徐懋庸特意推荐该书。参见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鲁迅藏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0~123页)。
⑰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鲁迅藏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0页。
⑱鲁迅:《由聋而哑》,摘自《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⑲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购买了勃兰兑斯《亨利·易卜生》,书内附易卜生1889—1890年间给“他的老友G.Brandes”的12封信。这对于鲁迅的启发意义巨大。参见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选自《鲁迅藏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8页。
⑳郑振铎:《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4期。
21胡适:《“证”与“据”之别》,选自《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2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48页、第367~413页。
23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24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25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全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9页。
26曾大兴:《从实证研究到学科建设——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某些经历和体会》,《人文集刊》2015年第2期,第81页。
27刘斯奋:《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文艺报》2004年9月16日第4版。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勃兰兑斯与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项目编号:20D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杜雪琴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55/99/132366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