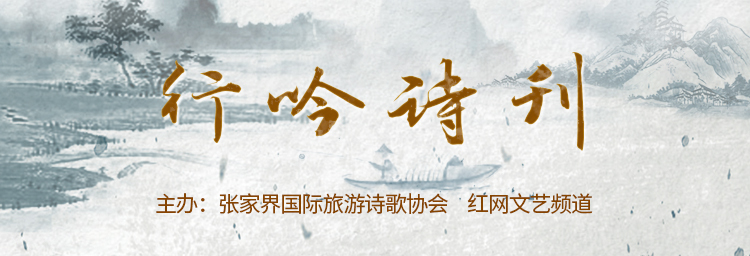

地域诗歌里的共享幻象及其精神生态
——阐析张家界诗群的艺术特色
文/卢辉
相关附件:行吟诗刊丨张家界旅游诗群诗歌
读张家界诗群的作品,我一下子又被带回梦幻壮美的张家界:奇峻高拔的武陵源,美轮美奂的宝峰湖,大气磅礴的天门山......它们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自然遗存与精神家园。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家界,走进张家界诗群,走进这一片心灵归属地。
一、自然风物与共享幻象
在我看来,张家界诗群所呈现的,大多是对张家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缘情。欧阳斌写给张家界的系列短诗、刘晓平的《过赶年的张家界》、阳春的《张家界纪行》、吕传友《吊脚楼上的梦》、胡小白的《在南滩,找属于我的位置》等,这些作品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对张家界的偏爱:“我们往山上走,还有一声不吭的影子/为可能长满阳光的地方,为数不多的执念//无论延迟/或踌躇/南滩就在那儿/必须像玫瑰长刺一样,富有耐性/去经过一片湖泊(我愿这样命名狭窄水域,无根的水)/四处游荡的小路/还有因等得太久,牛群湿漉漉的眼睛”(胡小白《在南滩,找属于我的位置》)。按理,久居仙境张家界的诗人们,理应得到自然界最完美的包裹。不过,像胡小白这样的诗人并没有因为久居而溺于其中,而是在一次次的“出圈”中赋予自然界全新的形象。或许,张家界的诗人们早已知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理。于是,他们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总以为/一定有一道门/隔着天与地/隔着人与仙/隔着你与我//近了,才知道/天门,无门”(欧阳斌《天门山》)说真的,地域诗要写好不易。因为,特征性的景点,仅靠一二次游历哪怕多次游历都很难“积淀”成有内涵的地域诗。因为“应景”的地域诗一旦局限于视觉快感,就可能导致它只有“像”或“不像”的功能性。为此,好在地域诗,没有一味地在“像”或“不像”之间纠缠,而是将景点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糅合在一起,不仅仅作为游历的视觉意象,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人文异象与自然现场互为交错的文化品相。即,不是景点的图景式重现,而是景点在瞬间呈现与经验表达之间的博弈:“张家界的石峰,挺立/在空间、时间和想象里/相互间从不模仿,彼此间弥补不足/就像我可亲可敬的张家界姐妹/每一种形象都是一种人生的方式/经年经月经日,成为历史和风景”(刘晓平《过赶年的张家界》)是的,正如刘晓平的《过赶年的张家界》,他需要对应景的那部分——自然的也罢、人文的也好有一种特殊的认识。即善于把应景的那部分“打入”异质的环境中,启开另一个隐秘世界,避开地域诗的伪抒情,将自己的一次次精神探险侵入其中,并与当下进行合理的互换、摩擦、融通、渗透,由此产生精神历炼和精神探险之后的主观景致与精神空间。
在我的印象里,不管是古典与现代的地域诗大多重在可读、可视、可思。因为,只有可读,才能入心,只有可视,才能入眼,只有可思,才能入脑。这“三可”的融通,读者才有进入其中的可能。这种可能,不单单是立此存照的具象,而是上升到时空、影像、心象的三维透视,即时到、影到、心到,有了这样的三维立面才能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获其物:“我在缆绳的终点登上绝顶/九百九十九级石阶如天幕般垂下/再远些,群山被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束成朝拜的姿态。这一臣服,就是几千万年//众生只会惊叹你峭壁忽然洞开,玄朗如门/或仰头观止,或俯身咏赞,或驾机穿越/只有我懂得,那是你聚集天地智慧、学富万年的/脑洞大开”(阳春《天门山》)。是的,像阳春这样的地域诗,衷情于心与物产生奇异关联与连锁反应,衷情于幽微而深远的语境,形成自己心理意义上的一道若即若离的“距离”风景。那么, 好的地域诗,为何不会沦入应景的窠臼,其最大的妙处,无论是它可见的空间,可听的时间,还是它可触的生命,可感的经验,都能把精神与生命的影调作为文字编码与灵魂密码嵌入诗篇中,使地域诗总有一种如影随形的神秘感、时空感和历史感,构成了诗歌别样的世界:“刚刚诞生的风/正好穿过/昨天的裤腿/吊脚楼上挂着一片云/山寨的人/今天能看见/寨外的人/明天也能看见”(吕传友《吊脚楼上的梦》)的确,吕传友的《吊脚楼上的梦》在他睹物的情结里有一种断代感和现世情结里的无力感。然而,诗人并非只是一味地沉湎,而是将昨天与今天,乃至未来的混搭情结归于本土情结。可以说,张家界的诗人们,一直仰仗着这份本土情结,给予生与斯长与斯的张家界以魔术般的力量。这种力量采用的就是“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办法,把新颖、清新的感觉与亲切、常见的事物,把不寻常的感情状态与具备亲和力的逻辑条理,把毫不懈怠的判断力、稳重的自持与本土情结协调起来,共同组合成缤纷的共享幻象与精神世界。
二、自然幻象与现实再造
读张家界诗群的作品,我们一定会被他们优越的组织幻象的能力所折服。尽管他们在自然与现实的层面,没有急于去开辟繁富复杂的自然与现实组合而成的“第二奇观”。然而,他们的幻象从来不受张家界的空间所限制。恰恰相反,由于他们的奇妙幻象与本土情结存在着相互吸引、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美妙的平衡点。比如小北的《九人堆记》、袁碧蓉的《九十二个太阳》、全迎春的《南滩之夜》、吴远山的《雕刻自己》、潇雪溟枫的《狗子滩》等,这些与张家界看似缘定而又独具特色的自然风物一直在荡涤着我们的心灵。这些诗人总是力图通过奇妙幻象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事件、形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仍然像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所见的那样,与我们的整个感觉领域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联系:“世界上最好的匠岩,是永顺的修世界上最大的吊脚楼/一百个石礅/是一百个木头站立的地方/醉了酒的邓土王,数一百个石礅,只数到九十九/派家兵追杀,九个匠岩葬于此”(小北《九人堆记》)是的,要想还原好“九个岩匠”,那怕是幻象都必须是真挚的,必须微妙到每读一次都会使人有以种如临其境的感受。凡是真挚的诗,不管它是在梦幻般时刻写出来的小曲,还是源于人们所梦想的伟大诗篇,不管是哪一种,都必须具备完美与微妙,就这点而言,小北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在这里,我注意到,像小北这样完美与微妙的表述,在张家界诗群的作品里还有很多。不错,在他们注重幻想的同时,现实也作为幻想的附着物而存于他们的内心。这是因为张家界的诗人们把诗看作是一种联合的东西,而不是分立的东西。就算见到的是微乎其微的水过“石墩”,也是一次精神的礼遇或文化的溯源。的确,当一个人与永恒的境界交流,想用见微知著的方式,却又无法判断自己能否通过这个途径达到永恒境界的时候,内心总是忐忑的。因此,对自然界的倾诉过程,就是不断消解忐忑的过程。因为,此时重要的是诗人自身所获得释放的过程,感受到可能被倾听的惊奇程度:“当我在日记本上连续画下/九十二个太阳时/我把本子和笔都扔进了湘江里/沿着湘江一直走/曾经江水浩荡的铜官江滩/成了一座由太阳和风挖掘的墓场/我到达未曾到达之地/在一只失去船头的渔船上坐了很久/在一条嘴巴高撅的鳜鱼边蹲了很久/是否应庆幸/那些年挖沙时,留下的/一个个深坑,留住了一滩滩江水”(袁碧蓉《九十二个太阳》)。的确,当袁碧蓉《九十二个太阳》)是在倾听大自然的状态下而发力的。在这里,被她加以客观化的九十二个太阳不只是她个人的敏锐观察与细心倾听,还有赖于她的生存经验与精神折射。由此可见,袁碧蓉既然属于熟悉湘江的人,她肯定对人间的感情经验特别敏感。于是,她特意安排了“九十二个太阳”,与人类的精神相遇,就像她肯定要与前世今生来年相遇一样。
记得,雪莱曾把想象看作是一种“看不见的影响”,并且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出自内心的力量。按这样的观点,张家界诗群的诗人们就是充分运用想象——看不见的影响,把他们一系列无意识的思想放射出来。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处在“看不见”的地带,就不再依赖于自己的知识和技巧上的熟练,而是受某种强烈情绪的支配,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引导,尤其是对共享幻象情有独钟:“提得多了/你的名字肥沃起来/星星开始发芽/想象开始抽穗儿//草/背着我的双脚/随风奔跑”(全迎春的《南滩之夜》)是呀!名字肥沃、星星发芽、想象抽穗......若按柏拉图的说法:人的天赋是靠想象状态得来的,也就是说,想象状态是诸神的一种赏赐。就这一点而言,全迎春似乎深得诸神的青睐。的确,张家界诗群告诉我们:想象的存在不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依个人的独特性而进行的心理上的再造映象。因为,想象从原来知觉的实际内容中仅仅选取那些与人当时心境有关的材料,因而,想象总带有主观色彩:“拒绝汉白玉,拒绝大理石,拒绝/纯水晶,去大山溪,捡块小小的/朴素的石头。拒绝雕刀,/拒绝彩釉,拒绝精致的盒子/斧头,凿子,木棒都行/总之,在故乡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雕刻”(吴远山《雕刻自己》)是的,正是想象,使吴远山《雕刻自己》的主观色彩特别浓郁。在这里,词与词、语句与语句的联结,都是以想象为构成法则的。诗人始终沉浸在“雕刻自己”的主观想象之中:经验与超验、印象与幻想、景物与心境,融入到诗行独特的音调、节奏与结构之中,使故乡所见与人类经验存在于共享幻象之中并相互关联。的确,张家界诗群的很多作品以共享幻象为根基,不断把自己的过去投向未来,超时空,超生死,化瞬间为永恒:“狗子滩全白了/它放开了一整片芦花/风一片片的甩过来/石头也白了/一具孤零零的肉体穿过/山河晚照/从头到脚的芦花/让我苍老了三十岁”(潇雪溟枫的《狗子滩》)实际上,可以这样说,这一系列的“超越”,都是在狗子滩上进行的。这些泛白的看似自然的现象却非同一般:这一现象既属于人的时间现象,又属于超时间的人间仙境。在这里,芦花的白不是原有意义上的白日梦,而是新的时间建构,是时间的投射,一个有意味世界的诞生。
三、心灵归属与精神生态
从寻找心灵的归属地到共享幻象的演绎,归根到底,张家界诗群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张家界诗群由异质写作与本土文化共同组合成的共享幻象向我们呈现的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精神生态,而且是人类心灵的价值以及超越时空的永恒精神。刘年的《蚯蚓歌》、陈颉的《狗尾草》、王馨梓的《窗口》、典铁的《错误的意义就在于反复被尝试吗》、陈叶锋的《期盼又一个金色的黎明》、胡良秀《我所能说的》、江左融的《苦瓜》等作品一再向我们呈现出:人是有限的时间性的存在,只要自己在时间中操劳,才能把自己从暂时性的时间中解脱出来。正是在共享幻象的支配下,张家界的诗人们满怀着奔涌的冲动和充沛的力量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让读者与诗人一道当了一回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间人:“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软下来/我愿你是一条蚯蚓/如果一定要把长江比成什么/它像一条蚯蚓,断成那么多节,依然活着//水里,蚯蚓在挣扎扭动/都以为它在跳舞,没有一条鱼相信/它体内有个钢质的问号”(刘年《蚯蚓歌》)众所周知,刘年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然界有形或无形的心灵撞击,他的诗就受益于自然的启迪,他善于将神秘而又灵动的自然物象拉回到人的身边,把自然物象和人类经验组合在一起,给它们一种稳定的结构。说到刘年所衷情的“自然”,那些和我们相遇的事物,有时并不处于我们想象到的时间和空间里,或者说,即使它现在或过去具有一种特定的位置,却因为时过境迁,只在那个位置上若即若离。因而,像刘年这样的诗人懂得将时过境迁的许多事物重新“拉”回来,直接诉诸于感情、意愿和目的,他的《蚯蚓歌》就有这样的特点,让平平常常的蚯蚓因为与长江关联在一起,平添了几分灵气与境界,其格局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自然,究竟是先得其“形”后获其“意”,还是先有“意”而变其“形”?请看陈颉的《狗尾草》:“放慢风的节奏,狗尾草/一举擎天的柔软姿态/是不是自然界的合理安排/或者是某种预约//风中的昭示,可以很快就会散尽/可我还是想留下/找寻她细小坚韧的花蕊”。很显然,由于“意”在先,狗尾巴草之“形”已被异化,陈颉取后者而为之。这样看来,面对自然,诗人有二种姿态:归于自然,归于其道,是一种;源于自然,超于自然,又是一种。陈颉抓住了后者,赋予自然以“人格化”:“六月,整个山坡摇头晃脑/漫山遍野向我涌来”。的确,狗尾巴草显然是为了后一种“源于自然、超于自然”而准备的。不难看出,王馨梓的《窗口》则善于把人类在自然界所遭遇到的情感波动通过“窗口”呈现出来:“明天就要离开/这扇窗/去往广阔的天地。//两棵桂花、三棵玉兰、五棵香樟/一棵柚子、红枫,喜鹊、画眉、麻雀/将衍生成,整座森林”。透过窗口,使自然客体与人间社会有了一个亲和力的关联,让我们感觉到自然风貌与人类精神有着不一般的因缘关系。可以说,人的生命极易被大自然无穷的生命力所牵引、所影响,极易被大自然引入到一股潜流之中。这时,诗人肯定不能无所作为。那么,面对自然,既有人定胜天,也有敬畏自然。这复杂的两面,给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空间。请看典铁的《错误的意义就在于反复被尝试吗》:“写完诗后的空无感类似于夜禽/抓住深夜某节树枝而其声飘忽,又似飘渺。//细雨下的庭院随父辈撤走之后涌现的围栏/常迫使我返回的被芭蕉浓影遮掩窗下。//时辰隔着灯光渐渐生成词句间的玻璃。/清冷与困惑充盈着逶迤而来幽蓝色的溪谷。//但沉思总能带来几次折断枯枝的声响。/一只猫头鹰由刚刚踏空的部分猛然扑入这纸中。”在自然与现实之间,这首诗所呈现的是:抓住枝节后的飘忽、被芭蕉浓影遮掩的窗下、幽蓝色的溪谷、几次折断枯枝的声响、猫头鹰猛然扑入纸中......这一切看似幻象又不是幻象,正是在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前提之下,现实才多了一个像纸一样源于自然又超于自然的存在物。
桑塔雅纳说得好:“看得见的景象还不是诗歌真正的客体”。为此,陈叶锋的《期盼又一个金色的黎明》写出了关于自然与人类的诗歌,他的诗不时呈现出与自然界丝丝入扣的心象:“没有月亮的夜晚/即使月亮岛上/美丽的花/也是看不见的/只有漆黑的魅影/迎合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点亮平静如水的心境”,相信这种平静如水的心境是人人都会喜欢的。在当下,作为诗人的“我”一旦被置入繁富、驳杂的大千世界,怎样才能从常规通向高处而不至于沦入琐碎,这就考量着诗人如何在智性与良知的驱动下,在现实尺度、生态指涉与心灵图景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的确,诗人的心灵有时真像是一个储藏器,收藏着无数感觉、经验、现象、即景、词句、意象......如此众多的集成,重新融合成新的东西。以江左融的《苦瓜》为例:“无数条茎蔓四下扬臂、潜行/柔嫩的卷须在风中伸张触手/尽力攀扯、拉拢、吸附一切可能/只为挤进一隅/安身、立命”。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江左融对苦瓜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动的“浮现”张力,仿佛与语言自身“承载量”的那种张力有所不同,她很善于打开遮蔽在大棚底下不易显形的苦瓜那种“图景张力”,我把这个图景张力当成是诗人自己独有的“精神道场”。在《苦瓜》一诗中,“无数条茎蔓四下扬臂、潜行/柔嫩的卷须在风中伸张触手。”那么,为何苦瓜“只为挤进一隅/安身、立命”会有那么大的图景张力呢?那是因为“这些生的艰辛,苦的养成”所带来的图景张力不正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相容、相生、相对的临界点上的折射效应吗?这样的图景张力所呈现出的不正是独具个性的精神之光吗?的确,一首好诗,总会包裹着一个隐性的精神生态,总会不时地展开人类的精神图景。
其实,人类的精神图景与人的独特心境息息相关。的确,一首诗要将精神图景化为独特心境并非易事,尤其是这个“实体”的构成既要让人充满好奇心与期待感,又要让人觉得它符合人们的情感温度和理想秩序,尤其是这个实体要符合普世情怀。古今中外,脍炙人口的图景张力诗不再少数:有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海明威的“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了/太阳每天升起/大地永远存在”;有泰戈尔的“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的心已经飞过”等等。这些图景张力的诗句,着实让读者在那种匀称、松弛的时空转换中接受到一种“被洗涤”的惊觉感。由此可见,“图景张力”诗的神性不是语言“造”出来的,它不仅有自然生态的秘境,还有灵犀“内挂”的一盏灯;不仅有万象的因果,还有生命的轮回。
四、自然之道与诗意自然
自然之“道”(规律)与自然之“数”(秩序)在我看来都可称之为诗意的同义语。而“道”生万物与“数”显神性,则是自然之道与诗意自然的绝佳配置。当你读了张家界诗群的作品,你就会自然而然萌生出古往今来,为何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哲人与诗人总能联袂打造出真、善、美的最准确的等价物:道与数。即自然之“道”(规律)与自然之“数”(秩序)。为何像古代深刻的思想家老子或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都能在自然之“道”(规律)与自然之“数”(秩序)中看到了万物的本质。或如老子所云:夫物芸芸,各归其根;或如圣经所说:造物主正是借助于重量、度量和数量,从混沌中创造了大自然。为此,站在自然的“道与数”的节点上,我把李宗群的《冬至》、赵斯华的《开端》、曾小山的《苹果》引了出来。
自然的哲学,不在于对自然发现了多少,而在于人与自然彼此“会意”了多少。在李宗群的《冬至》里,诗意的自然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的:“金色的太阳照在世上/这个城市,有些脱水//屋子里桌子,椅子,床/杯子和饭碗都有寒症/它们齐声咳//它们都是我的骨肉/它们爱我,并爱上了我的咳嗽”。写冬至,恐怕很少人会这样以“咳嗽”入诗,偏偏李宗群剑走偏锋,在这个冷热交接的节令,他以“咳嗽”包揽万物,创造出该诗的“奇巧”之功。是的,因为任何成熟的思想都是以自然与现实为“托”而成立的,诗歌相当大的作用,能激发人们感知自然的存在,使处于道与数结构中心的自然客体能与诗人在相遇中被彼此会意,彼此照亮。的确,世间万物,与我们相遇的人和事,大多直接诉诸人的想象、感情、意愿和目的之中,并与人们的思想进行短暂的对接,以赵斯华的《开端》为例:“在羊水里开始觉醒/通过一节小小脐带/透过子宫,外面有一个大大的世界/然而,还太小/只知这是人生梦的起点”。如果说,“在羊水里开始觉醒”的话,那么,赵斯华正是利用这一“觉醒法”,把人的生命以“透过子宫”的方式呈现出来。从本源上说,当生命出现时,生命的记号早已存在。那么,遵循生命的“道与数”,生命都具有一种特殊的“说话”性质,一种令人惊奇的特征:这种特征总是力图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事件、形象、有生命的都仍然像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所见的一样,与我们的整个感觉领域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联系,曾小山的《苹果》也有这样的特点:“清晨,只有一颗被咬过的苹果,/浑身湿透,坐在那,空洞地望着我/伤口周围,安静地渗着细小的血液/我可以作证,她刚刚才接受洗礼,/它还是纯洁的,但是我拒绝出庭”。不难发现,曾小山的心目中的苹果,就在他极力建造的自然之“道与数”中,诗人就是想把自然的“道与数”变成一种独特心情的实体,这种心情与构成我们日常内心感情生活的那种偶然的、变化不定的心情是明显不同的。可以说,人们日常所用的语言仍是杂乱无章的,而曾小山的语言,善于从日常那个杂乱无章的混合体中吸取精华,创造出一种自然的理想秩序:“带着温度,皮肤还有弹性,一动不动/一个模糊的形状反复地在眼前旋转/直到被风扇吹散,在空气中发酵出/上一季鲜果的味道,是小虫们喜欢的”不是吗?在这微风中,苹果的律动毫不间断地贯穿始终,诗意关系始终符合于和声关系,苹果的“气息”便是一个“美”的现象。为此,在曾小山应看来,所谓的自然“美”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和谐的、合成的延续体。
由此可见,“诗意的自然”深藏于自然的“道与数”之中。按莱维斯的定义,诗就是“自然之道”。当然,这种“道”并不一定是视觉意象,这种创造出来的“道”的外观并不一定要与真实的事物、事实、人物或经验的外观等同或对应,它在标准的状态下是一种纯粹的幻象或一种十足的虚构事物,这样一种自然事物的“道与数”便是一种精神生态,便是自然之道的精神图景与自然法则。为此,不管是诗意自然,还是自然之道,它们构成材料都是自然与语言。这种语言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结构和一定形状的虚象,是一种再现了某种新的人生经验的虚象。借助这个虚象构成成分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借助于这些成分之间的平衡和非平衡,就产生出一种有机性的幻觉,也就是“生命形式”的幻觉,这也是张家界一批有着探索意识的诗人们追求的目标。
总之,这一辑张家界诗群展示,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因为,张家界这次展示的诗歌,没有停留在自然风物描述性的视觉意象,没有把卡口放在“像不像”的功能上。
这些作品好就好在没有一味地在自然风物的“像”与“不像”之间纠缠,而是将地域诗的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时代属性糅合在一起,并把地理与风物不仅仅作为状物取样的视觉意象,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造化异象与心理事件互为交错的诗歌地理。从上述诗歌的评赏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张家界诗群为中介的“诗歌地理”讲究的是诗歌地缘,而不是简单的地理标签。说到底,缘,就是一种关系: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它融渗了地缘、人缘、文缘、血缘。可以说,以张家界诗群为中介的“诗歌地理”融合了上述的“四缘”的关系,形成了诗歌地理所具备自然素养、历史品相与时代气息,这也正是张家界诗群的价值所在。

卢辉,高级编辑,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三明学院特聘教授。作品散见《文艺报》《光明日报》《文艺争鸣》《长江丛刊》《诗刊》《十月》等,为国内多家重点杂志、网站特约评论员。主要著作《卢辉诗选》《诗歌的见证与辩解》《看得见的宽》《七层纱》《红色的碎片》《纸上的月亮》《惠水长流》等七部,有大量文学作品分获福建省政府文艺百花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榜、第三届“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第五届(2017-2018)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现代青年》年度十佳诗人、第三届中国天津诗歌奖、第三届杜牧诗歌奖、中国(海宁)徐志摩微诗歌奖,入围第六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终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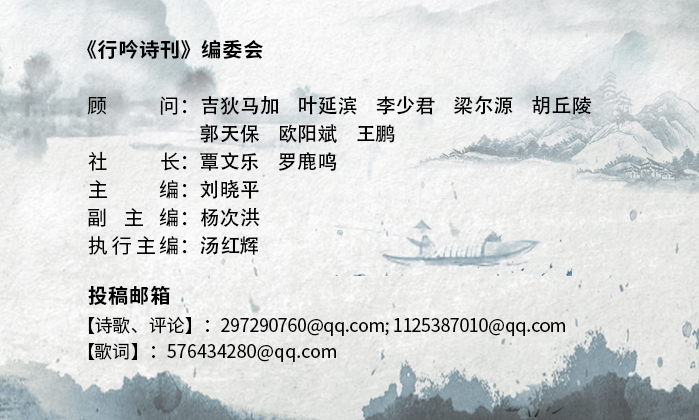
来源:红网
作者:卢辉
编辑:施文
本站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链接。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54/51/131660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