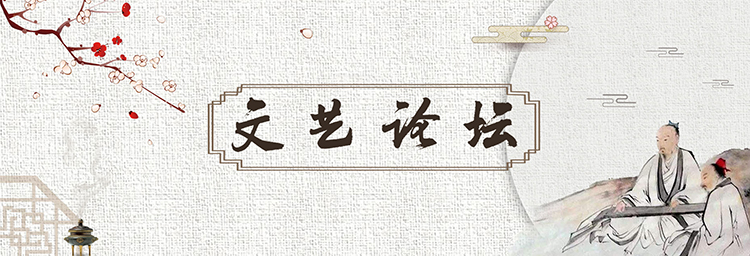

新社会主义文艺的兴起及其待解问题
——以电视剧《功勋》为例
文/张均
摘 要:以电视剧《功勋》等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文艺”的兴起,是近年文艺创作领域引人瞩目的现象。它对传统社会主义文艺的修复与提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于打破以“整体现实”(民族/国家)为逻辑依据的叙事惯例,转而全力以赴地将“整体现实”深深嵌入“人”的情感与利益之中,从而使民族/国家从“人”的“情理”内部自然地生成、结晶,二在于创造性地跳出自由主义视界,重新阐释了作为“必要的善”的国家的内涵。不过,其重建历史连续性过程中去自由主义与去阶级化的双重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耗损了此种文艺回应历史与现实的能力。当代文艺创作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及解决力度。
关键词:《功勋》;社会主义文艺;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却也是研究障碍最多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在新启蒙运动以“文化胜利者”身份主导的历史改写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义文艺(1949—1976)沦为难以被“看见”的他者。如果说这个世界“存在着多重现实,每一个群体都有它可以声称是‘真实的’世界观”{1},那么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呈现的“现实”则遭到拒绝,其合法身份、资源价值一度变得可疑、模糊。但最近十余年来,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因素再度浮现,并从“霸道总攻和他们的精致受兽”之间“资产阶级公子的文化表演方式”{2}中溃围而出,构成了颇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电视剧《大江大河》(1-2部)《山海情》《功勋》《觉醒年代》等即为代表。它们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文艺的复活,而是当前影视创作对之激活、吸纳与转换的结果,可名之为“新社会主义文艺”。那么,新社会主义文艺怎样吸收并重建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又面对着怎样的有待解决的难题呢?对此,可以电视剧《功勋》(郑晓龙,2021)为例试作分析。
一、“人”的再度启动
一般而言,歌颂英雄的主旋律影视难有收视率的保证。但2021年5月22日民众在雨中夹道送别袁隆平先生的动人情景表明,即便在文化生产全面陷入“资本的囚笼”的今天,民众也未完全被收编。正因此,《功勋》才得以进入大众视野。《功勋》形式新颖,由八个单元剧串联而成。其取材皆来自现实中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于敏、申纪兰、屠呦呦、袁隆平等),其中不少人享有崇高声望。但这种取材有如双刃剑,既赋予了《功勋》在题材上的重量,也使之面对观众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的压力。
其实,讲述“新英雄人物”故事并以之映射时代与国家的成长,是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孜孜以求之事。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电影《董存瑞》《英雄儿女》《小兵张嘎》《上甘岭》《红色娘子军》等皆用力于此,其中既产生了难以重现的人物经典(“重写文学史”论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亦因一体化制约而多有流弊。“弊”在何处?主要表现为国家作为“整体现实”对于“人”的压制与遮蔽。对此,1957年钱谷融即已明确指出:
文艺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但)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这样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整体现实”,他之所以要描写人,不过是为了达到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目的,完成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任务罢了。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人呢?{3}
对于“整体现实”与“人”之关系,能力不俗的作家自能处理妥当,然而更多作者却坠入其中,把“人”(英雄)写成了“整体现实”的木偶,有本质而少个性,进而造成了此种传统在1980年代的溃败。
不过,《功勋》却未蹈此覆辙,它更像是为不满于“资产阶级公子”故事的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可以有和应该有的样子。其八个单元剧的完成度都比较高,尤其《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广受好评,力压同期上演的同题材电影《长津湖》。不过,这其间重要的并非主旋律对商业大片的胜利,而是它可能的文艺史意义——它标志着新近文艺不但顽强地将“整体现实”重新拉回到文艺之中,而且有意识地避开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以“整体现实”(民族/国家)为逻辑依据的叙事惯例,转而全力以赴地要将“整体现实”深深地钉进“人”的情感与利益之中,要让民族/国家从“人”的内部自然地生成、结晶。对此工作,传统社会主义文艺缺乏足够的敏感,但《功勋》却汲取教训,对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予以修复、提升、完善,最终形成了“人”的再度启动。这种再启动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不以“整体现实”为叙述逻辑,而寻求以“人”的逻辑叙述“整体现实”。依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的意见,“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情理”若得,则“人”的逻辑基本确立。从《功勋》所叙抗美援朝、研究杂交稻、基层扶贫等家国大事看,它们都被建立在“情理”二字之上。比如,在《默默无闻张福清》单元中,曾经的战斗英雄、来凤县建设银行退休老干部张福清从未对人(包括家人)提及自己的英雄过往,一生都在基层工作,建水渠、修水坝、筑工路,不但自己辛苦艰劳,也拖累了家人的生活与工作(其女儿因耽误治疗而终生不能自理)。按照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写法,将其“成长”直接写成受党感召、大公无私即可(如《创业史》之梁生宝),但编创人员显然觉得如此处理难以构成深层情理。毕竟,“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4},无私、高尚总是稀见的德行,张福清高尚之举的背后应有更深层的人性根据。对此,剧中受到野战军嘉奖的排长张福清说:“我向烈士们发誓,我要做他们没有做完的难事,打他们没有打完的硬仗!”他后来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是在兑现誓言。《功勋》如此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永丰战役中,张福清所在6连共计120人参战,牺牲113人。2019年,老英雄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感到悲伤、悲痛。虽然我完成了任务,但牺牲了不少战士。在永丰战役中,跟我一起突击的还有两个战士,我们一起是 3 人突击组,永丰解放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从此以后,我找也找不到,再也没见过。党和组织给了我最高荣誉,但常常想到这些和我并肩作战的同志,有很多已经牺牲、不在人世了(讲述者泪流满面)。{5}
这种独特心理在医学临床领域被称为“幸存者的内疚感”(the guilt of the survivor),即“遭遇创伤事件后与自己有某种关系的人不幸死亡或受伤,而自己幸运地逃过一劫,个体坚持认为自己对他人的死伤负有责任,内心充满了痛苦的内疚情绪。”{6}因此,内疚,张富清隐瞒功绩,而以最基层干部身份将一生奉献给了偏僻山区。《孙家栋的天路》中发射场工程队队长、“独臂英雄”李东海扎根于荒凉之地的理由与此类似,也在于“为死了的人争口气,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如此对生活的细心发掘,使《功勋》中的民族/国家不再外在于人,而成为个人情理的自然的“果实”。《袁隆平的梦》单元也有此种“整体现实”与“人”的关系的重置。袁隆平原本研究红薯并小有成绩,但他为什么又转向杂交稻研究呢?电视剧专门设置了一个小故事,即袁隆平初到农村、房东临死前都没能吃上一碗白米饭。此事对袁隆平刺激甚大,并直接构成他的梦的来源。这种将家国之梦深深扎根在普通可亲的人性之中的叙事处理十分可信,可以说是补齐了传统社会主义文艺的“短板”。
甚至,为了夯实“人”的情理,《功勋》还大胆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文艺裹足而不敢前的题材:逃兵。《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开篇即处理逃兵问题。志愿军战士小安东之所以要当逃兵,当然是因为怕死,但小安东又自称“不是怕死”,这其间是否存在更深层的情理?导演抽丝剥茧,步步深入他的内心:原来他担心自己牺牲了,无以报答用羊奶救活了他、把他养大的二妞,“我的命是二妞给的,我的姓也是二妞给的,我为她做什么都值”。在剧中,指导员李延年给七连战士讲了小安东与二妞相依为命的故事,然后问全连战士:“大家说说,二妞这个姑娘好不好?”得到所有战士一致的响彻山谷的回答:“好!”这样饱满、扎实的人性,使逃兵小安东也成为一个可亲、让我们内心深深触动的“人”。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曾说:“电影艺术的全新表现方法所描绘的不再仅仅是海上的飓风或火山的爆发,而有可能是从人的眼角慢慢流出的一滴寂寞的眼泪。”{7}剧中小安东流下了眼泪,七连战士们也流下了眼泪,新社会主义文艺以此更深刻地成为“人的文学”。
(二)《功勋》人性逻辑的发掘,不仅以“人”的情理为据,还将之设定为叙事终点。在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中,英雄成长最终都以个人汇入国家、以国家形象的完成为终点。《功勋》改此惯例:战斗胜利、杂交稻研究成功、青蒿素提炼成功,但这些成功不仅是“整体现实”的完成,更是“人”的圆满的达成,且后者才真正居于故事与意义的终点。在李延年单元中,经过教育的小安东重上战场,但战友们都不愿他到危险的位置战斗,都希望他能存活下来与二妞过上幸福的生活。战斗到最后一刻,指导员却命令小安东回营部报告,明显是要给他生存机会。这是中国革命最闪光的人性。结尾时,不仅战争取得胜利,而且小安东也重返家乡,与二妞结婚并生了一堆以牺牲的战友命名的孩子。在此,中国人灵魂最深处的“家”构成了革命的归宿。在申纪兰单元中,新婚的申纪兰未及见上丈夫一面,丈夫即随部队出发了。此后申纪兰学接生,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但渴望完整的家,始终是她内心充满牵挂、不安与期待的一份情愫。在此单元结尾,她的“劳动才能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的女性权利斗争获得了国家承认,她也与从未谋面的丈夫意外相逢,有了一个圆满的与国家共成长的家。
以上两层设置,将“情理”贯穿于叙事始终,可谓对传统社会主义文艺迟到的“补课”。当然,这并非说后者对此缺乏探索,而是说其“始于人”比较局狭(主要限于物质生存欲求)、缺乏对更广泛的人的“热情”的探究,“终于人”则颇为少见。这是莫大遗憾。其实中国革命原本即是事关“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现实实践,经过“补课”的《功勋》呈现的正是革命本色。朱光潜曾言:“文学作品之成为文学作品,在能写出具体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8}《功勋》无疑因情理之深入而有了“深刻的情致”。
二、何为“国家”
以《功勋》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文艺,之所以呈现出社会主义文艺的理想样子,还因为它逆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主流而动,重新阐释了“国家”的丰富内涵,成功还原了久被遮蔽的国家与人的真实关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国家而言,强势中央政府一直是民众生活安宁、国家强盛的基本前提。新中国的成立更是如此。它的存在,远不止于所谓“必要的恶”,同时更是“必要的善”:正因为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利(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受到国内豪强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威胁,中国共产党才动员民众奋起反抗并谋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借此推进国家工业化,作为全体国民共同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对此复杂历史面相,需要冷静、深入的把握。然而改革开放时代的知识界往往拒绝以历史化态度深入其中,而更倾向于将新自由主义国家观当作抽象共识,并以此裁断历史。与此相关,改革开放时代文学也多从自由主义入手,着力呈现个人在国家压力之下的无助、破碎以及孤立、怀疑的情绪。以《功勋》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文艺是对此种国家阐释的有力“纠偏”。
仍是在李延年单元中,指导员李延年面对逃兵的动员工作,以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不曾有过的深度,也在自由主义目力不及之处,深入阐发了国家与个人的共生关系。剧中小安东临阵脱逃,理由直接、有力:若不能活着回来,他就永远无法兑现对救命恩人二妞的承诺。这的确是国家与个人关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往往回避(其中英雄似乎意识不到死亡将毁灭一切的残酷事实),而改革开放时代文学则往往以此轻率否定国家、伸张个人权利。《能文能武李延年》不循旧例,迎难而上。在剧中,李延年并未像连长那样批评小安东“贪生怕死”,而是向全连战士讲述了只有他和八班长才了解的小安东与二妞之间的动人感情。当然,其讲述若到此为止就只能是佐证自由主义故事:它恰好证明“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等自由主义理论,剧中七连战士听了小安东故事后都很同情即是明证。但李延年将故事继续往下讲,并讲成了社会主义故事。李延年说“其实在我们的国家,这样的可爱女人多了,千千万万”,接着他请五班长讲了他老婆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的“好”,请副指导员讲了他对象的“好”,又请大家闭眼默想自己的父母、兄妹和亲人:“如果这些个事情(暗指美军轰炸朝鲜村庄)发生在你的家乡、你的亲人身上,你们会咋样?”讲至此时,所有战士(包括观众)都能听懂一个铁的事实:我们投入战争,保卫的不是“国家”这一抽象符号,更非“不可容忍的祸害”,而是我们的亲人,是一个又一个的二妞、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二妞、现在的和将来的二妞。此即社会主义国家观:国家的确有治理机器之性质,但它也是“千千万万”个二妞的集合。
可以说,李延年单元为深陷自由主义迷思的当前文学重新阐明了国家被遮蔽的内涵。此种国家其实接近于古代的氏族:“在氏族社会中,个人完全依靠他的氏族来保护。氏族的地位就相当于后来国家所居的地位,氏族拥有充分的人数足以有效地行使其保护权。”{9}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同样如此。关于后者,对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雷蒙·阿隆曾讽刺道:“他们同样满怀恐惧地描述着个人今后将置身于其中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个人将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其他个人中,人们将彼此争斗,并同等地服从于市场的偶然性以及行情不可预测的起伏波动。由此,‘组织’的口号取代或补充了‘解放’的口号,即通过集体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使得弱者免遭强者的摆布,穷人免遭富人的利己主义的伤害。”{10}雷蒙·阿隆自有其能见与不能见,但反读这段批评,正好可看出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特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保护民众不受资本的伤害。新中国初期采取的工业化、合作化等政策乃至今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实都以此为基础,并以国家力量参与世界竞争。对这其间国家的具体境遇及其内在的复杂张力,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基本上是付之阙如。《功勋》一剧,虽然取材范围主要在“前三十年”,但它能够跳出自由主义视界,重新阐释作为“必要的善”的国家,可谓是当前斑驳、混杂的文艺中令人喜悦的探索。
置诸文艺史,《功勋》这种国家阐释有两点值得记取。(1)作为“必要的善”的国家阐释,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并不为新见,但它之所以比“红色经典”更具号召力,还得益于这种阐释与“人”的逻辑发生了静悄悄的融合:国家不再外在于“人”,而变成“人”的情理的自然延伸。在李延年单元中,七连战士义无反顾踏上战场,不是要放弃自己生的权利,而是要保全自己亲人、同胞生的权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说是《功勋》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从技术层面看,这种关系重建实际也“补正”了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之失。在文学中,国家的确属于“整体现实”,但人才是“整体现实”得以存在、附着的所在,假如人不能以其情理在艺术上立起来,国家又将焉附?这其间辩证关系,很接近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对于写作而言也是如此:抓住了“人”并由其情理推导出国家,国家自然能在艺术上成立。反之,若通过取消个人逻辑或压制个人情理的方式凸显国家,国家多半也会沦为空洞符号。此前传统社会主义文艺即多有类似“人地皆失”的尴尬。(2)因为国家成了温暖的、聚集“千千万万”个二妞的存在,那么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具有了沉甸甸的重量,就构成了总体性“历史”。仍是在此单元中,李延年面对了最为残酷的问题:“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这段陈辞荡气回肠,总体性历史也在此真正落地,构成万千生命的来源与归路。
不过,国家被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文艺获得新的进阶,与其说是由于编创人员的才华,不如说是近年来国家力量引导的结果。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一度濒于危亡边缘,但百年之内重归复兴之路。其间逆天改命之悲壮之伟大,并非复制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来。与此相应,其文学/文化生产也不可能用新自由主义有效阐释这段历史与人心,“任何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深刻了解之上”“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历史,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11}遗憾的是,改革开放时代文学一直在试图使用新自由主义叙述这段社会主义历史。《功勋》的出现,可说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实践自然的而又迟到的结果。
三、重建历史连续性
无论是对国家的重新阐释,还是对“人”的再度启动,都含有话语转型之意味,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社会主义文艺的未来是一片坦途。其实,目前这股潮流主要出现在国家管理比较到位的影视领域,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情况又大有不同。除个别作品外(如《问苍茫》《人境》),其实很难读到有类似倾向的作品。这是否与此种文艺兴起未几、辐射范围尚有待时日有关呢?也许如此,但依笔者之见,这与它重建历史连续性的新努力有更深关系。这在《功勋》中表现为两层特殊的叙事处理,不大为人注意,然而却都易引起争议并最终制约创作发展。
(一)1976的隐匿与去自由主义处理。《功勋》中有一些细微却震动人心的细节。譬如在张富清单元中,1976,这个中国当代史“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似乎被疏漏了:在第16集近结尾时,上一场景是高洞群众送别张福清,下一场景是一群跳土家舞的青年,不变的鄂西民居,相似的深情氛围,波澜不惊,仅跳舞中一个当地青年对张福清儿子说了句家常话——“听说你考进来凤师范学院了,以后进城来找你”(恢复高考是1977年),然后此集结束,第17集一开始,即打出字幕“1981年冬”。在此,曾在各种史述中作为“时间开始”的1976消失无踪。这当然不是“疏漏”,其实《功勋》八个单元都未突出1976。相应地,20世纪60—70年代特殊的政治生活场景也较少呈现。年龄较大、熟悉电影《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的观众对此可能会有所不适。当然,这并非突如其来的叙事处理。依戴锦华之看法,这至少是从电影《建国大业》(2009)就开始了的“新主流叙述”:“(《建国大业》等献礼片)以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为基本逻辑,不仅有效贯通了曾组织在异质性逻辑中的历史叙述与脉络,而且成功地‘回收’了曾遭放逐的、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时段”“它将曾被赋予创世纪、新纪元、断裂意义的历史事件以历史接续、连续贯通的逻辑进行叙述”,这种“平滑、连续的历史叙述,既是支撑着主流意识形态或曰合法性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获得有效确认的外在标识”。{12}此种“新主流叙述”包含两层剥离:既剥离了阶级史述,也清理了仍为多数知识分子所信任的自由主义史述。后者尤其意味深长。实则1976之所以成为重要“历史时刻”,主要出自自由主义视野。自由主义以1976为界,将当代中国分为前后断裂的两段。此种“断裂论”至今仍塑造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历史想象(如文学研究中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但它显然是对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道路缺乏认识、理解的结果。鉴于此,201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不可相互否定的重要论断。这种提倡推延至文艺界、学术界,即是要求我们摆脱外来理论限制、根据中国现实实践重新理解新中国70年艰难、曲折的历程,重建当代中国史之连续性。
而这,正是“新主流叙述”的来源。《功勋》张富清单元中作为自由主义叙述重要“历史时刻”的1976的隐失,意味着一种不基于欧美视界而基于中国自身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连续性的形成。从《功勋》八个单元剧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申纪兰的提案》始于1946年),无论是“李延年们”血洒朝鲜,还是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孙家栋、于敏等科研报国,抑或是申纪兰、张福清等的基层奋斗,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社会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叙述,不是事关自由的单一叙述,也不是个人主义英雄之闯荡世界,更非权力与资本对民众的拯救,它以国富、民强(多数人自由)为重要目标,以“人民创造历史”作为基本史观。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叙述的升级改造,也是近年“中国道路”论述的文艺版本。
然而,不可讳言的是,此种“新主流叙述”所提供的历史连续性在近十年小说、诗歌创作中尚未得到有效传播。原因何在?显然这是并不轻松的话题。毕竟,1976的隐匿,勾连的不仅是史观的变易与调整,而是对数代人(尤其知识分子)难以被整合、化约的另一种青春、经验与信仰的删除。福柯说“历史带给我们这样的观点:我们处于战争之中,而且我们通过历史进行战争”{13},但《功勋》能否在历史书写的“战争”中赢得优势显然还是未知之数。可以说,如何减少“历史学家的技艺”、如何兼顾面包与自由、如何在多数人的利益与少数人的权利之间寻求结构性平衡,都是此后新社会主义文艺颇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敌人”的删除与去阶级化问题。《功勋》另一不大引人注意却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敌人”被删除了。准确地说,是国内“敌人”被删除了。整体而言,《功勋》八个单元剧未出现一位具体的国内“敌人”(如地主、资本家或贪污官员等)。当然,剧中也有冲突,譬如于敏与另一位数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但究其根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他们还成了真正的朋友。所以,《功勋》在令人感怀的同时也引人深思: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并非如此“单向度”。比如,申纪兰的故事始于1946年,张富清长期工作在落后的鄂西山区,势必会触及地主、土匪、土地改革及地方权力关系重组等复杂问题。但如此种种基本上都被舍弃。《功勋》如此处理,可名之为“去阶级化”。当然,有论者以李延年围绕逃兵事件所做的思想工作为例认为该单元仍存在阶级政治,其实不然,剧中李延年的思想工作所援取的是国家主义而非阶级政治。而以国家主义替代阶级政治的故事策略,是“新主流叙述”长期以来的默认规则。推其缘起,既与当前中产阶级文化不再接受传统社会主义文艺所谓“仇恨政治”有关,也与中共中央体察时局、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尤其后者,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局面下,以儒家仁德之念,提倡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化解积怨、美美与共,无疑高瞻远瞩。但文艺创作是将之作为深层次哲学命题涵孕故事,还是直接挪用为“可以叙述之事”与“不可叙述之事”的遴选标准,其实大有区别。从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实际来看,主要集中在后者,即在事实遴选行“去阶级化”之实,《功勋》“全是好人”的局面即由此而来。
以上两层,无论是去阶级化处理,还是去自由主义处理,都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萨义德说:“回顾过去是解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14}《功勋》可谓鲜活的文本。然而以回避而非对话的姿态处理不同的声音与利益,未必是最妥当的选择。总的来说,《功勋》以及相似的《山海情》《觉醒年代》等电视剧的确给了观众久违的亲切感,呈现了社会主义文艺所能有、所应有的美好样子,重塑了后者在当前创作格局中的影响力,但它也仍然存在“道阻且长”的问题。新社会主义文艺是否能够突破影视领域而在小说等领域形成新的文学潮流,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容自由主义的部分经验,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与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保持灵魂的对话。莎翁有言: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社会主义文艺在解决目前所遇问题后,当有比资产阶级故事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注释:
{1}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2}毛尖:《凛冬将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66~67页。
{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4}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02页。
{5}张富清口述、童雁整理:《老英雄张富清的初心和本色》,《档案记忆》2019年第7期。
{6}厉舒晴、孙洁、吴和鸣:《幸存者内疚及其心理机制研究进展》,《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10期。
{7}贝拉·巴拉兹著,何力译:《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8}朱光潜:《谈美·谈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版,第148页。
{9}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4页。
{10}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1}李云雷:《“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及其探索——读刘继明的〈人境〉》,《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12}戴锦华、王炎:《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4页。
{13}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14}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张均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9/60/126928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