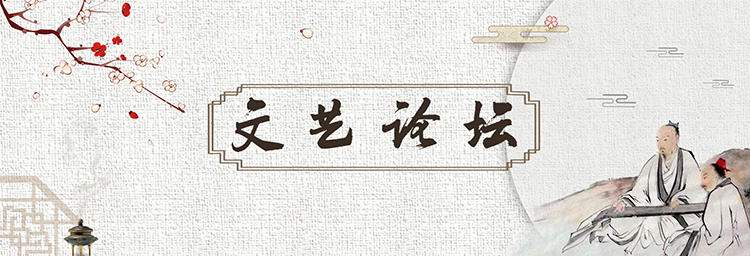

情境性故事片的结构框架
文/文先军
摘 要:故事片可以划分为情节性的和情境性的两大类。情境由空间、次要人物和主人公的身心条件三种元素构成,它们的表现形式是次要人物主导的事件和主人公在故事时间之外经历的事件。情境性故事片有持存性、相继性和并存性三种结构框架,相对于情节性故事片,反映了更为完备的关系范畴。
关键词:故事片;情节;情境;范畴;结构框架
故事片剧作理论迄今为止提供的结构范式都是对情节的描述,在情节点上进行切割,划分不同的阶段,规定每个阶段的功能和时间长度,比如三幕式、八序列、十五节拍表和英雄旅程结构等,将不是以情节为主体的故事称为非情节、反情节或者小情节的,否认它们具有稳定、普遍的结构,认为它们是散文化、碎片化和非线性的。
戏剧理论将非情节的内容称为情境。黑格尔在美学史上首次界定这个概念。萨特提倡情境剧理论①,写作情境剧和情境小说。中央戏剧学院谭霈生教授沿着这条线索发展出戏剧本体论,把情境而不是情节当作戏剧的本体,提炼构成情境的元素,归纳出三种情境的运动形态。他在20世纪80年代将这些研究成果移植到故事片领域,但是影响甚微。倒是电视剧理论界,受美国情境剧及其理论的影响,普遍接受这个概念。
为什么电影剧作理论长期坚持把情节当作结构的唯一基础?戏剧本体论本身存在瑕疵,还是在向故事片移植的过程中没有作出适应媒介的调整?本文在辨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对情境在故事片中的具体形态的观察,尝试提炼故事片中情境的构成元素,归纳以情境为对象的故事片结构。
一、电影情节驱逐故事的谬误及其根源
情节在故事片中被推崇为结构的唯一手段,从实践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因为以情节为主体的故事片产量一家独大。但是在理论上还长期存在对情节和故事这两个概念认识不清的问题,形成了把情节当成故事甚至取代故事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汉语和英语都允许把这两个词语当作同义词使用②。
在电影理论界,近些年被引用得比较多的是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关于故事和情节的定义。他认为情节包括表演出来的事件和无关乎剧情的元素。后者指字幕和无声源音乐等③。故事有一部分出现在影片中,与情节重叠,即表演出来的事件,而另一部分是观众对这部分内容的扩展性想象,或者导演构思中的所有事件④。也就是说,情节等于故事片这个文本本身,囊括经典文艺理论中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完整的故事只出现在导演和观众的头脑中,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被情节驱逐出了影片这个客体。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近年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剧作理论家,也是把故事看成素材,认为情节是对素材的选择和排列⑤。国内一位学者在援引波德维尔的观念的基础上,将情节发挥为“是对故事的讲述”“讲述故事的具体环节”⑥。这种情节即影片的观念,一旦运用于具体的影片分析中,立刻就暴露出它在逻辑上的荒谬性。这位国内学者在分析《城南旧事》《黄土地》等影片时,又认为它们虽然有故事,但情节较少,只注意构筑意象、经营氛围和抒情风格⑦。显然,他已经遗忘了自己关于情节的定义,没有将意象、氛围和风格看成讲述故事的具体环节。他不自觉地回到了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关于情节的定义:通过因果关系联结起来的事件⑧。
福斯特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位明确区分情节和故事的人。但是要注意到,他是在长篇小说这种特定的体裁内作出这种区分的。他定义故事为按照时序安排的事件,或者说是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叙述⑨。故事和情节既可以重叠,因果关系覆盖时序,也可以分开,福斯特以沃尔特·司名特(Walter Scott)的小说《古董商》为例,说明逻辑松散甚至没有关联的事件,仅仅在时序上排列起来,也有可能引起读者对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件的期待。
波德维尔的理论实际是对福斯特的定义的电影化改造。他将时序和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又根据电影的本性,加入空间的规定,指出故事片中的事件必须是发生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因果关系的。这个综合性的规定本身是符合故事片的媒介特征和艺术本质的,相对昂贵的制作成本和短暂的时间长度不允许故事和人物脱离因果关系而任性发展,像在长篇小说中一样,必须尽可能让影片在不中断、一次性的放映过程中被大多数观众当下理解。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是实现这种理解的前提。但是他把对因果关系的设计泛化成创作中的一切思维活动以及一切被设计出来的内容,这才得出字幕也属于情节的荒谬结论。
实际上,情节概念扩张的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一方面区别了情节和故事,奠定了情节概念的基础,即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的组合⑩,并且只把情节看成构成戏剧的六个部分之一{11},但是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混淆情节与故事、情节取代文本的种子。在陈中梅的译本中,故事一词共出现六次{12},除了最后一次等同于情节以外,在其他语境中,都是指戏剧作者用来编排情节的素材,是历史和神话传说中与情节有关的所有事件{13}。但是,亚里士多德一直使用同一个词“muthos”来表示两个概念,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后来概念混淆的根源。此外,他虽然基于戏剧的摹仿性质划分六个部分,但是划分的具体标准不统一。情节、性格和思想是摹仿的对象,言语和唱段属于摹仿使用的媒介,戏景是摹仿的方式。他没有详细解释这些标准,也没有讨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按照近现代的观念,性格、思想就是情节的内在动力,言语是情节动作的形式之一,戏景是情节展开的先天条件,而唱段已经基本被取消,或者演变成导演的主观表达手段(音乐)。
二、对电影故事、情节与情境的重新界定
与情节相对立的情境到底指什么?只有情节概念被澄清,它和故事、文本之间的关系被梳理清楚之后,情境的内涵才会清晰地显露出来。
故事片最初指内容虚构、时长超过34分钟、在电影院作为主要节目放映的影片{14}。后来被普遍认为是表演虚构的故事的影片{15}。尤其它的中文名,从最初的“影戏”到最后确定的“故事片”,都强调这种文本通过影像媒介呈现的是(戏剧性的)故事。所以,将故事仅仅当作素材或者联想材料赶出文本,等于否定这个在百年电影史中发展起来的概念。
在故事片的本质规定至今还被普遍接受并且有效的情形下,故事必须回到影片中,成为内容的总体。电影故事就是影片中所有事件在时空中的组合,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构成整体,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能局限在一种范畴内,如波德维尔的定义,因为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的认识并不是只有因果一种,而且已经出现的故事片对关系的表现也并非单一的。事件整体的界定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的定义,但是删去了关于材料构成的原则——摹仿,避免涉及形式和手段,混同于文本概念。
既然故事是文本内容的整体,那么情节只能是它的下属概念。亚里士多德和福斯特都依靠因果关系定义情节,实际上指的只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人物通过自由意志选择动机,动机就是情节最初的因;动机设定追求的目的,人物朝着目的实施一系列动作,最终将目的实现出来,成为现实,或者毁灭目的,这都是最终的果。从因到果,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外化过程。而机械论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是外来的力量,对人物来说是盲目的必然性。这种关系不仅仅在物理和化学的层面发生,当人屈服于外在力量和内在本能而活动时,这种活动在性质上也是机械的、被动的。在正常长度的故事片中,机械论的因果关系难以独立推动主人公完成动作过程。所以经典文艺(包括电影)理论中的情节,指的是主人公在动机驱使下为追求特定目的而完成的一系列事件。动机和目的构成特定的因果关系。故事包括不同关系的事件,情节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情节是故事的下属概念。罗伯特·麦基恰恰把这个内涵赋予故事,同时又把它作为素材赶出文本{16}。
黑格尔定义情节,强调的就是内在力量有目的的外化过程{17}。他把这种力量叫作“情致”,是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在个体内的充塞渗透{18}。个体要把自己的情致实现出来,必然遇到其他个体的情致的反对。它们相互斗争,产生动作和反动作,这个冲突的过程就是情节。
美国剧作理论家约翰·霍华德·劳逊(John Howard Lawson)观察到人们对戏剧和电影中因果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抽象为线性的链条。他认为任何一个果都是多种因导致的{19}。可惜他对多种因没有展开辨析。但是基于观察的结果,他把戏剧和电影事件的整体划分成内部和外部两大体系,是极其具有启发性的观念。简单地说,内部事件是人物的自觉意志爆发的结果,外部事件是社会环境的必然性的体现{20}。内部事件就是情节,而外部事件就相当于情境。情境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环境,是一个艺术学概念。根据黑格尔的界定,处在抽象静止状态的普遍精神是不能直接导致动作(情节)的,它首先必须将差异面分化出来,落实在不同的个体身上,成为具体的存在。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说,周围这些不同的差异面的体现者,就构成了“具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这就是情境{21}。德文 “bestimmte”,朱光潜先生译为“定性”,现在普遍称为“规定性”。情境区别于日常环境的关键在于:环境的成分往往是芜杂的,它们的性质暧昧不清,处在相互干扰的状态,不能统一成整体。情境的规定性却能通过具体的人和物对处在其中心位置的主人公施加一股定向的压力,迫使主人公作出反应,构成冲突,导致动作(情节)的产生。谭霈生继承黑格尔的情境概念,强调情境是情节的基础,将两者等同是常识性的错误。
实际上,情境独立于情节的观点,在《诗学》中就能找到萌芽,具体体现在17章、18章和24章。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结构分为结和解两部分。结由剧外事件(素材)和剧内事件构成,始于素材事件发生的源头,终于剧内事件主人公的处境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22}。因为舞台限制,剧外事件不能通过动作表现出来,只能通过言语和唱段穿插进来。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穿插进来的内容不能算在情节之内{23}。他又将悲剧分为四种。有关第四种悲剧的名称和简要说明的文字已经遗失,有学者根据词源学的考察将其阐释为情景剧以及根据存留的作品举例推测为穿插剧{24}。在谈到史诗的结构时,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史诗使用语言进行叙述,与戏剧相比,能够穿插更多的内容,讲述同时发生的事件。他高度赞扬荷马史诗的结构,认为其一方面具有编制精致的情节,另一方面通过穿插丰富了作品的内容{25}。他所列举的穿插内容,就是黑格尔定义的情境。
将情境降格为环境,作为下属概念纳入情节,是情节等于文本观念的体现,也是目前剧作理论中流行的看法。情节认不清自己,当然也就认不清对象。相对于戏剧,这三个概念在故事片中表现得更为纯粹。因为这种艺术形式用来叙事的基本材料是动作,肢体动作的成分和重要性要多于、强于言语动作。而在戏剧中,后者明显多于、强于前者。肢体动作构成的事件,比言语动作叙述出来的事件,计算起来要直观得多。因此,在故事片中,情节和情境从视听觉上就能被区别。情节是主人公为了追求动机所设定的目的而实施的所有事件,而情境是由他人主导的事件以及主人公在故事时间之外做的事件,故事就是这些事件的总和。
三、情境的构成元素
谭霈生根据他对狄德罗、黑格尔等人的情境概念的理解,将构成情境的元素分为三类:具体的时空环境、对人物具有影响的事件和有定性的人物关系{26}。在戏剧和故事片中,这些元素的种类都是不变的,性质是相同的{27}。但是第二种元素的性质——影响力——缺乏对程度的界定。任何被选择排列进入戏剧和电影中的事件对主人公都是有影响力的,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而已。故事片三幕剧作范式的确立者悉德·菲尔德(Syd Field)正是根据这种程度差异,区别出情节点Ⅰ和情节点II——情节线上的关键性事件。仅仅指出具有影响力,确定不了情境事件。在《论戏剧性》一书中,谭霈生将它称为特定的情况,通过与情节事件对比的方式,试图说明它们是能够促使人物采取行动、产生冲突的事件,往往发生在戏剧开幕之前。这种论述终究没有触及到清晰的本质。第三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元素本身,只是元素间的关系。
萨特是唯一清晰而且周密地论述这个问题的哲学家。在《存在与虚无》中,他将个体面临的处境分析为:我的位置、我的过去、我的周围、我的邻人和我的死亡。在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总论中,还谈到了“我的身体”{28}。位置是个体在空间中的立足点,只有占据具体的位置,周围的事物对个体的规定才显示出来,个体的行动才能由此出发。过去在时序上是相对于个体选择了新的目的、准备付诸行动的瞬间而言的,在内容上指个体在这段时间内拥有的所有人生经验。周围仅指个体能够用来作为工具和手段的事物,它们对于实现目的而言,要么是有助益的,要么是敌对的。邻人也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目的,在行动中相互干扰。他的戏剧《隔离审讯》涉及的就是这个主题,人物在其中喊出了“地狱就是他人”的名言。死亡的意义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它总是逆向地影响着个体的选择,也就是说,个体作出的任何选择总是基于生命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身体条件也影响着选择。
萨特反复指出,处境成分本身是中性的,在缺少个体的目的的前提下,是不能对它们进行价值判断的。唯有目的才能照亮它们,将它们的价值显示出来,是敌对的,还是工具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处境的哲学分析吻合了艺术情境。他的术语所说的基于目的的虚无化过程(个体的自为存在),对应被动机驱动的情节。而以上分析的处境结构,是个体的自在存在,对应情境。这些具体的结构成分,是提炼情境要素的基础。
尽管萨特反对将周围与位置混同,但是他也注意到,位置为周围奠定了基础{29}。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将两者在情境内合成一个要素:空间。空间标示出人物的位置,同时规定他(她)行动的工具性条件。人物要在情节内行动,情境必须为他(她)提供场所和工具。
人物过去的所有经验不可能都出现在故事内,只有与动机关联程度极大的经验才会被提取出来。或者用萨特的话说,动机将它们照亮,呈现在观众眼前或者耳朵里。美国公路片《塞尔玛与路易丝》(又译《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1991)中,路易丝看到塞尔玛正被男子强暴,掏枪击毙男子。她的反应与自己在故事发生前的经历有关,她曾遭受强暴,而且在司法上没有获得公正的对待。悉德·菲尔德将这类事件称为“人生轨迹事件”,认为它们会渗入潜意识,影响波及人的一生{30}。这也就是谭霈生所说的发生在大幕打开之前、具有影响力的事件。
2021年出品的美国科幻电影《芬奇》(Finch)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死亡逆向影响人物选择的故事。主人公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设计制造出一个机器人,教它照顾自己唯一放心不下的宠物狗。在故事持续的大部分时间内,死亡从未来影响他现在的行动。在一些科幻和灾难片中,地球或其局部行将毁灭的信息,成为催生人物动机的重要力量。毁灭与死亡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与过去的事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未来影响人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和未来的事件可以归为一类。这个未来可以包括在故事时间内,出现在相当于情节的最后一幕的位置。
邻人,主人公周围的人,是故事片中的次要人物。以主人公的动机为标准,他们要么作为反对力量阻碍主人公动机的实现,要么作为帮手协助他(她)。在以情节为主导的故事中,他们的确是在主人公及其动机被确定之后,根据主人公意志力的强弱、能力的大小和完成目标的难易程度,按照阻碍和协助的关系进行匹配的。还有一类次要人物,不直接参与情节的发展,而是为了塑造复杂的主人公形象而设计出来的。当主人公内心存在多个维度时,设计相应的次要人物,让主人公与他们交流,使得心理内容通过动作外化出来。谭霈生强调他们与主人公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把握了次要人物的本质的。但是作为元素,还是要落实到人物而不是关系上。
特定的身体、心理条件,往往影响主人公的行动能力。《芬奇》在主人公去世前,一直注意描绘他的身体逐渐恶化的过程。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导演的影片《记忆碎片》(Memento,2000),主人公只能记住10分钟以内的事情,但是要完成为亡妻复仇的任务,这种独特的心理条件使复仇过程更为艰难。
综上所述,故事片情境的构成要素包括:空间、次要人物和主人公的身心条件。这些要素在故事片中,都要以可见可闻的形式运动起来,形成事件。次要人物的运动形成由他们主导的事件。从主人公的身心条件可以追溯出过去的事件,推知未来的事件。因此,情境的表现形式是他人主导的事件和主人公在故事时间之外经历的事件。
确定了要素,联系质的规定性,就能从量上规定情境。空间相互关联,次要人物基本没有改变,事件能够按照统一的性质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情境。前两个条件是感性的,通过视觉就能进行判断,因此具有直接的操作性。一般来说,空间完全改变,而且和前一个空间没有逻辑关系,尤其是次要人物甚至完全更换了,就可以判断,这是另一个情境。
根据情境事件和情节事件在整个故事中占有的时间长度的比例,可以将故事片分为两大类:情境性故事和情节性故事。情境性故事是指情境事件占主导的故事,反之亦然。任何性质的故事片都不可能没有情境,但是完全没有情节的故事片的确存在,例如苏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导演的《镜子》(Mirror,1974)。
另外需要强调,不能将任何要素脱离情境整体而抽象出来。比如次要人物,尤其是作为主人公帮手的次要人物,当他们服从于主人公的意志、参与到主人公主导的事件,也就是情节中时,他们所做的事件只能看成是情节内容。只有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独立做出的事件,才能归到情境中去。
四、情境的结构和关系
谭霈生归纳出三种戏剧情境的结构类型(也称为运动形态),这是他的情境理论中最具有独创性的部分。第一种是集中于主线路的运动形态:情境与人物相契合的运动是单线发展的,单线并不是只有一条线,可以有多条线,但是其中必须有一条是主导性的{31}。结合他列举的戏剧作品来验证,他所指的这种形态实际是只有一个情境的情节性故事,情境伴随主次情节发展,而并不是以一个情境为主体、情节短小的故事。第二种是链条式的运动形态:全剧由许多相对独立的情境构成,它们依靠统一的主人公或者总悬念联结{32}。第三种是并列交错式的运动形态:人物众多,却没有统领全剧的中心人物,每个人物都发展出独立的情境,这些情境不能像第二种一样,通过中心人物或者总悬念联结在一起,而是分流成一条条小溪,有时相互并列,有时此隐彼现{33}。这两种形态都包含多个相对独立的情境,一种能够通过形式手段联结成整体,另一种在形式上则是分散的。这两种类型的故事都是以情境为主导的。
这三种结构形态对于建立情境性故事的结构框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但是还不能直接应用到故事片领域。它的第一种结构不属于情境性故事的范围。此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戏剧本体论》对它们的描述都是现象性的,没有抽象为概念,对每一种结构的定性并不清晰、严谨。
实际上,这种划分已经显示作者对量和关系的范畴的直觉,只需要把这种直觉发展成知性,就能将范畴运用于被描述的对象上,使它们上升为概念。主线路式的结构,如果将它的内容矫正到纯粹的情境上来,那么从量的范畴来说,它只包含一个情境。其余两种包含多个相对独立的情境。再精确地划分,相对于多个人物分别发展出来的多个情境来说,一个主人公或者总悬念统领的多个情境可以看成他(她)或者它的全部情境。也就是说,这三种结构从量的范畴来说,是按照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来进行划分的{34}。
任何事物在时间中存在的样态,无非是持存性、相继性和同时并存{35}。由单一情境主导的故事,描述的就是这个情境在故事时间内的持存过程。由主人公或者悬念串联起来的全部情境,必须在前后相继的过程中展开。主人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悬念的结与解也需要时间的单向流动作为先天条件。而并列交错的多个情境在故事时间(而不是讲述时间)内基本上是并存的。
关系是在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确定了时间样态,相应的关系范畴就能被整理出来。单一情境的故事着力发展具有规定性的情境的多种属性。属性多样,情境才是具体的、活跃的。这些属性能够统一为本质,情境才能作为整体出现,不致涣散为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情境就是一个实体,能够独立存在。属性是它表现出来的偶性,依存在实体上。从关系范畴来规定,单一情境的故事结构描述的是依存性与自存性的关系{36}。例如塔科夫斯基的影片《牺牲》(The Sacrifice,1986 ),也有一个情节——主人公请求女巫拯救。但是它用更多的时间描述主人公置身的情境:即将被导弹攻击的小岛。整部影片是寓言性的,情境的规定性只能从象征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人类仅仅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必将毁灭自己。这个情境包含多重属性,从对立的方面发展情境:放纵欲望和寻求精神拯救。
在时间上相继的情境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罗伯特·麦基在区分大情节和小情节故事类型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主人公对待目的的态度。如果是主动的,那么他就会通过动作发展出大情节来。而如果是被动的,他就没有能力发展出情节,这样的故事是小情节型的{37}。被动主人公基本上被当作因变量,用来测试情境(自变量)的性质和强度。相对而言,情节性故事基本依靠目的论因果关系来组织,而这种在时间中相继的情境基本通过机械论因果关系编织成故事整体。
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导演的《萨蒂利孔》(Fellini Satyricon,1969)和《卡萨诺瓦》(Fellini’s Casanova,1976)是典型的反映机械因果关系的相继性情境故事。主人公都是在性欲的支配下,不断追逐释放欲望的对象,他们的纵欲行为始终没有质的变化。在一个时空内追逐一个对象,构成一个情境。当这个情境被外力破坏后,他们匆忙地、不经反思地闯入下一个情境。他们在情境中受到外在和内在自然的摆布。
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勃廖夫》(Andrei Rublyov,1966)直接用小标题将影片分为10个情境,并且标明绝大部分情境的年份,这些年份是相继的。情境之内与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这是一部关于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的影片。鲁勃廖夫虔诚地信仰东正教,希望通过画圣像向人民传播信仰,但是情境中由他人主导的事件,不断冲击他的信仰,几乎导致他否定信仰。这些事件对他的压力,是机械性的。但是受到铸钟少年的感召,他不再注重信仰的现实效果,只为信仰本身而行动,这种反思与重新选择的过程,体现出最高意义上的主体性,实现了人的目的,因此在这些情境内以及相互关联的情境之间反映出目的论因果关系。而作为序幕的情境,讲述一个农民乘坐热气球被摔死的事件,则与其他情境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只有所有其他情境的规定性显露出来后,这个为理想牺牲肉体的农民的情境才能通过性质的类比而与它们取得联系。
因与果在时间上是不可逆转的,在前的为因,承接而来的是果。但是在时间上并存的事物之间,可能互为因果,作为因的事物也受到被它影响的事物的影响,后者也同时作为果和因而存在。这种关系被康德称为协同性关系,表现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列交错的情境基本体现出这种协同性。费里尼的《浪荡儿》(I Vitelloini,1953)和《阿玛柯德》(Amarcord,1973)是这种情境结构的典范。《浪荡儿》讲述了四个小镇青年的故事。他们沉溺于本能生活,害怕和拒绝成长。他们没有明确的动机,没有发展出完整的情节,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汇聚成相对独立的情境。《阿玛柯德》更是采用这种结构的鸿篇巨制。它将整个小镇上的人作为主人公。除了出场较多的人物蒂塔(Titta)发展出一个主动性不强、时值也相对短暂的情节外,其他重要的人物都只拥有自己的情境,而没有发展出情节。
综上所述,依照时间样态的名称,可以将谭霈生描述的结构现象抽象为相应的概念:持存性、相继性和并存性的情境结构。这些概念同时含有关于量和关系范畴方面的规定。
一部以情境为主导的故事片往往只采用其中一种结构,但是也发现了融合三种结构的作品。《镜子》描述导演本人与亲人之间相互隔阂的关系。它的主体结构是相继性的,童年时代父母的关系、少年时代母亲的生活状态以及现在“我”与母亲、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在少年时代的情境中,又发展出一个并存性的情境:孤儿阿萨菲耶夫(Asafyev )报复教官。现在情境中既包含一个持存性情境,“我”卧病在床,不能与母亲正常交流,这个情境绵延在整个影片的放映时间内,又发展出一个并存性情境,即西班牙男人讲述童年经历。
相对于划分层次和阶段、分配了时值的情节性故事片的结构范式而言,本文关于情境性故事片结构的观察和归纳还只是框架性的,不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但是这些框架否定了含混不清的情节观念长期以来对情境的独立地位的否定,肯定情境性故事中存在稳定、普遍的结构,能够为评论和创作这类故事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概念。对情境元素的提炼及其表现形式的观察,为框架的细密化奠定了基础。关于情境结构能够反映更完备的关系范畴的观察和推理,是对这类故事片价值的证明。
注释:
①国内也译为“处境剧”,参见[法]让-保罗·萨特著,施康强译:《萨特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2页。“情境”“处境”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situation”。
②《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3页。《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130页。
③④[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著,彭吉象等译:《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第80~83页。
⑤{16}{37}[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第224页、第49页。
⑥⑦李显杰著:《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第58~59页。
⑧⑨[英]E·M·福斯特著,冯涛译:《小说面面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版,第93页、第29页。
⑩{11}{12}{13}{22}{23}{24}{2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4页,第63~65页,第78、82、106、125、169、170页,第106页,第131页,第126页,第131、134~135页,第162、169页。
{14}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third edition).New York: Webester’s New World 1997,P496.
{15}《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86页;[美]大卫·波德维尔、 克里斯汀·汤普森著,彭吉象等译:《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33页。
{17}{18}{21}[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9页、第295~296页、第253~254页、
{19}{20}[美]J·H·劳逊著,邵牧君、齐宙译:《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第248~250页。
{26}{31}{32}{33}谭霈生著:《戏剧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第196页、第202页、第213页。
{27}谭霈生著:《电影美学基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28}{29}[法]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94页、第612页。
{30}[美]悉德·菲尔德著,钟大丰、鲍玉珩译:《电影剧作问题攻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36~137页。
{34}{35}{36}[德]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第166页、第72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文先军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646742/91/1294225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