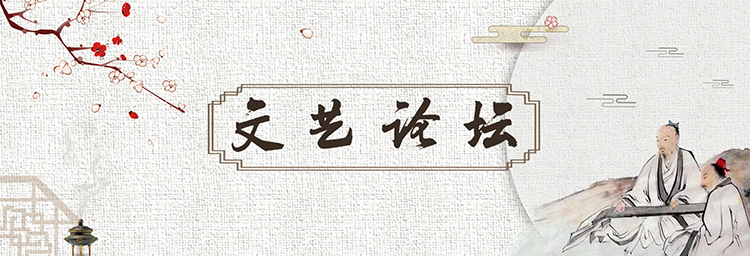

“艺象”概念及其阐释效力问题论析
——以朱志荣的艺象观为例
文/陈娟
摘 要:“艺象”概念的提出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意象思想资源,也吸收了现当代以来美学发展的成果。意象是心物交融所创构的审美结晶,艺象指称的则是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和蕴含的作为呼唤结构的意象。艺象既是审美心象的物化形式,也是艺术欣赏活动中的审美对象。艺象具有共相与殊相相统一、感性与理性相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统一等理论特征。“艺象”是美学与艺术学相交叉的枢纽,对艺术问题有着较强的阐释能力。“艺象”补充和深化了审美意象创构论,但在内涵、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拓展空间。
关键词:意象;心象;艺象;艺术活动;审美对象
艺术活动中的意象问题是意象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艺术问题的关注贯穿在意象美学的研究中,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叶朗、汪裕雄等美学家的论述中都或多或少涉及艺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象”被确认为“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一个专用的术语”①,并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进入21世纪以来,意象研究在概念溯源、内涵分析、理论建构等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这在带来“意象”研究的深入化、体系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分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意象研究中的“艺术”维度的问题。随着意象研究的深入,需要为艺术活动中的意象加以专门化、区别化的命名,朱志荣提出的“艺象”概念所解决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朱志荣长期在艺术学与美学研究领域耕耘,逐渐建构起以意象为本体、美与意象互释的审美意象创构论美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艺象”概念。“艺象”是“意象”所统摄的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所指称的是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作为呼唤结构的审美意象。“艺象”处于审美活动与艺术活动的交叉区域,容纳了意象的创构、传达与再创造的过程,以其特殊性拓展和深化了意象创构理论。同时,艺象贯穿在艺术活动中,对艺术活动有着较强的阐释能力,对艺象的探索也是对艺术规律的探索。可以说,“艺象”理论超越了美学与艺术学二分的学科壁垒,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二者之间的理论间隙,是中国特色美学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生长点之一。
一、“艺象”概念的历史沿革
关于“美”与“艺术”的观念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但是作为学科的美学与艺术学,却都产生于西方近现代,且二者自诞生以来,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问题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美学不可能不研究艺术,艺术学不可能不涉及美学,但美学与艺术学作为两种学科却有着各自专属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美学与艺术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在西方美学与艺术学本身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层新的困难,即宗白华先生于1934年所讲的“西洋的美学理论始终与西洋的艺术相表里,他们的美学以他们的艺术为基础”②。可以说,如何发现和发展与中国艺术实践相表里的中国美学理论,是中国现代以来美学与艺术学的重要任务。宗先生又于1979年写道:“中国历史上,不但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美学思想,而且在历代的著名的诗人、画家、戏剧家……所留下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往往还是美学思想史中的精华部分。”③这种思想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学发展指出了方向。中国美学理论必须关注中国古代的艺术实践以及艺术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美学与艺术学及其研究对象问题,中国学者需要给出自己的解答。朱志荣顺应这一时代问题,从美学与艺术尚未分离的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出发,以“意象”为中心来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象创构论,并在艺术本体的层面上提出“艺象”概念,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对艺术活动中意象问题的关注,与中国美学对意象的研究几乎同时发生。中国古代的意象论述多以诗论、文论、乐论、画论、书论等为主要语境,因此在艺术领域探究意象问题,或以艺术活动为例证具体论证意象理论,是现当代美学家的论述中常见的思路。朱志荣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意象问题,其早期著作《审美理论》中涉及对艺术意象的讨论,可以视为其“艺象”思想的萌芽。他将意象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艺术意象三种类型,并认为艺术意象的独特性在于“艺术意象在鉴赏者鉴赏活动之前,就已由艺术家创构而成,并通过物化形态表现出来”④。这里的“艺术意象”是指以艺术为载体的意象。在“意象”问题得到廓清之前,对“艺术意象”这种复合词的讨论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朱志荣在意象研究领域持续耕耘,2011年已有学者将他的思想总结为“意象创构论”,并对其理论特点、存在问题、学理原因等作出分析⑤。在此后的十数年间,朱志荣陆续发表《论审美意象的创构》《再论审美意象的创构》《意象论美学及其方法》《论艺象的创构》等系列论文,进一步推动意象创构论思想的完善和意象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朱志荣将意象看作一种物我交融的心象,认为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于心中创构的审美结晶。出于对意象的“心象”特质以及艺术活动中意象的独特性的认识,朱志荣提出了“艺象”一词。
以“艺象”指称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意象,这是从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资源出发的。意象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易》,然而《周易》中的意象思想中不仅包含审美意象,还包含心理意象等意义。朱志荣在当代意象理论建构的视域中,对艺术问题进行论述,以“艺象”为枢纽,将美与意象统一在艺术创造中。但他的这一做法也受到学界的质疑,如有学者指出,他“忽略了‘意象’和‘审美意象’的区别”⑥。对此,朱志荣写道:“中国古代人们很少用美来评价艺术,但是用意象评价实际上就是审美评价。”⑦由于意象是对艺术之美的评价,因此意象获得并主要是审美含义。至于意象作为一个艺术品评范畴,如何成为美学的核心范畴,朱志荣指出:“在中国古代诗歌和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品评中,一般不用‘美’而用‘意象’范畴进行评价。”⑧这样,作为艺术品评范畴和审美范畴的意象就被统一起来。他还进一步写道,“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更多地是指艺术美的本体形态”⑨,意象是美的本体形态,直接与美联系在一起,而不需通过艺术这一中介。但是对意象的理论研究仍然无法脱离艺术,原因不仅在于艺术是审美的集中表现,还在于艺术创造是对心象的物化。朱志荣将意象界定为主体心灵在审美情境中受到外物感发而在瞬间生成的心象,这种心象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次审美活动的完成,如果不对其加以物化,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审美沟通将是困难的,民族的审美经验也就无从积累。由于中国古代意象论大多以对艺术作品的评品为论述语境,对历代意象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艺术活动中意象理论的研究,因此,从使用范围和指称对象来讲,“艺象”概念是对中国古代“意象”概念的回归。
“艺象”作为一个出现在当代语境中的学术术语,吸收了近现代以来的相关成果,从而具有超越中国古代“意象”意涵的部分。从“艺象”概念本身的历时性使用来看,“艺象”经历了由合成词到具有独立地位的学术术语的转变。“艺象”较早出现在学术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值形象思维讨论的成熟期,“艺术形象”有时被简称为“艺象”。随着意象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意象思维对形象思维的取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意象”并用的情况逐渐增多。在随后的发展中,随着“形象思维”的沉潜,“艺术形象”逐渐走向了对具体艺术作品的分析。陈望衡的“艺象”论述可以看作对“艺象”在当时使用情况的总结:“艺术本体应为艺象。何谓艺象?艺象,首先它是情感造形的产品,就这而言,它是审美的。其次,它是一种技艺制品,它需要将艺术家审美的结晶物态化,这就需要艺术技艺与艺术传达媒介的参与。最后,它作为艺术消费品,必须考虑社会需求的各种因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因素。”{10}这里对“艺象”的三种规定是非常有意味的,但“艺象”毕竟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术语,这种理论光辉并未绽放应有的光芒。这些讨论虽然是在复合词的层面使用“艺象”,但可以视为对艺术活动中意象问题进行探索或者说是以“象”论介入艺术问题的先声。朱志荣在审美意象创构论的理论体系中重提“艺象”,吸收了形象思维研究的成果,认为“形象”与“意象”二者“应该统一到意象中来”{11},从而将“艺象”上升为具有独立学理地位的术语。意象创构论强调意象是物我交融的浑融整体,但在具体分析中,“象”被区分成物象、事象及其背景,“意”受任意一种“象”的感发而与其密合无间都能够生成意象。对“物象”的重视是古典意象论中的应有之义,而对“事象”的重视则是对“形象”的继承和深化。
“意象”是从中国古典美学衍生至当下的一个贯穿性的核心概念,“艺象”与“意象”同出一源,是“意象”在艺术领域的自然延伸。美学与艺术学的分界毕竟是人为建构的外在壁垒,对于意象研究来说,必然涉及“美”与“艺术”这两个方面。正如叶朗所指出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始终要指向一个中心,这就是审美意象”{12},而如何以意象为中心实现不同层面的贯通,则是一个新的问题。朱志荣写道:“美、审美和艺术问题这三者在我的意象创构理论中是统一的。”{13}而“艺象”概念的提出为三者在学理层面的统一提供了契机。在意象创构论的视域中,“艺象”是意象在艺术领域的专门指称,又由于“艺象”吸收了现当代以来的美学研究成果,从而具有当代价值,能够构成中西美学比较和艺术融通的基本点。可以说,“艺象”处于审美与艺术的交叉地带,容纳了美与艺术的创造及传达等诸多问题,通过艺象论述来弥合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理论间隙,搭建起美学理论与艺术批评实践的桥梁,是一种弥合美学与艺术学之裂隙的中国式回答方式。
二、“艺象”的内涵指向
意象是艺象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但艺象依然保持其独立性。相较于现有研究中将意象视为审美对象、心理表象、心中之象、表意之象、感性存在等,朱志荣将意象定义为审美活动的结晶,强调“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意象创构的过程”{14},对意象的探索就是对审美规律的探究。就意象生成的具体方式而言,朱志荣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心象,是物象或事象及其背景与情意在心中融为一体,是体验与感受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物理事实”{15},“物象、事象及其背景”构成生活世界,“创构”则强调意象生成的过程性和主体的主导地位。这也就是说,意象属于“心象”的范畴,但却有着物我交融、生成性等规定。这是朱志荣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尚象的思维传统出发所作出的界定,与主客二分思维笼罩下的界定有着根本区别。朱志荣的这一思想是对“意象”的超越性意涵的揭示。但是对“美”与“意象”的形而上价值的论述还必须通过具体的审美和艺术实践加以完善,这使得作为物化形态的“艺象”的提出成为一种必然。
首先,“艺象”作为专门术语而出现,是当代美学对艺术活动中意象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为基础的。讨论艺术问题离不开意象,是当代美学家所达成的共识。如叶朗教授在“美在意象”的标志性观点下写到“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16},并认为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就在于“看这个作品能不能呈现一个意象世界”{17}。而施旭升教授在“艺术即意象”的标志性观点下写道:“艺术的全部奥妙都体现在意象之中。”{18}朱志荣教授则在“美是意象”的标志性观点下写道:“艺象则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生成的意象的构思和传达,同时也是欣赏者审美观照和再创造的对象。”{19}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在意象”“艺术即意象”还是“美是意象”,都认为“意象”是艺术的本体,只是称呼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通过这三种观点对郑板桥“三竹”说的论述来加以说明:叶朗认为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过程是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20};施旭升认为“作为艺术创造的核心,意象的个体生成过程,即是郑板桥所谓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过程”{21};朱志荣则认为“‘胸中之竹’即意象,‘手中之竹’是对意象的艺术传达,即艺象”{22}。三种论述的共同点在于都重视“手中之竹”对“胸中之竹”的凝定,而凝定之后的形态,朱志荣将之称为“艺象”。简圣宇对意象的生成过程进行论述时写道:“个体主体在自己的意识中创构的‘心象’无法直接传达给其他主体,需要通过文本意象作为中介来触发和对话。”{23}这里所讲的“文本意象”也实际上就是朱志荣的“艺象”概念。就意象与艺象的关系而言,前者作为艺术家的“胸中之竹”,是个体性的、无法量化和比较的;而后者作为“手中之竹”,却具体呈现在艺术作品之中,随着艺术品的公开化,可以成为公共的、被量化和品评的对象。
其次,“艺象”有三重内涵:艺术家审美结晶的物化形态,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作为呼唤结构的审美意象,以及艺术欣赏活动中的审美对象。这三重内涵分别对应着意象在艺术活动中的三种形态。其一,艺术家首先是具备审美能力的主体,其在审美活动中产生审美结晶,即作为心象的意象,而“艺术创造是通过特定的媒介构思和传达审美活动中意象创构的过程”{24}。艺术创造是审美意象由“胸中之竹”成为“手中之竹”的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得以被体认的物化形态。其二,艺象既不是艺术家在创作之先所产生的心中之象,也不是欣赏者所看到的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而是处于一种待完成的状态,即当某物被称为“艺术品”时,它已经完成了心象的物化、从审美结晶凝定为艺象。艺术作品是艺象的载体,艺象寓于其中并等待欣赏者以其为基础生成新的审美意象。其三,艺象是艺术欣赏活动中的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核心就是意象的创造,艺术欣赏的核心就是意象的欣赏”{25}。也就是说,艺象作为意象的物化形态,是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共同指向。在艺术活动中,艺术语言是作为符码而存在的,但符码本身并不是审美的对象,其所蕴含的艺象才是审美对象。艺术作品有其物质属性(语言符码),这是艺术作品的存在基础,但艺术欣赏活动是在艺象的基础上创构新的意象,是艺象对欣赏者情感的唤起。
在意象创构论的视域中,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对意象的创造性传达而生成艺象的过程。朱志荣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出发,指出:“艺术美的本体形态从实质上讲是心象的构思与创造,通过艺术符号加以传达。”{26}艺术家作为审美主体,其在审美活动中面对的审美对象是复杂多样的,所创构的意象也是多样的,但并非艺术家所有的意象都会体现在艺术创造中,艺象所呈现的是经过选择的、能够体现艺术家个人风格的意象。也就是说,艺术家在审美活动中感物动情、触物起情,生成了作为心象的审美意象,这是艺术创造的起点。对于艺术家来说,“创造意象本身就是在畅神。从一个方面说,创作是作家的一种不得不然的冲动”{27}。这种强烈的分享欲支配下的艺术创造就是以传达审美意象为目的。而意象之所以必须通过艺术创造来传达,是因为艺术创造的传达并不只是手段,其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传达方式影响着艺术创造的效果。同时,艺术创造是将审美意象物化的唯一的方式。“艺术创造是通过特定的媒介构思和传达了审美活动中意象创构的过程”{28},虽然从广义的艺术思维方式上讲,造物也是艺术,无形有象的“道”也带有艺术意味,但毕竟只有具体的艺术创造才能将审美意象物化并固定下来。审美活动所创造的意象无法通过说理性的语言描述等非艺术的方式传达,艺术创造是将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心中之象物化的唯一方式,艺术创造的“艺术”属性正在于其超脱功利考量、以审美而非实用为基本指向。
总之,正如意象存在于一切审美活动之中,艺象也存在于一切艺术活动中。以艺象为出发点,将意象创构论渗透进艺术创作和批评等艺术实践活动,这是朱志荣意象创构思想从美学理论走向批评实践原则的重要步骤。由于艺象根植于艺术活动之中,朱志荣在艺象论述中尤其关注不同类型的艺术,并认为以艺术作品为中心进行中西理论对比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他写道:“我们应当关注现当代中西艺术的意象性问题,如小说、戏曲等再现型艺术的意象性、西方艺术作品中典型形象与意象的比照、当代表现艺术的意象性等。”{29}无疑,中西方艺术作品都包含审美意味,审美必然产生意象,只是创构意象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中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在艺象的视域下,美学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也不是美感问题,而是必须落实在作为审美活动结晶的意象上,尤其是意象的物化形态上;艺术学的内容也不再是由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等构成,而必须加入作为艺术本体的意象维度,将艺术与其他审美活动联系起来看待。
三、“艺象”的内涵及其意义
如前所述,艺象是指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作为召唤结构的意象,既是作为审美结晶的心象的物化形式,也是审美对象。由于意象是物我交融所创构的心象,心象的生成具有瞬间性、个体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和对审美活动的规律进行总结时,不得不借助作为其物化形式的艺象。朱志荣认为,意象“是物我交融、主客统一的本体”,而“艺术意象本体是意象本体的特殊形式”{30}。在意象创构论的视域中,艺象由意象衍生而来,但由于其与艺术作品的依存关系而具有更为具体的理论属性。对艺术意象本体之理论特征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比直接分析意象本体更为直观。“艺象”虽然是“意象”的子范畴,但是却具有相对独立和具体的理论特征。
首先,艺象是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艺象中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一方面是指艺术活动需要艺术家与欣赏者的共同参与。艺术家的心中之象是艺象创造的基础,而欣赏者再创造的意象则是艺象的最终完成;艺术家的心象对艺象具有引导作用,但欣赏者的再创造持有对艺象进行改造的创造能力,甚至有可能超越艺象并使其获得全新的价值。但另一方面,艺象所指涉的主体间性是其本身的固有特征。艺象本身作为召唤性的意象结构,并不具备自足性,而是在欣赏者的再创造中实现其价值。“每一次艺术欣赏,都是一次意象的再创造,一次意象的重构”{31},在这种重构中,艺象被欣赏者补足而获得新的意义。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红楼梦》每被阅读一次,“林黛玉”的形象就激发起读者的情感而形成审美意象,“林黛玉”作为艺象,其具体形象并非确定不变的,而是有待读者的建构,这种建构就是对曹雪芹所创造的艺象的再创造。艺象的主体间性具体表现为生成性。生成性是意象的根本特性之一,也是艺象的根本特性之一。审美意象作为心象,其生成性体现在其创构过程的恒新恒异上,而艺象作为一种存在于艺术品中的、有待被补足的形态,其生成性则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艺象的创造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艺术家在艺术材料的选择、运用等任何一个步骤中所做的改变都会影响艺象的呈现,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炼字”“改字”等现象就是如此;二是艺象作为审美对象,欣赏者在其激发下所创构的审美意象是生成性的,每一次艺术欣赏都是以艺象为基础创构新的意象。
其次,艺象是共相与殊相的统一。艺术创造是基于人类共同心灵的特殊创造,艺术作品赋予了审美心象以物质形式和承载物,使其由个人的变成集体的。艺术欣赏以艺象为基础,朱志荣认为“艺术作品的欣赏从‘同情’到‘会妙’到‘再创造’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32},“同情”是欣赏者能够进入审美情境的关键,而“同情”的产生基础就在于艺术家对民族审美传统、人类审美情感、基本审美形式等审美共相的把握;“会妙”的侧重点则不同,“妙”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其指涉的正是欣赏者对于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殊相的体察和会心,这种殊相既包含艺术家的个性人格、情感、志意等,也包含艺术家使用的个性化表达手段、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等。艺象是依托于艺术作品的整体之象,在审美共相的基础上又体现着殊相。从这个层面来讲,艺象正是一本万殊之“本”,月印万川之“月”。同时,“艺术意象还作为基因、原型和传统而对整个意象演变的历史产生了润物无声的影响”{33},艺象以其特殊形式参与到民族审美传统的塑造之中。因此,艺术创造既是将审美心象物化的过程,也是传递民族美学精神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时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所创造的艺象是符合民族审美精神和心理的,同时也能够体现时代的审美精神和心理;另一方面,艺术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品承载着艺术家的创造进入到其他时空,也就是说,艺象以其特殊性参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迭代之中。
第三,艺象的创造过程体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审美活动是感性活动,但艺术创造却包含着理性的成分。作为学科的美学与艺术学,二者的分歧在于,美学以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审美活动是感性活动,美学因此被视为“感性学”;而艺术活动却包含着理性的、非审美的成分,如艺术技巧、艺术材料、艺术评价等。正所谓“审美意象的创构在本质上是超越概念的”{34},如果说当代美学的全部努力在于以理性话语揭示和描述感性活动,那么在中国古代却不然,中国古代的“象喻”批评方法调节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象喻”本身依赖一定的感性,但其在整体上所指涉的却是理性判断的结果。实际上,艺术家的取象、运思、对体裁和题材的运用等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相较而言,对艺术创造过程的描述就是用理性语言来描述感性过程,这是艺术理论和美学的任务。艺术鉴赏是审美活动,但艺术批评是理性观照活动。优秀的艺术批评家对艺术品中审美意蕴的揭示,是艺术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面。“意象的创构以感性对象的价值特点为基础,经历了‘感知—动情判断—创构’的过程”{35},其中“判断”是一种理性判断,创构则是一种理性指导下的自觉活动。
总之,“艺象”虽然是意象创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有其独特性和独立性。相较于此前将“艺象”作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象”等复合词的简称,朱志荣将“艺象”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提出来,认为“艺象”是艺术作品的本体,并以“艺象”为枢纽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索。对朱志荣的相关观点进行检视,可以看到,他在美学层面对意象进行考察时,重在探究意象的形上意涵、意象的本体、意象的生成机制、意象的逻辑基础、意象的结构以及意象的一般特征等;而在艺术学领域对意象的探究则集中在艺术创造的思维方式、艺术创造的过程、艺术效果的形成以及艺术欣赏心理等方面。意象创构问题是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共同主题,也是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共同主题,因而,意象创构论美学具有古典美学向现代转换、理论指导实践两方面的意义。
四、“艺象”论的拓展空间
整体而言,审美意象创构论以艺术理论为起点,并拓展而成为审美理论,而“艺象”理论是从审美领域向艺术领域的延伸与拓展。因此,“艺象”理论一方面凸显了意象理论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有待补充和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主要表现在“艺象”概念本身的内涵问题、意象创构与艺象创构的关系问题以及艺术活动中意象的形态变化问题等三个方面。
首先,“艺”的指向及“艺象”的结构问题。如前所述,“艺象”与中国古代“意象”的使用语境与适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同时“艺象”也将“艺术形象”涵容进来。但艺象作为意象术语的子概念,仍然需要在“艺”与“意”的辨析问题以及其所引起的意象与艺象的结构差异等方面作出充分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所涉术语具有显著的“概念间性”特征{36},故而在使用“艺术”和“艺象”时,需要对其内涵进行考察。中国古代的“艺”是融形而下的“技艺”与形而上的“道艺”于一体的,正如朱良志指出:“‘易象’犹‘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37}这与近现代以来西方影响下所使用的“艺术”一词并不等同{38}。中国古代“艺”的观念与西方现代艺术体系中以“美”为标准的“评价性定义”和以“艺术建制”为基础的“区分性定义”{39}。这两种“艺术”观念之间的差异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以来作为学科的美学、艺术学、文学理论等研究中的一个先天问题。张法更是将中国当前的“艺术”概念分为“文艺”、作为学科的艺术学中的“艺术”以及非艺术学科中的艺术三个层次{40}。“艺象”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而出现,其所指涉的对象需要从“艺”的方面进一步澄清。与此相关,朱志荣在对意象本体进行论述时指出:意象本体“是象、神、道的有机统一”、“而艺术意象是通过艺术语言传达的,体现了言、象、神、道的统一”{41}。在这里,他将“言”的有无作为“艺象”与“意象”的一个区别,“言”所指涉的也就是作为表达形式的艺术语言。但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意象研究中“‘言’‘象’‘意’的三项联动结构,这是早期理论的基本范式”{42},这里的“言”有两个层面,既是指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也是指作为表达方式的艺术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言”是先于“意象”而产生的,而作为艺术言说方式的“言”却是以“意象”为基础的创造。
其次,艺术活动中意象的形态变化及其引起的相关问题阐发。艺术活动中至少存在三种意象:艺术家审美活动产生的意象(A),艺术家对A进行传达而产生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中包孕着的具有潜在审美价值的意象(B),欣赏者通过B感发自己的志意而产生的审美意象(C)。C不以A为目标和目的,但却受到A的指示和引导。B存乎艺术作品中,是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的本质。艺术作品离不开意象,但意象不一定产生于艺术活动。艺术家的审美活动是艺术创造的基础,而欣赏者的欣赏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前者对后者具有引导作用,但后者持有对前者进行改造的创造能力,甚至后者可能超越前者并使其获得全新的价值。这里需要进一步阐发的问题有两个:其一,艺术欣赏和批评的对象问题;其二,在艺术批评中,艺术欣赏所再创造的意象与艺象之关系问题,或者说艺术批评的地位问题。就前者来说,朱志荣认为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动态生成的心象,每一次审美活动都伴随着意象的生成,相较于其他审美活动,艺术欣赏中所创构的意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审美对象有着特定的指向性。朱志荣认为“艺术创造的核心就是意象的创造,艺术欣赏的核心就是意象的欣赏”{43},这也就是重新界定了艺术鉴赏和接受的对象,将艺术鉴赏的对象从艺术作品替换为艺象。虽然他一再强调艺术语言参与了艺象的创造、不是传达的工具而是艺象的肌肤等,但是将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艺象作为欣赏对象,仍然是对艺术作品本源地位的取代。就后一方面而言,朱志荣在美学领域建构出作为审美机制研究的意象创构论,当将其移植为艺术批评原则时难免发生矛盾。艺术欣赏是审美活动,但艺术批评是理性观照活动。艺术欣赏指向意象的创构,但艺术批评除了关注意象创构的效果以外,还关注该效果产生的原因,即对艺术技巧的揭示和艺术规律的总结,这些是溢出艺象批评之外的。艺术批评作为一种阐释,是对艺术活动中所蕴含的重要的人类文化底层逻辑的揭示,以出色的阐释使得在艺象创构方面表现平庸的艺术作品焕发活力的例子并不少见。脱胎于意象创构论的艺象论在艺术批评领域固然有其优势,但是艺象也必须超越其美学的理论语境而全面参与到艺术批评实践中去。
对艺象理论的完善而言,上述两个方面尚需有更深入的阐释。笔者认为或可通过以下方式加以完善。首先,中国古代的意象思想是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因此“言—象—意”的统一不只发生在艺象层面,也发生在意象层面。如果回到意象论述的原初语境之中,换一种视角来看,可以发现,“言—象—意”之间并不是线性的递进结构,而是一种回环结构。以王弼的言论为例,他写道:“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44}“言”与“象”之间、“象”与“意”之间存在明显的往复结构。也就是说,表达者由“言—象”承载其“意”,其“意”既是“言—象”的出发点,也是目的所在;而对于“言”的阅读者来说,“象—意”则只有通过“言”才能抵达。王夫之在认同王弼“言—象—意”结构的同时,提出了对“得意忘象”的反对,《周易内传》中写道:“自王弼有‘得意忘象’之说,而后之言《易》者以己意测一端之义,不揆诸象,不以象而征辞……求以见圣人之意,难矣。”{45}王夫之反对“忘象”,而强调对阅读者而言,必须强化“言—象—意”之间的依存、往复关系,在对“言”的反复涵泳以及由“象”到“言”的往复过程中求得“意”的深味。因此,对意象创构而言,意象的生成性不仅体现在“意”的多变与“象”的多样性上,还应该体现在“言—象—意”之间的回环深入结构上。对艺象来说也是如此,艺术欣赏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反复阅读和品味,在这个过程中,“言”与“象”“意”之间是彼此巩固、逐步深入的。由此而言,艺术作品中的“象”与“言”是一体共存关系,艺术作品与艺象也是如此。其次,艺术批评与艺术欣赏活动二者却必须区别开来。正如王夫之所言,“言可以著其当然,而不能曲尽其所以然;能传其所知,而不能传其所觉”{46},也就是说,艺术语言是有局限性的,对“所以然”“所觉”的洞察必须通过理性洞观的语言来加以揭示,也就是批评语言。审美活动是感性活动,对审美活动规律的揭示却是理性活动。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并不基于感性或理性二元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基于超越性的“道”。艺与道的关系贯穿古典艺术创作论和艺术品评的始终,从先秦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7}到清代的“艺者,道之形也”{48},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视角,在这种视角中,艺术创造是直接师法于“道”的,艺术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家心中之象的传达,还是对艺术家所领悟到的“道”的传达。正如朱志荣所讲,“意象作为审美创造和艺术创造的产物,其最高境界必然是体道的”{49},当代艺术渗入日常生活,在创造审美情境、提升审美能力的同时,也有将艺术庸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从意象创构论的角度来看,“艺—道”关系这一视角仍然是艺术批评的重要视角。
总而言之,“艺象”思想伴随着意象论述而发展,是中国特色的意象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艺象”的提出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意象思想资源,也吸收了现当代以来美学发展的成果。“意象”是心物交融所创构的审美结晶;“艺象”则指称的是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意象。相较于偏重于美学理论建构的“意象”,“艺象”则既是艺术作品中作为呼唤结构的审美意象,也是艺术欣赏的对象,对艺术活动有着较强的阐释效力。在当代美学语境中,如果说对“意象”的讨论是对审美活动及其规律的形而上探究,那么对“艺象”的讨论则是对审美与艺术活动的具体描述。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来看,意象是尚象思维下各种产物的共同原点,这个原点在纵向上贯穿了人文学科从古至今的发展,在横向上则提供了一个艺术学、美学、文学研究等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地带。“意象”美学的理论建构是与中国特色的艺术活动相表里的,因而“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核心术语;与之相应,“艺象”是美学与艺术学相交叉的枢纽,有其独立的理论地位。从“艺象”的视域来反观“意象”,也能够对相关问题如意象的结构、内涵、创构过程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注释:
{1}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
②③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第31页。
④{25}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第246页(该书1997年《审美理论》为第1版,2005年第2版更名为《中国审美理论》,2013年修订再版)。
⑤王怀义:《朱志荣意象创构论美学析疑》,《艺术探索》2011年第5期。
⑥韩伟:《美是意象吗——与朱志荣教授商榷》,《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⑦{11}{22}{31}朱志荣:《论意象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答简圣宇等教授》,《东岳论丛》2019年第1期。
⑧{15}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内涵问题——答冀志强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⑨{13}{26}{29}朱志荣:《意象论美学及其方法——答郭勇健先生》,《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
⑩陈望衡:《审美本体、哲学本体及艺术本体》,《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12}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14}朱志荣:《论美与意象的关系》,《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16}{17}{20}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第243页、第248页。
{18}{21}施旭升:《艺术即意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第131页。
{19}朱志荣:《论艺象的创构》,《江淮论坛》2020年第5期。
{23}简圣宇:《论意象生成的递进过程》,《人文杂志》2021年第2期。
{24}{28}{34}{35}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
{27}朱志荣:《中国文学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30}{33}{41}{49}朱志荣:《审美意象本体论》,《复旦学报》2021年第4期。
{32}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36}简圣宇:《“概念间性”:中国传统意象范畴的词汇构成与观念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3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109页。
{38}相关辨析见王琢:《从“美术”到“艺术”——中日艺术概念的形成》,《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李建中、孙盼盼:《“艺”与Art:中西艺术观念的比较与会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9}高建平:《艺术边界的超越与重建》,《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2期。
{40}张法:《中国艺术观念70年演进——对中国型艺术学的出现—关联—发展—成就之反思》,《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2}田义勇:《“意象”研究钩沉与反思——兼论“意象”内涵及其审美特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3}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页。
{4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45}{4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67页、第566页。
{4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页。
{48}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自叙。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陈娟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2022/10/25/119753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