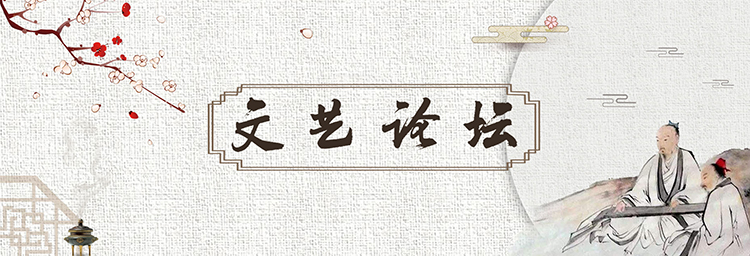

唐诗人,或火山的沉寂时刻与爆发时刻
文/李德南
如果时光倒流到2013年,那天的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青年,沿着绿树成荫的人行道,穿过许多红墙绿瓦的建筑,中间可能还走了一点弯路,然后才走进一栋宿舍楼。具体是在哪一层楼,我有点记不清了,应该是三楼吧。听到敲门声,我出来开门,看到一个偏瘦的、斯斯文文的青年。他问,请问是李德南吗?我答,是的。“我是唐诗人,这是我的真名。”
这是我与诗人第一次见面。
那一年,我正在中山大学师从谢有顺教授读博,诗人则因准备报考而前来中大旁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话题颇多。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这大概得益于两点:我们平时都话不多,而见到还不太熟悉的人,我们都多少会生怕冷落对方,会下意识地多说一点。此外,那时我宿舍里的一些书成了彼此友情最初的桥梁。围绕着书,还有书的作者,书中的观点,我们聊得颇有兴致,也颇为投入。
此后不久,诗人如愿地考进了中大中文系。我们见面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了,对诗人我也开始有更多的了解。仍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如果要为诗人其人其文找一个比喻,大概可以说,诗人如一座火山。在日常生活中,他时常是沉默的,正如火山的沉寂时刻;不过,一旦进入到阅读和写作中,诗人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正如火山的爆发时刻。
诗人喜欢阅读,读书的速度颇快。他在暨南大学做博士后期间,还有博士后出站留校工作后,先后主持了几个读书会。是几个而不是一个,我想这多少能说明他在阅读上的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张罗见言读书会,在一个微信群里和朋友们讨论读什么作品。按照惯例,读书会的活动是每月一期,每期读一本书。现在问题来了,围绕着三部长篇小说,到底读哪一部,先读哪一部,大家的意见不太一致。诗人说:“那这期就三部作品一起讨论吧!”他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那时候,他尚在暨南大学做博士后,年轻,尚未成家,时间充足,精力充沛,正在最好的阅读状态。那次活动他是主持人。在和大家讨论作品时,诗人游刃有余,思想火花不时闪现,正如一座有着巨大能量的火山。
诗人和周明全做过一次访谈,其中谈到,诗人在本科阶段就大量地读了宗白华、朱光潜,还有柏拉图、贺拉斯、尼采、海德格尔等美学家或哲学家的著作。像尼采、海德格尔、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很多人都是在硕士、博士阶段才会去阅读的,甚至在哲学专业里面,有的教授穷其一生能真正读通其中一位,比如成为海德格尔专家、康德专家,就已经很了不得了。诗人在本科阶段就能去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无疑需要勇气,也需要热情与才情。
比之于他的阅读状态,读诗人的文章,更能感受到火山爆发式的情景。诗人在中山大学读博期间,我曾有好几次约他参与写文章或做文学访谈,每次他都能很快就完成,提前交稿。黄子平教授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个是喜欢阅读,另一个是害怕写作。两个说法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振效果,也让不少文学研究者、批评家深有共鸣。我就是如此。每逢要写文章,我总得或多或少地做心理建设。诗人则既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在他的文章中,时常能看到喷涌而出的思想火花。这和他热爱阅读、善于思考是有关的。诗人很早就展现出良好的阅读准备和学术直觉,确定了可以持续用力的学术领域——围绕文学与恶展开研究,在文学伦理学的领域持续耕耘。这既是他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也是他在读博期间,甚至更早就开始着力关注的领域。在《恶、罪与审美》《恶的审美伦理——理解现代叙述中的“恶”》《“恶魔性”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策略》等文章里,诗人曾谈道,他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现实世界并不缺乏恶,而人们却对恶知之甚少。此外,在文化、文学、哲学中,恶都是一种重要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理解恶,也是人之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甚至是过上良好生活的必经步骤。这一学术领域的确定,充分体现了诗人的学术敏锐。这是一个学术难点,也是一个学术热点,要做好,要做出新意,并不容易。诗人收入《文学的内面》一书中的文章,就多是围绕这一领域而展开的。他能围绕这一学术领域而展开探索和思考,同样体现了他的勇气、热情与才情。
诗人硕士阶段读的是文艺学专业,擅长思辨,对于法国哲学尤感兴趣。我读他谈文学伦理方面的论文,还有关于陈希我、迟子建、王威廉、盛可以、路魆的作家作品论,觉得在修辞风格、理论资源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尤其是和他的同龄人相比,辨识度是很高的。他的文章,文风汪洋恣肆,充满激情,也有理论的热情。读他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他在思考上的迅疾与凌厉,能感受到一种倚马千言的快意。当然,写得太快,也可能会相应地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文章在表述上并没有很精确地传达他的意思;在有的文章里,他对要探讨的问题还没有想得很透彻。有一个阶段,诗人对于这样的困惑本身就是看重的。比如在《行动之内,更有良知——由〈80后,怎么办?〉引发的思考》这篇文章中,诗人谈道,他知道自己关于《80后,怎么办?》一书的看法尚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又认为这一思考的过程,包括未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他乐于和大家分享这些困惑,也乐于袒露自己的困惑。
读诗人的《文学的内面》,我会想起巴塔耶的《文学与恶》。这两本书都有巨大的写作激情,有难以掩藏的锋芒。而正如巴塔耶所说的,《文学与恶》中“有些文章有时需要重写,因为当初我的思想常呈纷乱状态,只能作模糊的表达”①。类似的时刻,在诗人的写作中其实也有。诗人在读博一、博二时,曾写过关于城市文学方面的文章,其中虽然有许多的思想火花,不乏洞见,但是在论述上尚不够清晰,对相关论题的论述并没有很好地推进。后来,经过诗人多次修改,这篇文章在表述和思想深度等方面,就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喜欢阅读、喜欢写作,使得诗人很早就打开了学术视界。他有思考的禀赋,又善于倾听,尊师重道。他后来在谢有顺教授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也包括在暨南大学师从蒋述卓教授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所写的不少文章,都显示出大格局和大视野,在表述上既保留了思考的锋芒和热度,也有了沉稳的气度。这依然是唐诗人,却又是一个脱胎换骨后的唐诗人。
在读硕士时期,诗人受法国哲学,尤其是受德里达、巴特的影响颇深。他在硕士阶段,还有在博一、博二期间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带着解构主义的气息,有着怀疑的精神。解构之于他,是言说的方法;怀疑之于他,则是思想的精神。他还时常从身体、恶等不太为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所重视的议题入手,去运思,去言说。有一个时期,诗人写文章时常用提问的语气。他喜欢用问号,连续地使用问号,并不是因为缺乏自信。相反,他的发问当中,时常有着难以掩藏的锋芒。他是有见解的,可是他并不期待一个必然的答案,也不执着于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或者说,终极答案在他看来,是可疑的,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系列文章,也时常显示出激进的一面。他的怀疑,指向他人,更指向自身。当他展开批评时,他不是把自己剔除在外的,他对自我的批评,比对他人的批评远为严苛。他的求真意志,是在这样一种张力中迂回地生成和表达的。如他所说:“我之所以对文学批评保持着持续的热情,不是喜欢批评他人,而是可以通过他人的作品感知一些全新的生命经验,可以在辨认差异中不断地自我批评、自我完善。批评家不是骂人的专家,而是可以借着作品与世界与作家与自我真诚对话的人,这种内在的对话既补益于批评家的自我建构,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去完成新的调整。”② 这使得他的写作和研究,既有锋芒,也不乏包容。
在最近几年所写的文章里,诗人不断地自我校正、自我提升,对于文学伦理的思考也日渐深入。在经过偏重解构的阶段后,诗人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都有所调整。诗人最早发表的一批文章,都致力于“揭橥恶”,对致力于“揭橥恶”的作品高度肯定,勇于为之申辩。有时,甚至会申辩过度。这是应该尽力避免的。然而,哪位批评家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完全没有偏见或误差的批评,是理想,却很难完全实现,“即使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
在近期的写作中,诗人在继续“揭橥恶”的同时,也致力于“呵护善”,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变得更为辩证。这样一种区分,不是绝对化的。比如在他较早时完成的一篇关于迟子建《群山之巅》的文章中,他就认为:“残酷的现实在作者的叙述中,没有让恶扼杀善,也不让罪抹除人性之光。她书写出了发自人性深处的光芒,她让这些光穿透了文本中的黑暗,也穿透了读者沉郁的心灵……她始终保持着对时代黑暗、罪恶的凝视,却又能够用自己坚信的灵魂观念赋予笔下人物实诚的赎罪特征,实现了对现实的凝视,同时也守护了人的纯正灵魂!”③不过,在更早的时候,他确实更喜欢那些能不管不顾地深入到恶当中的写作。而在最近的阅读和写作中,他对那些绝望与希望同在、黑暗与光亮并存、凌厉伴随着暖意的作品,对更为复杂难辨的作品,也有了更多的肯定。比如在关于郭爽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的一篇文章中,他就指出:“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是可清楚看到的一些庸常生活,它们没有什么光彩夺目的元素,普通得让我们看不到意义所在。这些人物、以及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件,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今天所谓伟大历史而言,是一种普遍的无名状态。这种无名,就是一种巨大的晦暗存在。但是,看不到意义难道就不活了吗?自然不是。郭爽真正要表现的,不是庸常无望的生活本身,而是表现那些潜藏在琐碎日常中的具体生命如何维持活、如何开展爱,她要叙述出内在于这些平凡个体的生命意志,这是壮阔一面,也是光之所在。”④此外,诗人既保留了以往就有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又加重了对不同道路的寻找与开拓。他的《共和国精神与中国当代小说70年》《后虚无主义写作——论“90后”的青春叙事》,还有和蒋述卓教授合作的《文学批评与思想生成——建构一种广阔的文化诗学理论》等文章,代表着他在不同领域的新思考。
由于诗人所选的一些议题的性质,也和他自觉选取的言说方式有关,读他有的文章,也许首先得到的并不是愉悦,尤其是审美的愉悦。正如火山的爆发,那是一个力与破坏并存的时刻。正如不怎么起眼的火山灰其实有着丰富的养分,诗人的文章也蕴含着独特的思想养分,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品,对于那些关注存在苦难的作品,诗人投入了许多的精力,进行富有洞见的解读,予以道义上的支持。他认为:“面对苦难,文学最有挺入其中的必要,作家应该努力用笔尖进入人的苦难遭遇中,深入人在面对苦难时的精神世界,去揭示人在灾难、疼痛面前所能出现的人性可能与灵魂状态。”⑤诗人喜欢这些作品的锋锐和刺痛感,也认为阅读这样的作品可以锻造人的伦理感受。他的《盛可以论》等文章,也深得作家和读者的认可,成为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献。
在答应诗人写这篇印象记后,我曾很快就定了一个题目,叫“临界状态与片面之词”。在我看来,要理解诗人,“临界”是一个重要的词。这大概有几重意思。首先,他虽然姓唐,名诗人,但其实并不怎么写诗,而是主要从事文学研究、文艺批评。这是一种临界状态。此外,诗人生于1989年。在以代论文学,也包括论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诗人会有一种临界的感受:“把我列入90后,我就有点不舒服。不过,把我列入80后,我也不舒服。在80与90之间的那个点上,该属于什么后?我是游荡在所有‘后’之间的孤魂野鬼。我对于代际划分,从来就不觉得有多么重要,甚至总想着从边缘、异质去打破各种代际隔阂。”⑥而从当下的现实处境来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处于临界状态中。这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在加速度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改变着人类自身。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文主义的知识与价值都受到巨大的挑战,形成了存在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等层面的多重危机。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转折时期,人们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具体到诗人的个人生活,他已告别事情相对少、也相对单一的读书时期,不得不迎向层出不穷的事务。最近和诗人见面,我们除了一如既往地对许多问题有探索的兴致,也发现诗人逐渐多了一些迷惘和倦怠,甚至有点悲观。类似的感受,在我也是有的,只是很少表露。
对于种种问题,我和诗人有共识,也有分歧。我们都认为答案不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唯一的。期待诗人能够找到他切实想要的答案和道路,自如地把握他的沉寂时刻与爆发时刻。我相信诗人有这样的能力,毕竟,他是一座充满能量的火山。
以上种种,是我关于诗人的部分印象。印象记或许终究是有些片面的,以上这些不过是我的“片面之词”。更为重要的,当然是去认识诗人本人,去读诗人的文章。我想,生活中的诗人,写作中的诗人,会比我所理解的诗人更为准确、远为生动。
注释:
{1} [法]巴塔耶:《文学与恶》,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唐诗人:《批评即对话》,《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③唐诗人:《风俗、道德与小说——论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摘自《文学的内面》,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105页。
④唐诗人:《生活本身自带光亮》,《文学报》2018年12月20日。
⑤唐诗人:《比苦难更痛的是心死——论东西的〈篡改的命〉》,摘自《文学的内面》,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
⑥唐诗人:《代后记:成为学院批评家——周明全访谈唐诗人》,摘自《文学的内面》,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李德南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2022/10/20/119579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