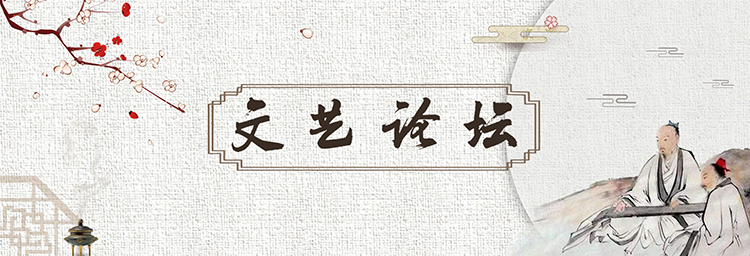

电影《代码46》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论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形象
文/蒋卓伦 张建安
摘 要: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呈现出敌托邦与异托邦两种城市形象,作为敌托邦充满了暴力与危机、封闭与限制、疏离与冷漠;作为异托邦显得或陌生、或隔离、或混杂,二者是他者空间与未来时间、虚构与真实在“未来上海”中相交融的结果。西方科幻电影采取了从再现到拟像的方式来建构“未来上海”形象,“未来上海”形象作为叙事空间在电影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故事容器与叙事动力的叙事功能,现实中上海的未来感与地方感成了“未来上海”形象的建构基础。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形象建构的启示意义,主要有敌托邦背后人类对科技发展隐含危机的恐惧与焦虑,以及异托邦背后西方对东方的自我投射,其实质仍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延续。同时,亦可见科幻电影对城市的“未来考古”价值,以及科幻电影对城市形象建构的局限性。
关键词:西方科幻电影;“未来上海”;敌托邦;异托邦;形象学
上海,自从1924年被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魔都》①一书中将其定义为“魔都”后,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因为其传统与现代并存、东方与西方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以及长期处于高度繁荣和快速发展,持续给世人以变化幻莫测和日新月异的“魔幻”感,“魔都”实至名归。近年来,上海这座城市常常出现在西方科幻电影中,“魔都”上海的“魔幻”内涵又增添了一些面向未来的意味。中外文学史上,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可以成为表征城市和认识城市的重要方式。作为当今最受欢迎的电影类型——科幻电影,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科幻电影,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未来上海”城市形象。英国科幻电影《代码46》(Code 46,2003)和美国科幻电影《致命紫罗兰》(Ultraviolet,2006)、《神奇四侠:银魔现身》(Fantastic 4: Rise of the Silver Surfer,2007)、《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2009)、《环形使者》(Looper,2012)、《她》(Her,2013)等作品,都展现了幻象中的“未来上海”形象。
一、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形象的多面性
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有虚构和真实两种,前者没有现实城市为原型,往往如空中楼阁一般虚幻;后者有现实城市为原型,集中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伦敦、巴黎等西方大城市,当西方科幻电影将视野逐渐扩大到了东方,上海这个东方明珠就是首选对象之一。总体而言,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呈现出敌托邦和异托邦两种空间形象
(一)“未来上海”的敌托邦形象
敌托邦(dystopia),也称为恶托邦、反乌托邦等,是乌托邦(utopia)的反义词。“乌托邦”一词源自希腊语,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即十分美好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依靠想象的地方。相应的,敌托邦也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依靠想象的不美好的地方,敌托邦常常就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走向其反面的结果。乌托邦和敌托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虚构极度美好,后者走向另一个极端。
“未来上海”在西方科幻电影中,或是暴力与危机之城,或是封闭与限制之城,或是疏离与冷漠之城,都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倡导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背道而驰,是典型的敌托邦形象。在《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中,上海市中心发生了严重的有毒物质泄漏,人们拼命地逃出城市,上海成了汽车机器人对决的战场,大量的建筑、道路在打斗中遭到严重损毁,整个城市岌岌可危。《神奇四侠:银魔现身》中,拥有超能力的神奇四侠为了拯救地球,最后与大反派“银影侠”在上海决一死战,城市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致命紫罗兰》中生化人女战士紫罗兰在城市中与军方展开搏斗,不时地出现上海东方明珠塔,城市成为上演暴力冲突的舞台。《环形使者》中,时空杀手乔为了躲避追杀逃亡到上海,他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在这里继续为钱杀人,又在这里被人追杀,并痛失爱人,城市的天空每天都阴霾笼罩,仿佛危机四伏。《代码46》描绘的“未来上海”,城外是荒漠,城外人拼命想住进城内,管理者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进出,于是城内城外两极分化。城内虽是繁华的都市,但人的生活并不如意,情感处于孤独状态。影片开头男主角威廉刚到上海时,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问司机:“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司机回答:“不是生活,只是存在着而已。”《她》中有大量上海的城市场景,电影讲述了一个真实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谈恋爱的故事,城市以大量陌生人聚集为特征,人与人除了基本的寒暄之外,深入的情感交流,城市已然变成了人类情感的荒漠,每个城市人仿佛巨大城市空间中的一座座孤岛。
(二)“未来上海”的异托邦形象
上海作为一个东方城市,在西方科幻电影中的形象,必然是西方视角中的他者,当这种他者面向的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成了相对于主体的异托邦。异托邦(heterotopia)原为医学领域的专业词汇,指错位或冗余的器官组织,也可作动词使用,意指器官的移植。从构词法来看,“hetero”意为“其他的”,“topia”同样也是乌托邦(utopia)和敌托邦(dystopia)的词根,意为“地点”“场所”,都是空间概念。异托邦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福柯于1967年提出,不同于乌托邦和敌托邦都是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虚构空间,异托邦则是指一种实际存在但又不同于自身的“他者空间”(the other place)②。具体来说,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其异托邦形象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陌生。上海,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无疑是个典型的异托邦。《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中上海郊区挂着“帝国进出口”的工厂招牌和《神奇四侠:银魔现身》中上海满大街的汉字招牌都用文字营造了一种直观的异质文化环境。《代码46》中,男主角威廉刚到上海,从落地机场开始,他就像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一样好奇地观察和体验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第二,隔离。《代码46》中的“未来上海”城内城外天壤之别,进出必需通行证。通行证由斯芬克斯公司掌握,女主角玛丽娅在该公司的上海分部工作,她曾经在城外的荒漠里生活了十年才得到了入城的通行证,深知城外生活艰难的她,偷偷帮人伪造证件,而男主角威廉正是来上海调查此案件的。电影将玛丽娅设定为用威廉母亲的脑细胞克隆出来的克隆人,与威廉相爱并怀孕,违反了当时有关基因控制的“代码46”禁令,于是被强制堕胎并驱逐出城市。在“未来上海”里,人的自由流动甚至情感都是被严格监控的,“斯芬克斯知道一切”,活像福柯的“全景监狱”③。
第三,混杂。在上述几部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混杂着地缘、文化、种族大相径庭的各色人等,似乎显示着上海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甚至还包括机器人、克隆人、超人、外星人,但相互之间的壁垒和矛盾却无处不在,于是要么兵戎相见,要么冷眼旁观。尤其是《她》中,城市表面热闹繁华,混杂聚居的城市人看似在物理空间上越来越近,但在心理空间上却越来越远。
(三)敌托邦与异托邦交融的“未来上海”
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的异托邦形象,其陌生、隔离、混杂的特征,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不平常、不自由、不安全,这与“未来上海”的敌托邦形象有诸多内生逻辑关系,具体表现为两点。
第一,时间与空间的交融。异托邦和敌托邦在时空维度上,一方面是空间上的异质,即让对象位于远离主体的远方;另一方面是时间上的异质,即将时间推向未来。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就是这种他者空间与未来时间两种形态交融的存在。《代码46》中的“未来上海”是威廉从美国西雅图飞越了大半个地球“闯入”的异托邦,那时的克隆人已经合法,玻璃投影电视、VR拳击游戏等对于当时(2003年)尚属未来科技成果,难怪片名也被翻译为“未来密码46”。《环形使者》的故事时间设置于2044年,时间旅行已变成现实,黑帮组织非法利用该技术“干净”地杀人,专门负责处决那些被从未来传送回来的人的杀手叫“环形使者”,但他们最终必须杀死传送回来的未来的自己完成“封环”,才不会给顾主留下麻烦。“环形使者”乔因为破坏了这一黑帮规矩,不得不飘洋过海逃亡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这里就是远离西方世界的避难所。
第二,虚构与真实的交融。“未来上海”中的“未来”是一种将时态推向未来的虚构形态,不必对当前和未来的现实负责,而“未来上海”中的“上海”确是真实的空间概念,“未来上海”是将未来时间和现实空间相交融建构的科幻电影文本中的城市。《代码46》将阿联酋迪拜黄沙漫天的城外景观与上海现代建筑鳞次栉比的城内景观,共同建构出一个城内文明与城外蛮荒相互对立又隔绝的“未来上海”。《环形使者》中,当乔站在外滩望向黄浦江对岸时,除了东方明珠电视塔和环球金融中心大厦等最典型的摩天大楼之外,还出现了几栋现实中并不存在、规模更宏伟、设计更奇特的超高层建筑。而乔与他的中国妻子为躲避追杀而隐居的上海郊区,其实取景于广西三江县的程阳八寨。根据《她》中洛杉矶的天气预报、男主角西奥多曾在《洛杉矶周报》工作等相关信息可知,故事发生地其实设定为洛杉矶,但却有不少的画面取景于上海,上海成了洛杉矶的“替身”,上海与洛杉矶的画面交替,组成了一个既像上海又像洛杉矶,或者说两者都不太像的虚构的未来城市。
二、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形象的建构艺术
西方科幻电影如何建构出敌托邦与异托邦交融的“未来上海”形象,既有影像文本不同于文字文本、科幻电影区别于非科幻电影的因素,又有叙事空间在科幻电影中独特的空间叙事功能的因素,同时存在上海这个东方的国际大都市历史与现实的自身因素。
(一)从再现到拟像的“未来上海”建构方式
同样是影像中的城市,非科幻电影中的城市通常都有一个原型供模仿,影像对城市进行再现,看上去像不像成为前提条件,而科幻电影中的城市则可以不需要原型而直接虚构出本身不存在的城市形象,这就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到了鲍德里亚的“拟像”。“拟像”指的是后现代社会中极有真实感却没有原型、没有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鲍德里亚认为:拟像的“形象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是其自身纯粹的拟像”④, 拟像的“形象不再从属于外表序列,而是进入了仿真序列”⑤。在视觉化的图像时代,甚至可以说一切都是超现实的,是由符号所组成的拟像,一切真实也都是一种感觉上的真实,各种视觉符号取代了现实,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拟像社会。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就从简单的镜像式再现,转化成了比现实的上海更具真实感的拟像。《神奇四侠:银魔现身》和《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两部影片其实并没有亲赴上海取景,微观的街道、居民区、厂房等场景在摄影棚和当地唐人街拍摄完成,宏观的超人或机器人在高楼大厦间打斗的场景则主要交给后期特效。《代码46》中上海与迪拜、《环形使者》中上海与三江、《神奇四侠:银魔现身》中上海与长城、《她》中上海与洛杉矶,都运用了蒙太奇式的拼贴手法。《致命紫罗兰》中整个城市围绕着实验室而建,到处都是庞大而怪异的建筑群,时不常出现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拼贴在一大堆莫名的建筑群中,局部是上海,整体却哪里都不像。科幻的题材和未来的时态为“超真实”的拟像提供了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正应了“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的现在这个时代”⑥。
(二)“未来上海”中故事容器与叙事动力的叙事功能
空间作为叙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既可以是故事容器,也可以成为叙事动力。前者只是故事发生地,并不推动叙事,仅仅因为空间必不可少而存在,故事容器是可以随意替换的空间背景。当空间具有了叙事动力的功能时,则可以推动叙事,而不能随意地替换。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作为一种叙事空间,同样不同程度地具有故事容器与叙事动力两种叙事功能。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是一种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拟像,甚至可以没有原型,那么故事发生在具体的哪个城市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已设定的故事发生地即作为叙事空间的城市,塑造成适合该故事发生的环境,发挥出更重要的空间叙事的作用,令人相信那些虚构的未来故事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会发生,甚至只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必然会发生。在科幻电影中,空间的叙事功能取决于影片所建构出的叙事空间。包括《神奇四侠》和《变形金刚》系列电影,以及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等“漫威”(Marvel)系列在内的科幻电影,都是典型的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主题,电影中各国人民面临各种威胁,各大城市成了遭到各种破坏的敌托邦,超级英雄挺身而出,城市转危为安,世界恢复和平。这样的情节就自然将故事发生地设置为包括全球各大城市的世界各地,如《神奇四侠:银魔现身》涉及日本、埃及、拉脱维亚、撒哈拉沙漠、格陵兰冰川、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美国纽约、华盛顿、英国伦敦和中国上海,《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也横跨了中国上海、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多个世界大都市,这类电影简直就是一张微缩版的世界地图。然而,所涉城市在片中的叙事功能几乎都是简单的故事容器,除了代表性的建筑之外,较少独特且真实的城市特色,所涉城市还可以任意地被置换或增减,所以上海出现其中也仅说明自己是个国际大都市。而《致命紫罗兰》和《环形杀手》中的“未来上海”也并没有超出故事容器的叙事功能。相反,《代码46》中的“未来上海”的空间特征对故事情节的推动作用不可取代,对外严格封闭、对内处处监控、内外差别巨大的敌托邦城市,让玛丽娅为人制造假证这一反抗行为变得合情合理,才有威廉前来调查然后与玛丽娅相爱并让其怀孕的情节,才会引出片名的主题——“代码46”——克隆时代的基因繁殖禁令,所以此片中“未来上海”作为叙事动力的空间叙事功能至关重要。《她》中的“未来上海”虽是洛杉矶的“替身”,但它看起来更现代、繁华、美好,甚至像不现实的乌托邦。城市的这些特征,却给这样一部以都市人心灵孤独为主题的影片提供了足够起到反衬作用的空间环境,于是包括男主角在内的千千万万寂寞的都市人才会将情感寄托在人工智能上。
(三)未来感与地方感兼备的“未来上海”建构基础
尽管因为科幻电影的故事和城市都天然存在虚构性,故事发生的原本城市变得不再重要,但实际能成为科幻电影故事发生地的城市却屈指可数,那么西方科幻电影对上海格外青睐的原因,不仅仅是现实的上海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国际大都市。
第一,时间维度的未来感。城市的未来感,仅从视觉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城市的建筑景观超出了当前的整体风格,而符合人们对未来建筑的想象。未来建筑并不等同于批判复古主义、主张“暂时性和过渡性”⑦的“未来主义”建筑。建筑的未来感大体上需要大规模密集的摩天大楼建筑群和造型新异甚至奇特的单体建筑。上海陆家嘴拥有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为代表的摩天大楼建筑群,视觉景观上足以比肩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摩天大楼所组成的城市景观,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综合实力的视觉表征。上海最具符号意义的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其球体结合塔尖的造型一度被称为“未来建筑”,几部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均离不开这一未来建筑。
第二,空间维度的地方感。地方感是某个空间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让空间具有可辨识性,背后是这个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对于城市而言,城市中的建筑、街道等景观是城市空间中随时间而沉淀和更新的实物性文化符号,而并非通过简单模仿或拟像就能迅速机械复制或建构的空间形象。上海极强的地方感来源于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和更新,它是中国最早的近现代城市,在20世纪初就被誉为“东方巴黎”,吸引着中国内地和西方的投机者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来“掏金”,各国租界并立,社会环境复杂,上海就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一块法外之地,黑帮横行,犯罪丛生。繁华的另一面还潜藏着西方人眼中的“罪恶之都”,“魔都”的“魔”中或多或少地参杂有“恶魔”的贬义。更有甚者,上海(shanghai)在英文里是个动词,有“被欺骗、被强迫”⑧的含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上海既是充满异域风情和致命诱惑的东方城市,也是遍布混乱与罪恶的人间地狱,上海的地方感由来已久且不断累积。
三、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形象建构的启示意义
西方科幻电影中建构的“未来上海”敌托邦与异托邦形象,与现实中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形象显然相去甚远,这不免让人尤其是让中国观众产生迷惑和不满。然而,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形象却颇具启示意义。
(一)敌托邦背后的科技批判
并非只有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是一个糟糕的敌托邦形象,而是几乎所有的科幻电影中的城市都让人很悲观,究其原因,则要从科幻本身来追根溯源。科幻从字面意义而言即科学幻想(science fiction),是基于已有的或可能的科技而进行的虚构,这是与基于宗教或神话等非科技因素而虚构出的玄幻、魔幻、奇幻的最本质区别。然而,科幻本质上不是科学,而是以幻想和虚构为特征的文学艺术类型,这一点和其他的文学艺术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科技因素增加了幻想的合理性。
曾经,敌托邦来源于西方宗教中的末世预言,其中城市的毁灭意味着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但是毁灭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复兴与重生。随着现代性思潮的深入,科技渐渐取代宗教成为人类用来连接现在和未来的手段,而且是让人类可以主动地创造和影响未来、而非被动地等待未来的一项重要手段。具有科技理性的人类警惕着科技在人类发展史上扮演曾经由宗教扮演的上帝角色,为了警惕科技万能的新的乌托邦幻想,而将末世预言的敌托邦转加给了科技。于是,基于科技幻想的科幻就可能反过来成为对科技的反思,这种反思折射出人类对科技发展隐含危机的恐惧与焦虑。
西方科幻电影中“未来上海”敌托邦的背后均能看到这种恐惧与焦虑。《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和《致命紫罗兰》反思的是机器人和生化人技术对人类的利弊;《环形使者》假设了如果时空穿梭技术被用于作恶将会对人类有何危害;《代码46》批判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技术剥夺了人的自由,并且试图用爱情挑战克隆技术的科技伦理;《她》试验了一次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可能代替人类的情感;《神奇四侠:银魔现身》中地球可能被外星的黑暗势力所吞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科幻电影中敌托邦背后的科技批判,是对科技的辩证与谨慎态度,反映了人们不断进步的理性的科技观。
(二)异托邦背后的自我投射
尽管科幻电影中的城市形象基本都不美好,但当西方科幻电影将敌托邦赋予远在东方的上海时,异托邦背后的自我投射意义就不容忽视了。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西方是看的主体——自我,真实的上海是被看的对象——他者,“未来上海”就是西方看(以及想象)上海时从西方文化视野中所投射出的关于上海的镜像。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被东方化了”⑨,同样,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也被“上海化”了,即“未来上海”已不是其“实然”,也不是可能发展成的“或然”,而是西方眼中的“应然”。从这种“应然”的“未来上海”形象,可以发现西方将自我投射到他者的自我审视。
《代码46》中的“未来上海”是西方文化所排斥的“科技极权主义”笼罩的封闭城市和两个西方人发生不伦恋情的陌生城市;《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和《神奇四侠:银魔现身》中的“未来上海”是陷于危机并等待西方的超级英雄拯救的灾难城市;《环形使者》中的“未来上海”是西方的亡命之徒避难的法外之地;《致命紫罗兰》中的“未来上海”是西方的生化人以暴制暴的无名之城;《她》中的“未来上海”是建构西方的未来城市时用到的景观素材。王德威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异托邦就像是一种处理危机的空间设定。”⑩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就是将敌托邦投射到一个隔离于主流空间之外的异托邦中,以此来反观自己的危机。这就已经从简单的西方镜像,演化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复合文本,通过这个复合文本,西方可以反观自己,东方也可以一探西方。
归根结底,这样的投射其实还是由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延续。近一世纪过去了,尽管上海以及上海所代表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方视野中对上海形象的刻板效应难有根本改变,哪怕是西方科幻电影也不例外,只是多了些高楼大厦和科技元素,意识形态深处对上海和中国仍存在偏见和误读。
(三)城市与科幻的独特关系
城市与科幻电影的关系却非常独特。科幻电影所建构的城市形象,并非对城市原本的复制,而是可以超出原本的拟像,甚至可以是没有原本的纯虚构。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不是镜子一般的原样复制,不是地图一般的符号再现,也不是工程图纸一般创造现实的图形依据,更不是城市未来的可视化预测。那么城市与科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科幻显然不是关于现实的,而是关于未来的,且人类未来是属于城市的,因此,科幻应当是关于未来城市的。{11}这样一个三段论的推理揭示了科幻与城市尤其是未来城市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未来”是一个相对于现在尚未到来的模糊的时间概念,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倾向于将“未来”设置于现在可以影响或可以期待的近未来,而不是对现在意义甚微的无限遥远的未来;近未来也不会是过于短暂的以后,否则未来想象会因为马上可以验证而失去意义。科幻中的未来应当“足够长来放松限制短期结果合理性的束缚条件,但又不能太遥远而失去已知和熟悉的基础”{12}。同时,现在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时间概念,每一个现在对应的未来都不一样。科幻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而是对现在的寓言,在詹姆逊看来,科幻中的未来想象并非科幻未来主义的创作,而是一场“未来考古学”的思想实验。“‘考古’意味着‘回溯事实’,而‘未来’则指向‘尚未到来’。但这恰恰体现了科幻作品尤其是反乌托邦科幻作品的根本特点:在观念之中对尚未发生之事进行考古式回溯和反思。未来因此具有了历史性,而我们所处的当下则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现在。”{13}
然而,科幻电影对于城市形象的建构有着明显的局限,主要包括:一是大同小异。科幻电影中的城市,无论西方的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方的上海、香港、东京,除去少部分符号化的形象,其余大都属于无地方感的景观,可以随意拼贴。二是形象单一。无论原本城市如何,在科幻电影中几乎都是不美好的敌托邦。这是科幻与未来之间本质区别的表现。因此未来可能实现甚至正在实现的美好的绿色城市、节能城市是几乎不会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三是城市的空间叙事能力有限。从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上海”形象可知,城市空间对情节的推动并非来自充满细节且独具特色的城市环境,而是来源于科幻电影模式化的叙事方式。
总体而言,虽然西方科幻电影选择上海其实存在很大的经济因素,是一种“市场诱惑下的去政治化的文化示好”{14}。但是,通过对以上若干个案的分析依然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不能依赖西方科幻电影去讲述中国的城市故事,否则不仅跳不出敌托邦和异托邦的局限,更大的缺失还在于,中国城市在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城市问题,是西方很难看到也很难看懂的。然而,中国科幻电影对于传播中国城市声音、促进中国城市健康发展守土有责、任重道远。而至于真实的中国未来城市到底会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既不是美好的乌托邦,也不是糟糕的敌托邦,更不是他者的异托邦,而是存在于中国自己的面向未来的现在的城市中。
注释:
①原版为日本小西书店1924年版,最新中译本为[日]村松梢风著,徐静波译:《魔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法]米歇尔·福柯著,王喆法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③[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页。
④⑤Jean Baudrillard,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p.6.
⑥[德]费尔巴哈著,荣震华译:《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⑦[意]马里奥·维尔多内著,黄文捷译:《未来主义:理性的疯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⑧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⑨[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6页。
⑩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8页。
{11}[美]卡尔·阿博特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创新团队译:《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2}John R. Gold:Under Darkened Skies: The City in Science-fiction Film,Geography, 2001,86(4):337-345.
{13}张跣:《科幻文艺中的反乌托邦:关于科技与人的预言式探索》,《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14}张天潘:《另一种“东方主义”——好莱坞的中国元素背后》,《南风窗》2013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艺术教育研究所)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蒋卓伦 张建安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2022/09/02/1177982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