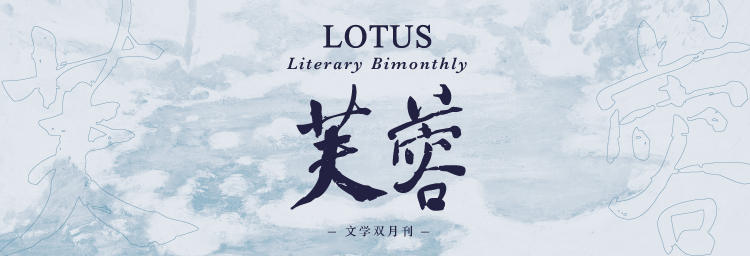

没听说有什么坏消息(中篇小说)
文/方晓
马格在想着要不要把芭比娃娃也扔进帆布袋时,传来了敲门声。他拉开铁栓已有点吃力,铁栓像是生锈了,半个月前,从茅山疗养院回来后他就再没有碰过它。门外站的是周仙,在冬天清晨灰白的光线中一身黑衣,脚边有个包裹。
“很抱歉。”周仙说,她嘴边呼出的白雾让声音听上去模糊不清,“本不该来打扰。我还不知要怎么补偿你们。”
这不是她来的目的,马格想。“如果你来是为这个,你可以走了。”他又等了一会儿才说。面前的这个女人,尾端染黄的头发上插着一朵蜡梅,脸上略施淡妆,眼部没有失眠的迹象,在冷风中显得消瘦,但或许说成苗条更合适。有股暗香向马格袭来,他挪开挡门的身体,像是指望她一眼就能看清黑暗房间里的杂乱,“我还很忙。”
“今天的局面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她说,但显然不是指此刻。
“我,我们没有怪罪过你们。毕竟,你们儿子也没了。我是想请你帮个忙。”周仙说。事情发生之后,她还是第一次登门,之前也没有。
马格露出克制厌烦的表情,准备一等她说完,立即拒绝。
“我打算今天去看唐桥,医院要求送些日用品。昨晚我给茅山疗养院打了电话,知道你要去,我原是想顺道去看下你夫人的。”周仙眼里有种求取信任的渴望,这让她看上去有些楚楚可怜。“但刚才,公司通知我九点前赶到机场,去外地参加展销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的业绩一直很糟糕。我不知道失去了孩子,要是工作也没了,还能怎么活下去。”
马格记不起来她做的是图书还是化妆品生意,但无论哪种,一个女人在清晨说这样的话,总犯不着去怀疑。“我把包裹带给唐桥?”他问。
“是的。第六医院。”
马格想了片刻,点点头。
“你见到唐桥,如果他愿意见人的话,”她突然蒙上脸的笑容近乎羞涩,“请代我解释下。真不知要如何谢谢你。”
“没必要。”马格说,又用眼光将她包裹了两秒钟,“像你说的,顺道。”
马格把芭比娃娃扔进帆布袋,似乎刚才已有什么替他做出了决定。芭比娃娃混在八音盒、铅兵、木偶、儿童漫画、泰迪熊之间,像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一团污秽的药棉。它曾是葛米儿最喜欢的玩具,但马格无从求证她是买给自己的,还是他们未出生的孩子的。唯一留下的是毛线针,说不定以后他也需要织毛衣打发时间呢。然后,他开始重新布设房间,半个月来,他需要从房间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杂乱中随时感觉到葛米儿的缺席。现在他努力回忆她去疗养院前的模样,挪动家具重归原位。
在门口,他像个要远行的人那样回望了室内一眼。他把帆布袋塞进车后座,再打开后备厢,将包裹扔进去,关上后盖;紧接着他又打开了,拉开包裹拉链,里面只有几件衣服、被单、牙刷和剃须刀。没有一样东西能体现出一个妻子角色的存在。他又在车里寻找了很长时间,确信能让葛米儿联想到孩子的物件全都被装进了袋里。
发动车后,马格才看见挡风玻璃前已经飘起了零星的雪花。五分钟后,他开过湘湖公园。搬来这里已有三年,他进去的次数却屈指可数,它是葛米儿喜欢来的地方。如果她走出家门,那一定是来了这里。转过一座山丘,他看见了那幢淡青色的二层楼房,是周仙的家。马格来过一次,受葛米儿指派参加唐禾的葬礼。即使在那天的悲伤和混乱中,那个家里每样东西仍然在它该在的地方,简洁、雅致但又不失奢华,能看出女主人的修养和顾家。与他家里不同。马格放慢速度开过去。门关着,但二楼窗户有条狭缝,墨绿色的窗帘在冷风中抖动。周仙那样的女人是不会容许这种现象发生的。马格确信她还在家。
雪渐渐大起来,看样子还要无休无止地下。马格开上大路,没有往南,沿这个方向直行三十公里就可到达茅山疗养院。他朝北慢慢行驶,数着路边的垃圾桶,在第四个垃圾桶边停下来,将帆布袋丢进去。然后他掉转车头,经过刚才的三岔路口,再往前两里是个小型加油站。马格看见一辆红色凯迪拉克停在那儿。有个女人坐在车里,车窗上的热气模糊了她的面容。一个男人正从营业厅里出来,向车走去。他穿着紫色皮夹克,稀疏的头发柔软地贴着头皮,看上去有五十多岁,面具般的微笑和举手投足都在表明他极力让自己显得年轻。直觉告诉马格,车里的女人就是周仙。他想,无论如何,在冬天偷情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路过第六医院时马格没有停留。即使唐桥急用包裹里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让他多等一会儿呢?对一个寻死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是急切需要的了。雪已经下得密不透风,虽然尚未在地面上沉积,但房顶、树枝和山巅都已被稀稀落落的白色覆盖。谁也不能担保世界不会突然一片白茫茫,分不清道路和沟壑,而他绝不想被困在茅山,在一个精神病院里过夜更是他无法忍受的。他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从山脚开始,就几乎看不见路了,有四次他不得不停下车,站到风雪中探清方向。在半山腰的直角转弯处,车熄火了。窗外是空落落的悬崖,他长时间盯着毫无目的的飞雪,脑海中空空如也,却又觉得身心俱疲。他像个狂躁的赌徒那样接连打火,觉得是在与死神赌运气,车再次启动后,像一片树叶在飓风中飘摇。快到疗养院时,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他认出其中有银杏、香樟、云杉和梧桐,它们被雪装饰着,深灰与洁白间杂。半个月前他第一次来时,无法辨认它们,这是否表明他已经从慌乱和悲凉中挣脱出来了呢?
葛米儿的主治医生已打过七回电话,除询问一些他理应知道的问题外拒绝透露任何情况。他最近一次在电话里也只是说,你来,我们当面谈谈。在医生办公室门口,马格停顿了片刻,似乎想做好面对最坏消息的准备,但念头刚冒出来他就动静巨大地推开门。已经没什么是不能接受的了。电话里声音苍老的医生原来是个刚三十出头的男人,或许才二十六七岁,黑框眼镜,板寸头,圆脸上耸立着一个几乎四方形的鼻子,他开门见山:“我们肯定,她精神没问题。”马格长出一口气,却立即又发觉自己并没有真的放松下来,他等着医生继续说下去。“但我们发现她脑袋里有个模糊的东西,还不太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然后,医生建议转到第一医院,说那里有同学能帮上忙,但马格未经考虑就拒绝了。“我们去第六医院,”他说,他觉得最好还是找一个理由,“离家近。”
这里不像精神病院,更像一处洗尽铅华的隐居地,马格走在木质地板上时这样想。像走在民国时代的废弃阁楼里,脚下的动静能穿透雪雾传到山那边去。看不到任何现代风格的东西,或者说一切都被无法察觉地隐藏了起来,包括可能会被想象成凶器的物件。休息大厅里有一些人在看电视,有一些人在看着看电视的人。或许他们都什么也没在看。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跑步,马格既听不懂旋律也不理解路线。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牵着护士溜达而不是被护士牵着的人,嘴边露出含义不明的微笑。吹口琴的人和敲饭缸的人显然是在合奏,声音古怪刺耳,但站在五步开外的书柜旁读书的人看上去没受到任何影响。这里一定有和他一样只是来履行探望义务的人,他逐一缓慢扫过所有人的脸庞,但最终承认自己分辨不出,没有鲜明的不同特征,或者说——没有区别。一个人从很远的角落里叫喊着跑过来,要抢夺他手中的花,他赶紧逃离了。
马格进病房时,葛米儿正在把少得可怜的几件衣物装进包裹,动作仿佛患有强迫症的导演在重复一个毫无必要的慢镜头。一个打扮得像神经错乱的花蝴蝶似的中年妇女,看见马格进来,立即爬下病床,兴奋地紧贴在他身后。一个年轻男人亦步亦趋跟着她,从他皱着眉头的紧张模样,马格判断他是个正常人。他悬在半空的两只手,与女人的衣服仅一寸之隔,似乎在防范她下一秒就要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她昨天才来。”葛米儿说,是在解释这一切,她永远都知道他在想什么。马格来不及点头,又听见她说:“她在这类行动中获得了存在感,或许还有融入感。”她的声音没有降下来,也没有温和几分,又直视着年轻男人说,“他当然也不想一直精神紧张,但这样做毕竟又可以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孝子。”
葛米儿总是说这样的话。她的判断力就在舌尖上。
马格将窗台上花瓶里的花取出来,已经枯萎了。是送葛米儿来的那天从山上采的,那天他问葛米儿还有什么需要时,这是她唯一提出的。马格将路上摘来的蜡梅插进去。
“你明知道我今天出院,还带来了花。”葛米儿语气清幽,但马格确定里面并无过多含义。他不知该如何解释,如果说在采摘时他还能理解自己的行为,那现在他也同样不理解了。“是啊,我还带来了花。”他说。
他慢慢俯下身,用夸张的脸部动作带有示范意味地嗅了嗅,然后看着葛米儿,希望她能明白指引,但她立刻将眼光转向别处。过去很久,她的声音又突然传来:“如果可以,我想请你把它扔掉。”冷漠,干燥,又不容置辩。马格愣了几秒钟,然后照做了。他把蜡梅扔到楼梯转口的垃圾桶里,站在那里抽烟,有几个人在雪地里踢球,他看了半天也弄不明白他们的规则,他想,要不要现在就独自离开呢?他回到病房。
葛米儿已双手抱腿坐在床上,像只寒冷的蚕蛹。马格判断不出对他的重新出现,她是悬心落地还是仍然厌烦。他站到窗边,雪雾浓重的视野里只有空落落的天空和两根横穿而过的电线,应该是一只鸟,一动不动地站在电线上,像电流里鼓出来的脓包。他听见葛米儿在身后轻声喊他。他回过身来,那一对母子已经并肩躺在床上了,都睁大眼睛看向屋顶,安静得像两只毫无生气的木偶。“我们饭后再走好吗?我请你。”葛米儿说。她的脸上竟然闪过一丝羞红。他有些奇怪,但只是点点头,他不知道该不该提醒她时间。
“这里只有一餐饭。食堂二十四小时供应,因为每个人突然想吃饭的时间从不一致,也从不固定。”她说。
他们坐在食堂的卡包里。葛米儿点了牛排、红焖羊肉和比萨,还有咖啡。这些都是她以前绝不会碰的。她甚至还想给马格要一瓶酒,但被拒绝了。“是啊,等会儿我们还要回家。”她说。她的声音变得清亮甚至悦耳,在马格听来,就像一道能穿透她心灵尘垢的强光。
“医生应该还没告诉你,”话突然在马格嘴边消失了,他等了很长时间它们才颤抖着重新回来,“葛米儿,我们还回不了家。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今天回不了。”
“那你打算把我送到哪儿呢?”她立即轻声问,没有不解、失望和愤怒,也没有任何质疑,就像他们不过是在玩一场过家家的游戏。
“为什么这么问?”马格说。他其实还没想好要把她带到哪里去。“我原本是来接你回家的。”他说。
马格不知道该不该希望雪继续下,好可以延迟做决定。但他第七次看向窗外时,葛米儿说:“雪停了。”他立即起身,隔着桌面拉起葛米儿,像得赶紧逃难似的说:“我们走。”
坐在车里,看着眼前吞噬一切的白色,马格双手紧握方向盘静静等了一会儿。他逐渐意识到心里正升腾起一股冒险的快活劲——这是他婚后还未曾有过的体验。“那么我们现在去哪里呢?”他问。
他没听到回答。他扭头看向葛米儿,她的脸比雪色还要苍白。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葛米儿终于开口说话,表情与其说在调侃,不如说有种刻意的俏皮,“如果你打算带我回家,还会问我吗?”
第六医院。马格想起自己对医生这么说。当时他很肯定,现在却好像不了,而且仍然不能确定唐桥的存在和这个决定有没有关系。
葛米儿窝在前座里,尽可能缩小自己,看上去像个正在受冻却又听之任之的布娃娃。今天葛米儿看他的第一眼,仿佛他只是个陌生人,现在几小时过去了,他们仍然没能亲密起来,但毕竟,不也没变得更加陌生吗?他似乎不该指望,他又做出什么努力来改变呢?他松开脚刹,任由车缓慢向前滑动,葛米儿已经闭上眼睛,似乎快睡着了,她的脸像块冰冻的大理石,所有温度都从上面无情褪去了,她并非出于对他的信任才躺在车里,而是对任何危险都无所谓,现在只有这点他能确信。
他们在相亲会上遇见,然后鬼使神差走到一起——如今看来再没有更合适的词汇可以形容。至少有三年时间,孩子仿佛一个绝缘体,远在他们之间的情感脉冲之外,但突然有一天,葛米儿说想要个孩子了,而且立即、马上、现在就要。从那一刻起,她就再也不能从这个念头中逃出来,它紧攥着她一秒钟也不放过。为可能即将到来但还远远没有影子的孩子,她准备了十个孩子都用不完的物品,除掉购买玩具和衣服,她还自制玩具和编织衣服。此刻像滑行在无边无际冰面上的车就是为孩子准备的——“如果我们有个孩子,那么我们就需要一辆车。”她说,“我们要送孩子上学,送孩子去同学家参加聚会,或者全家去郊游。”马格认为,想得太长远,是经济和精神的双重透支,但他如她所愿。里程数显示两万公里后,孩子仍然未能出现。但葛米儿没有放弃希望,反而以更热切坚定的步伐一往无前地走上了迎接孩子的道路。她去上胎教课,她买来《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从我们的孩子有意识的第一秒,就要让他明白这个世界。”马格想表达反对甚至抗拒,但她一本正经的模样总是让他不忍心这么做。她是出于对我们生活的希望或许还有热爱才会这样吧,他宁愿这样自我安慰,他无法辨析她错在哪里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从哪条岔路开始走上了歧途,他只知道,这条岔路一定是他没有身临其境过的。
然后,在他们试图制造一个孩子的第三年,葛米儿开始黄昏时在小区广场上溜达,逗弄见到的任何小孩,不久后整个白天都守在那里。有些电话打给马格,保安也来家中造访过几次——葛米儿惊吓了一些孩子。马格不知道要如何处理,但一点也没向葛米儿透露——似乎惧怕会引发什么更坏的后果,或许某一天她突然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只能也只需等待,就像等待一个伤口自动愈合。一个疯女人拐骗小孩的流言在小区里传了一阵子,马格不知道葛米儿听说没有,是否能意识到主角就是她,但从她身上看不出一丝迹象,没有难堪,也没有委屈。她没收敛但也没变本加厉,她从来没有真的带个小孩进入家门,在孩子们得到警告不再靠近她后,她也并未像个真的疯女人那样纠缠不清。很快,马格发现她有了新的交流对象,广场上的各种雕塑,鸟、马、人或者花。她把它们当成了孩子。然后,她伪装成孩子,表演给马格看,紧接着,她把自己当成了孩子,吵闹着要和电视里的孩子们玩。马格想不到的事情她全都做了。他从来不反对有个孩子,他或许本来也想要个孩子,但“孩子”这个名词从他的嘴边绝迹了,它和它所能代表的一切成了他生命中最令他头疼的东西,最糟糕的。
他在一天夜里用胶布封住了葛米儿的嘴。她的情绪也成了遮蔽他理性的烟雾。
第二天夜里,这个办法仍然控制不了她令他也要发狂的举动,他将她绑在了床上,狠狠地抽打她。
葛米儿消停了。有半个月,她成了一个无声的存在。只有那时时刻刻投来的怨毒目光,能向马格证明她还活着。
一天下午,她去了幼儿园。她被两个警察押回来,后面跟着园长。她在幼儿园里追逐、辱骂、殴打所有能逮到的孩子。“她怎么可以那样对待无辜的孩子?而且不是一个,是全部。”园长看向马格的眼光仍然倾泻着浓密的惊恐,仿佛他才是幕后指使的黑手。
让马格理解不了的是,园长的眼光像一根根箭镞射中他心房的同时,却也将那里的空洞填满了。她三十出头,身材匀称,哪怕在极力表现盛怒之中,举手投足依然满是优柔的少妇韵味。就像娇艳欲滴的花蕾,马格想。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碰过女人了,他笃定地道歉:“对不起。她疯了。”
他们搬走了。来到现在租住的山中。每天,马格要开车一小时才能到达他工作的电视台。附近只散落着少量建筑,偶尔有一些度假的人来居住,少见孩子,没有幼儿园。
即使到这时,马格仍然相信,并不是婚姻出了问题葛米儿才变成这样,她并非在指望有个孩子来挽救已经破灭的爱情。孩子,不过是一个她因为机缘巧合才突然意识到然后就想得到却一直得不到的东西。马格起先还试图把家中会提醒她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叫孩子的东西的所有事物扔掉,在大街上他甚至想成为她灵敏的眼罩,遮挡所有类似的事物。但很快他就放弃了,他坚持不了和葛米儿这样一个女人战斗,更不可能战胜她。葛米儿与那些事物之间仿佛有种天然的、无可抗拒的相互吸引力,能立即彼此发现和无限接近,然后无可挽回地成为对方全部情感的寄生体。也是在这时,马格才发觉有件事早已惊悚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一年多,他和葛米儿没有性事了。渴望有个孩子的葛米儿竟然丧失了对性最为浅表的兴趣,都懒得装一下给他看。他也变成了自己厌恶的人,不顾时机提出做爱的要求,而她要么无声拒绝要么激烈反抗。然后有一天,他强奸了她。
茅山疗养院已经被白雪掩盖,看不见了。原野变得开阔。除掉车轮几次打滑,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实际的危险,马格感觉自己是在用意念驾驶,就像花样滑冰运动员在空中旋转。葛米儿还在座位里紧缩着身体,衣领包裹了她的半张脸,但哪怕在睡梦中,她的眉宇间依然泄露出失落和痛苦。转过两个弯道就要看见第六医院了。他注意到葛米儿不知何时醒了,正盯着前窗外空茫的白色。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对彼此都做了什么,马格想问她,但没有问出口。过了一会儿,他问:“在想什么呢,葛米儿?”
“我什么都没想。”她立即回答。
“我们去以前那家医院?”他问。他是指主治生殖健康的医院,他曾逼迫葛米儿一起去检查。在城市另一头,与他们现在居住的山中有半城之隔。
葛米儿只是点点头。马格不明白这代表同意,还仅仅表示听见了他的话。半个月过去了,她还是这么不以为意,仿佛他随便把她扔到哪里,她都不在乎。马格压制住伤感,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他突然提出建议:“也许我们可以回家。”
“不,现在,我还不想回去。”
“为什么?”他问,“即使你脑袋里真有什么,它也不是一天生成的,所以缓几天也没什么。”他等着她反对,但没有等到。“我们还是先回家。”他又用强调的口吻说。
“葛米儿!”他侧头喊她。她也在看着他,但眼神里空无一物,连怀疑或者警觉都没有。他说:“葛米儿,请原谅,我还是想说,我们拥有彼此,这就足够了吧,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包括孩子。你答应我一声好不好?”
她脸上先是露出一种息事宁人的笑容,然后慢慢闭上眼。
在第六医院门口,马格停下车。“那就这里吧。”他说。(节选自《芙蓉》2022年第2期方晓的中篇小说《没听说有什么坏消息》)

方晓,1981年生于安庆,数学学士、法律硕士,现为法官,居杭州。小说散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作家》《山花》《江南》等期刊,有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
来源:《芙蓉》
作者:方晓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2022/06/13/113812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