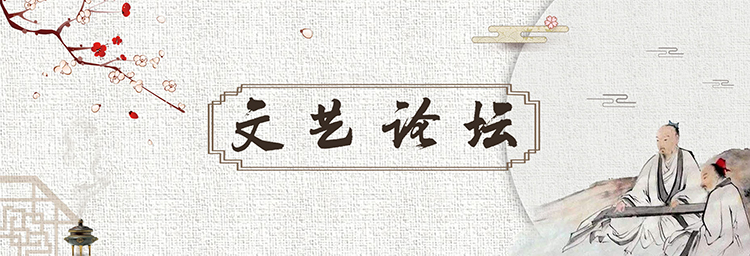

东亚四季美学观念的形成及其拓展
文/蒋述卓
摘 要:四季意识是东亚文学艺术的深层文化因素,它渗透并联系着东亚民族的宇宙观、时间观、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命运观。本文揭示了四季观念与东亚民族美学意识的形成,也具体论述了四季观念及其所展开的“月令图式”在东亚文学艺术作品叙事结构、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叙事中展开。探讨东亚四季美学的形成及其拓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东亚文学艺术风格和特征的形成,进一步理解东亚美学的独特形式和美学建构的奥秘。
关键词:四季意识;岁时节令;月令图式;东亚美学;叙事
四季意识是东方文学艺术的深层文化因素,它渗透并联系着东方民族的宇宙观、时间观、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命运观,也具体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叙事结构、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叙事中。探讨四季意识与东亚美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东亚文学艺术风格和特征的形成,进一步理解东亚美学的独特形式和美学建构的奥秘。
一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幅员辽阔,跨纬度较广,气候复杂多样,总体上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是世界上季风最典型、季风气候最明显的地区。灾害性天气频发,夏季多降雨,东南部有台风,冬季又有寒潮,西北部与北部还有冰灾等。由于农作物生长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原始初民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四季意识。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尚书·尧典》就记载,尧帝曾命羲氏与和氏为掌管天地四时的官。甲骨文中已出现春、秋二字。春秋时代,中国古人就利用土圭实测日晷,有了“二至二分”的观念,确定了冬至、夏至与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同时在宗教活动中有了四时之祭,提倡依时而行。{1}《左传》僖公五年里已记载有了分(春分、秋分)、至(冬至、夏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八个季节的区分,由此形成了岁时活动,并开了重视季节与政治的关系的先河。{2}《管子·四时篇》就通过古人对阴阳的观察认为天地通过四时寒暑交替来化育万物。阴阳的观念基于天气和气温的观测而来,它们的出现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诗经》中的《公刘》篇是周人的史诗,里面就写到他们的先祖后稷被举为农师,十几代之后传至公刘,公刘的一大功绩便是率领部落由邰迁到豳(今陕西旬邑),其中写到公刘到豳之后相地治田:“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所谓阴阳,就是山的向背寒暖,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关于节气以后又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至西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名称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先人对于四季时空变化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并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反映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四时的变化不仅成为影响万物生长凋零的原因,也成为人们情绪与心灵变动的动因。《诗经·豳风·七月》里不仅描写了季节的变化与劳作的过程及其与万物变迁的联系,也写到了春天里女子的思绪波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子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此,郑笺解释“女子伤悲”是“感其物化也”,这是符合春心摇荡而引起女子伤感的原意的。后来的《淮南子·缪称训》所说“春女思,秋士悲”也是指的这个意思。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小尾郊一说:“一般说来,四季之中季节变化最为显著的,对人类感情的震撼最为强烈的,是春与秋。”{3}他以魏文帝曹丕、曹植、西晋的张载、张协、刘祯、陆机、阮瑀等的诗句为例,指出“在文学中,把秋作为悲哀之物加以表现,以及这种表现的固定化,实际上是从魏晋之交开始的”。{4}“魏晋以后的文学中所表现的秋天景物,绝大部分是和《月令》一致的。”{5}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的春与秋短暂,由此产生出被扩展了的爱惜与寂寥之情,结果使之成了最易感受的、更深沉细腻的诗歌所表现的季节。”{6}在另一方面,古人还将四季的更迭、春秋的变化与时光的流逝联系起来,从而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时间的不可把握,在文学的表现中就将时间与空间的咏叹融为了一体,产生一种天气与人事、与人生交融的交感意识,也是美学意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伤春悲秋就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将自然与人事、与社会融为一体的集体无意识。
对此,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从《礼记·乐记》的“感物而动”到陆机的《文赋》“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明诗》《物色》和钟嵘的《诗品·序》,形成了一条“物感”美学理论的显著线索。其中尤以刘勰的总结最为著名。他在前人文学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于《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矝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7}中国古典美学中这一最有显著特色的“物感”美学就来自四季意识,它不仅是中国抒情文学的源泉,也是叙事美学的源泉。自魏晋之后,中国文学以四季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已经形成固定的格式和传统,并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逐渐丰富与扩张。
在东亚的日本,虽是岛国,南端和北端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的气候差异,但主要的部分位于中部处于温带。气候温和,空气潮湿,四季的变化较为缓慢而有规律,整个列岛处于柔和的环境之内。山脉贯穿于南北狭长的地形,森林较多,日本的文化形态是从对植物的感受与思索开始的,其美学意识也从对自然尤其是对四季的变化与感受开始建立的。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认为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基本语词中的最重要的概念都是来自植物的”。{8}“诸如静寂、余情、冷寂,也大多与植物由秋到冬的状态有关。”{9}中国学者也指出:“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对四季的变化、植物世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人从这种感受中找到了独特的四季自然之美。”{10}《古事记》《日本书纪》里就有了日本人对季节感的萌芽。《万叶集》中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作品,反映出日本人对四季的强烈关心和感受。全卷的许多诗歌是季节歌咏,有些卷如卷八、卷十则完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种类,分出“四季杂歌”和“四季相闻”,就是爱情的歌咏也与四季变化中的自然风物结合起来。日本赴唐学习过的弘法大师遍照金刚在其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一篇里也认为“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立意”。{11}到了中世的诗歌集《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和歌集》,目录中春、夏、秋、冬各自独立。而春 、夏又各分上下,所占比重尤重,季节感趋于明确。发展到近世的俳句,“每首俳句必须有一个季题,季题就是与四季有关的题材,范围极广,举凡与春夏秋冬四时变迁有关的自然界及人事界现象都包括在内”{12}。季题成为俳句的结构要素,它不仅增加俳句的姿色,也成了一种审美习惯。所以,日本文学史家久松潜一称日本文学是“季节的文学”。{13}
正是在对四时风物推移的感受和描写中,日本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物哀”美学。像中国对春秋的关心和感受一样,日本的《古今和歌集》里,也表达出对四季尤其是春日樱花的伤感和秋夜的愁思。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里写到源氏公子对四季的看法,“四季风物中,春天的樱花,秋天的红叶,都不可赏心悦目。但冬夜明月照积雪之景,虽无彩色,却反而沁人心肺,令人神游物外”,{14}这里面已经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情物相融意识。但日本人没有将这种对物与心的体察关系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 “物感”美学,而是在此创造出两个新的概念“物之心”与“事之心”,并将它们的合一称为“物心人情”,从而建立起他们独有的“物哀”美学。“物之心”是指人心对四季景物的感受,日本文艺理论家本居宜长指出:“例如,看见异常美丽的樱花开放,觉得美丽,这就是知物之心。知道樱花之美,从而心生感动,心花怒放,这就是‘物哀’”;“能够体会到他人的悲伤,是因为知道其悲伤所在,就是能够察知‘事之心’,而体味别人的悲伤心情,自己心中也不由得有悲伤之感,就是‘物哀’”{15}。本居宜长还举出一些具体的作品来谈何为“知物哀”,如《源氏物语》中《桐壶》卷有“虫声唧唧,催人泪下”;“听着风声、虫声,更令人愁肠百转”。《柏木》卷有“看到你,像庭院中的小树那样一无所知的样子,我更加哀伤”。“这些都是面对不同时节的景物而引起的物哀,而随着当时人心情的不同,对同一种景物的感受也有所不同,悲伤的时候所见事物是悲伤的,开心的时候所见事物是开心的。”{16}“物哀”是四季的美学,也是日本文学艺术的源泉与传统。
二
有“感物而动”的“物感”美学作为基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无论在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上都注重季节与人的交感、景色与人伦的比附。先秦时期的“山水比德”说发展到魏晋,则进一步演化成“心物交融”的理论,四季的转换也被染上浓浓的人间世情。季节的表达既假借物色来完成,也借人对时间与生命流逝的咏叹来赋予社会与美学的意义。此时,时间的流转带动了空间物色的改变,而空间的变化又在时间的流变中得以扩展,人的感情则是一条经线,将时空串联在一起,实现了心物融合。“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7}正恰切地道出了其中的心物交融美学结构的秘密。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如《诗经》中的《七月》,它是按照季节与农事的安排来展开叙述的。有些写四季的诗如误为陶渊明所作的顾恺之的《神情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其结构虽是按四时为序,但却是短诗,说不上典型,何况它所反映的四季的生机主要还是表现一种人的感情与精神的投射。在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子夜四时歌》里,有记载晋、宋、齐的清商曲辞,其中有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其中春歌中以花落隐喻青春的易逝而无人相邀,夏歌中以莲花隐喻青春的爱怜与爱恋,也有一种时令的感怀和淡淡的忧伤。乐府是民间的歌谣,他们与魏晋时期的文人对春秋的歌咏相呼应,一道成为文学对季节的表达载体。初唐时期一些文人的应制诗,分别以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仲秋、重阳和除夕等为题,虽是奉和之作,但也反映出当时宫廷的一些祭祀节令的仪式以及民间的岁时风俗。在当时的一些边塞诗、送别诗、闺怨诗里,四季的自然物象与作者的情感抒写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些著名的诗篇更是将伤春与伤世之感渲染到极致,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就以花开花落的循环往复抒发了光阴流逝的无情和人事变化的无常。四季意识也构成了初唐诗歌繁复的自然物象和时空咏叹相互交织的鲜明特色。
但到小说里,则有了按季节来叙事和展开情节与人物关系的艺术处理方法。“物感”美学在小说里便转化为一种人物情感、心理乃至家族的盛衰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情节叙事。
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了。
《金瓶梅》的整个故事从温暖的春天开始,结束在萧索风凉的秋天。西门庆家的盛衰与季节的循环常常相合。《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出场是在冬天,贾母说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她收拾房屋,另作安置。为表现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作者安排她在春天里葬花,其实是在暗示她的红颜薄命。她初次生病时是在秋天,秋雨季节,阴晴不定,她读的诗词是《秋闺怨》《别离怨》等,自己作的词也是《秋窗风雨夕》,其中有句为“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她所喜欢的诗句和审美习惯,也被安排是喜欢秋天的枯荷,“留得残荷听雨声”。一年之后的中秋,她给“寒潭渡鹤影”对出的联句竟然是“冷月葬花魂”。她的心情一直与季节的推移相吻合,她的命运也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变换。她焚稿而亡时是正月,冬天时节要生火盆。这里边既有抒情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了叙事的安排。而贾宝玉最后的命运也是以大雪纷飞的冬天而告结束,小说也由此写出了贾府的衰败终成定局。
在这两部小说中,时序的运行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及情节的推进紧密结合。其中最有深意的就是将一些主要人物的生日与节令安排在一起,如《金瓶梅》里李瓶儿的生日在元宵节,吴月娘的生日在中秋节,潘金莲的生日在元月九日。《红楼梦》中的一些关键的活动也安排在节日里,如中秋节众姐妹的诗会和三月花落时分重建诗社“桃花社”等。这两部小说还很懂得冷热的对比,常常会将一些热闹的活动安排在冷清的秋天或者冬天,相互映衬,以增加小说叙事结构的美学张力。《金瓶梅》里曾四次写到元宵节的欢乐,李瓶儿邀请西门庆为她庆生则是书中的重头戏之一;《红楼梦》中元春省亲安排在寒冷的正月里,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却衬托出元春心情的悲楚,省亲的热闹之后的大半年便出现大观园的变异以及宝黛关系的直转而下。四季的轮转正暗示着人生命运的无常,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祸福相依”“否泰相转”以及世事循环轮回的宇宙观相吻合,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相生相易”的艺术辩证原理。
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这种美学的基因依然存在并得到转化与发挥。
中国当代舞蹈家杨丽萍的舞剧《孔雀》是以四季为分幕来结构作品的。《孔雀》的主题是自然、生命和永恒的爱,它被看作是东方舞蹈之美的代表,它既是关于孔雀的故事,又是关于人性的寓言,体现着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融相通。在舞台的音响和灯光设计上它以四个季节的四种主色调为主,是四种色彩基调的多重变奏。在强调四季更迭的鲜明效果中,让观众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轮替。西方舞剧的经典之作《天鹅湖》,黑天鹅和白天鹅的整体色彩决定了舞剧色彩上黑白分野,在情节上建立起一种善恶对立的形式与结构,而《孔雀》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劫与循环,它的冲突和解决是向内实现的,奉献与爱最终让生命在四季更替中找到答案。这是东方人对生命的阐释方式:内敛,隐忍,历练,渡劫,回归。东方叙事中的四季与生命体验的特征紧密缠绕,四季的“变易”即通向生命的“永恒”。
中国当代导演程小东的作品《白蛇传说》是从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改编而来的,其中白蛇与许仙的故事也依照四季来展开。许仙上山采药和与白蛇相遇是在草木葱茏的春天,而最后白蛇被关进雷峰塔则是在万木萧杀的秋天,许仙守塔就在默默清扫落叶与纷纷大雪中度过,一切归于沉寂,影片结尾的字幕缓缓升起,一种空无与荒凉感留在观众的心里。
中国当代电影《无问西东》虽然在结构和叙事上并没有依照四季作明确的序列编排,但是从四季出发来设计四个故事的时空背景的构思令整个影片具有一种跨越春夏秋冬、天南地北的辽阔质感。民国青年学生吴岭澜在飘雪的冬天倚着枯树迎着飞雪拉琴;1960年代王敏佳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蝉音不绝的夏季,她最终在一场滂沱大雨中辗转重生,而陈鹏与她告别后走入的背景是黄叶遍地的深秋;1930年代学生沈光耀选择参加空军,也是在金秋季节飞上湛蓝的天空;张果果的故事贯穿影片的开头与结尾,故事又与四胞胎新生婴儿有关,它发生在冬春交替之际,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希望。四个故事各自时空独立,又交织进行,可以视作是以四季审美观念为基础的多线索叙事实践。导演李芳芳注重视听元素的细腻铺砌,将四个季节的自然特征加以突出表现,影片不时渗出“碧云天,黄叶地”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般的古典诗词般的中国意境。
当代作家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从腊月写起,展开她的芳村叙事:进入五月,春天转为夏季,一切事情就变得忙碌起来,人物的活动、矛盾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家庭内开始吵起架来,村里的皮革加工厂也热闹起来,随着秋季的到来,皮革厂与村委会的矛盾开始加剧,秋雨落下来的时候,村里便出现了摔了一跤病得不轻而又被子女们遗弃的老莲婶子喝农药自尽的悲剧。到下一个腊月和夏季的到来,一切都在继续着,依然是吵架的归吵架,乡村乱象依然是乱象,等到春节的时候,连从北京城里回来的小梨也被乡村的攀比风感染开始胡诌起来。“风吹过村庄。把世世代代的念想都吹破了。”{18}四季的轮转人事的变化让作者的悲伤感深深地从纸面上透出来,让人感伤不已。
日本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就利用季节的变化来展示自然美,并用四季来丰富人物的精神世界。如紫氏部的 《源氏物语》,用季节的各种物象来表现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感情纠葛,也以季节的推移来映衬他的感情起伏与波澜。比如,紫上去世是在年终岁暮,作者以当时的自然景物来暗示源氏生涯的终结。这种结构也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与紫氏部同一时代的清少纳言,其著名随笔作品《枕草子》在开篇的第一段就对四季的美作了精彩的描写,她将春天破晓的紫云,夏天暗夜的流萤,秋天傍晚的乌鸦归巢、大雁列飞以及日没后的风声虫声,冬天早晨下雪下霜时分的火盆烧炭,当作一种极有意思和情趣的物事来看待,充分展示了日本文学的四季意识。《源氏物语》里就写到当时在皇宫里挂有古代画家画的四季景色画;在室町时代,还出现绘制四季的屏风画。为了遮盖大面的墙壁,日本的艺术家会将一些中国绘画大师如马远、夏珪等所创造的山水范本合并成一幅巨型图画,从右到左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19}当时著名的日本画家雪舟到中国旅行,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也画过一套中国画的四季山水图。后来他回到日本做全国旅行,还作了一套从春到冬的四季山水长卷。{20}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其著名的讲演词《日本的美与我》中,一开篇就引用日本道元禅师和歌《本来面目》中的句子“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来展开言说,在结束时又再次提到它,说它是“讴歌了四季的美,其实富有深刻的禅宗哲理”。{21}他的作品许多都与季节中的旅行相关,如《雪国》《伊豆的舞女》等。
以四季譬喻人物的手法在日本文艺作品里也可寻见,如广为流传的日本民歌《四季歌》就以四段歌词将对春夏秋冬的歌咏与友人、父亲、爱人、母亲四类人物的美德联系起来。日本导演市川崑根据谷崎润一郎小说改编的电影《细雪》,讲述一个家族中四个女儿各自的婚嫁选择与人生境遇,其中四时的风物与女儿们的锦绣和服相映衬,透出极致唯美的东方意境。影片开篇即是京都赏樱的场景,结束于雪子出嫁后大阪迎来的第一场初雪,春樱、红枫与纷飞的细雪伴随着三女儿雪子的相亲和出嫁,这些片段就如以“花事”喻人,托风景寄情的含蓄俳句。《细雪》充分展现了日本民族的“物哀”审美意识,即将对“季节流动”的观感与“人生无常”的感悟相联系,“物哀”中“哀”的概念早已超越了最初“哀苦”和“悲怜”的狭义情感,而表达为通过“静观”而“知事之心”和“知人之心”的心理体验,更是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将优美、艳美、婉美等种种审美要素都摄取、包容、综合和统一过来,从而形成了意义上远远超出这个概念本身的特殊的、浑然一体的审美内涵”。{22}
“‘四季’意识作为一种文艺传统对日本电影创作者的构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3}日本电影《小森林》是一个以四季为纲的结构手法,全片分成“冬春篇”和“夏秋篇”,原著者五十岚大介在其漫画原本中并没有安排鲜明的四季结构,但在导演森淳一的改编之下,“将这些散漫的章节根据季节进行归置,梳理成一条较为清晰的时间线”,{24}四季递进与女主角市子的人生阶段嵌合,构成逻辑十分流畅且自然动人的叙事篇章。故事从市子回到故乡小森并在这里农作、回忆,思索自己人生的道路,至她决定再次离开闯荡,多年后又回到小森,在一个春天的市集与村民们一同迎接新生活。女主角的向内自我探索和外部世界的时间流逝、万物变迁不时呼应,并且产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夏之闷热难耐是市子内心的困囿,秋之收获甘甜是市子尝到自己努力付出的回报,冰封大地之冬象征了深藏的往事和亟待破冰的心事,春回大地之时市子又回到了故乡,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从结构上看,电影《小森林》的改编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和充满寓意的形式,并借这个形式抒发了人物充沛的感情和生命探索历程。另外,“是枝裕和在《海街日记》的改编中同样选择了以四季作为故事发展的时间线索,一来体现了日常生活中时间流逝的感觉,二来暗示对人生起伏、风景流转的譬喻”。{25}
韩国导演金基德的《春夏秋冬又一春》又是一个典型例子。全片以四季循环结构叙事并与“欲望、历劫、救赎、轮回”的主题萦绕丛生,正如它的片名所揭示,影片叙事按照春、夏、秋、冬乃至又一次春天来临而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形叙事时空,四个季节分别与一个僧人人生的四个年龄阶段相对应。影片开始时,万物萌生的春对应童僧的无知和启蒙;下一篇则是躁动的盛夏,僧人已长成情窦初开的少年;肃杀的悲秋,青年僧人在犯下杀人之罪后重返寺庙寻求谅解,至冬季是服刑后回到寺庙的中年僧人的自我救赎;一个陌生妇女来到寺庙并留下了一个男婴被僧人收留,至下一年春天来临,男婴又成长为一个顽童,重复着曾经的童僧做过的恶作剧,预示周而复始的世情轮回。四季意象在这里化为具有佛教意义的象征体系。影片没有采用观众熟悉的按照因果律推进情节的叙事方式,而是采取一季一篇的“章回”结构,篇章之间的空隙耐人寻味,而相同空间、不同季节拍摄的寺庙及周围的空镜头将篇章充分衔接,这些表现“季节”的空镜头不仅仅只是过场场景,也是导演专注刻画的对象,通过对光影和色调的控制,导演精心营造了不同的四季氛围,令观众生出一种光阴荏苒、世道人心循环往复的感慨。
三
在中国,在认识四时的同时就有了四方的世界观,商代就有了“四方”与“四方风”的说法,也有了对五行即五种物质元素木、火、土、金、水的认识。《尚书·甘誓》里夏后启就指责有扈氏有侮“五行”,说明五行观念在夏初便已形成。《尚书·洪范》也记载了古人从治水斗争中认识到的原始的五行思想。到春秋中期又有了“天六地五”的分类,即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地有五行——水火木金土,也建立起了五行相生相胜的概念。《左传》里有了五味、五色、五声、五名、五材、五行、六气的说法,还有了五行之官。到了战国时期《管子·四时》的时候,四时的阴阳升降与德政结合起来,有了春夏主生主长主建主奖赏、秋冬主收主藏主闭主刑罚的理论框架,它“以五方之位为框架,配以相应的天象、天时、气象、动植等自然物件作为构建,从而将天地人物四者合于一个整体的思维框架之内,进而深入到每一方位众多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结上,探讨人在不同季节的相应行为”。{26}这种框架经过邹衍的倡导成为五德终始说,经过阴阳家的整合又形成了独有的月令系统。最初出现的《月令》是关于时令的书,直接与指导农业生产和技术相关,现存的《礼记·月令》则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在形式上以四季为序,以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为主干,运用五行学说统筹安排宇宙自然和自然人事活动,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贯穿天地人的月令系统。月令系统将四季分属五行五方与五色:春配木,东方,青色;夏配火,南方,赤色;秋配金,西方,白色;冬配水,北方,黑色;土无时可配,居中,黄色。它利用“五行相生,隔一致克”的理论,构成了万物与人事的相生相克关系。有学者指出,《月令》“将战国中期以前所达到的对于天文、历法、律吕、物候、农事、祭祀、刑政等诸多层面的认识成就与已经物化或准备物化的文化成果,整合为一个完善的思想系统”。{27}这时的四时通过五行的配属将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自然与人事联系起来,构成了万物流转循环的模式,这种模式经汉代董仲舒的再度演绎,人之数与天之数纠缠在一起,出现了著名的“天人感应”理论。
关于四时、方位、颜色与文学艺术的表达,在最早的《诗经》里就可寻找到它们的身影。如《诗经》中的《子衿》《出其东门》与《宛丘》三首诗,有四季,有方位,有颜色,就与迎神送神的民俗相关。《子衿》是迎春神的祭祀,故青年人穿青色之衣而舞,而《出其东门》是将春神送出东门之外的歌,夏与秋等候在东门之外,故姑娘们穿白色和赤色的衣在东门外歌舞迎接,其中的“缟衣”是白色的,“缟衣茹藘”是在白绢衣服上染上红色。《宛丘》中的鹭是白色,其歌是迎接西方之鸟,即西方的神灵,以祈求夏季顺利地结束。{28}这些诗歌反映的现象从艺术人类学角度看是民俗,还没有后来《月令》所反映的相生相克观念,但也可以见到五行观念的萌芽。因为一些宗教的禁忌和祭祀活动都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迎神与驱疫的仪式就是最早的宗教艺术活动,孕育着后来的宗教观念和文艺样式。《月令》图式的建立不仅仅影响到天文、历法、人事、政务等活动,在后来也影响到中国文学艺术时空观的表达,影响到文学艺术中人物关系的处置乃至人物命运的安排。
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就是这样的一个标本。唐僧取经,本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经过民间的故事流传逐渐增加了它的传奇性和神异性。故事从唐经宋元的发展,到明代的吴承恩则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因为作者给唐僧取经的故事增添了许多神幻色彩,其中佛道因素变得浓了,最明显的就是用阴阳五行的关系来笼罩唐僧师徒五人的关系,并让它们构成了前往西天取经的推动力。小说在前二十二回主要就是叙述唐僧如何在如来的指导与帮助下收服了四位徒弟,先是在两界山收服了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孙悟空,孙乃从石头(属土)里蹦出来的金猴(土生金),孙有火眼金睛,但怕火;次收了白龙马,马在十二生肖中属火,火生土,白龙马在小说中被赋予当唐僧坐骑的任务;在高老庄收了猪悟能,猪在十二生肖中属水,猪八戒原是天上掌管天兵水军的天蓬元帅,水生木,在小说中八戒被说成是“木母”,意即水乃木之母的意思,猪悟能就具备了水的元素;最后在流沙河收下沙悟净,在这一回即第十九回里作者通过诗词明确说是“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29}沙僧属木,由悟空帮助收服。而唐僧乃灵山金蝉子转世,蝉由土孕育而生,属土。唐僧虽是凡人,但孙悟空说他“未超三界外,见在五行中”。{30}因为木克土,所以沙僧在流沙河吞吃了唐僧九次,最后被收服则被调和成为土了,故小说中后来就用“黄婆”来指代他,因为土色为黄。至此,五行齐备,作者在第二十二回的诗里就写道:“五行匹配合天真,认得从前旧主人。炼已立基为妙用,辨明邪正见原因。今来归性还同类,求去求情共复沦。二土全功成寂寞,调和水火没纤尘。”{31}“二土全功 ”指白龙马与沙僧,一个可以生土,一个可以克土的被收服变成土,二者都可以有助于唐僧西行取经。为了让读者掌握唐僧师徒五人的五行属性,作者在小说的回目和里面的诗词中不断提示,如在第三十二回、三十八回、四十一回、四十七回、五十三回、八十九回的回目上出现“木母”“黄婆”“金木土”等词语。在第十九回、二十二回、五十七回、五十八回、六十一回的诗词中出现“五行”“五行匹配”“五行生克”“和睦五行”等说法。这种五行关系的调和既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关系上,也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展开的重要因素。如五行山更名为两界山,是因为收服了孙悟空,走出两界山就意味着小说“进入了新的叙述天地”。{32}又如第四十二回,悟空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熏得差点丧命,就是悟能救治过来的(火克金,水克火);最后,悟空能成为“斗战胜佛”,也是跟随唐僧取经的结果(土生金)。孙悟空的两次被逐,小说里说他们是“中道分离乱五行”。{33}等到他们都和睦了,也就到了西天了,“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天”。{34}“对于五行合一的正确理解应在大的总体范围内进行,把它们相合相离两种进退不同方向的运动——即五行生克作用——联系起来。”{35}当然,作者吴承恩并不是完全受五行关系的束缚来展开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的,他不过是为了增加故事的神秘色彩,相反,他将他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也带入了作品中,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当时产生讽刺与批判的效果,从而赋予唐僧故事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也以五行结构来叙述当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就产生了五行相克的影响。在书中,贾宝玉属土,林黛玉属木,薛宝钗属金,三人构成相生相克关系,古代合婚要讲究五行相生相成,由此,“金玉良缘”被视为正宗,“木石前盟”则注定难成,贾宝玉最终玉碎,在冬天的一场大雪中出走,酿成悲剧。曹雪芹当然也不是简单地为五行相生相克所束缚,而是写出了人物所处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写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大家族必然衰落的趋势,但在结构上、人物关系与命运的预设上他还是有意识按五行相生相克关系去安排的。美国的汉学家浦安迪教授还就《红楼梦》的寓意从阴阳五行的逻辑关系提出过《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具有“二元互补性”以及“多项周旋性”, 也看到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生相克以及循环交替模式。{36}
在当代作家中,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智慧来结构作品,并展开对人物关系的描写。如《射雕英雄传》中,用五行来构建乾坤五绝(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关系,他们的名字、居住地、着装颜色、使用的绝技和兵器,全部都与对应的阴阳五行暗合起来。在小说中,东邪(黄药师),属木,居桃花岛,着装青色,吹的乐器是箫;绝学是落英神剑掌、旋风扫叶腿、兰花拂穴手,制的独门灵药是九花玉露丸,都与木相关。他最怕的人是西毒,因为金可克木。西毒(欧阳锋),属金,居西域白驼山,着装白色,乐器是铁筝。他老是算计东邪黄药师,因为金克木。他最怕的人是南帝,因为火克金。南帝姓段(与“煅”同音),属火,号“一灯大师”,独门绝技为“一阳指”,灯、阳都属火,赤色。他佩服洪七公,因为洪七公属水。七丐(洪七公),属水,着黑色,必杀技是“降龙十八掌”,龙与水相关,所以他用此招管用。中神通(王重阳),属土,着黄色,黄冠束发。又如在《碧血剑》里,袁承志如何破温氏五老的“五行阵”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何破,也要用到可以构成相克关系的工具。金庸在写这些方面是花过心思的,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精心地镶嵌在他的武侠世界里,让阴阳五行的观念贯穿在小说里以形成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并让人物的成长与顺天和道(天道、人道)紧密结合在一起,赋予故事与人物更丰厚的寓意。
在古代朝鲜,高丽末期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里,曾引用到《唐三藏西游记》的平话,足见当时看《唐三藏西游记》已经是常事。到百回本《西游记》传入朝鲜,更是对许多文人产生了影响,如洪万宗、沈縡、李圭景的著作里都出现过《西游记》的内容。朝鲜半岛在古代接受中国的农历,对阴阳五行也不陌生。但具体到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却比较弱。
至于日本,古代历法就使用中国的农历,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改用公历。刘晓峰曾经指出:在中国“历书的颁布,是天子的权力。诸侯要从天子处接受历书,并传授于万民。因此历书中的时间,就不仅是物理的时间,而是政治的时间。颁朔之礼,自周官太史讫于清朝,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它构成了东亚主体性的时间秩序。而节日体系附丽于这一时间秩序之上,其文化影响力因而广泛辐射于周边国家地区并不断融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之中。到今天,它们已经根植于东亚各国和地区特定的文化风土之中并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淘洗,业已和生活于这片土地的民众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37}在古代日本,有专门负责历法的政府机构阴阳寮和负责制作历法的阴阳师,历史上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精通阴阳五行和天文地理,后来在传说里成为日本“降妖除魔”的第一人。中国古代历法传入日本是在公元602年,由百济僧人观勒带入日本,当时传入的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采用中国历法在公元604年,明确的文字记载见于《政事要略·御奏历》条所引《儒传》以及《经籍后传记》,“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原注)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38}随着中国古代历法的采用,很多中国的节日如元旦、人日、端午、七夕和重阳,都传入了日本,随从二十四节气,成为日本年中行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周七曜的说法也按照日月火水木金土来排列。这也影响到文学艺术家以阴阳五行来展开他们的理论。镰仓时代的文论家石见女式谈论和歌,就用天地阴阳五行观念,认为和歌五句三十一字,“五七五七七,五行、五常、五方、五季也”。{39}同时还将第一句到第五句分别以春、夏、秋、中、冬以及东、南、西、中、北以及相应颜色相对应。但是后来的本居宣长反对这种说法,在《石上私淑言》中,他认为用阴阳五行来谈论和歌的起源以及用五行、五常、五伦来论五句是虚幻无据的,古代日本根本没有这种东西,阴阳五行也是自命不凡的中国人提出来的。{40}这与本居宣长一贯反对将日本的文学、文论与中国文学、文论相比附的做法相一致,但这并不证明阴阳五行的观念没对日本产生过影响。在对中国小说《西游记》的传播上,日本从奈良时代起就传播唐宋时期唐三藏的故事,到江户时代,《西游记》全本传入日本,更进行了商业化的运作与传播,在文人和民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文人还结合日本国情进行合理化的想象与改造,实现了对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本土化形象创造。关于这方面不少论著和论文都有研究,成果颇多,本文就不再进行论述了。{41}
至于在日本的小说中阴阳五行的明确影响,可见的有江户时代的小说家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中间的八义士肩柳就懂得隐形五遁术(木遁、火遁、土遁、金遁、水遁之术)的火遁,传说这是中国道教张道陵发明的法术。在该书第二十八回里八武士中的肩柳向他救下的滨路陈述了他从小就学习火遁之术的来由,在第二十九回里,他与额藏争夺宝刀时就使用了火遁术,跳入火坑中逃之夭夭。{42}《八犬传》将中国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的故事和神奇情节掰开揉碎,改编移植穿插在日本小说中,成为一种日本创造,个别的情节中可以见出阴阳五行在小说人物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阴阳五行观念及其方术在作品中担负着重要的关节作用,是不能不正视的。从四季意识延伸出来的五行观念与整个东亚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美学生命力息息相关。
注释:
{1}{26}{27}具体参见肖汉明:《阴阳:大化与人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第92—93页、第98页。
{2}[日]井上聪:《先秦阴阳五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3}{4}{5}[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一以魏南北朝文学为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第33页、第53页。
{6}[日]松浦友久著,孙昌武、郑天刚译:《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7}{17}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选自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7—478页、第479页。
{8}{9}[日]今道友信著,蒋寅、李心峰等译:《东方的美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1页、第192页。
{10}{13}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第38页。
{11}[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选自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12}彭恩华:《日本俳句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4}[日]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
{15}{16}[日]本居宜长著,王向远译:《日本物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66页、第67页。
{18}付秀莹:《陌上》,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45页。
{19}{20}[日]秋山光和著,常任侠、袁音译:《日本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96页、第100—102页。
{21}[日]川端康成著,魏大海、侯为等译:《川端康成十卷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26页。
{22}[日]大西克礼著,王向远译:《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的三大关键词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23}{24}{25}蒋励:《从〈小林森光〉到〈小森林〉:论漫画跨媒介呈现策略及启示》,《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期。
{28}[日]井上聪:《先秦阴阳五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5页。
{29}{30}{31}{33}{34}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第951页、第273页、第721页、第754页。
{32}{35}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第196页。
{36}浦安迪著,刘倩等译:《浦安迪自选集》,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0页。
{37}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16页。
{38}参见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的“汉历东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3页)一篇以及日本田中健夫编:《善邻国宝记·续善邻国宝记》,集英社1995年版,第34页。
{39}{40}见王向远译:《日本古代诗学汇译》(上卷),昆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第1003页。
{41}可参见孙莉:《〈西游记〉原型故事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张丽、蓝青青:《〈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在日本的接受与影响》,《淮海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等等。
{42}见[日]曲亭马琴著,李树果译:《南总里见八犬传》(卷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第28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26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蒋述卓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2022/05/25/113084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