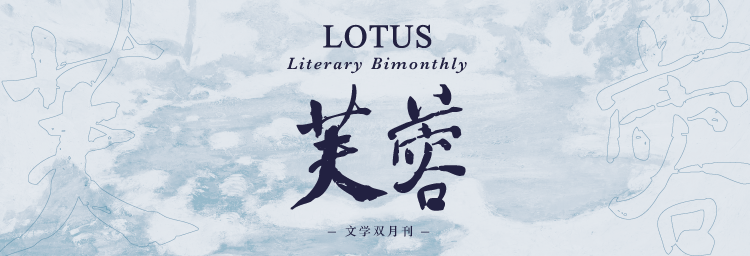

活着
文/黛安
一
痛是在熟睡中骤然降临的。身体的天空腾起一道道闪电,我被击醒。
突如其来。尖锐,陌生。小腹,右边,稍往下,巴掌大的一片,一只匕首在搅。也不知夜里几点,卧室黑静如渊。痛醒的我迅速下床,打开屋门。
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
年少时,母亲有一次被左邻右舍手忙脚乱抬到地排车上,胡乱盖了床被子,跑着拉去了公社卫生院。刚过完年,冰溜子还挂在屋檐上。母亲满脸的汗,紧闭的双眼,众人杂沓的脚步,被面上大朵的牡丹,路上飘荡的尘土,是那个早春留给我的所有印象。
下楼敲邻居门。痛让我的头、肩、背、腰,一低再低,好像要把自己像个物件样对折起来。门打开,先是一只小狗,它汪汪两声就停下了,怔怔地望着我,像个眼神纯净的孩子。狗能在夜间看见游荡在人间的鬼魂,它也一定瞬间洞悉了我:来者不是危险的入侵者,而是亟待拯救者。蹲坐在地上的我,身体比一只小狗高不了多少,此刻,我们都是孩子。惶惑不已的夫妻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男人跑下去开车,女人返回卧室拿什么,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挪下楼。共一百零三阶。一百零三,十几年间,我反复上下,这个数字少说也重复四万次了,得意忘形时轻盈的脚步噔噔噔宛若踩在琴键上。可是这一次,它变得无限漫长,让接近大地,变得近乎痴心妄想。
天色还早,晨光熹微。寂静中,夜的黑绸布正在被漂洗般一点点变淡。车子在小城空旷的街道上一路飞驰。女人抱着我,持续的剧痛要把我撕裂开了。我不知道痛来自哪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不知道它会带给我什么。我只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有深爱的人与物,我迷恋尘世的灯火,这人间的繁华与寂寥,我还没看够。我想活着,一一亲历。
二
那一年,载着母亲的地排车是木头的,两根车辕弯曲的弧度一模一样,那是父亲杀了地头的一棵槐树,找身为木匠的东邻居把树干一分为二做成的。还没开春下地,还没给轴承上油。咕嘎。咕嘎。咕嘎。轮子里栖着一只鸟。轮子每转一圈那鸟就叫一声。地排车跑起来之前,父亲以最快的速度给轮胎半撒了气。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大雪下了几场化了几场。路上总有车要走。庄户人不会因为雪天就不出门。暄软的路面先是烙下一条条深深浅浅的车辙,一夜之间,就冻成了一根根肋骨。乡间的路和人一样,软的时候捏不成个,硬的时候能让刀刃卷了边。不给轮胎撒点气,母亲全身的骨头难保不会被嘎嘣嘎嘣颠散了架。驾车的是父亲。没有谁比他跑得更快。家里头顶的天空,得两个人一起撑着,他要车上的女人活着。他跑着远离死,奔赴生。邻居们推着车帮跑。车帮上挤不下的,跟在车后跑。后来,跟在车后的青年,中途把父亲替换下来拉着车接着跑。他们要让村里的这个女人活着。她有婆婆,有男人,有四个丫头,有一屋顶的炊烟,一天井的驴啊猪啊鸡啊狗啊。她走了这些怎么办?她必须活着。
蜷曲在被子下的母亲不断扭动,像一只大虾米。母亲第一次向我们呈现出这种姿势。一向,白天,只要从床上下来,她会立马变个人:脚底生出风火轮,眼睛里生出火苗,肩上隐约生出一对翅膀。她通体发光。在田间,她照亮了黑色的泥土,青绿的庄稼,回到家里,她照亮了堂屋,饭屋,驴棚,猪圈,屋门旁的石榴,西窗下的香椿,驴槽前的笨槐,南院墙根的脆枣,院墙外的洋槐。她照亮了整个天井上空的槐香和鸟鸣,更照亮了我们的叫声。是的。我们常常会叫:娘,我饿。娘,我冷。母亲劳碌的样子,像一根移动的柱子,她走到哪里,顶到哪里。她在院子里,天空就不会塌下来。她在屋里,房顶就不会塌下来。她在我身边,我的梦想就不会塌下来。我从懂事起就想走出被庄稼和树木环绕的密不透风的村子,走向遥远的未知的远方,好像那里有一个日出一样的锦绣前程在等我。没上学,连自己名字都画不像的母亲撑着我们的家、我们的日子。只要她站着,我们家天井就煌煌烨烨,屋里就亮亮堂堂,夜里我们的呼吸就能抵达月亮和星星。那次躺在地排车上的母亲,是她少有的收起风火轮,熄灭火苗,缩回翅膀,让身体与天空和大地保持平行的一次。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女儿,加上奶奶和父亲,我们家七口人——至于爷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虚妄的词语。他属于有着烽火与警卫员的历史。他走向大地深处时,正妻少子幼,而他自己,亦如日中天。母亲的命分成了七份,像一棵树的七根树枝,哪一根都不能提前死去。她得完整地活着。
三
父亲与地排车的关系很简单,他是驾驭者。车上装的多是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玉米,小麦,白菜,土豆,萝卜,青草。很少有瓜干。我们这里是平原,山里的薄地才种地瓜。有一年,大概附近哪里建了家糖厂,村里突然种起了甜菜。中秋那一阵,地排车上就满是暖烘烘的甜馨味。又有一年是花生。掉在地上的鲜花生,捡起来吹吹尘捏开就吃,细细地嚼,嘴角会流出一股白嫩的水,像奶。花生沙土里种才好,因为它要自由地呼吸,我们村的地都是黏土,所以花生都是河南人种。麦秸、秫秸也要地排车从地里拉出来。所有作物的茎秆中,没有比麦秸的颜色更好看的了。一根,两根,十根,一百根,一千根,一万根,还看不出什么,但是十万根一百万根一千万根一亿根就不一样了。麦穗脱粒,新麦粒黄中泛绿,美如琼玉。麦秸晒干,在空地和房前屋后垛起来。有的怕淋了雨,会苫个同样用麦秸做的大草帽。每个麦垛都在盛夏的阳光下安静地闪着光,那是秋收后,土地献给村庄的金字塔,是村庄的神。秫秸也是神。干透的秫秸扎成捆,一捆捆斜立着攒成垛,晚上,人、鸡、鸭、狗、驴都睡了,唯有秫秸的叶子醒着。它们在风中哗啦啦响一整夜,星月一样守护着我们的村子。麦垛与秫秸垛以美学中的形象和声音与我们一起活在村子里。当它们最终交付给灶膛,会变成蓝色的炊烟,灵魂一样升上天。地排车也装土地需要的东西,比如,种子,猪圈里的肥。父亲架着车行走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播种与收获之间,把地需要的给地,把牲口需要的给牲口,把人需要的给人,把天需要的给天,把神需要的给神。
地排车拉着母亲,是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地排车上装过石头、水泥、液化气罐。他穿着中山装,每一粒扣子都整整齐齐系好,鞋帽干净,牙齿洁白。儒雅的父亲拉着地排车去山上,去工厂,去风雨轻易就能抵达的地方,去到我们空荡荡的日子深处。
但是那天,驾惯了车辕的父亲意外地躺到了车上,他一时失去了驾驭者的身份。
这与麦秸有关。
四
村东有一家造纸厂,用麦秸造。父亲在那里干活。不知什么时候,他后脑勺上长了个疖子。在乡间,长疖子是很平常的事。人们都说,疖子好了比没长过还舒坦。父亲经历过战争、生离死别、饥饿,一个疖子算什么呢。但是,疖子大概是被粉碎麦秸扬起的尘感染了,剧烈的头疼像一只猛兽袭击了他。或者,一把刀飞进了颅内,左搅右拧。活到三十三岁,他还是第一次被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物击败。父亲捂着头跑了八里地去找母亲舅家表哥,他是个远近有名的兽医。一个连大骡子大马都能对付得了的人应该可以应对一个疖子。不是的。我想父亲其实也明白。他肯定不是糊涂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最风华正茂的年龄考进省城会计学校读过书,他能在算盘上正确而娴熟地打出乘方开方。他会唱歌。会吹口琴。会弹脚踏琴。会跳交谊舞。这不奇怪。他小名“公子”。词语是有力量的。一个词,像一把剑,穿透了他曾辉煌而特殊的少年时代。他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但谁也没法改变历史这条滔滔奔流的大河,他终于不得不跌入尘埃,像一根麦秸一样微不足道。那天,当兽医的表哥外出了,父亲只好东倒西歪醉汉一样回了家。他扑在炕上,抱着头,一只场院里碾麦子的碌碡一样,从炕头骨碌到炕尾,从炕尾骨碌到炕头。年轻的母亲吓坏了,她放下手里的活,架着父亲去了公社卫生院。一度,父亲把头靠在了母亲肩上。这在他们是少有的亲昵。即使是夜间,他们也像大多数夫妻一样,分睡在炕的两头。是疼痛,把父亲和母亲羞于示人的一面展现在了那个仲春的高天阔地之间和地里劳作的人们不经意间的注视里。接诊的是刚毕业的小马大夫。书本上的知识让他很肯定地将父亲的情况诊断为脑膜炎。住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仅没减轻,父亲头痛得还更厉害了。或许就是从这一次开始,一个饱读医书的年轻人切实理解了什么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的成长才刚刚开始。他的锐气就是这样一次次被锉短、磨平,最后才露出智慧的边边角角。还是一位姓王的老医生,说,不是脑膜炎,应该是脓毒血症,毒已扩散到全身,得赶紧转院,再不转院,命怕是保不住了。
这是母亲想不到的。母亲刚刚二十六岁,大姐三岁,二姐八个月,而我不在这世界的任何地方,只存在于父亲的欲望与母亲的子宫对新生命的期待之中。转院要花钱。家里没钱。没钱母亲也不能让她的男人死。他得活着。他们才新婚几年,他们一起垒了院墙,一起盖了猪圈,一起在天井里栽了槐树、枣树、香椿。万物萌生,他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更重要的是,他们才生了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女儿要投奔他们,她们还在云彩上,还没来得及上路。母亲要让父亲活着,他们要一起将我和小妹从云端接下来,领回家。我和小妹不去别人家,一心只做他们的女儿。
母亲跑去大队部借钱。干部们正在开会。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会开不成了。队长与我们是本家,他的爷爷与我的曾祖父是亲兄弟。他做主让大队借给母亲五百块钱。父亲是独子。大队不得不派了两个壮劳力,都是我们刘家姓的,用地排车拉着父亲紧急转院。
就这样,父亲躺到了他惯常用的农具——地排车上。与十几年后的母亲一样,身体不再像一株长势正好的庄稼,昂扬地垂直于天空,而是像一股流水,匍匐在大地上,柔若无骨。他不知道,相同的动作,他在提前给母亲进行一次预演。这次给地排车半撒气的是二舅。二舅提着暖壶,跟在地排车后一路小跑。车子消失在春深处,消失在母亲目光深处。她转身回家,面对父亲生死未卜的局面,又忐忑又沉着地等候着生的消息,像是静候一个新生命的来临。
五
拉着地排车转院的是外人。但其实父亲有弟弟,小他十一岁,同父异母。战争,历史,或诸多无法说清的因素,让父亲长到十八岁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弟弟。他俩一个叫公子,一个叫贝子。终其一生,兄弟俩也没见过几次面。一个黄金一样的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贝子叔叔时他的样子。
贝子叔叔躺在床上,金黄金黄的。我们驱车几百公里赶到,一进屋,我就被他露在薄被外面黄澄澄的脸镇住了。我从没见过那么黄的脸,像密密地刷了一层金粉。那是六月,叔叔家在一楼,有个小院,院子有棵木瓜树,油绿的叶子间,正垂着一只绿色的木瓜。开着窗,我看看木瓜,再看看贝子叔叔的脸,觉得更黄了。我走到天井,站在树下,仰着头,对着那只果子突然无声落泪。
活下去呀。我在心里对叔叔说。
那时候,父亲已经以另一种物质形式住在了小小的匣子里十多年。如果叔叔再沿袭父亲,让人将自己的躯体投入一场大火,然后他乘着火的翅膀飞走,那我在世间就没有父辈那一代至亲的亲人了。我有过姑姑。以前舅姥爷家的表叔们都说,从没见过那么美的女孩子,她的眼睛定定地看谁,谁就会被她看魔怔,像喝了迷魂药,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豫剧,她听一遍就会唱,看一遍就会演,腔调、招式,都像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专业演员。然而她的美,竟被一场最普通不过的疹子销蚀殆尽。她在最好的年龄匆忙遁入无形,像一只蝴蝶没入花丛。
活下去。我对着那只绿色的果子祈祷,仿佛它是上帝。阳光里,它明亮、新鲜,像一个初生的婴儿。
可是贝子叔叔没有丝毫留下来的意思。我蹲在他的床前,把一只紫的透亮的葡萄剥了皮放在他干裂的唇上,他轻轻把头扭开了。他已不屑于人间的任何食物。当他从医生递给他的那张纸上看透了自己身体的秘密时,他第一个想到了大地。他想回去。他想把自己像一粒种子一样种进地里。为此,他安排好了所有一切,连寿衣都是亲自试过的。他那么魁梧的人,竟买了小号的,他预想到了自己的身体会像烈日下的果子一样皱缩,只剩下黄金包裹下白灿灿的骨头。
守在身边的婶婶是贝子叔叔的第三个妻子佩兰。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平静与淡淡的忧伤。她把悲恸藏了起来,不让难得来一次的我们窥见。像是穷人待客,勉为其难地把自己最好的呈上来。也可能,大悲是珍贵的,越用越少。贝子叔叔先后娶了木莲、蒲芹、佩兰三个女人。这些,还在他七八岁时,一个算命的瞎子就看透了,说他得讨一挑子半老婆。挑子,就是扁担。一根扁担两个筐,加上半,就是三个。果然。第一个婶婶木莲,身材阔壮,是那种男人的大方脸,与叔叔仿若兄妹。第二个婶婶蒲芹我没见过,据说两人像两只刺猬,越好越相克,无奈只好各奔东西。第三个婶婶佩兰,是那种黑眸子核眼的俊。核有两个发音。在我们的方言里,读第二个,“胡”音。贝子叔叔除了他日常的一面,做什么都风生水起,养牡丹,织网,打鱼。他日夜守着牡丹,谙熟每个品种的脾性。他从魏紫、赵粉、姚黄、二乔、洛阳红、御衣黄、酒醉杨妃、白雪塔、豆绿十个珍品中各挑出一盆,从还没开花,就把它们围成圈放在一起,让它们每天彼此观看,喜欢上对方。开花后,那些花全都伸向中间,拼命奔向对方,试图将对方占有、吞噬。花开得最好的时候,贝子叔叔把它们分开了,互不相见,让它们彼此思念。最后,贝子叔叔嫁接了一株。那株牡丹,同时开出了绛紫、浅粉、嫣红、明黄、玉白、豆绿、深墨几种颜色的花朵,他像给女王献宝,送给了木莲婶婶。木莲婶婶欣喜地看着那些诡异的花朵,不时弯腰凑上去闻闻。木瓜树下,木莲婶婶将他织了一半的网从自己头上罩下去,从网眼里有几分顽皮地看他。贝子叔叔吐出一口烟,看着光影中有些魔幻的女人,说,木莲,你是我网住的一条大鱼。才不是。木莲婶婶有些娇嗔地说。她从来说话算数。她用行动为自己的话做了注释。她为贝子叔叔生下白蔻、白果、白薇三个儿女后,像一条大鱼,成功逃脱了叔叔的网,回到了永恒的时间之海。我没问过贝子叔叔,与木莲婶婶在一起的日子,是不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生与死两件大事,贝子叔叔认为,他已经把第一件做完了,正在做第二件。第一件需要整日奔波,第二件只要躺下就可以了。他自己不动,他让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心脏赛跑。他像一个看龟兔赛跑的置身事外的裁判。
快一个月了,他空荡荡的胸腔里只有偶尔从喉咙跌下的几滴冰水。实在焦渴时,他就舔一口雪糕。那是他在人间最后的美食。大地还在,天空还在,可是贝子叔叔拒绝与我们一起享用它们了。他自己做主,执意要离开。离开之前,他先给自己穿上了一件金缕玉衣。
叔叔一定是痛的。那样的症候,几乎,生在体内的任何部位都是斩不尽的野草。它先是长时间不动声色,待被感知到,已成汹涌之势。它扩散,蔓延,所向披靡,不可遏制。最后,一一结出蒺藜之果。千万个魔鬼在体内疯狂地左冲右突,不分昼夜。人非钢铁之躯。谁都会痛。没有人可以幸免。我以为叔叔痛时得一支接一支地注射度冷丁,那抽空的小玻璃瓶一只挨一只闪着冰冷的光——就像二十多年前婶婶离开时一样。但,并没有。薄被掀开时,叔叔的前胸后背贴着几片指甲盖大小的,类似创可贴的东西。我问表妹,她说是芬太尼透皮贴,一种麻醉性镇痛药,贴一次管三天。表妹多年间跑医药,深谙各种最先进的止痛药,那一定是她搞来的。她说,快到第三天时,不等看出叔叔痛,她就把旧的揭下来,另找个地方贴上新的。贴过的地方,不能接着贴,得过段时间。只要贴上就不疼了吧?我问。表妹说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在心里说。表妹还说,自从叔叔决定不吃不喝不再起来的那一刻起,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三天两头地往他身上贴芬太尼。她不是上帝,她只是他平凡的女儿,她留不住他,只能把他的痛拿走,让他的水分、血肉,在安静中自行消隐,让心脏,像一列退役的老火车,慢慢驶向终点站。
“真好,”我说,“如果那时也有芬太尼就好了。”
话题至此戛然而止。那些没说出的话,我和表妹都明白。那一年她十四岁,我十七岁。我坐了四百里的车,在一个深冬的黄昏推开叔叔家的门,把父亲求人弄到的两盒度冷丁交到叔叔手里。他已经学会了熟练地打针。不久,被子下痛到汗湿的木莲婶婶,脸上露出了重生般的笑容。
岁月贫瘠。只有两盒。
后来,后来,后来……我和表妹几乎同时开口,聊起了别的话题。我们不约而同把彼此从后来的日子里引开了。后来的日子是一只匣子,盛着木莲婶婶最后的声音。那些被声音的剪刀裁碎的日子,我们真想忘掉啊,最好从未有过。
但她最后很平静,脸上带着笑。她本来就好看,走时,像个少女。表妹突然说。
表妹去忙,我回到叔叔床前。那一天,叔叔说了很多话。他甚至是喜悦的。“尕妞。”他望着我,不止一次地唤着我的小名,问我这问我那。我们差点就谈笑风生了。
不久,贝子叔叔终于得偿所愿。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从土里像一粒种子萌发——正鲜枝嫩叶地活着。
我时常想而且愿意相信,我的叔叔贝子,还是个天真的孩子。
六
我被女人架进了急诊室。抽血化验,打小针。已经多年没在屁股上打过针了。一只小玻璃瓶,薄薄的砂轮在瓶颈处划一道,啪一声掰断,瓶身倾斜,细长的针头伸进去,吱吱抽净,当的一声,瓶子扔掉。针管竖起来,针头朝上,拇指轻轻一推,涌出一滴,接着,在臀上棉棒消过毒的一小片地方,像一次小小的投掷,针头猛地一扎,液体缓缓进入身体。如果单独摘出这一连串的动作,它如行云流水,简直进入了美学的范畴。但这会儿,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听不见了,针扎时也只是臀上微微凉了一下。大片的、巨大的、不明所以的疼痛早就掩盖了一支小小的针头对皮肉锐利的进攻。针一打完我就从窄窄的检查床出溜到了地上。坐不是,躺不是,没有一个姿势能让痛妥协一点点。就那样歪斜着。外套是邻居家女人的,乳白色的半身羊毛大衣,里面,是我没来得及换的棉质碎花睡衣裤,脚上是宽大的卡通棉拖鞋。我也一定面色晦暗,头发蓬松而凌乱。痛把我的力气与尊严毫不客气地敛走了。我一直没流泪。痛把泪水也一并敛走了。
尊严、力气、容貌、泪水,我都能交付出来。我甚至可以不顾以睡衣与拖鞋示人的羞耻。但我不会交出全部。我有一只稀世陶罐,今生我只用它存储一样最珍贵的东西:我在人世的时间。我不想轻易交出陶罐。我在世间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得活着。
曾读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系列小说。他与华盛顿·欧文被誉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自一八二零年自费出版第一部小说《戒备》到一八五一年去世,三十年间,库柏曾尝试边疆冒险、航海冒险、革命历史等不同风格的写作。《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的《最后的莫西干人》《探路人》《拓荒者》《大草原》《杀鹿者》中,《最后的莫西干人》我读了小说后,又找来电影看。而实际上,在这之前,自然,与大多数人一样,电影的同名曲,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已听过无数遍。后来对库柏的步步深入,也是始于这首曲子。二〇一八年在北京读研,住在八里庄南里的鲁迅文学院,有一天上午,为着什么事,我先后几次经过同学桃子的房间。她房门虚掩。清明时节,院子里,一株大树上紫色的梧桐花开了。每次经过,隐约的花香一样萦绕在她房间门口的,都是同一首曲子,就是《最后的莫西干人》。她听了整整一上午。我无从揣测彼时是什么样的心境让她深陷其中,只知道,同样的旋律,我们有着同样的热爱。电影中,导演迈克尔·曼把镜头推向苍茫的群山和茂密的森林。在那里,他还原了一场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冷热兵器混用的血腥之战。“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我会去找你,无论要走多远,我都要找到你。”勇敢的莫西干人霍克依对被他营救的门罗上校的女儿可娜说。后来,当我专程跑到国家大剧院,现场倾听印第安艺术家亚历·桑德罗跪在地上虔诚演奏《最后的莫西干人》时,心里又无端想起这句话。
活下去。
活下去。
女人把我扶到轮椅上,推着去做彩超。神奇地,我的身体成了战场,刚才的那一小股液体如千军万马,呼啸而至,痛溃不成军,不得不一点点撤退、抽离。我吧嗒睁开眼睛,像是风暴过后,重新打开院门。
我打开院门迎接母亲回家。
七
我家在村口,跨过一条窄细的黄泥巴路就是田野。我不时从家里跑出来,长久地站在地头。长大以后离开家乡,每每回望故土,印象里总是田野绿得无际无涯,大概,与我那次等待母亲时无数次伸长了脖子的张望有关。黄澄澄的路在我的目光尽头拐了个九十度的弯,我不得不先看向麦地,再找寻另一条看不见的路。经冬的麦苗暗成了墨绿色,我的目光顺着麦垄,一直伸到天边。那时我想,如果给我一匹马、一条皮鞭,我就能骑着马穿过无数的麦地,一直跑到天的外面去。那天村里有户人家发丧,人们抬着祭桌,抬着纸糊的轿子、纸糊的马、纸糊的丫鬟、纸糊的房子、纸糊的摇钱树。风把白色的马鬃和摇钱树上金黄的元宝吹得簌簌响。我眼看着这纸糊的荣华富贵被抬去不远的一块麦地后,点着烧成了灰。繁华从火里像马一样奔腾而出,攀着烟铺的路去了另一边。有一刻我想,如果母亲死了会不会也这样。刚一想,就呜呜呜来了一阵北风,像是哭。脚冻疼了,我跳起来。我不断地跺脚,想要把刚才的念头狠狠 死。母亲不能死。我也笃定地认为母亲不会死。她天天下地干活,东坡、西洼、南膏腴、北皇华,一年四季,她反复奔赴这些地块,唯独医院,她连生孩子都没去过。那怎么行呢?人除了不能像麻雀站在电线上,是哪里都得去一下的。就像一天,村里来了一只观光氢气球,有的人就飘上了天,从天上往下看我们的村庄,和绿色海水一样包围着我们村庄的树木与庄稼。池塘里也要去。住在池塘边的盛茂二爷爷每年都会穿上一身鲜海带一样的皮衣裤下到水里踩藕,踩到就用钩子钩上来。藕上都是细滑的黑泥,清水里一涮就白生生的了。不知谁说,藕节熬水喝能治流鼻血,二奶奶在窗台上晒好了包起来留着,谁家小孩子鼻子破了,就去她家要。牛皮里也要去。去牛皮的不是别人,正是会踩藕的盛茂二爷爷。他总在大门外的池塘边摇着蒲扇喝茶乘凉边吹牛。他吹得最多的是,他睡觉不盖被子,盖云彩。而且,每天盖的都是新的,就像每天盖一床新被子。早晨,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天上最干净的那片云彩摘下来,锁在柜子里,晚上拿出来盖。要是下雨怎么办?我们故意问。他说,他会看天,下雨前,他会提前多摘几片云彩存起来。云彩是香的。他说。多香?我们又问。那时,面前的池塘里开满了荷花,他吸一下鼻子,说,比荷花香一百倍,和栀子花一样香。我们都知道他家有一棵养了多年的栀子,开很多很香的白花,按他的话说,比天上的星星都多,香得让人发怔,傻了一样。他还说,如果哪天冷,他就在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再摘一片,晚上盖两片,一片白云,一片彩云,白的贴身。后来,全村的人都不再喊他的名字,而叫他大吹——大吹哥,大吹叔,大吹爷爷。他三岁的外孙喊他大吹姥爷。他无不高兴地答应。都说,他不吹牛会死。那就吹。他靠吹牛活得滋滋润润。那些不着边际的句子,在贫瘠的年代里,给了大家活着的乐趣。南河也要去。有一次村里几个人去南河捉鳖,遇到了一条大鱼,孬叔一个猛子扎到了水里。后来他说,那鱼比会打酱油的小孩都大。那鱼看着他,不跑,而是摆着身子倒着游,红嘟嘟的嘴一张一张,像是一声声叫着他的名字,让他跟着走。他像被鱼下了蛊,果真跟着,身不由己。那时南河里常年挖沙有很多无底的大坑,他不知道大鱼要把他带到只有大鱼知道的地方。他说他好像掉进了深渊,漆黑、冰凉。他后来活得儿孙满堂,多亏一同捉鳖的人里有水性好的,把他捞出来放在牛背上控了半下午水。孬叔醒过来睁开眼第一句话就问,我还活着吗?他爹恨恨地说,你死了!说完转身就走了。人家都说,他是看儿子没事了高兴的。从此,大家都说南河里有鱼妖。医院,母亲是不是注定要那样去一次呢?那里有一扇通往死亡的门。有的人去了,被关进了那扇门里,再也没回来。我想要一匹马,我要快快去卫生院把母亲接回家,像接我最小的妹妹。
母亲没坐地排车,是父亲陪她走回来的。她从天边一直往回走。在远远的麦地的那一端我就认出来了。她的身形与走路的姿势,世间独一无二。风火轮重又回到她的脚上,翅膀重又回到她的肩上。别人的翅膀都是从背上长出来的,母亲的不同,她长在了肩上。事实上,别人都没长翅膀。后来,母亲一直走在我用目光给她铺的柔软的绸缎一样的路上。我没迎着母亲跑过去,而是转身跑进天井,跑进堂屋,对大姐、二姐、小妹说,咱娘回来了!跑进里屋,对奶奶说,俺娘回来了!我的音调不高不低,正好盛下我所有的欢喜。我从小就知道,好东西要收掖着,不可轻狂与奢靡。不然,会像握在手心的水,张开就没了。当时是上午,一夜北风后,太阳高挂在天上,屋檐上锥形的冰凌有如水晶,闪着耀眼的光。小妹抢先从屋里跳出来,紧接着是大姐和二姐。天真冷啊,我们跑着,笑着,哈出的热气一朵朵昙花一样开满了天井。我们奔出去拥着我们的母亲把她迎进家,像再次迎接父亲的新娘子。
八
父亲被人拉着转到了五十里外的——那时叫泰安地区——中心医院。过完年,农历二月二十三,天还冷着。快进三月了,谁想到又下了一场大雪,“厚得没过了脚脖子。”多年后二舅对我说。二舅三十岁,小父亲三岁,像父亲一样,有两个女儿。大的与大姐一样大,小的与二姐一样小。两个表哥,像我一样,尚未出生。那时的我们,在哪里呢,在夜晚的星星上吗?母亲是二舅的三妹,他不能让妹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陪护父亲的事,像一副担子,落在了他肩上。这样一来,我们家和二舅家,里里外外,都是只剩了一个女人撑着,下地干活,照顾老小,喂牲喂畜。父亲曾有个妹妹,宝琴——是的,前面说过,但我忍不住想再说一次——异常美丽,喜欢唱戏,唱念做打,无师自通。也难怪,自小奶奶带着她看戏,曾连续看过两个月常香玉在郑州的演出。她有一身荷叶绿戏衣,水袖舞起来,天井里树上的麻雀会停止欢叫。她会抖袖,掷袖,挥袖,拂袖,抛袖,扬袖,荡袖,甩袖,背袖,摆袖,掸袖,叠袖,搭袖,绕袖,撩袖,折袖,挑袖,翻袖……但她长到十六岁时,拒绝了成长。她年轻的身体仿佛一小片肥沃的田野,鲜嫩的红色疹子,发了芽的种子一样,小兽的嘴一样,不断往外拱。她周身着了火。她热。她发烧。她晕头转向。她滑下床。她光着身子跑出了屋。那是天井里的树和树上的鸟雀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一个少女鲜美的裸体。黯淡的院落突然出现了一朵硕大的白色栀子花苞。疹子没出完她就死了。没人知道,那场雨后春笋般的疹子,是来取她的性命的。“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传说中的宝琴让我很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多年后,我读到了罗恩·拉什的同名小说集。他的目光又一次投向阿巴拉契亚山区。故事里,粗粝的生命纠缠于暴力与柔情,希望与恐惧。每个故事都精致、纯净、冰冷、闪光、珍贵,宛若钻石。罗恩的文字,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照亮着世界。书捧在手里,我眼前时常出现那个叫宝琴的女孩。如果彼时的她不那么华美,我的人生中就会有“姑姑”这个词语,我就可以常常姑姑长姑姑短地叫。但她不肯。她是一道长度为十六年的光,短暂地闪耀之后,留给奶奶的,是长久的荒凉。
父亲这次住院,奶奶不知道,是不是无形中或许有双看不见的手,像一把镰刀,高悬于她命运的头顶之上,像上两次一样,又要将她唯一的儿子也收割走?她是标准的小脚,让人用地排车拉着去过医院一次。那时父亲已经治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好。见到奶奶,父亲哭了。奶奶说,不哭,你二哥撇家舍业照顾你,好好治,我和香在家等你。香是母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奶奶一向这样叫,香这,香那。父亲也是。
母亲一次医院都没去过。家里家外的事像一捆绳子,将她牢牢拴住了。她只有一天天在心里盼着她的男人活着,并且回家。
那一年,田野里缺少了二舅和父亲这两个壮劳力劳作的身影,两家都只分了三十斤小麦。那是两个家庭一年的口粮。整整一年,饥饿像秒针,繁密而均匀。每个人的腹腔里都有一个空旷的深谷,吞咽唾沫的声音,回荡其间,长久而响亮。
正像转院之前的王医生所言,父亲得的是脓毒血症,且已蔓延全身。外三科八号病床上的他,迅速消瘦。毒像一条蛇在他的体内乱拱。拱到哪里,哪里鼓起一个大包,像是提前在他身体上找寻筑造坟墓的最佳位置。最后,毒素聚集到了大腿根。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父亲眼看着自己河床里的水越来越少,几近干涸。得了同样病症的几个人,已经相继离开了那个病房。
“要治好,必须知道是哪一种细菌感染。”主治医生对父亲说,“取样化验,不打麻醉最好,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
“能。”父亲肯定地说,“只要能活下来。”
父亲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医生先让他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半个世纪前,这句话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出现在各个场景。我读小学时,每次做课间操,总要先集体齐声朗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进了手术室,父亲的头颈、胳膊、腿,被绑缚在手术床上。没打麻醉,手术刀活生生剥离一片肉的整个过程,父亲咬着牙没吭一声。痛,在一个强烈地想活下去的人面前失去了威力。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整个医院只有两支红霉素。其中一支,在主治医生的争取下,进入了父亲的静脉。父亲的生命之河从此一天天充沛丰盈。
后来我多次想,我的生命,最初就在那支红霉素里。
七十一天后,农历五月初五,等父亲再次回到村庄,走进家门,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根花椒树的树枝做的拐棍。他的双腿已经细到撑不住他的身体。他瘦得全身只剩骨头。
那天是端午节,他像个讨饭的,佝偻着腰站在自家门口。
刚吃完午饭,母亲正要喂猪。她打开圈门,猪没有像往常一样直奔拌好了食的猪槽,而是摇着尾巴跑向大门口。南墙根,麻秆围成的栅栏里圈着十来只鸡,有一只扑棱棱飞了出来,其余的也一只只跟着往外飞,一落地,就伸着头往大门口跑。母亲吃惊地转过身。她看到了大门口那个男人。他正咧着嘴无声地傻笑,像个傻子。
他瘦得脱了形。即使他瘦得比手里的那根花椒树枝还细,母亲仍然一眼就认了出来。泪突然涌满了她的眼窝。猪圈到大门口十来步,母亲把猪食勺子一扔,小跑着奔过去。你可回来了。母亲说。他还在傻笑。母亲也一下子扑哧笑了。
住了两个月零十一天的院,终于,父亲活着回来了。他看着母亲笑,母亲看着他笑。他三十三岁,母亲二十六岁。直到母亲笑着笑着又哭起来,满脸是泪,他们才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慢慢往天井里走。风突然大起来,枣树、槐树、石榴树,纷纷摇响了自己的叶子,像是拍响了万千只小手。那头黑猪领着一群土鸡走在最前头,二舅提着好几个网兜,跟在最后头。娘!娘!母亲欣喜地忙不迭地喊。听见动静的奶奶抱着十个多月的二姐站在屋门口,身后,三岁的大姐牵着她的衣襟。娘。父亲喊了一声。公子回来了。奶奶说。回来了。父亲回答。回来了!母亲重复道。除了我和小妹,这个天井里所有的生命,人、牲畜、花木,全都目睹并迎接父亲的归来。那一刻,父亲是凯旋的王。父亲进屋后,天井里盛满了初夏明亮的阳光,像开了一天井的花,瑰丽、饱满、盛大。父母正年轻。重生后的他们,每一个夜晚都甜蜜而丰美。也是从那时起,我和小妹正式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在几年后四月初四那天,正是春天最好的时候,推开母亲的生育之门,一步迈进家里;又隔了几年,小妹选在农历八月十五,月圆夜,晚上九点整,一脚踏进家门。至此,我们一家人全部到齐了,从那一刻起,我们七个人互相陪伴,一起活着。
我以为人会一直活着。
直到十四年后,奶奶离开。我眼看着父亲把一个木头匣子深埋于大地。
又过了十六年,父亲离开。我眼看着大姐把一个木头匣子深埋于大地。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从此筑起了一座宫殿,它堪与世上任何最好的宫殿相媲美。奶奶与父亲,住在那里。
他们换了时空,以死,永恒地活在这世上。
九
石头。
直到现在,我依然想不清楚那块石头在我身体里是如何形成的。照穿了我腹腔的仪器显示,输尿管里有一粒八毫米乘五毫米的石头。输尿管的粗细我不知道。它不均匀,它像我体内的一条黑暗的隧道,宽窄有度。我曾去过四川的宽窄巷子,在那儿尝过有名的小吃“三大炮”。我说,掌柜的,来一份!只见一壮汉一边答应着“好啦”,一边手握三个糯米揉成的元宵大小的圆球,走至离食摊大约两米处,高举右臂,突然向着对面斜支着的铜锣一样的圆箕用力投掷,只听“砰!砰!砰!”三声,圆球正好滚进圆箕下的锅里;转眼,另一壮汉把圆球捞进小纸杯,插一根竹签递过来,大声说,三大炮好咧!——当我体内那块石头经过逼仄之处时,它被卡住,那一刻,它像一门大炮,对着我“砰!砰!砰!”密集开火。它这样一个坚硬的生命,在我体内凭空孕育、生长,多年间我竟毫不知情。这个夜晚,它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它的存在。
多喝水,让它出来。急诊科的医生看着片子说。
如果一直下不来怎么办?我问。
那就激光碎石。
回到家,东方一片嫣红的曙光,太阳将升未升。坐在阳台落地窗前,看着眼前中心花园晨风中团团涌动的浓绿,听着弯弯绕绕叫声如织的繁密的鸟鸣,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惊吓。
我像这世间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我在活着。
花盆里的薄荷与藿香鲜汁旺叶的。平时我只是给它们阳光、清风、清水,再没别的,它们却绿满了盆,越来越有模有样。读书写字乏了,我喜欢静静地坐在阳台草编的蒲团上,不饰修剪的花花草草与我近在咫尺。我曾长久地注视着它们。它们日夜陪着我,给我好看的颜色、好闻的香气,与我一起活在这世上。
我把薄荷和藿香成簇的尖尖掐下三五朵,塞进一把火山石烧制的拙朴的小茶壶里,再捏上十几二十几根红花泡水喝。红花来自伊朗。在那个遥远的国度,优质的阳光照耀它,肥沃的土壤滋养它,让它欣欣然活成了红花里的极品。它把自己最核心的好集中在蕊上。一根根纤细的蕊,红到发紫,沏出水来却是亮晶晶的明黄。澄澈,潋滟,又有碧绿的薄荷或藿香的叶片漂漾其中,很好看。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第一次,我臣服于一粒石头。那个上午,我在书房里,每写几行字就喝一小杯水。后来,我的体内流淌起了一条大河。预感告诉我,那粒神秘之石就要被冲出来了。
果然。
捡起,洗净,置于掌心。豆粒大小,棕褐,不规则的多棱状,阳光下,有如钻石,灿灿然闪着宁谧的光。不相信我的肉体曾铸造出这般物质。但却是真的。这一关我过了。未来还有多少场战斗等着我去输赢呢?无从知晓。只知道,接下来,我是自己的王,我要同自己的肉体,保持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
——从一粒钻石开始。

黛安,女,山东肥城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十月》《天涯》《山花》《新华文摘》等。已出版《青青子衿》《月光下的萝卜灯》《稻草人与蝴蝶》。多篇散文被收入年度选本。曾荣获第五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泰山学院。
来源:《芙蓉》
作者:黛安
编辑:施文
本文链接:https://wenyi.rednet.cn/content/2022/04/28/111755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