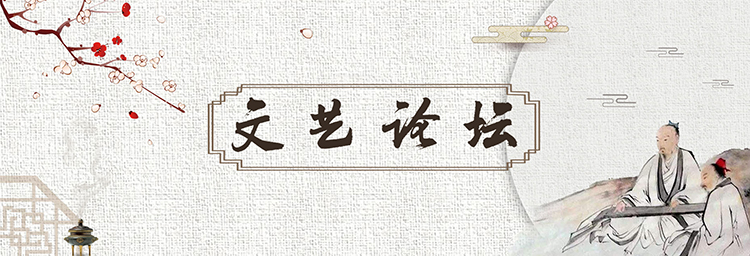

意义生成的悖论与人工智能文艺的事件性
文/胡疆锋
摘 要:人工智能文艺是生成,是独导,是断裂,是悖论,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当代文艺值得关注的事件。生成性构成了人工智能文艺的内在逻辑,也催生和创造了新的情感主体。以《庆余年》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文艺体现出人类对事件的兴起和撤销时的复杂态度,也反映了人工智能在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境遇与挑战。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艺;事件;悖论;生成;撤销
2023年底,一款名为《完蛋!我被大模型包围了》的原创游戏在中国爆火,这是一款充满挑战性和趣味性的解谜游戏,玩家可以在其中轻松学会大模型提示词的运用。游戏发布后迅速走红,激发了玩家与各类AI斗智斗勇的兴趣,服务器很快被挤爆,后来由于服务器压力和维护强度等原因,游戏被迫关服。主创团队接着推出了续作《我把大模型玩坏了》,也成功吸引了玩家的关注。现在看来,这款系列游戏的“暴得大名”真实再现了大放异彩的人工智能备受瞩目的现状。“完蛋”一词,既带有惊喜,也不乏恐慌;既是人们面对AI时的欢呼和凡尔赛式的炫耀,也流露出人们难以缓解的不安。这些情绪和症候都有事件性,正如德勒兹所说的那样:“在言语活动中上演的单纯事件,超越了它们出现时的条件和完成时的情况,就像一首乐曲超越了人们演奏它时的状况和人们对它的演奏。”[1]人们预感到AI会创造奇迹,但又不知道除了奇迹还会发生什么,仿佛是主人在接待一个任性的贵宾,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跃迁式发展,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关注重点不再是AI到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而是它还不会做什么。同时,人们对AI的态度似乎越来越焦虑,甚至有人用“最后的时代”来描述AI时代,语气颇为悲壮:人类文明有过很多高光时代,但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AI时代”这样被称之为最后的时代,文明即将被自己发明的AI时代全面征服。[2]我们从中也可以体会到AI时代人们的百感交集。
在《意义的逻辑》一书中,德勒兹曾经以“瓷器与火山”为小标题揭示了事件将至时的复杂意味。瓷器看似与火山毫无关联,但瓷器的明确性、脆弱性和火山的不稳定性、爆发力最终都指向一种关于意义生成的“悖论性”。瓷器精致、华丽,对人们来说“亲密而熟悉”,条理分明,但瓷器易碎,容易出现裂缝甚至破碎、坍塌,这种“沉默的、不可感知的、表面上的裂缝”即“表面的唯一事件”,这种裂缝“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外在的,它处于不可感的、非物体性的、理念的边界。”[3]这种裂缝会扩大,裂开的最终不仅仅是瓷器,还会有大峡谷、沟壑、山脉和火山,“噪音与沉默在终点的爆裂声和爆炸声中紧密和持续地交织在一起,这些爆裂声和爆炸声意味着裂缝的整个运作,体现在物体的深处之中,与此同时,内外的作用使物体的边缘变得松弛。”[4]德勒兹在这里说的“瓷器与火山”,是作为事件的意义(sense)的生成状态,这种生成既包含了意义的明确性,也包含了向无意义过渡和转化的模糊性,意义和无意义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之中。
在我看来,AI正是德勒兹所说的“瓷器和火山”,它的兴起正在和将要制造越来越多的“裂缝”和“爆炸”,必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AI的出现预示着可能改辙人类历史的事件的发生,无论怎么重视也不过分。限于专业和篇幅,本文将在概括事件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人工智能文艺的事件性特征。
这里说的“人工智能文艺”,既包括人工智能参与的文艺作品,即人们运用语言大模型进行的文艺创作,如微软小冰、清华九歌的诗歌写作,人工智能长篇小说《天命使徒》,“深度巴赫”(DeepBach)谱写的圣咏清唱剧,Sora生成的视频影像,等等,也包括关于人工智能的文艺作品,即科幻文艺、网络文艺中对人工智能形象的想象和塑造。从事件理论的视角看,人工智能文艺是生成,是独异,是断裂,是悖论,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当代文艺值得关注的事件。
一、多学科视野下的事件理论
事件(event)的词源来自拉丁词ēvenīre,有“在外”(ex) 和“到来”(venire)的意思,是当代哲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的常见术语。从20世纪后期至今,学界出现了“事件论”转向的趋势,事件“正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丰富谱系的,在动变、转化与独异中超越形而上学的新思想方法”。[5]许多理论家对事件都有专论。不过,虽然人们倾向于把事件与“重大”“改变”“有影响力”“非常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从整体上看,事件目前仍然是一个人言人殊的术语,正如有学者概括的那样:事件“是一个广泛使用的,但极其模糊的概念。关于它的本性、特征和关系,人们并未取得一致意见”[6]。
比如,叙事学、经济学、传播学和哲学等学科的事件话语往往大相径庭。在叙事学中,事件是故事(story)的基本成分,[7]“事件(event)是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文本、故事、素材(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是叙事理论的基础。[8]这样的界定基本上等同于“事件之不存,故事将安焉附”或“无事件,不故事”。类似的,经济学对事件的界定也非常宽泛,如普利司通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事件”,“创造性、兴奋性和热情是事件的前提”,策划事件是营销策略的核心,“让我们成为人类,将我们区别于田野的走兽。”“消费者正逐步把事件当作能够消费的产品来看待。”[9]这种看法也基本取消了这一概念的特殊性。在传播学和媒介学中,戴扬等人基于电视媒介的考察,认为事件是特殊的表演,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是对惯常的干扰,干扰正常播出乃至生活的流动,是仪式性表演,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10]这又把事件的范围大大窄化了,比如肯尼迪遇刺不是事件,而肯尼迪葬礼是事件,因为后者是经过策划并宣传过的。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不同学科对事件的理解各有侧重,其内涵有着云泥之别。
相对而言,哲学领域特别是西方激进哲学领域的事件概念更富有张力,更具启发性。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过程哲学”的视野中研究了“事件”,他认为宇宙是一个过程,宇宙永远是“一”, “宇宙永远是新的”,事件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单位,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的最终实体”,“这些被表示的事件必定包括遥远过去的事件和将来的事件”。[11]“一个现实机缘就是一种限定类型的事件。”[12]怀特海将事件视为构成现实世界的终极单位,强调事件的动态性、变化性和相互关联性,这与传统哲学的静态、孤立的实体观形成了鲜明对比。齐泽克在《事件》一书里列举了纷繁多样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明星绯闻、政权更迭、艺术冲击等,他认为:从日常生活中的意外到宏大神圣的事情,事件“都是带有某种‘奇迹’似的东西”,如宗教、爱情和新的艺术风格的兴盛等,最简单纯粹的事件就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13]他同时强调了事件的可撤销性或去事件化。齐泽克对事件的论述更为宏阔,也非常具有启示性。
注释:
[1][26]〔法〕吉尔·德勒兹著,刘云虹、曹丹红译:《批评与临床》(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2页、第1页。
[2]爱好有点多:《最后的时代,AI时代》,2024年6月13日。
[3][4][17][18][19][20][24][25][35][44]〔法〕吉尔·德勒兹著,董树宝译:《意义的逻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42页、第243页、第4页、第5-7页、第11页、第166、67页、第284、104页、第17页、第90-93页、第8-9页。
[5]刘阳:《事件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6]〔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王珂平等译:《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7]〔美〕杰拉德·普林斯著,乔国强、李孝弟译:《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8]〔荷〕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9页。
[9]〔美〕C.A.普利司通著,陈义家、郑晓蓉译:《事件营销》,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3、Ⅶ页。
[10]〔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麻争旗译:《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11]〔英〕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著,张桂权译:《自然的概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版,第16、44页。
[12]〔英〕怀特海著,李步楼译:《过程与实在》,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8页。
[13][4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王师译:《事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第191-192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事件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2AA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团队)
(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胡疆锋的《意义生成的悖论与人工智能文艺的事件性》)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胡疆锋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