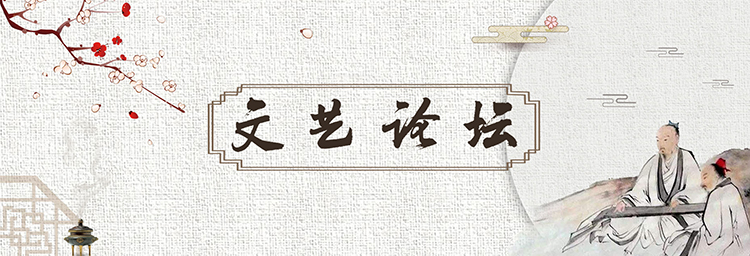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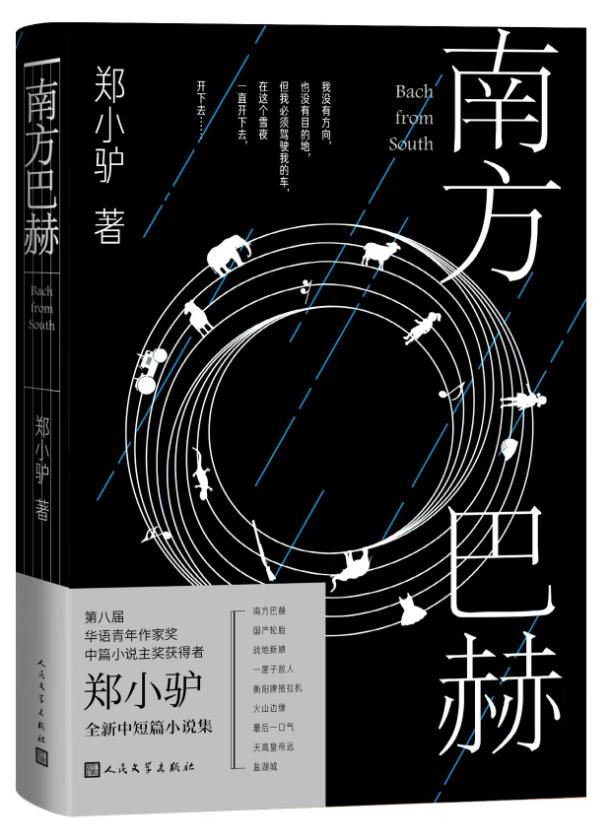
孤独、复调与“未完成”
——评郑小驴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
文/秦红玉
摘 要:郑小驴在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中对“透明”与“同质化”的追问,无疑是犀利而尖锐的。他将“小人物”置于一个复杂多变的空间,着力刻画其追寻姿态与孤独处境,强调“透明社会”中“距离”与陌生化的重要性;赋予“自然”声部明确的主观目的性,使其既承载一部分叙事意图,又修补了“人类”声部的情感裂隙;纵然,社会的“透明”使“小人物”的探索充满了误解和绝望,郑小驴仍以流动性和未完成性的创作理念,赋予他们在复杂而混沌的人生“莫比乌斯环”上持续奔走的希望。而这种“流动”的文本和“未完成”的故事,恰恰彰显了郑小驴小说的独特审美与现代性特征。
关键词:郑小驴;《南方巴赫》;孤独;复调;未完成性
在“传统作家与网络写手齐头并涌,严肃创作与市场写作各求其趣”[1]的21世纪,文学创作已然在数量上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数字时代的虚拟性和自由性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化的主题,更是打破了纸媒时代文学写作的时空局限,但数字时代的开放性和快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作品的严肃特性和审美趣味,使其趋向同一性、同质性。文学一旦失去它的审美性,就将永远失去它基本的活力。[2]那么,文学创作者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继续秉持严肃的写作原则,用冷静而个性的笔触剖析现实社会中人的生活现状和生存困境?郑小驴给出了两个关键词作为解答——“孤独”和“未完成”。2024年3月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包括9篇小说,即《南方巴赫》《国产轮胎》《战地新娘》《一屋子敌人》《衡阳牌拖拉机》《火山边缘》《最后一口气》《天高皇帝远》和《盐湖城》。郑小驴将自己和笔下的“小人物”们置于“喧嚣的孤独中”,始终对“距离”保有极大的热情,纵使陷于俗世尘烟的“莫比乌斯环”,也在不断地探寻,个人陌生化的“巴别塔”碰撞所产生的冲突和矛盾,直接导致了“小人物”的颓然和绝望,而小说的片段化叙事和未完成性又始终为“小人物”留下了一种通向“远方”的希望。在这之间,自然风物作为社会之外的“声音”,正努力地调和个人“巴别塔”之间的猜忌和冲突。可以说,小说集《南方巴赫》既是郑小驴对中国当代文学中陌生化写作的呼吁,也是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应当彰显严肃性、反思性和审美性理念的又一次试验。
一、“透明社会”中“小人物”的自我追寻与孤独姿态
“透明”,是数字化时代的特征。韩炳哲认为,“数字化时代的透明社会所追求的不是心灵的道德净化,而是利益和关注度的最大化”[3]。换言之,与古希腊哲人追求的“透明”、近代思想家探寻的“澄明”不同,在这样一个资本、信息与利益深度耦合的时代,“透明”已然跃出了理性思维的轮轨,成为一种禁锢人、限制人的因素。韩炳哲指出,“透明社会是一个揭露与曝光的社会”[4],这种“曝光”看似使社会中的一切都变得可见,但实际上允许被观看的只有具备“展示价值”的那一部分。“只有当事物被展示出来并得到关注时,才拥有了价值”[5],因此,数字时代的人们不懈追求“展示自我”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展示—利益”不断循环中获取的“透明”,是理想中正义、幸福的透明吗?答案是否定的。数字化时代的“透明”实际上是“不透明”的,这是资讯、数据、技术的透明,却是人与人、社会与自然间的不透明,“透明社会是一个不信任的、怀疑的社会,信任感日渐消失”,“社会的道德基础脆弱不堪”[6]。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将被彻底暴露在日益增加的海量信息下,而思维与心灵将永远被困于玻璃罩中,看似一切都“透明”,实际却是止步于“展示”,永远无法实现“理解”。在此基础上,郑小驴敏锐洞察到“透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巴别塔”,互相充满了误解、暧昧和绝望。面对这样一种个人生存的困境,郑小驴和他笔下的“小人物”没有驻足观望,也没有沉迷展示,他们虽然是孤独的个体,“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地”,但仍旧驾驶着他们的车“一直开下去”[7]。
在新世纪的“底层写作”中,“许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人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8],这种因思维惯性和精神惰性而产生的问题是严峻的。郑小驴已然意识到能拯救小说的不是骇人听闻的情节,也不是道德说教,更不是人性救赎,于是,他在人物形塑时将作家的主体意识隐匿,以极度客观、冷峻的视角刻画底层人民,使其摆脱非黑即白、非喜即悲的刻板印象。因此,他笔下的“小人物”很难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等二元观念评判,这种复杂性和差异性恰恰是对民众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
“孤独”和“追寻”始终纠缠交织在小说集《南方巴赫》的9个故事中,郑小驴笔下的“小人物”总是在不断追寻的过程中,遭受、拥抱、享受着孤独。郑小驴从不吝啬赞美孤独,“孤独能激发人的想象力”[9],而想象力正是文学写作所必备的。“孤独”不仅为小说人物提供了私人化的空间,更是赋予了他们不断探寻的勇气和动力。郑小驴善用孤独将小人物隔绝,有意将其放置在一个复杂、陌生且充满矛盾的社会中,观察他们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双重层面的异化。文本流露出对陌生与距离的热情无疑是在强调“他者”的意义,这是郑小驴抵御“透明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的尝试。在小说《南方巴赫》中,郑小驴借金宏明之口表达了对“孤独”与“私人空间”的青睐:
我喜欢车内的感觉,安全,私密,踏实。这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汽车是工作地点和家的无人地带,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一个人开车在家和公司之间的路上。”[10]
金宏明在透明的社会中找到一个半封闭状态的个人空间——表哥三岛的标致206,他喜欢私密,享受孤独,这个“无人地带”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是肉体的独处和精神的“隔离”。这种私密空间的“神圣不可侵犯”感与小说篇首的《马太受难曲》节选遥相呼应,“石碑”会“化作舒适的枕头”,“墓穴”是“灵魂的安息之所”,“我们无比幸福地在那里安睡”[11],正如金宏明将“最快乐的时光”定义在家和公司之间的汽车里。
逃离和阻隔是小说人物体验孤独的方式,郑小驴都在努力尝试让孤独紧裹人物的身心。小说《火山边缘》里“我”被“命运的球杆”推离北京,朋友们不理解“我”为何要将自己“流放”到偏远落后的塞内加尔,但“我”知道“荒凉和孤独正好是我喜欢的”,“离家万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可以完整地拥有自己,拥有一个个不受干扰的静夜”[12]。“我”主动选择了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塞内加尔就是“标致206”,是“无人地带”。由此,便产生了“距离”,而“距离”的产生对抵御“透明”是至关重要的。“空间距离的削弱带来的是精神距离的消融”[13],“透明”让沉思和睿智缺位,人们开始依赖呈现和经验。这也是郑小驴呼唤“远方”的根本原因,当“远方不再提供故事,只提供日常化的经验”[14],那么写作便会掉进同质化的陷阱。而“离北京越来越远”的“我”在面对妻子秋怀口中“琐细的日常生活”时,却始终能感觉到这一切在“时间和距离面前的无力和脆弱”[15],“我”享受“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无拘无束,所有烦恼和忧愁都被丢进记忆的垃圾桶”[16]。有意思的是,在日常经验性的认知中,“距离”代表时间或空间上的相隔、认知情感方面的差距等,且总与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印象一同出现,象征着疏离、冷漠等压抑情绪,因此,人们总是在追求拉近距离。而郑小驴在否定“距离”消极性的同时,也挣脱了日常经验性的认知,重申“距离”的重要性,甚至让其充当人类精神的卫道士。
小说《最后一口气》的“孤独”是被动的,源自“我”(罗涛)曾经亲手砌起的高墙。“我”在弥留之际走马观花地回忆了平凡又普通的短暂一生,最后,又回到“枫丹白露A区8栋18层1801户”,这是当年工地出事摔断腰椎神经的地方。可最终,“断桥铝合金门窗”“双层中空玻璃”和曾经“像一件艺术品”的“冰冷的墙面”,将“我”与屋内温馨的一家三口隔绝。郑小驴对建筑工人等“小人物”的刻画笔触是客观而冷峻的,主人公情感由隐忍压抑到歇斯底里,最后轻飘飘地归于一句“统统都不重要了”,看似是情绪在爆发后趋于缓和,实际却是坠入沉沉的无助和绝望。“将我彻底挡在外面”的结局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在席卷“我”的同时,也侵入了读者的内心,这正是距离与陌生的魅力。此外,《国产轮胎》中“生活在局部地区”的小湘西,《天高皇帝远》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副乡长刘小京,意识到“两千多年都未曾改变,来这儿两个月又能改变什么”[17]的省城记者小韩,以及“站在人生的边缘”迷茫的大学生村官彭理,《盐湖城》中“世上最孤独”的“多余人”刘明汉等,都是被孤独包裹的小人物。
无数“小人物”在透明的社会中追寻着自我,享受着“自由”,但当他们发现这种“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随之来的分裂感与落差感便会引起心理和精神上的焦虑、惶恐和暴躁。而当他主动揭开“透明社会”的“伪自由”面纱时,他便以“孤独者”的姿态从人群中出走。小说《战地新娘》中的群演老王便是一个觉醒的“孤独者”,他的沉默和“冷冷的”“充满了蔑视”的眼神在一众聒噪的群演中显得鹤立鸡群,他躲避“我”的镜头,拒绝握手,与“我”保持着距离。老王是“枪声一响,就要死”的炮灰角色,对“从一个剧组死到另一个剧组,每天变着法去死”的现状,他从一开始“他们让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我再也不怕死了”的漠然,到“恶心死了”的愤怒,到最后所有倒地阵亡的群演都复活站起来而老王无动于衷,以及他“充满了无尽的嘲弄”的目光。[18]这种唏嘘和揶揄何尝不是对“透明社会”和“伪自由”的嘲弄?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是老王“孤独”的第一层。然而,“更情愿站在美好生活的对立面”[19]的郑小驴并未给这个“小人物”摆脱孤独的机会,他用《最后一口气》对《战地新娘》进行补足,留给老王和读者的只剩更深层、更绝望的“孤独”。先看《战地新娘》中老王在愤怒阶段与“我”的对话:“‘这个剧搞完,老子再也不干了,我去当建筑工也比这个有意思,对吧?’我说是的,我很认同你的观点。他紧紧握住我的手。”[20]然而,通过前文的讨论可知,《最后一口气》中建筑工的绝望比起老王只多不少,那么希求成为建筑工的“老王”在面对建筑工罗涛的人生时,又该作何反应?郑小驴将《最后一口气》(第七篇)安排在《战地新娘》(第三篇)之后,想必是对老王的回答。只不过,这个回答彻底打破了“我”的肯定,阻挡建筑工人的冰冷墙面最终也将老王一并隔绝。这便是老王“孤独”的第二层。《盐湖城》中由“抵抗”到“预备顺从”再到“避无可避的反抗”的“小人物”刘明汉,亦是如此。
“当今社会中,到处洋溢着对‘透明’的热情,而人们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下对距离的热情”[21],因此,郑小驴以“孤独”重建距离,实现陌生化,这不仅是对私人空间的保护,也是对过度逼仄的生存境域的开拓。在信息过度曝光、生活依赖经验、交流止于展示的时代,唤醒对距离的热情意味着唤醒人们的好奇、沉思与想象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脱下那件标志着“其他的当地人”[22]的角色外衣,真正与“他者”重逢,才能抵御“透明社会”的侵袭。
注释:
[1][8]洪治纲:《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4期。
[2]秦红玉:《严肃精神与时代现场——论郑小驴长篇小说〈西洲曲〉与〈去洞庭〉》,《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3][4][5][21] 韩炳哲著,吴琼译:《透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页、第60页、第102页、第6页。
[6][14][22][52] 郑朋:《透明的噪声》,《文艺争鸣》2021年第5期。
[7][10][11][12][15][16][17][18][20][25][26][27][28][29][30][31][32][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9] 郑小驴:《南方巴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2页、第19页、第1页、第180—181页、第181页、第194页、第273页、第140—142页、第141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8页、第185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8页、第194—195页、第238页、第242—243页、第245页、第246页、第32页、第296页、第72页、第262页、第309页、第314页、第55页。
[9]郑小驴:《我的所来之路》,《青年作家》2023年第4期。
[13]韩炳哲著,程巍译:《在群中: 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19]郑小驴:《去洞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节选自2024年第4期《文艺论坛》秦红玉的《孤独、复调与“未完成”——评郑小驴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秦红玉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