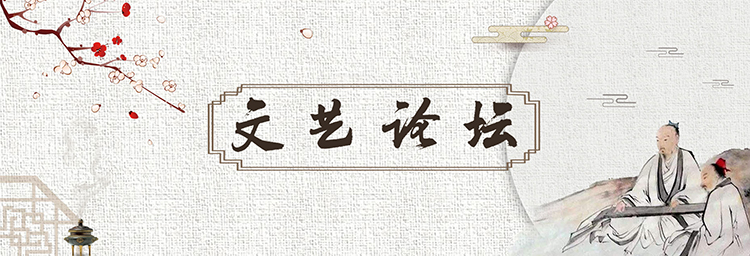

“文学人”书写模式及当代意义
——以残雪长篇小说《激情世界》为个案的考察
文/王迅
摘 要:作为残雪最新长篇小说,《激情世界》显示了作者小说审美观念的裂变。这部作品表层的通俗性抑或鲜明的“肉感”是阅读感受的第一层次,是作者哲学思想嬗变的结果。作为艺术发生机制不可或缺的两极,理性与非理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范畴贯彻在小说人物的世俗生活与文学生活中,同时也体现在小说人物的评论言说之中。“文学”与“人”的关系视域中,残雪为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文学人”书写方面提供了不乏开创性的实验文本。
关键词:残雪;《激情世界》;“文学人”;精神化;世俗化
迄今为止,残雪的实验写作已近40个年头。与20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形式实验不同,残雪的写作归根结底依托于哲学的底蕴。这并不是说残雪小说表达了哲学主题,而是说哲学在残雪叙事中已内化为一种小说修辞学。中短篇小说也好,长篇小说也罢,残雪文本所蕴含的哲学意蕴是一以贯之的。长篇小说《激情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的哲学品格同样依赖于小说艺术的本体性,流淌着残雪执着于她所虚构的文学世界的探索激情,而且这种激情是对世俗化和精神化的双重敞开,构成一种“文学”与“生活”互相交织的精神大厦的基质,彰显了以“身体”与“精神”互为本质的艺术哲学为基本内核的小说修辞学。
一、“难懂”到“易读”中贯穿的美学裂变及其叙事学
阅读《激情世界》,我们多少能觉察到残雪小说叙事艺术的新变。残雪小说一向给人晦涩难懂的印象。但这部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关系还是情节故事,也无论是小说修辞还是叙事话语,我们理解起来似乎不用花费多少心力。与《最后的情人》《吕芳诗小姐》《赤脚医生》《水乡》《五香街》等此前长篇小说相比,其文本表层追求变革的实验色彩确实淡化了许多。这是否意味着残雪小说朝着传统叙事“回归”呢?这恐怕是很多人阅读文本之前会产生的疑惑。况且,对残雪“新实验小说”来讲,没有形式上的“实验”,何以体现其写作的“实验性”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雪小说创作“突变”是值得关注的。厘清残雪创作的来路与去路,结合新世纪文化语境来探究其文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此基础上廓清小说审美意识嬗变的深层原因,不仅关系到深刻把握和理解残雪小说创作个案的问题,也有利于考察和反观新世纪文学发展态势中残雪小说艺术新变的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通俗化转型背景下,《激情世界》作为一部迟到的“转型”之作,昭示出残雪求新求变的审美渴求。此前,残雪的写作等同于艺术探险,那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灵魂之舞,是对艺术家灵魂裂变历程的探秘之旅。这种虚无体验的描写延续到新世纪创作中,如《边疆》及大量中短篇小说。然而,《激情世界》则显示了残雪试图从行为艺术表演的场所——灵魂城堡中走了出来。小说语言清晰、质朴,所指非常明确。“所指”的清晰化引人侧目。小说中几对男女主人公日常交往的情节线索与情感故事非常清晰,与《XXXX》等副文本构成互文关系。主人公在系列“副文本”的解读参悟中发现“自我”,解读“自我”,发展“自我”,大大降低了小说阅读的难度。同时,枝蔓横生的情感线是小说中一道迷人的风景,费与寒马、悦,寒马与费、晓越,小桑与黑石、仪叔,小麻与小桑、仪叔,雀子、黑石与柏铭等,他们的情感生活又与其文学生活相伴随。尤其是费、黑石、小桑挣破“生活之网”的精神突围充满神秘感,引发读者探一究竟的冲动,为小说抹上了悬疑色彩,成为提升这部小说可读性的重要因素。
这部作品表面上褪去了前期创作中艰深晦涩而压抑怪诞的叙事风格,似乎降低了阅读的门槛,而事实上,这是一部残雪挑战自己的雄心之作,是一部酣畅淋漓地发挥其艺术创造天才的典型范本。这源于作为小说家的残雪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应当说,把哲学与文学、生活与文学、肉体与精神演绎得如此水乳交融的小说艺术实践,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某种意义上《激情世界》是残雪对精神城堡的一次突围:把世俗的、肉体的范畴纳入哲学化的叙事体系,对爱情进行全新阐释,成就了一次不乏开创性意义的实验写作。
当代文学研究中,“身体”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包含着丰富的话语内涵。这个术语的使用基于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写作”现象。如陈映真《某一个日午》、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包含着历史、政治、文化的身体隐喻,为“身体”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受到学术界关注。“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①而对残雪来说,“身体”并非全然是“欲望”的代名词,也非抵抗权力宰制的政治话语,而是一个写作学意义上的哲学范畴。“身体”话语绝非残雪迎合读者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通向精神叙事的结构范畴而存在的。残雪小说所贯彻的身体哲学如其所言:“我的架构都是随意的,也从来不列提纲和规定故事的走向,而是沉浸在一种朦胧的营造中,写到哪算哪。但这种随意却是高难度的,因为必须符合深层的情感逻辑,也就是身体逻辑。”②残雪的写作看似“随意”,但显然并非毫无逻辑可言,背后隐藏着深层的“身体逻辑”。这源于残雪高度的理性自觉,只不过由于其文本的非理性、超现实特征,这一点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那么,如何理解残雪的“身体逻辑”,它在残雪小说中有怎样的体现?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考察残雪近年来哲学研究心得及其写作中将哲思审美化的过程。
在专访中残雪多次谈到其所撰写的批判西方经典哲学的专著《物质的崛起》③,其锋芒所指不乏象征意味。残雪被誉为“东方的卡夫卡”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情有独钟,而“跟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几乎都没有关系”⑤。然而,如今残雪一反常态,开始对其写作所依凭的西方话语展开猛烈攻势。这种大跨度“转变”在访谈中得到印证:“我从追求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精神境界起步,到中后期向追求一种新型物质文明境界转向,其跨度比一般的作家都大。”⑥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哲学在残雪眼中并非绝对完美。因此,她开始把目光转向“本土”:“我是中国人,特别热爱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中国的物质文化渗透到了我的血液中。但我同时又热爱西方人的精神文化,不知疲倦地在实践中向他们的文化学习。经过四十年的实际操作之后,我终于将两种文化元素在文学中融为了一体,现在已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⑦这里“中国的物质文化”对残雪而言等同于“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应该说,这种认识论转向深刻影响了残雪的创作,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小说美学,姑且称之为“物质”美学。
残雪的“物质”美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起源于对西方哲学中“精神”这一概念既定认识的反省。关于西方哲学中“理性”的强势地位,恩格斯尖锐指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⑧而残雪对理性/精神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只是近些年来,她意识到一味强调理性/精神的重要性有失偏颇,觉察到在审美认知中“物质”的同等重要性:“在以往的西方哲学主流中,物质、感性总是处于精神之下的次要地位。我则呼吁,被压制、被遮蔽的物质要崛起,与精神互相融合,平等地合二为一。”⑨如这部小说中小麻与仪叔作为灵魂与肉体的“双重伴侣”,超越了此前与男友之间纯肉体的交欢。值得注意的是,残雪哲学思想变化之于小说创作,在于她更强调“身体”逻辑的原发性价值,如小说第二部中寒马对《神曲》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解读,认为但丁由于没有令他刻骨的爱的对象,所以没有意识到“身体”功能,只能依仗于“僵硬的模式”,使作品不免生硬。而托尔斯泰在“观念”与“身体”的功能认识中摇摆不定,对安娜的塑造“遵循着身体发挥的规律”,而不是只听从“观念”的律令,所以,托翁在写到安娜之死便大哭起来。依照寒马的解读,安娜的形象在托翁叙事中因“身体逻辑”而站立起来,成为世界小说人物画廊里不朽的瑰宝。相对而言,列文的形象就逊色很多,那是因为观念的痕迹很重。其次,从叙述视点来看,《激情世界》关注世俗日常中的人及其处理情感的方式,且毫不掩饰其精神伦理背后的物质维度,构成肉体与精神互相纠缠而又互相推进的叙事结构。以第三部为例,黑石称雀子为“物质女孩”,其实并非贬义。正是雀子对世俗生活的执着与热情激活了黑石的“身体”,启动了他的情感,因此他体悟到“文学不应是纯精神事物,而应更偏向于人的肉体”。显然,小说人物的艺术观念与残雪“身体先行”或“物质先行”⑩的写作观具有同一性。最后,大量对话中世俗趣味的融入,充实了“精神”与“肉体”互为本质的审美机制,把貌似通俗的故事推向中西哲学交融的高度。如寒马与小桑的对话:
“寒马,你这么快就已经上路了!”小桑提高了嗓门。
“多么奇怪,我先爱上文学,然后就爱上了费!好像两个就是一个?”
“一点也不奇怪,寒马。文学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你就爱了。”
以上对话显示,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身体”与西方哲学里的“精神”实际上是互为本质的两个范畴,两者具有同质性。这种异质同构的艺术哲学与残雪“新努斯自然观”相契合,它是“哲学领域里千年争论中产生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一个中和,它以东方元素的参与有力地将这两派包容于自身,重组出一个崭新的图形。它的本体论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交合为自然”。而此前作品《吕芳诗小姐》《最后的情人》等所显示的那种努斯与逻各斯那种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在近期创作中则有所弱化。因为残雪写作的“终极设定都是倡导物质的缘故,物质就是质料体和生命体”,“处处让肉体和灵魂凝成同一个事物,所以肉体才能焕发出如此生动的力量”。因此,这部小说表层的通俗性抑或鲜明的“肉感”是阅读感受的第一层次,是作者哲学思想嬗变的必然结果。残雪对“激情”的界定,显然超出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范畴,而是一个哲学化的术语。因此,要进入文本阅读的核心层次,就要考虑残雪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否定性认识。
二、阅读、写作与评论的“一体化”
在叙述方式上,《激情世界》的“形式”追求并不那么明显,残雪试图打破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常规模式,而借助中西哲学话语的融通与更新来展开人类未来生活的想象。小说人物对副文本《XXXX》的阅读与评论,作为残雪叙事的重要策略,参与男女主人公情感故事的建构,并纳入小说的叙述系统,构成小说叙事的动力,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了小说美学的独特创造。然而,残雪不只是借人物之口对“副文本”发表评论,而是将人物融进“副文本”的世界。小说主人公生活在“文本”里,生活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显然,残雪的实验写作开始走出现代派小说艺术的表层空间,拒绝对读者构成阅读障碍的形式迷津,通过阅读、写作和评论的融合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接受美学意义上探索阅读的多种可能。
文学评论的前提是阅读。对残雪来说,阅读与写作同等重要,具有相似的艺术机制。残雪的写作有“即兴”特征。这种特征贯穿到小说人物文学生活的精神机制中。不难发现,读书会上的发言都是即兴的,对小桑来说“就好像自己里面有个自动发音装置一样”。与这种“即兴”评论相对应,寒马的写作也不像传统写作那样深思熟虑,而是从笔端“自动”冒出来:
“她一坐下来句子就来到了脑海中,好像它们不请自来一样。她接着昨天的境界一直写下去,妙语连珠,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吃惊了。她一点都用不着刻意营造,词语和句子排着队等在脑海里,只要她手上的笔一牵动它们,它们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那么有定准,那么老练。她的操作同以往相比完全变了样!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她不太清楚,她只是觉得有趣就写下来了。这些句子有点奇怪。然而它们多么有灵性啊,毛茸茸的,一串一串的,每一串都显得那么饱满和独立,像肥沃的地里的草本植物群一样,理直气壮,自成一体,形成各式图案。”
这段文字是对寒马写作状态的描述,它与小桑的文学评论都显示出“不请自来”的灵感机制,其中所显示的审美机制与残雪所称的“自动写作”何其相似!实验小说的创作机制就贯彻在人物所描述的阅读感受中:只要是谈小说,小桑就没有明确的思路。尽管如此,她却在心底有冲动,这种莫名的冲动迫使她说出一些话……这种言说几乎就是残雪关于文学写作的现身说法,非常精准地揭示了实验写作作为无意识与审美冲动并存的行为艺术的本质。又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网状物”,旨在暗示艺术创造中潜意识的发生机制,它“从暗处袭击我,扰乱我的思路,却又不给出一条出路……你想证实,却得不到回应,所有的回应全都似是而非”。这种艺术机制的揭示又全然基于“现实”的体验,与主人公在惠城所遭遇的那张“黑暗又温情的网”相契合。这里所阐释的审美经验在文学阅读中被称为“阴面”和“阳面”。在小说评论中,晓越虚构了读者G,通过G的阅读经验的讲述勾画出文学的理想之境,把文学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而寒马则将理想中的艺术发生学同日常世俗生活联系起来:“文学的内核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埋在每个人的心田里。它的生长依仗于人的那种内视的目光。那么人的内视的目光又是如何产生的?我想,它正好是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馈赠吧。”从审美思维特征来看,读者G实际上等同于寒马与晓越的“合体”,两者珠联璧合的发言既阐释了文学与日常的内在关联,又预示了他们未来结合的可能性。残雪通过日常世俗与理想之境的张力结构演示了“身体”与“精神”互为本质的关系。
如果说阅读、评论副文本《XXXX》的审美思维与残雪创作思维存在诸多层面的可比度,是残雪对实验小说解读模式的一种演示,那么,我们不妨把寒马的写作视为残雪“自动写作”的生动表演来分析。寒马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不同凡响”的作家,其作品《远征》发表在京城文学杂志《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残雪的写作不就是一次次精神的“远征”吗?由于这种写作的超前性,能够真正接受的读者极少,所以残雪才把自己的写作定位在“未来”:“最具有终极关怀的属于未来的作家”所写的“关于人的未来可能性的本质小说”。但这只是对文本本身从接受学意义上的界定,其实残雪并非绝对悲观。寒马小说以飞跃悬崖抵达极境收尾,暗示了残雪新作突破了西方哲学中的“彼岸”观念。此前的作品(如《边疆》《新世纪爱情故事》等)所预设的极境是无法抵达的,不过是彼岸虚幻的精神象征,而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小麻与仪叔、小桑与黑石、晓越与寒马,都在灵与肉的“远征”中挣破了重重障碍,最终抵达了极境。
“评论”与“写作”在小说叙事中的融合有利于揭示艺术发生学的精神机制。作为艺术发生机制不可或缺的两极,理性与非理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范畴贯彻在小说人物的世俗生活与文学生活中,同时也体现在小说人物的评论言说之中。残雪强调,她的小说是“潜意识”与“理性”合谋的产物。黑石在读书会上关于“无形之网”的发言演示了关于艺术发生机制的深层探索。黑石扮演具有冒险精神的行为艺术家。在探索中他意识到,不必回避“生活之网”和“情感之网”,而应主动与“网”合为一体。在理性规约下,所有的“网”反过来成为他行动的动力,而不是障碍。在第二部中,晓越在与寒马的感情抵达佳境时道出同样的体悟:“网不是用来绊倒人的,而是用来塑造人的。”“网”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理性对生命力的规约,是艺术发生机制中的塑形装置。因为“理性是一种压榨,为促使写作者的生命力爆发”,“让感觉的浪潮在制约下汹涌”,两者是“制约与突破”的关系。“网”是残雪小说中“肇事者”实现精神成长的隐形道具。她说:“我的小说中出场的每一个角色都心怀一种肇事的欲望,他们卷入冲突,挑起冲突,在冲突中成长。冲突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需要躲避的事物,而是机运,是自由意志的操练场所,也是提升自由境界的基本方法。”黑石就是这样的“肇事者”,他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神秘而又无休止的海上之行,便是“提升自由境界的基本方法”,可以视作艺术灵魂的探险之旅。
由此推断,如果把小说人物分为两个系列,那么,黑石、寒马的“破网”之旅所代表的是努斯的一极,他们是自由境界的“开拓者”,是非确定性的单元,而费、晓越则构成逻各斯的一极,是确定性的单元,某种程度上他们参与了命运之“网”的编织,在暗中引导努斯成形的过程中完成使命。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具有绝对性。小说人物都存在“诗意”与“自审”的双重气质,这种两面性是艺术家两极化生存的必备条件。比如,小桑就集“诗意”与“自审”于一身,既有强烈的自审意识,又不乏女性的激情。在残雪视野中,这两个系列实际上互文本体,两个就是“一个”。由是,对致力于写作的寒马来说,她与费“在文学上是一个人”,在创作中把费纳入其中,把努斯和逻各斯合成“一个”,一方面是作为努斯的“牵引”和“悬置”的突进运动,另一方面是在“高度的自律能力”作用下不断“刷新语言的所指”。而致力于文学研究与传播的晓越则肩负两个方面的使命,一方面作为寒马的伴侣及其欲望的“引诱者”,让寒马从世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另一方面,他与寒马都是“本质文学的追求者”。寒马小说属于“小众文学的最上面的那一块”,一开始不为大众所理解,所以,离不开晓越的评论与推介,隐喻着残雪小说本身所面对的接受现实。基于文学阅读的惰性生态,黑石与费创办“鸽子”书吧,其目的就是改变文坛对实验文学的冷淡态度:“在文学的前沿树立标杆,解放人的思想和体验,推动文学上的新启蒙。”同时,寒马充当自己小说的评论者,无疑是残雪创作与批评一体化文学实践的自况。邓晓芒曾指出残雪创作重要特征:“她对于自己的文学行动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对自己的作品和她所欣赏的作品作出远胜于一般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在这个意义上,《激情世界》双线结构的叙事美学,既是源于残雪集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于一身的审美实践,也是残雪小说的精神机制与叙事路径的艺术演示,从艺术实践的意义上显示了小说家审美活动中的理性自觉与自审意识。
(节选自2023年第5期《文艺论坛》)
注释: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美学意识形态·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②舒晋瑜、残雪:《我站在世界文学交流的前沿》,《红岩》2022年第5期。
③残雪在大量访谈中提到这本书。最初其锋芒指向萨特哲学,后来将批判范围扩大到整个西方经典哲学,其核心观点是“建构起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哲学”。参见笔者与残雪的对谈《自由表演的行为艺术就是我们生活本身》,《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④罗璠:《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⑤Charlotte Innes,The New York Times,Sept24,1989.
⑥残雪:《我不直接写困境,我是未来的文学》,见《三联新闻周刊》2021年第42期。另,残雪说:“为年轻人和未来社会里的人写作,传播最美的情操,是我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见《作家》2015年第15期。
⑦残雪、舒晋瑜:《实验小说是本质文学》.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⑨残雪、张杰:《最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哲学的境界——残雪访谈录》,《青年作家》2018年第7期。
⑩残雪认为:“我们日常的物质生活,人的身体,就是说身体可以搞出哲学来,这是没有人提过的,这是我自己独特的哲学观,没有任何人提过的。所以我的创作,三四十年的创作都是身体先行,理念就在身体当中。”参见陈小真关于残雪的访谈:《残雪回应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得奖对我来说是一件小事》,《潇湘晨报》2022年10月5日。
⑪残雪、邓晓芒:《旋转与升腾——新经典主义文学的哲学视野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⑫残雪:《探索肉体和灵魂的文学——访美讲演稿(下)》《名作欣赏》2017年第4期。
⑬残雪:《残雪文学观》,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第25页、第91页。
⑭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
⑮残雪、邓晓芒:《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⑯残雪:《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新世纪文学选刊》2009年第3期。
⑰残雪:《残雪·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⑱残雪称其所揭示的是“残雪”这位艺术家的艺术自我之谜。它既是演示一种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型哲学原理,也是用艺术家自身的肉体来做实验,看看这个生命体的张力有多大,能达到什么层次的创新。见《探索肉体和灵魂的文学——访美讲演稿(上)》,《名作欣赏》2017年第1期。
⑲程德培:《折磨着残雪的梦》,《上海文学》1987年第6期。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王迅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