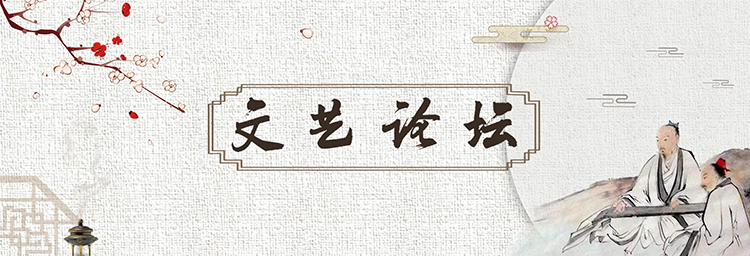

黄一骏/摄
乡村振兴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民俗文化表达
文/田振华
摘 要:民俗是乡村生活、文化的重要载体。乡土小说民俗书写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文学上和审美上的思考。本文重点以赵德发的《经山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叶炜的《还乡记》、付秀莹的《野望》等近几年涌现的乡土小说民俗书写佳作为例,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现状、价值、问题和未来。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土文学;民俗书写
民俗是乡村生活、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又是乡土小说的重点书写对象。我们把乡土小说民俗书写放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来探究,既有现实意义,也有文学审美价值研究的内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民俗作为乡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乡村的消失而日渐消逝。各个地域民俗的多样性,代表着中国乡村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乡土民俗文化的挖掘和复兴。可喜的是,乡土小说乡村振兴书写的诸多作品都对乡土民俗进行了大量的观照。但乡土民俗的复杂性、地域性特征以及民俗与乡村振兴结合并恰当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难度。本文重点以赵德发的《经山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叶炜的《还乡记》、付秀莹的《野望》等近几年涌现的乡土小说民俗书写佳作为例,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现状、价值、问题和未来。
一、让民俗文化“活”起来: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现状
自新文学革命以来,民俗一直都是乡土作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从现代文学中的鲁迅、沈从文、萧红到当代文学中的赵树理、柳青、郭澄清,再到新时期以来的贾平凹、莫言、张炜、迟子建等作家莫不是如此。民俗书写曾在对“启蒙”和“现代性反思”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已经成为学界民俗叙事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集体共识。即使到当下,民俗依旧是乡土小说重点书写的对象。但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今天,乡土小说民俗书写与乡村振兴有着怎样的关联,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民俗如何进入文本,即这一时期乡土民俗书写呈现怎样的现状。今天的乡土小说民俗书写既要在继承过往民俗叙事的基础上深入展开,又要呈现乡村振兴视域下新的时代价值。可以说,这也给乡土作家提出了挑战。在笔者看来,民俗内涵的乡土文化和乡村文明,与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有着内在的关联。乡土作家民俗叙事,一方面是通过对过往民俗的书写,挖掘乡土民俗的当代重要价值,重新让乡土民俗文化“活”起来,进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学上和审美上的思考;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又促进了乡土民俗文化的复兴,进而为乡土民俗书写提供现实参照,为作家的乡土民俗叙事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乡土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他们书写的乡土民俗要么是儿时的记忆,要么是通过间接经验获取的民俗知识。可以说,当下乡土作家的民俗叙事,是一种民俗的再认识,或者是霍布斯鲍姆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这种民俗的再认识就有了文化表征的意义,即乡土作家通过对过往民俗的书写,表达作家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思考。按照斯图尔特·霍尔的观点,“民俗”作为地方风景和地方之“物”的存在,本身不会产生意义,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①此外,乡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增添适应时代的元素。乡土作家会通过对当下经过现代转化的民俗的书写,展现民俗之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民俗文化的现代转化,使得民俗成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经山海》是赵德发的现实主义书写力作,作品中提及的诸多举措:对地方传统曲目“斤求两”的挖掘并将其列入市级“非遗”名录、以海边民俗踩高跷下海推虾为基础创办《海上高跷》节目、因地制宜举办楷坡祭海节和“鳃人之旅”项目等,都是在地方原有传统民俗基础上的创新之举,其中既有对传统民俗予以改造以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举措,又有将传统民俗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的探索。这既给现实生活中传统民俗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参考,又给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土作家民俗书写提供了借鉴。此外,《经山海》被改编成电视剧《经山历海》在央视播出,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这无形中使得小说文本及电视剧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当然,这种“软”推动或文化推动的方式,有时候更多的是以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的,但又是内在而长久的。同样在付秀莹的《野望》中,作者甚至直接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各个节气名作为每个部分的小标题贯穿全篇,作者以大量富有诗意的笔墨,倾情描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芳村”的变与不变。芳村人依旧在“二十四节气”中与自然、土地、气候等相互交融下生产生活着。作品中,作者使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芳村这地方”,如:“芳村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本家院房里,小辈儿们都要到老辈儿人家里去磕头。去磕头的都是男人家,凡成家立业的男人,不论年纪长幼,只论辈分高低。芳村有句话,萝卜不大,长在了背(辈)儿上。”“芳村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吃过饺子,都要到坟上去,烧纸,点炮,端着饺子,带着白酒。”②“芳村这地方,出了门子的闺女,正月里要回娘家,叫作回门。”③在《野望》中,诸如此类的地方民俗书写比比皆是。虽然乡村振兴的春风已经在芳村吹响,一系列政策已经落地生根,但是芳村依旧保存了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诸多民俗元素,那种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等礼俗和传统文化元素依旧深深扎根在芳村人的心中。这些礼俗和传统文化元素的再发现,无疑为当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参照。我们要恢复那些被破坏甚至消逝了的传统民俗,让民俗重新成为建构乡村生活、规范乡村道德、传递乡村情感的重要力量。
民俗书写,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或传统中的民俗,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书写,一定有其内在的差异。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作家一定也有着自我的民俗选择,有意无意地展现着各自的价值观。如果说“五四”以来乡土作家站在现代性视角上进行的民俗审视,大多是从“民俗启蒙”和传统文化批判的视角展开的话,那么,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作家的民俗选择,则更多是从本土化视角进行传统民俗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和再呈现。当下的乡土作家会有意无意选择那些符合现代社会潮流或者正在现代乡村发挥作用的民俗进行书写。这样看来,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趋势,无形中影响了作家的民俗选择。如在关仁山《金谷银山》中,范少山作为新时代的“梁生宝”或“新乡贤”形象,他的民俗选择很明显受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特别是在作品的最后,范少山带领村里的小孩背诵“村志”的场面,明显可以看出范少山想要带领村民重新学习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志民俗文化的愿望。当然,这一定也是作家的选择,更是作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观念的直接体现。在叶炜的《还乡记》中,主人公赵寻根忆苦思甜寻找童年的民俗记忆这一情节,既可以看作是一种乡愁的体现,又与当下不忘初心的价值观念异曲同工。赵寻根作为离乡的知识分子,返乡后多次与小学同学一起去观看“伏羲女娲”庙,试图再次挖掘“伏羲女娲”的民俗传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意象的再发现,这同样是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而进行的民俗选择。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既是作家主观情感的选择,又是他们理性思考的结果。民俗作为乡村的一道文化“风景”,成为传递他们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和寄托。作为记忆中的民俗,作为民族文化“活化石”的民俗,乡土小说能够让民俗文化“活”起来。在乡村日渐衰败而不得不进行乡村振兴的今天,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乡土作家民俗书写的重要贡献。
二、文化共同体的彰显与当代“根性文化”的重建
进入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书写民俗,特别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书写到底还能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怎样的文学上和审美上的思考?笔者认为,正是我们经历了几十年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丢掉了乡村文化中本不该丢失的那一部分,才显得当下作家民俗书写尤为急迫。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于个体而言,提高了个体的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但是也无形中使得现代人变得日益呈现个体化、原子化状态,人与人之间由原本呈现的不可割舍的关联状态,变为越来越陌生的状态。这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的力量,重拾原本属于我们的共同体的意识。民俗就是集体意识和行动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就是对文化共同体的彰显。“当一个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一定自信的时候,寻找自身文化认同的时期就到来了。”④民俗既是现实人生活的展现,又是文学表达的重要载体,还展现着深层次的文化意义。民俗除了与个体情感产生直接关联,还是整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这种关联彰显的就是“中华文化共同体”。
通过世代传承以及共同坚守,民俗已经成为一种连接民众之间“文化共同体”的载体。在中国,这种文化共同体既有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而产生的小的文化共同体,又有多民族共享的民俗中产生的大的文化共同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会形成属于自我独特的民俗样态,这已经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与历史久远、地大物博而又民族众多的中华民族本身直接相关。生活在某一地域的人们,其身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地域的烙印,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是那个地域民俗文化特征的外显。这种对地域性民俗的坚守就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小的文化共同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的节日、饮食习惯、服饰装扮、话语方式的差异,就是最好的体现。这种地域性的民俗之所以是民间文化共同体,是因为这些民俗是这一地域中所有人约定俗成而自觉坚守的。在付秀莹的《野望》中,芳村人的讲究,芳村人的伦理,芳村人在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中形成的家族(庭)关系,芳村人的“社会面向”(贺雪峰语)等依旧延续了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内核。如“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有讲究的。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升天”⑤,芳村人一直遵守着这样的“讲究”。再如瓶子媳妇与翠台在对话时说道:“论起来,我家他爷还认着广聚他奶奶哩,他爷跟广聚他爹,算是干兄弟,瓶子跟广聚,算是干堂兄弟。”⑥干兄弟、干堂兄弟这样的称呼,也许只有在保留着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芳村还存在着这样的“社会面向”。同样的,当赌徒有子因为赌博欠下巨额债务后,是芳村的亲邻帮他渡过了难关,后来有子母亲被气死,在丧礼上,亲邻们都回来帮着料理后事,才帮有子渡过了难关。这在城市之间形成的陌生人社会,也许是看不到的现象。实际上,在贾平凹前几年的乡镇书写作品《带灯》中,已经有过这样的思考,乡镇综治办主任带灯为处理好她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没有采用强权控制的方式,而是选择和农民做“老伙计”的方式,拉近她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这种“老伙计”的关系,同样是乡土民俗中所涵盖的内容。我们通过付秀莹、贾平凹等作家的民俗叙事,看到了当下乡村或乡镇依旧保存了传统社会的小家与大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村里面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共同体意识。
按照贺雪峰“乡村社会面向”的理论推演,村庄中小的共同体会汇聚成大的共同体,而大的共同体汇聚成更大的共同体,也就是在差异中不断寻求到了同一,这种同一背后的文化样态就是中华“根性文化”,即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也就是代表中华文化整体特质的那种文化,同样是今天我们乡村振兴要挖掘和倡导的那种文化。只有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绵延不断、世代流传,这就是集体认同的力量。所谓认同,“本质上是对自我根源的不断追寻,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问,是对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⑦。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等的终极追问便不断产生。如在叶炜的《还乡记》中,主人公赵寻根从城市回到农村给祖宗迁坟,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逝去的祖宗找个好的“归宿”,也就是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这既满足了他父亲的愿望,同样又是他内心认同后的选择。赵寻根的爹给他打电话说道:“寻根,寻根啊,麻庄出大事了!咱们老赵家的坟场被大水淹了!麻庄矿发生了坍塌,村东已经是一片汪洋大水。你赶紧回来一趟看看吧,咱爷俩得好好寻思寻思给列祖列宗找一个新的坟场!”⑧赵寻根听到列祖列宗以及他早逝的娘的坟墓被淹没,立马感到心痛不已,火速从城里回到麻庄。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祖坟、风水对当代人的影响。给祖坟选择一个风水宝地是地方民俗的体现,同样展现的是现代人对已故人的孝敬,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敬仰。现代人之所以依旧延续古代人的那种民俗文化、民俗心理和民俗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民俗背后的中华根性文化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另一方面是对孝道文化、宗族文化认识后的必然选择。归根结底,人是以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方式存在的。关于人的终极追问更多涉及的是对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⑨在中国广大乡村,这种确认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民俗文化。“民俗作为传承性生活方式,是一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层,也是多元文化中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它是一国文学艺术形成的基石,奠定和规范着一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流向。”⑩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作家民俗书写通过对民俗文化的挖掘,背后呈现的就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力量所在。换而言之,在乡村日渐衰落,乡土民俗日渐消逝的今天,在文化认同式微的当下,乡土作家通过民俗书写呈现中华“根性文化”,彰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根性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因,是滋生中华文化生长发育的基础。“民俗文化支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它潜移默化地养育了世世代代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成为民族凝聚的基础”⑪,更成为“根性文化”的标志。我们可以透过生活生产、岁时节令、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表层,隐约看到中华传统中深度的精神文化缩影。这一缩影很大程度上是古老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密码,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在当下的显现或隐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展现,可以更为直接和鲜明地显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每一个民族的这些差别性之间,习俗恐怕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构成着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那采取顶礼膜拜性质的宗教理解;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为一切阶层所共通的原语言;尤其不可能想象一个民族没有一种特殊的、仅属于它所有的习俗。”⑫可见民俗在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独特性中的重要作用。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背后,实际上都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民俗成为探究中华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路径。关仁山《金谷银山》中范少山带领村民重温“村志”的内容,既是地方文化的彰显,更是中华传统根性文化的结晶;叶炜《还乡记》中主人公赵寻根回乡对“伏羲女娲”传说的追踪,背后要找寻的也有中华“根性文化”元素,等等。这些都暗含着当下乡村振兴和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所必要和急需的元素。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问题和未来
当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给研究者提供丰富阐释空间,但同样也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乡土小说民俗书写如何才能恰当地与乡村振兴内在结合起来,而不是为了写民俗而写民俗,或为了展现乡村振兴而强行把民俗拉进来。怎样在文学作品中,以审美的方式搭建民俗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也是对乡土作家很大的考验;新一代缺乏民俗生活经验的乡土作家,如何突破经验匮乏的困境,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等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土小说民俗书写,存在民俗与乡村振兴强行关联的现象。当下部分乡土小说特别是偏向于纪实性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为了表现乡村振兴的实绩,大量呈现乡村中的民俗。一方面,这些民俗的真伪尚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这些民俗并没有真正很好地融入文学作品,这些民俗书写是为了民俗而写民俗的书写。有些民俗书写背后部分呈现的是作者过于明显的“主题先行”思路;有些民俗书写与作品中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关联度不是很高;还有一些民俗书写甚至显得多余而累赘,等等。这就需要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将民俗的呈现、审美的表达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进行通盘考虑,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真正需要的那些民俗,以富有文学性、审美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方面,赵德发的《经山海》、付秀莹的《野望》等作品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参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乡土民俗的日渐消逝已经是不可更改的现实,乡土民俗作为几代人的记忆,更多成为老一代乡土作家的回忆性叙事,那么新一代更为年轻的乡土作家如何面对饱含价值和意义的民俗呢?就目前来看,乡土民俗叙事的接续性明显存在问题,乡土民俗叙事的主体依旧集中在“50后”“60后”这一批相对年长的作家群中。当然部分有着农村生活经验的“70后”作家的民俗叙事也有较为集中的输出,甚至个别“80后”作家也在尝试乡土民俗书写的新可能。但遗憾的是,当下的“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作家群体,是城市生活经验丰富而农村生活经验匮乏的新世代,他们对民俗的了解更多地停留在长辈的言传和书本知识中。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民俗生活直接经验积累的机会。这样也就不难看出,为何当下更为年轻的作家群体,没有写出令我们满意的民俗书写文本,或者没有看到他们在民俗叙事中挖掘出新的可能。新一代年轻作家如何面对乡土民俗经验的缺失,从而写出更具时代性、新颖性的民俗叙事作品,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面对当下的民俗变迁,身居城市的年青一代作家,要有深入乡村甚至扎根乡村进而了解和认识乡村的执行力和意志力。这与乡村振兴对年轻人的诉求也是一致的。我们只有真正了解和认识乡村,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乡村。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付秀莹的《野望》、叶炜的《还乡记》中,都写到了新时代的年轻人返回农村建设农村的情节,这是当下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家面对乡村振兴的主动选择。面对乡村中民俗文化的振兴,新一代的年轻作家有着一定的使命和责任。一方面,他们要像人类学家一样,真正深入乡土民俗内部,找寻乡土民俗在今天的新变,发现乡土民俗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他们要像柳青创作《创业史》那样,增强扎根乡村的勇气,深入农村现实生活内部,甚至和新时代的农民打成一片,真正了解农村人的民俗生活,这样才能写出具有鲜活时代气息、生活气息的民俗叙事作品来。从柳青《创业史》的巨大成功来看,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当然,这也是给当下年青一代乡土作家的考验。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科技化较为发达的时代,同样是一个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亟待更新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文学的功能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学的信息传递功能日渐消失,思想传递的功能日渐提升。民俗书写同样是如此。可以说,依托中国的地大物博,整个20世纪的乡土文学,在地域性、独特性、差异性的传递上,总能不时给读者带来鲜活的阅读体验,而这种体验很多时候是通过地方独特的民俗风情传递出来的。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贾平凹等人凭借自我对地方民俗的大量展现,依然可以在读者面前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现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阳光之下无新事”,文学的信息传递功能早已被网络、自媒体等取代,几乎没有读者需要从文学中获取直接性的“新闻”。读者对文学的期待也已经从新闻信息的吸收转而到深度思想的获取。正如吴义勤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更复杂,也更残酷;网络比小说更迅捷,更直观,也更包罗万象。真正的写作变得分外艰难。作家仅有讲故事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思想的能力,才能穿越生活万象,澄清庞杂;不仅要凸显地域的优势,还要掌握人类化的整体视野,才能准确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现实。”⑬鉴于此,当下的乡土小说民俗书写,在传递地域民俗独特性的同时,更多是对自我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递。诚然,任何的写作背后都有着作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注入,但是,今天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一方面需要更为贴近当下的思想主流,从而引起读者大众的思考和共鸣,另一方面那些更为深刻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甚至需要更为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真正抵达读者的内心世界。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土作家民俗书写可以看作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再想象和再生产。同样,民俗作为现代人日常生活和未来精神指向的一种参考、一种补偿,乡土小说民俗书写在对时代和民俗变迁的回应、形式探索、美学建构、思想意蕴等方面,也都会展现独特的、新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近年来文学创作特别是乡土小说书写领域的重要收获,同时也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域。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研究,同样需要更换新的视角和思路,我们不能按照惯常对民俗文化的启蒙视角,也不能站在二元对立视角一味地进行现代性批判。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民俗书写,既是现代化背景下城市对乡村的回馈、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和观念对传统思维和观念的积极更新和干预,又是通过民俗叙事重新认识乡村文化,挖掘和发现乡村文化新价值、新内容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振兴不是城市或工业对乡村的馈赠或施舍,而是国家发展到现阶段一个本该就有的进程,同样是挖掘和复兴民俗文化背后彰显的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这就需要部分作家以警觉的心态,调整自我面对乡村振兴和乡土民俗的观念。乡土作家更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站在进化论的现代化城市视角审视乡土民俗,以此评判乡土民俗的优劣高下,同样也不能以一种追捧的态度过于抬高乡土民俗的价值,而是要深入乡土民俗的内部,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情怀,呈现民俗之于人的情感、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重要意义,以此彰显乡土民俗之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英]斯图尔特·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表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②③⑤⑥付秀莹:《野望》,《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2期,第44页、第45页、第17页、第20页。
④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⑦⑨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⑧叶炜:《还乡记》,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⑩ 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⑩乌丙安:《民俗遗产评论》,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⑪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⑫吴义勤:《哲思的格调——关于王威廉小说集〈非法入住〉》,《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第14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261)、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江苏长篇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2ZWC003)和江苏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项目“当代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1XFRS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田振华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