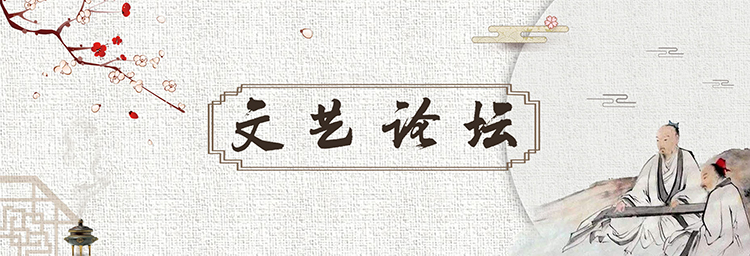

唐盛利/摄
“技术下乡”与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科技书写
文/范伊宁
摘 要: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不仅在政策和技术上给予了不同时期乡村建设直接有力的支持,更通过直观的生产效率和收益,改变农民生产劳动方式,进而影响着农民思想观念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以乡土小说中的“技术下乡”、农业技术员形象价值变迁以及“技术塑人”等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时期乡土作家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认识与变化,从另一个维度梳理以乡村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思考在当下乡村振兴建设中“科学技术何为”。
关键词:当代乡土小说;技术下乡;农业技术员形象;乡村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运动,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建设的重心很快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农业生产发展”上来,但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能够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人民政权只能给他们土地、耕畜贷款和农业贷款,号召他们组织起来生产,不能用某种魔术,使他们在骤然之间变富起来”①,因此乡村建设首先要面临的即是对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建设。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下乡与推广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产热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乡村土地制度改革及相关的“爱国增产运动”“改良农具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到新时期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等,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与更新,在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在以往的乡土小说研究中,农业科学技术以及农业技术员形象更多是作为乡土文学研究的背景,而将“技术”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不仅能够具体而有力地把握乡村建设的历史细节,而且能够聚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与局限,以及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农民观念与乡土文化。
一、“技术下乡”与技术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文学书写
“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②所谓“农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等具体建设内容。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推广新的种植经验,其中包括改进传统农作物种子,进行新品种育种、种植,推广使用新的种植方法;二是改良传统农具,使用现代农业机械,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展开。从种子培育改良、种植方法更新到传统农具改良、现代农业机械的使用,在生动鲜活的乡土小说细节描写中,明晰呈现出“技术”视角下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之路。
(一)新型种植方法实验与推广书写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对传统生产劳动方式进行升级改造,其中改良传统种子、培育高产量的新种子,推广新的种植方法等成为当代乡土小说书写乡村生活时代特征的重要细节补充与切入点。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对改良后的农作物种子在乡村的培育与推广书写较为鲜明,《创业史》中梁生宝不辞辛苦,远赴几百里之外买回“百日黄”稻种,向蛤蟆滩村民宣传新稻种的优势;《山乡巨变》中陈大春向盛淑君畅谈以后的规划时,提到将来要对“土果”种子的改良,将酸涩的“土果”改良成甜果;《三里湾》中玉生将六种谷种按照省里推广密垄密植的种植经验,分区种在试验田中试验谷种,寻找最适合本地种植的种子。刘玉堂在《乡村温柔》中描写隔壁村来学习“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而“头年地瓜大丰收,全仗了品种好,全县统一种上了胜利百号大地瓜”③。贺享雍长篇小说《土地之痒》不仅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结构、传统乡土文化和农民生活、情感的影响,还涉及了乡村建设具体措施在农村的实施与成果,其中,贺世龙对新的农作物种植方法的接受与否的描写,体现出农民传统种植经验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可能。
除此之外,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方法的另一要点是对农村种植技术与方法的改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建设中,一方面经过兴修水利、梯田,提高灌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改进种植方法,使用化肥、农药等,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三里湾》中三里湾的试验田不仅试验密垄密植的种植方法,还决计开渠引水,将三里湾的滩地变成水地,提高农作物产量;《山乡巨变》中关于“修水库,将干田变成活水田”实现增产的描写,作家大量描写关于“双季稻”的新种植方法,以及使用这种种植方法后稻谷产量的提升,如小说中刘雨生和邓秀梅论及秋收情况时说道:“水稻当然只能插双季,不过我们这里土质好,除开主粮收两季以外,冬春两季,还能收好多杂粮。”④“双季稻”的种植是品种与种植方法的革新,借助人物之口,小说不仅描写新的种植技术对粮食产量的提升,还表现了新的种植方法对土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通过现代种植技术在合作社的试验成果,显示出现代农业技术的优越性。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使得土地流转政策后形成的集约化经营更具优势,《金谷银山》中范少山到乐亭学习,借人物之间的交流向读者描绘了现代农业生产利用手机平台和电脑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实现农业“‘互联网+服务’,还实现了‘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销售’”⑤。同样将现代网络技术运用到乡村生产中的描写还有赵德发小说《经山海》,小说中吴小蒿了解到由海洋大学研究发明的“深海一号”全智能专利技术可以实现智能渔业养殖,提高渔业产量与经济效益。不同时代作家笔下有关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书写,不仅作为时代背景记录下不同时期农民的生产劳动方式,更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有情的乡村发展史记录。
(二)农业生产工具改良与农业机械化书写
现代农业机械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劳动效率,也改变了传统农业小农经营方式。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农业生产工具改良、农业机械初步发展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农具变迁书写中记载着乡村现代化的历程。
1959年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⑥,农业机械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因此对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而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机械化水平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写到有关农业机械相关内容时,更多呈现出农业机械带给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以《三里湾》为例,小说中的干部张永清向大家介绍“他在省里国营农场参观过的一架‘康拜因’收割机割麦子”时,因为大家想要知道的更详细,而张永清自己对于机器的各个部分没记住,只好表演,“他说,那家伙好像个小楼房,开过去一趟就能割四五耙宽,割下来就带到一层层的小屋子里去,把麦子打下来、扬簸得干干净净,装到接麦子的大汽车上……”⑦这段描写写出了在现代农业机械的超强生产力和工作效率面前,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精神面貌。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施行,标志着农业机械化建设被纳入法律,农业机械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统计,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90年的2.87亿千瓦,到2020年已增长至10.56亿千瓦⑧。和“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农业机械化书写相比,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描写更加深入,作家在看到农业机械化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思考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生活、乡村生态环境等的影响。
新时期矫健的短篇小说《农民老子》讲述了农业机械化在乡村推行面临的现实困难——经济问题,通过父亲“老牛筋”这样一位看似固执保守、不肯接受大型农业机械的老农民之口,讲述庄稼人种地的“经济账”,从而进一步引发作家对“教育农民”以及农业机械化现实问题的思考。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描写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捕鱼工具对葛川江生态的破坏;在贺享雍小说《土地之痒》中,贺世龙之子贺兴成先后买来手摇脱粒机、电动脱粒机、微耕机等,贺兴成购买的机器更新迭代之快,结合此前描写的传统农具与生产方式,呈现出一幅乡村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图谱。同时作家也描写了贺家湾过度开垦土地,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的现象;关仁山小说《金谷银山》借助农业专家孙教授之口反思使用农药对农作物的危害;《日头》描写矿产开采对农村环境污染;《麦河》中鹦鹉村因为青肥污染、水污染导致土地板结,影响植物生长,又因为农药、化肥等大量使用,造成了麦河水体污染;付秀莹小说《陌上》对芳村环境污染的描写等。作家从乡村生活的细节与问题,不断反思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化建设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不同时期乡土小说中有关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乡村应用的描写,展现了农业科学技术影响下农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乡村建设动态图,另一方面,从对乡土小说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描写的梳理分析中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作家在“农业科学技术”书写层面展示了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从“技术崇拜”到“技术理性”“技术反思”的思想变迁。
二、“技术定位”:农业技术员形象与价值功能变迁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机械在农村的宣传与推广,还需要实现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下乡”的重要媒介——农业技术员的参与。尽管“农业技术员”形象在乡土小说中多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作为乡村生产劳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推广者,这类人物形象可以联通乡村内外,多方面展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与问题。而农业技术员在乡村建设中地位与价值功能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对科学技术以及科技人员认知的历史变迁。
(一)“技术—政治”:革命语境下的农业技术员形象
和“农村新人”以及下乡的党员干部相比,作家对农业技术员形象着笔较少,而“十七年”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业技术员形象不仅承担着宣传推广新农业生产技术的责任,往往还需要参与农村合作化运动等行政管理工作,在劳动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在政治觉悟与思想道德方面更有着明确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技术员可以分为两大类:在乡村成长起来的有着丰富经验与创新精神的农民和经过专业培训、有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背景的“外来者”。首先是作家对生活在乡村中“劳动能手”的关注,受农村实际生产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需要依靠改良传统农具,在生产经验、技术方面,也需要利用传统经验,一些具有丰富劳动经验的农民被聘为技术员,如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农村的“劳动能手”成为研究员的事迹⑨,从农业生产“土专家”到现代农业技术研究员的转变,一方面肯定了乡村“劳动能手”的劳动与技术经验,另一方面也鼓励了更多农民积极参与现代农业技术实验与推广。“十七年”时期的小说中,同样塑造了诸多乡村“劳动能手”的形象。以《三里湾》为例,有着“小万宝全”称号的王玉生,不仅是乡村发明家,更是三里湾的农业技术员,“他分内的事是那些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农具,决定下种时期、稀密,决定间苗尺寸……一些农业技术上的事”⑩。小说突出了王玉生的农民身份,通过描写他对新政策的支持、对新生产技术的学习与掌握等彰显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特质。
除了对乡村“劳动能手”技术经验的现实肯定与文学书写,乡村现代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更需要专业人员的技术支持,因此作为“外来者”形象出现的“农业技术人员”群体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生产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人物类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训的干部下去,结合有经验的老农以及劳动英雄等组成提高生产技术的指导核心,不断地向群众学习,采用科学与经验结合的方法推动耕作技术”⑪,成为农业技术员的工作常态。而他们下乡后融入乡村生产劳动生活的过程以及农业技术员工作任务的多样性等细节在乡土小说中得以呈现。以《创业史》中的韩培生为代表,小说中韩培生作为农业技术员直至小说后半部分才出场,出场后的韩培生不仅需要承担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任务,还需要帮助互助组合作工作顺利展开,工作中他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指示:“要克服单纯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偏向,要帮助做点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的工作。”⑫而从他的日记内容以及蛤蟆滩村民对他的称呼由“韩同志”到“老韩”的转变,可以觉察到韩培生在推广农业技术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农村的集体生活。
这一时期乡土小说有关农业技术在农村推广及帮助农民丰产增收的描写,更多是侧重于从“技术—政治”的角度,在人物“现代科学技术”能力之外,更加注重人物所处的阶级立场以及思想觉悟。《创业史》韩培生在参加蛤蟆滩互助合作工作以及宣传推广新技术的过程中,坚定了入党的决心,在劳动中感觉到“生活在这班纯朴的庄稼人里头,饮食上虽然艰苦些,精神上却是多么愉快啊……生活在劳动者中间,使人更多地更高地要求自己”。⑬柳青在小说中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踏开了一条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的道路;后来,这条道路就变成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了。”⑭显然,作为“知识分子”的农业技术员,在这一时期下乡指导农民从事新的生产方式时,更重要的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融入乡村。因此,《山乡巨变》中谢庆元尽管是田里功夫行家,但是由于思想觉悟不高,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而社长刘雨生说到农业技术推广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位置时,更是强调了“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⑮。在这样的语境下,“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大程度上被“技术—政治”取代,“此时的‘技术’并不能归于单一生产力范畴,而恰恰属于某种生产关系层面——它充满了政治能动性,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创造性的理解”⑯。
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员形象,无论是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农业“劳动能人”,还是下乡的农业技术员,他们都并非单一的技术人员,更多带有阶级色彩,在宣传新技术的同时承担着政治宣传和社会实践的任务,在实践中逐渐融入农民群体,呈现出“农民化”“党员化”的性格特征。
(二)“技术—经济”:改革语境下的农业技术员形象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尽管农业技术员形象依然处于人物形象谱系的边缘,但是其专业性、专家化特征日益突显。作家笔下的农业技术员、技术专家形象更多从“技术—经济”角度彰显其专业价值,突显“技术”对农村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建设的重要性,人物形象塑造趋向于对农业技术员“专业化”“专家化”特征的挖掘。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提出“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强企业扶持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特派员队伍等相关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⑰。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专家学者型的“农业技术员”形象愈加鲜明。关仁山小说《日头》中金沐灶反思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缺少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想要“在村里建设一个农业技术培训班,聘请吕富仁教授前来讲课”⑱。《麦河》中的“农业科技特派员”李敏教授,继承父亲农科院专家李万春的研究方向,“掌握着全国领先的小麦种植管理技术”⑲,来到鹦鹉村和曹双羊的麦河集团签约合作,指导农民与企业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农业。《金谷银山》中范少山找“金苹果”“金谷子”种子与种植技术时,得到了农业大学孙教授的指导,在村委会设立实验室后,专业出身的欧阳春兰前来帮忙,最终让白羊峪“金苹果”“金谷子”种植成功,改善了白羊峪环境的同时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
“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产业振兴,更是人才振兴,通过农业技术的注入与学习可以促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尽管对乡村社会而言,他们仍旧保持着“外来者”的形象,但是农业技术员作为知识分子在专业性方面得到肯定与重视。农业技术员下乡过程中角色特征由“农民化”到“专家化”的转变,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观念的变迁,更折射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历程中社会对“技术”以及“技术”价值认知的变迁,将技术人才从行政工作中剥离出来从事专门性工作,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三、“技术塑人”:“技术下乡”与农民现代观念形塑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现代性的,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使之现代化。”⑳从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技术推广与集体劳动等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到新时期以来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影响农民的劳动方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科学技术”以实际的经济效益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形塑着农民的科学观念与现代价值体系。
(一)农民现代科学技术观念的提升与局限书写
在“技术下乡”的过程中,现代生产技术带来的直观益处能够改变传统保守的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在当代乡土小说中有关不同时期老一辈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与认知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接受的过程与科学技术的局限。
“十七年”时期,面对农业技术人员的短缺,“城市、工业开始以‘厂社挂钩、技术下乡’的形式,大力支援农业发展,培养农村技术力量”21。与“农村新人”对待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态度截然不同的是传统的、保守的老一辈农民,他们身上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农民现代科学技术观念的提升过程与科学技术教育的局限。面对涌入乡村的新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带来的冲击,有些农民将现代科学技术“神化”。如在梁生宝妈妈心目中“那些书籍和玻璃盒子贵重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她“对待农技员的东西,比敬神用的东西还要严肃”。22《山乡巨变》中盛佑亭家在毛主席像旁贴的对联“现在参加互助组,将来使用拖拉机”,与小说开头邓秀梅看见土地庙贴的对联“天子入疆先问我,诸侯所保首推吾”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对比不仅反映出农民对土地和粮食丰收的渴望,还反映出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认识的局限。因此,尽管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充满期待,却并未真正正确认识现代科学技术。有些落后保守的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则是不信任不接纳,如《三里湾》中的马有翼父母、《山乡巨变》中的菊咬筋、《创业史》中的梁大老汉和梁三老汉等,他们对新生产技术由拒绝到接纳的重要原因在于看见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一五’时期的19.9%提高到目前的55.2%,农业科技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23,在这一现实基础和人物逻辑思维线上,可以看到这类农民对待机械化、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态度的转变。如《山乡巨变》中李支书与亭面胡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对话:
“听说,株洲工厂造了一种万能拖拉机,能耖田,又能运输。将来,运灰送粪都不必要挑肩压膀了。”
“那就太好了,”背脊微弯的亭面胡赞道,“那我们的子孙不会驼背了。这个日子还有好久呢?”
“快了,只要齐心合意,苦战几年,各种机械都会下乡了。”24
尽管亭面胡以及李支书都没有见过这种“万能拖拉机”,但是农业互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农业现代化初体验,让他们对农业机械化和未来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经过农业技术员的宣传与指导,在劳动过程中农民逐渐掌握了现代种植技术以及农业机械的操作,局限在于随着技术的更新,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对新技术不了解的状态,正如《日头》中金沐灶所说的那样,“农民搭台,技术唱戏,技术已经成为咱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层面。本来应该作为主角的农民,现在却成了一个混沌模糊的符号,成了一个沉默的群体”25,因此农民的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培养等工作将仍是农村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内容与方向。
(二)“技术入心”:农民价值观念的现代变迁
在“技术下乡”的过程中,“农民把学科学、掌握技术与他们的生计联系起来,并使科学逐渐成为他们致富谋生的重要手段……从而引起广大农民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商品意识等方面的变化”26。从“技术下乡”“技术在乡”到“技术入心”,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运用与发展,不只改变了乡村的外部环境,更是直接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念,参与了乡土文化现代化历程。
乡土伦理“是在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27。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乡村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基于乡土特性,乡土特性的产生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28,因此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往往基于血缘与地缘的价值体系。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广过程中,“十七年”时期的土改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的展开,不仅确立了农民主体地位,重要的是通过集体劳动方式、劳动竞赛、劳动英雄塑造等肯定了劳动价值与尊严,在血缘、地缘伦理价值观念之外,无产阶级价值、劳动价值观念影响了这一时期乡村伦理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9而“离开互助合作的基础,甭想在单干农民里头,大规模推广农业新技术”30,在新的种植观念与劳动方式——集体劳动中,“劳动”本身获得了足够的重视,通过“集体劳动”将无产阶级的农民团结起来,无论是社会历史还是文学作品中,“十七年”时期对“劳动者”尊严的确立影响着农民的现代价值观念。《山乡巨变》中李月辉等干部带头参加集体劳动,人们从党和国家政策以及党员干部的行动中真切感受到:“如今,黑脚杆子都是政府看得起的好角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话不对了;如今的世界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动高。’”31《创业史》中农业技术员韩培生作为知识分子,因其在劳动中的优异表现,“妇女们大大称赞韩培生的吃苦耐劳精神,不眼高,瞧得起穷庄稼人”32,进而认可韩培生推广传授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农业机械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如小说《土地之痒》中贺兴成利用自己购买的农业机械提高自身生产劳动效率之余,可以通过使用农业机械给他人做工赚取金钱,尽管亲人邻里有所不解,但是在农业机械的便利高效面前,贺家湾的村民逐渐接受了市场经济规则。另一方面,现代农业机械化的高度发展将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人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下降,乡土社会“人—地”关系的减弱,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农闲时节进城务工,在血缘、地缘、劳动、阶级伦理观念之外,“经济”快速成为乡村社会伦理价值的一大标准。如小说《上塘书》中“房子”成为财富的象征,也成为村民判断各自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炸裂志》中明亮感慨:“这年月,啥儿钱你都可以挣。有钱你就是老爷姑奶奶,没钱你才是孙子和老鼠。”33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通过实际可见的新科学生产技术带来的好处,悄然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从“技术下乡”到“技术推广”,依托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不仅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改变了乡村结构,也影响着乡村文化形态。
现代文明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直接而又强烈地冲击着农民的认知与价值观念,影响了传统乡土文化的存在形态与发展空间。无论是不同时期“技术下乡”过程中农业科学技术的书写,还是通过农业技术员形象特征的变化展现“技术下乡”的作用机制,乡土小说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有情记录,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乡土文化深处的裂变,关注到了时代变迁之下作为主体的农民的观念变化。而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乡土文化的裂隙的表象与成因在作家有关“技术下乡”的多层次描写中可以寻到痕迹,由此可以对“技术”如何塑造现代人格、传递现代文明进行有效梳理分析,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中“技术何为”。
注释:
①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②[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③刘玉堂:《乡村温柔》,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④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第375页、第465页、第137页。
⑤关仁山:《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399页。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选自《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⑦赵树理:《三里湾》,选自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第114页。
⑧《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参见网址:https://data.cnki.net/Trade/yearbook/single/N2021120010?zcode=Z009
⑨《技术革命的先锋:“土专家”当了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1958年第7期。
⑩黎城联合办公室:《增产的保证——精耕细作提高技术》,《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2日第2版。
⑪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第397页、第408页、第398页、第413页、第418页。
⑫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⑬戴炳业、刘慧、李敬锁编:《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与实践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5—76页。
⑭关仁山:《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第294页。
⑮关仁山:《麦河》,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页。
⑯[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⑰宋学勤、杨越:《技术与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民塑造》,《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
⑱陈萌山:《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提升农业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0期。
⑲张维先主编:《农科教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⑳李良、韦潇竹:《传统“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与农村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第10页。
22.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摘自《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3.阎连科:《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26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9ZWB100)和江苏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项目“乡土小说的多重语言资源与文本转化”(项目编号:21XFRX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范伊宁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