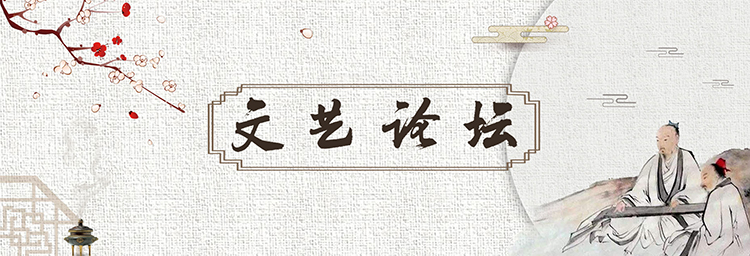

作为“未来批评”的“居间美学”
文/汪尧翀
摘 要:“居间美学”的核心任务是在当代世界中重新提出媒介物的意义问题。媒介物作为居于“世界”之中的诸文化对象,不仅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受制于体验轴结构,而且决定着“世界”的持存和演化。“居间美学”尝试将“世界”进一步阐释为自然-历史空间,反对“世界”作为“社会系统”的中性化,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由此强调解码媒介物由自然显象与社会力量共同聚合而成的社会-历史结构,把握其“非概念化本质”,挖掘其蕴含的进步性。“居间美学”尝试摆脱观念论美学的主体性基础,进而关切自然-历史空间的未来演化和解放潜能。重建媒介物的思想坐标,旨在澄清和确立当代美学转型的前提,不仅重塑了“居间美学”的历史任务,也使之在批评理论上有所作为,即作为“未来批评”发挥效能。
关键词:“居间美学”;媒介物;自然-历史空间;未来批评
“居间美学”强调任一种美学理论的建构,均依存于、受制于其关切对象的感性-特征,无论此对象是“艺术作品”,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对象。[1]这一断言除了旨在冲击理论建构之普适性前提、瓦解所谓“大写的美学”之外,并无意成为某种美学教义,而只是自我辨识为一个反思口号。反思乃是指引,引导“美学”的目光转向作为自然-历史空间的“世界”,尝试重建充满其间的媒介物的思想坐标。但毫无疑问,这种重建的前提乃是把握媒介物的“非概念化本质”,为此,必须设想一种“未来批评”!
一、 重提意义问题:体验轴与媒介物的形式
如今,我们早已置身于一个布满“文化对象”的世界,若以“复杂性”为观察尺度,亦可说“媒介物”在世界上呈现几何级数增长。是否还能将“世界”体验为一个“整体”——更多时候,这似乎专属于“理论”的体验——姑且不论,世界的庞大形象却如象征物一般,伴随着人类行动,尽管不可能再直接指导行动。遵循常规说法,在世俗时代,任何形而上学的秩序,已不可避免地让位给另外的去中心化模式;世界万物的崇高秩序,虽下降为以合理性为取向的社会进步,但总归还持留了某种信念。世界的理性化,虽遭遇若干阻滞,仍服从科学与技术驱动,不断反思实证主义投射下的阴影,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总之,无论“世界”是否存在所谓的“目的”,但设置或筹划某个目的,至少能成为世界演化的调节性理念。毫无疑问,真正能够指导人类行动的,必然是现代世界中分门别类的专家文化。尽管专家文化在人类文化行动或日常运行中,并不允诺相应的高度透明性,人们日用而不知,也毋需知晓。据说,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深切感知,在文化领域聚集起足够的负面效能。最终,现代性理论仿佛一则指向失落的寓言,在被专家文化犁得沟壑丛生的现代世界破碎图景的上空,召唤来一袭浓厚的云气,幻形为所谓“生活世界”整体。但正如海德格尔的划时代预言,关于整体的体验是否真实,必须以“死亡”引导中存在的本真状态来衡量,才得以见出真章。这种意义追问虽以极端或例外状态为取向,但犀利地挑明了“世界”的持存问题: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无所谓持存,更毋需演化。总之,意义的失落与亏空,无论归之于心性或归之于科技,确确实实是现代性文化的第一问题。
当然,上述诊断也可缩略至更基础的层面:文化对象的意义问题之于现代世界主体乃是根本性问题。对主体而言,若没有意义,无论体验还是行动,均无法设想,更遑论成为可能。意义问题也必然预设了关于“整体”之体验的可能性。用流行话语来说,体验总是与“事件”相关联,也就是与别的体验或他者相关联。所有这些关联,即所有事件和状态,建构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视域,此“世界”也必然面临持存和演化的问题。换言之,若要理解任一文化对象的意义,总是要以关于文化对象的体验作为出发点,同时,也总是要面临该文化对象所置身其中的“整体”(体验)的结构问题。“整体”究竟是可从文学上理解的文化整体,还是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经济规律之总和,抑或社会理论视域中的建构性“社会”,无非都是言之成理的观察视角,尽可以依托不同学科加以拓展。但不论如何理解“整体”,终归要涉及理论上多元视角的统一性,如此却可以说只有一种关于“世界”之同一性的基础性体验,即世界存在的“复杂性”。[2]除此之外,以社会文化之演化作为观察界面,世界不过呈现为上述各种视角之下的有意义的表象(片断)。同理,文化对象的意义,即是其“形式”,或者说,其显现的形式。这种形式源自对文化对象进行不同视角下有意识的加工,旨在维持和整理诸体验,从而使得关于世界的理解成为可能;更进一步说,使得关于世界的理解成为一个哪怕暂时的固定点,由此才能够给出关于世界有意义的理解,从而使得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得到削减。[3]
因此,文化对象的形式总是受制于“体验轴”——我尝试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试图描述主体关于文化对象的体验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描述体验之“自性”与“他性”的交互关系。具体而言,任何个体关于文化对象的体验,尽管(从主体这一方)看起来都是瞬时的、纯然个体的,即海德格尔所指称的,但只要考虑到任何体验必然是某种“表达”,体验“被给予”根本上只能是以语言-表达的样式,即对体验有意识的加工(意义加工必须以主体间性的效能为导向),便会提示出“关于差异的经验”。当然,本文更多将关于差异的经验关联于社会情境,因此在此类情况下,便可以称关于文化对象的体验必然具有体验轴的结构特征。显然,即便在科学领域,文化体验的形式也同样受制于体验轴,只不过,“关于差异的经验”会因“概念”的使用而发生变化。[4] 概念越抽象、越稳定,体验轴所带来的差异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关键在于,是否把通过概念来克服体验轴隔阂视为唯一的途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克服便与实证主义同声相应。那么,一旦转化视角,也可以说,概念恰恰掩盖了体验轴关于差异的经验,从而掩盖了媒介物“非概念化的本质”。[5]
若分而论之,体验的自性具有稳定的即时性特征,它毕竟是关于对象之感性特征的切身理解。主体虽然最终要以象征方式来维持体验的持续性,但归根结底,关于某个文化对象的体验,首要依存的仍是其最基本的感性-特征,或者说,“非概念化的本质”。如果我们以“媒介物”来取代所谓“文化对象”这一相对含糊的说法,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楚些。不妨将体验轴这种包含着体验之自性与他性的理解视域,称之为关于媒介物的事态。这样,媒介物的形式问题,即其意义问题,便关联着不同的事态,虽然诸事态不一定完全同时发生。譬如,关于一部智能手机的即时体验,我对它的享受、使用,或者说其上手状态,均属于体验的自性这一极。但对于(假设其在场的)另一个完全不懂得智能手机使用的人,比如我的外婆,她关于智能手机的即时体验,则是一种陌生感甚至惊异感。对她来说,智能手机完全是一个“神奇小玩意儿”,甚至需要从“缩小的电视”这种她所熟知的文化对象那里借用意象来进行理解。
实际上,体验的他性,不管参与者是否有所意识,始终在客观上与体验的自性一道发生,且所导致的“关于差异的经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关于智能手机体验的他性,一旦显现,不仅很大可能复现了任一个主体初次接触智能手机的体验状态,而且,本身例示了一个具有明显社会差异结构的场域。这种差异经验不以任何主体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同时,关于智能手机体验的他性,如果不能够在体验的自性上得到反思、澄清乃至转换——甚至可以说,在老年人那里,这种转换不仅受制于经济问题,而且往往受制于更真切的年龄、社会层级等问题,一言以蔽之,“数字鸿沟”——必定会导致体验的自性最终膨胀为某种单向度的体验,且只能是某种残损的体验。实际上,就连“我”,一个似乎不受数字鸿沟影响的主体,关于智能手机的体验,从一开始便难免是残损的,因为它业已遭遇了专家文化的鸿沟。这足以说明,关于媒介物的体验,从一开始便是某种居间性体验,即它更多表达为一种自我指涉的、自我中介的感知模式;它愈发自洽,愈发独立,就愈发让人一无所知。[6] 借用哈曼论及海德格尔的著名例子,也可以说,惟有在媒介物(用具)的破损状态下,媒介物的“在手性”才显现为一种范畴幻觉。[7] 现今流行的说法,即智能手机成为人的义肢,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义肢破损之际,使用者才能从其“有用性”中彻底摆脱出来,思考其真正的存在本质。
总之,社会的分层结构,姑且不论该结构在不同专业视野之下究竟是如何得到解释的,导致了体验轴隔阂。这种隔阂不仅存在于体验的自性一极,也存在于体验的他性一极,换言之,这种隔阂恰恰是以体验的自性与他性的相互指涉为前提的。体验的自性和他性只能通过媒介物的形式而给出,若要为此举一个例子的话,可以说,智能手机的形式给定源自其生产-设计:智能手机是一个“商品”。这种规定性不仅道出了其感性-自在的特性,而且也道出了其意识形态特征。关于媒介物的形式,即媒介物的意义,无法脱离这一基础性规定。当然,人们完全可以由此畅想,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之中,智能手机的生产和运用,不再制造任何数字鸿沟,而完全实现其上手性。此时,媒介物的意义恰恰在于脱弃了体验轴隔阂,甚至,是否应该设想这种脱弃本身便理应属于媒介物诞生的时刻,即属于媒介物通过技术(设计-制造)而生成的历史性本质之中。[8]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智能手机以其历史本质得到揭示的方式,即其历史性本质得到显现的方式,嵌入了社会世界之中:其进步性的一面,不再是其退步性(制造数字鸿沟)的一面。[9]
如果转而从当今关于智能手机的商品-消费美学出发,也能较容易地理解上述问题。在商品美学的视域之中,体验问题不过是强度的问题,而非基于体验轴形成的分层问题。有且只有一种“美”的体验,且这种体验被认为是对所有主体开放的,那么,问题就成了主体是否有能力去开启、去塑造自身感官。困难却在于,这里是否仍然逃避了“谁是主体”的尖锐问题。如果“美”不是真正对所有人开放的,不是为所有人所共享的,那任何关于“美”之合法性的论证不过是一种无病呻吟的视角主义,其核心仍是马尔库塞早已揭示过的文化代偿性,即“美”的体验尽可能地掩盖了社会结构性的剥削关系或商品关系,从而违背了其“自由”的初衷或目的。[10] 当然,如今审美主义已经愈发精致,但无一例外也愈发地把“自由”视为脱弃于社会历史空间的主体条件,并寄情于未经批判的文化对象。说到底,这类观点不过反映了论证水平的某种倒退。
一言以蔽之,类似关于意义问题的理解,只能在一个相当狭隘的美学视角之下,塑造出各种文化代偿模式。换言之,一旦把媒介物的意义(形式)与其社会意图(内容)彻底分开,关于媒介物的研究所建构起的诸学科,尤其是形形色色的“文化批评”便会去设想能够在诸媒介物的更迭之中,指明某种既存的理念:关键在于,类似既存理念的合法性,恰恰又是由取法“世界”之表象片段的诸学科来加以保障的。相反,也许不应该说,智能手机不过是抽象的“共享”理念的具现;实际上,唯有关于智能手机的正确理解和使用,才推动和例示了“共享”理念的出现,所映射的不是某个圈层爱好,而是社会结构的变革-进步。必须承认,媒介物的“进步性”是否属于媒介物之历史本质,而非简单归于其社会运用的后续推论,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但尚未提上日程的问题。但是,何以采纳这一立场,事关是否真正理解和坚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正运用一种工艺学批判。[11] 毕竟,如果无法摆脱文化代偿性,学术批判最终会沦落为话语游戏。当今大众电子传媒时代,这一切不是正在——千百次重复地——发生吗?连罗萨也把体验鸿沟的问题,转换为了媒介加速的问题,从而把真正的社会性结构病症,掩盖在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新异化理论之中。[12] 关于异化的体验,只要重新置于以体验轴为取向的具体社会情境之中,就会恢复为一种真正的痛感;若说这种痛感体验有什么指向和“目的”,那毫无疑问是一种关于社会启蒙空间的自然史需求。
(节选自2024年第3期《文艺论坛》汪尧翀《作为“未来批评”的“居间美学”》)
注释:
[1][16][20]汪尧翀:《居间美学:当代美学转型的另一种可能》,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第249—265页、第185—191页。
[2]参考〔德〕尼可拉斯·卢曼著,鲁贵显译:《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52—54页。
[3][4]参考〔德〕尼可拉斯·卢曼著,鲁贵显译:《社会系统:一个一般理论的大纲》,暖暖书屋2021年版,第56—59页、第40页。
[5]此概念见拙著关于“居间美学”任务的设想,即关切文化对象的“非概念化本质“。下文不再一一注明。摘自汪尧翀:《居间美学:当代美学转型的另一种可能》,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6]参考杜丹:《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
[7]〔美〕拉拉汉姆·哈曼著,花超荣译:《迈向思辨实在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5页。
[8]当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已经从价值及规范理论的维度,关注到这一问题。
[9]〔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14页。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选自马尔库塞著,朱春艳、高海清译:《艺术与解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165页。
[11]刘方喜:《超越“鲁德谬误”:人工智能文艺影响之生产工艺学批判》,《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
[12]参见〔德〕哈尔特穆特·罗萨著,董璐译:《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远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汪尧翀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