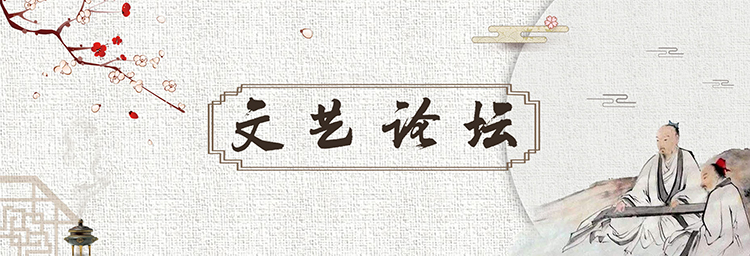

灵化山水的生命精神
——刘忠华诗歌解读
文/潘雁飞
摘 要:刘忠华诗歌善于抒写潇湘山水。村舍老巷、祠堂古庙的自然美景、厚重人文,它们自然交融,物我两忘,是灵化山水的生命精神的诗意呈现。其总体印象有三:一是采诗现场,见赤子乡土之袅袅乡愁;二是铸情造韵,见田园山水人文交融之意蕴;三是审美观照,见灵化山水之生命精神。
关键词:灵化;山水;铸情;生命
永州著名诗人刘忠华四年出版诗集三部:一是《时间的光芒》(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二是《一个人的山水诗经》(团结出版社2020年版);三是《对一条河流的仰望》(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版)。《时间的光芒》确实穿透了岁月的光芒,收诗跨度达30年,后两部是近三年诗情诗意的集中喷发,创作可谓丰盈,洋洋乎大观。诗人性格豪爽,耿直,亦不乏偶有聪明得可以的狡黠,名为“忠华”,故喜唱“爱我中华”与“长江之歌”,将爱国爱山水爱家乡与爱自己四合为一,吟唱时双眼噙满泪水,情感自然深沉。笔者耳闻目睹其三十年创作,多受其诗情诗意感染,将他的三部诗集翻阅一过,荦荦大者,得三点印象。
一、采诗现场,见赤子袅袅乡愁
众所周知,诗歌的源头——《诗经》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采诗,《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孔丛子·巡狩篇》也说:“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这说的是对民间歌谣的搜集与上达。刘忠华的诗歌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的重复。他是回到生活的现场,以触发灵感,从而自然而然创作出自己的诗歌来。正如他自己说的:“也就是我写下《在勾蓝,是可靠的》那一组诗之后,我迷上了行走:有时是随团队采风,有时候是邀上一两个好友,而更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在潇湘大地到处游荡。”“在都庞岭深处的空树岩村,《空树岩》这首诗就是一边等村里的盘大嫂打油茶,一边倚着车门一挥而就写下来的。”{1}又如100余行的《献歌:江华》的创作,诗人说:“(在生活现场)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山地民族艰苦跋涉的心跳,更深刻地理解了一个民族的迁徙史和精神史,返回家中后的第三天,我即一挥而就。”{2}分析其夫子自道,其诗歌的创作触媒就是对生活现场的观察、体验和感悟。而观察、体验和感悟自然会激荡出诗人的灵感,使之形成跳跃而灵动的诗行。
进一步阅读这些回到生活现场的诗歌,可以看出其创作机制又可以分为行吟畅想之诗与体验回味之诗两小类。
行吟畅想之诗是诗人行走中的吟唱和思绪的飞扬。如《对一条河流的仰望》之068号诗歌:
萍阳路的枫香
总想抱紧空气与光
黄叶渡的铁锚
总想抱紧流水与沙
潜于人间,很多次我尝试
抱紧流水后面的我
我们寒暄
说起早年旧事与小人书
说起南门码头,两个人
坐在青石上,在流水中
共同度过的童年
一帘流水,这时光的刀片
哗啦一下
划走了我们大半生{3}
萍阳路、黄叶渡、南门码头、青石、流水……移步换景,也改换感觉和情感,诗心诗情是流水,也是岁月的印痕。这里的行吟,不是古代行吟诗人式的,用诗的句式的叙事给你讲故事,而是诗人如屈原般行吟泽畔,诉说心曲,既有空间的移动,也有心理的行进、神思的畅想。再如《对一条河流的仰望》之121号诗歌:
在石头中开凿新的河流
又在石头中开凿出自己
每一天,他在河流中出出进进
也在石头中进进出出
一个人的河流中
他把自己封为王
一个人的世界中
他试图制造更大的
动静{4}
“河流”与“自己”融合为一,人在行吟中与河流同归于自然,自然是“王”,河流是“王”,“我”也是“王”。山水灵化了,自然灵化了。
体验回味之诗是诗人“我”的融入,是全身心的参与、俯仰,在体验之中咀嚼回味。《春天:四朵花》(组诗)里诗人写道:“寻到你时,我已翻过《恋爱大全》的最后一页/一条溪流和十八岁的冲动。”“姐姐,你知道一只蚂蚁的梦吗/他要爬到你的脸上/偷吸你脸上的诗情。”少年青涩的爱情冲动跃然纸上,显然是诗人曾经的回味,回味不仅仅是对往日情愫的眷恋,还有成熟后对今日现实的怅惘:“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我只想/在每一朵花下都安放一节/即将逝去的春天。”这种对采诗现场的叙述与动情点的把握,是融合深刻体验的回味,是入乎内、出乎外的跃动!是一个赤子对乡土的热恋,是一个爱人对情人的倾诉,是作者对乡土山水的深情颂歌!是含着泪水才爱得深沉的袅袅乡愁!
二、铸情造韵,见山水人文交融之意蕴
古人的山水田园诗意境优美,以意韵胜,但情感指向,未免有些消极,哪怕是恬淡,也难激发起人生的昂扬斗志,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逃入自然,隐藏自己,欲说还休。如陶氏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遁世,即便“结庐在人境”,也不过是“心远地自偏”。又如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其追求自然复归于自然。诸如此类,莫不如是。
刘忠华三部诗集绝大多数写的是山水田园。《时间的光芒》侧重描写具体的乡村(众多的村名入诗)与具体的山水,《一个人的山水诗经》视角更为宏大,着眼于“潇湘颂”“永州书”“人间志”,“潇湘颂”是永州两区九县的献歌,“永州书”是自然地理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对一条河流的仰望》写的是河流本身与河岸上的人生,以及诗人对河流的思考与情愫。诗人笔下的山水田园,除了其韵味、韵律、意境熔铸的美之外,情感蕴藏与情感指向是对自然的融入与涂写,是对山水的诗性语言的张扬,是对自我生命力的肯定。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歌咏美好。套用王阳明的话,你未读此诗时,此地与诗同归于寂,你但读此诗时,此地与诗一时明白起来。且看作者的《良村》:
双牌有良村,良村出良民
良民种良田,产良种
更产良心
潇水从上游走来,这个良家女子
良辰中的样子,像七月的葡萄
也像七月的丝瓜,葡萄藤和丝瓜藤
挽着昨夜娇柔,欲语还休
河流与村庄,我知道的不一定
比一只卷心虫多。它们向下的力量
超过我的内心
傍晚时分,河面上闪着
醒世良言,让良山上的夕阳
回眸良久{5}
诗人并不着墨山村的秀丽景色,而是从村名出发,展开整体的联想,展现村庄人事物的良善,写出良村之为良村的所以,是以人的美烘托山村景色的美。人文色彩尤其浓郁。可以说诗人大部分的乡村、山水田园、江河湖海诗歌都有这样的趋势,不是写景为抒情服务,而是抒情增添景色的魅力和美丽。有的诗歌甚至诗题就着了这样的色调,或者说是以此进行了标记,像《在南风坳,只想做一回琴童》《在勾蓝,被一朵蓝勾住是幸福的》{6}。有的则以专辑组诗的形式来低吟回味,如第三部诗集《对一条河流的仰望》中的《我对爱的理解深了三公分》(月光倾泻下来/河面高出了三公分/ 隔河相望的人/近了三公分/ 我对爱的理解/深了三公分)(076—119号)、《神,在流水中洗净自己》(139—184号)、《河流在埔尾村轻轻流淌》(159—190号)、《仰望河流时我看见了天空》(如“一个人仰望河流/河流也仰望他/他们彼此望着/没有一句多余的话”)(191—222号),无不如是。顾随先生说:“诗要有心有物,心到物边是‘格物’,物来心上是‘物格’。即心即物,即物即心,心物一如。”{7}诗人对此是有一定深刻理解与洞察的。可以说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歌并不太在意山水田园本身,而在意去感悟、去把握大自然有了人的活动的情韵和生机。如果套用改写茅盾在《风景谈》里的话,就是“自然是美丽的,然而有了人的活动与人的感悟自然也就更加美丽”。其造韵的旨归就是美丽的意蕴。
在情感表达上,之所以说是“铸情”,就是因为其诗情是与自然山水田园一同生长的,山水田园的描摹里自然潜藏着诗情人性,诗情人性又与山水田园融合为一。
《桐子坳村》诗人唱道:
秋收冬藏。世界
终要回到原来的样子。溪水埋头布道
黄金一样明亮的钟声,会为人间祈祷
画眉鸟和四喜鸟,大妹和小妹
唱着赞美诗。暮色哗啦啦拉下来
留在枝头的叶子,也随着暮色
在桐子坳里,哗啦啦响
“秋收冬藏”是喜悦,“布道”是庄严,“祈祷”是虔诚,鸟与姑娘交融的“赞美诗”,“叶子”与“暮色”组合的“哗啦啦”的乐音,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恬静的喜悦的醉秋图。整体上诗人于自然山水并无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无狂风怒号的悲怆,有的只是与自然山水一样自然的欣喜之情和自然人文的深潜玩味与感悟。《画眉山村》写历史上的“红六军团”,就有一种深刻的感悟:“八十多年后,一个秋天,丰收在望/无病呻吟的诗人,在画眉山村/捡起鸟啼砸下溅起的火花/捡回丢失多年的骨头与魂。”诗人写自然山水,写村舍老屋、古巷小桥、历史风云,就是将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让其水乳交融,于诗行诗意中发酵而至醇厚。
三、审美观照,见灵化山水之生命精神
诗人的《时间的光芒》看似写的是时间,实则写的是时间隧道里的一个个空间,第一辑、第二辑几乎都是以山水、村名为诗题,以诗心诗情或解说、或畅想。《一个人的山水诗经》分“潇湘颂”“永州书”“人间志”三辑,“潇湘颂”,为永州九县两区作“诗传”,抒写的是各县区山水特色与人文历史,“永州书”重在描写各县区的散点山水与人文,如《浯溪读碑记》《九嶷山的云》《阳明山令》《湘江源》《女书》《画眉山村》《瑶山谣》等,“人间志”将个人行走与思考和山水融为一体,偏重于对山水、对生命的思索。实质上三辑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都是对山水的对象化、情感化、诗化与灵化,即将诗人的生命体悟,将人类的灵性与精神投射于山水,使“物”皆着我之色彩,灵化了山水,人化了自然!从技巧与诗意写作视角而言,有三条路径。
一是思接千载的观照,以《一个人的山水诗经》最为典型。无论是对一个县区的颂歌,还是对一条河一个山村的吟咏,都体现出了思绪的翻飞、诗意的跳跃,诗人往往挖掘过往,从过往延伸至当下,并瞻望未来。特别是对县区的颂歌,诗人试图将历史长河中的文化一线贯穿,以诗歌的形式言说文化与文明,如《献歌:零陵》:“记住石头,泥土、渔翁与欸乃之声,记住霞客浮渡,记住/走过浮桥之后的千年之约:来与不来,我都会在东山之巅/在西山之侧,在柳子庙前,等你;在荷塘月色的朦胧之夜/在零陵渔鼓,永州血鸭与柳宗元异蛇酒中,等你;请记住/你我都不在的日子,一位僧人,唐代怀素,醉酒之后/挥毫写下的《千字文》;就像今天,一位行吟诗者/写下的这首献歌。”{8}不愧是历史文化名城,醉美的山水,深厚的文化,名人个性等,均跃然纸上,镜头淡入化出,极富韵致。
二是视通八极的默想。诗集《对一条河流的仰望》核心自然是吟咏河流,更准确地说是吟咏潇水及其支流。河流是焦点,但诗人在聚焦之外,仍然视通八极,大地、天空,太阳、月亮、云彩、雾岚、水下、岸边、荒村、野老无不触及,更重要的是,在审美观照迁移之时,诗人思绪也是流动的,虽然是一种默想,但也如流水一样,不舍昼夜。《河流太高了》之21号作品写道:“把河流竖起来/能否触及喜马拉雅?离喜马拉雅万里之外/一粒雪落在路灯下/它反射的光,刹那间/照亮萍阳路。”{9}近的视角与远距离的玄想,遥远的视角又与眼前脚下的路相映照,诗人伫立在潇水岸边,天地在眼前走过,大有巡天遥看之谓。诗意地行进,举重若轻,以一句“把河流竖起来”,便转动了地球!类似的还有89号的“把流水抬高一千公尺”,91号的“把河流悬挂成秋千”,146号的“把流水折成手绢”,207号的“一条河流飞起来”,都是类似的艺术营造。
三是物化诗心的通感。诗人于宇宙人生的所思所想,要艺术诗意地呈现,必然要通过物象,由物象而营造意境、意蕴。诗人于此自然明白,只是他的造境方法,是物化诗心的通感。诗人的诗心诗意诗情多以通感的方式加以物化,这也是诗人最具特色的物化诗心之法。山水犹如大荒山的通灵宝玉一般有了生机与活力,也有了预示与象征。如《对一条河流的仰望》之206号的“一个人仰望河流/河流也仰望他/他们彼此望着/没有一句多余的话”,68号的“萍阳路的枫香/总想抱紧空气与光”,82号的“一辈子浪里白条/一辈子过成鱼样”,135号的“水划燃了三次/灯盏仍然没有亮起来,”173号的“对母亲说:河流也会死的”,183号的“流水多么坚硬/流水是我的城堡”;在《时间的光芒》诗集中,《云飞九嶷》说“九嶷山,带着重孝”,《老埠头》说“花朵中隐藏忧伤”,《红军村》写人的感受“山里的寂寞/夜色一样,吸进心里/会疼”;在《一个人的山水诗经里》诗集中,《水井村》写“村里的春联都有酒味/村里的女人都有墨香”,《醉书,兼怀怀素》写怀素“醉过,才觉悟,自己是自己的酒/自己是自己的药/自己是自己的法帖/自己是自己的菩萨”。这些诗句与传统修辞通感既有相通处,又有不同处,更多的是诗人诗情诗意诗心感觉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互换、一种连接,因此让我们感受到了宇宙星辰、山河大地、花鸟虫鱼、四时八景、万千物象的生命灌注、诗意勃发、灵化生命精神。
总之,诗人的三部诗集,整体上体现了其基本的艺术追求,在不断变换的采诗现场,于万千物象中不断变换审美观照视角,灵化了山水,灌注了气韵生动的生命精神,感悟了宇宙人生、社会变迁,是当下视角比较独特的一种诗意表达与传达。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以潜隐流水作为观察世界的一个视点,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养育我们的故土之上,进一步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仰望河流时,以诗歌的方式尽力托举起那些卑微的事物,既有大地蕴含着的全部气质,更有山山水水的厚云与哀痛,以及从历史凹陷处掬起的眼泪。” “在流水背后,感受季节的流动与更替,尽心倾听生命的追求与奔跑的声音。流水,能让我把生活中的浮躁,化为养心的甘泉。”{10}
当然,如果从更上层楼的高度严格要求,刘忠华诗歌创作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是新变不够,缺乏艺术突破。其虽有一定创意,初露风格特色,却缺少艺术转换与创意变化,风格单一,不同内容的诗歌总有形式上、风格上、特色上的似曾相识之感,不能带来新变的惊喜。二是开掘不深,缺乏厚重感。打个比方,诗人的创作还只是“小调”,而不是“大戏”,诗歌打动人处只在表层情感,触及灵魂不够,更难以带来震撼。如《对一条河流的仰望》通过挖掘足可以写成一部《潇水史诗》,但却只停留于浅斟低唱。《一个人的山水诗经》“献歌”部分本是宏大制作,但写成后,多是史事与情感的诗行排列,少了些深入骨髓、让人震颤的诗魂律动。
为此,我们祝愿他,盼望他保持这种赤子诗心的竞技搏击状态,让诗人这种诗情诗心成为创作路上永恒的动力,继续喷发其诗情诗意,开拓他心底让人震撼战栗的潜能!
注释:
{1}②{5}{6}{8}刘忠华:《一个人的山水诗经》,团结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第4页、第102页、第145页、第2页。
③④{9}{10}刘忠华:《对一条河流的仰望》,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3页、第141页、第22页、第273—274页。
⑦顾随:《驼庵诗话》,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7页。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潘雁飞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