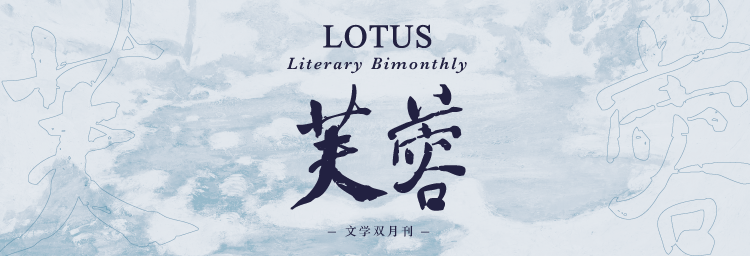

黑箱子 (中篇小说)
文/许玲
1
那天早晨醒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做梦了。我已经习惯一边吃着早餐,一边从梦境里捞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片段,不经咀嚼,便将它们吐在饭桌上。张兰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她说,这不可能,你不是没做梦,你只是不记得了。昨天打电话要你带瓶酱油回来,你那时正在超市里面呢,你都忘记了。她不无忧虑地皱起眉,听说老年痴呆有家族遗传,你爷爷就是这病,你得小心点。我恼怒于她总是武断地给我安上各种疾病名称,好像她是一个随身携带了超声机的医生,清晰地照出我的脂肪肝、脑血管硬化、颈椎病,还有心律失常。我们争吵了几句之后,我就开车出了门。
截至此刻,我最后一个清晰的梦是关于祖母的。梦里我很清醒地知道,她已经死去多年。当一个女人流着泪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差点以为她是一个陌生的老人,因为我从未见过她流泪的模样。当我看清她身上藕荷色缀暗花的旗袍,黑色带金丝的盘扣一直紧紧扣住下巴,眼泪也无法淹没她的冷漠表情之时,我马上就确定了——这正是我的祖母。一些年前,她和祖父一起并排挂在堂屋的神龛上方,被岁月风化的眉眼,模糊地附在发黄的照片上。但是,祖母一直保持着我印象中的倨傲神情,并未因为褪色而失去半分,这让她与其他做了祖母的女人区别开来。而祖父,和别人家堂前被高高挂着的慈眉善目的老头差不多。这没有什么,人如果有幸活到一定岁数,就会慢慢失去自己的特征。奇怪的是,无论我从哪个方向注视着祖父,他都能越过我的存在,盯着远方。我们家翻新过一次房子,几乎是原址重建,房子是他们留下来的,骨骼变形,内脏腐朽,不知道哪天就会中风猝倒。我将祖父取下来,放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和他面对面对峙良久。那个闷驴般老实、人皆可欺的老头死了才开始叛逆——我偏不看你们。我将他们顺手放在一张漆面斑驳的八仙桌上。等到新家建成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不见了。张兰将“他们”葬于一片早该归西的瓦砾朽木之中。
在梦中,祖母和我置身一间潮湿黑暗的房子里,无窗,四周的墙壁有着粗糙坚硬的质感,如同一个被水泥糊起来的四方盒子。屋中间有一张被抬高的木板,她默不作声,径直朝它走过去,躺了上去,竟是一张床。我在齐膝的淤泥中以一种艰难跋涉的姿态走近,床板上厚厚一层稀泥,她的身体一下子陷了进去,只露出一个脑袋。她就用这脑袋看着我,却不说话,像一个讨伐者。我颇觉愤慨,大声质问,你怎么睡在这地方呢?这是谁弄的?
我醒过来之后,猜不出这个梦的含义。因为祖母几乎不走进我的梦里,一如她生前性情生冷,不喜人接近。而且,这样的事情在她活着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她的房间,包括她整个人都一尘不染。我回忆起整个梦境,她都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想,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早已记不起她的声音,她那时可以整天不吐出一个字。我将这个梦告诉了张兰,她却认为这个梦另有寓意。更年期开始之后,她将所有超出正常人生轨迹的事情都解释为命。她说,除了命,怎么去解释这些奇怪的事情,不是你,不是我,为什么是他?早一秒,晚一秒,这事情就不会来。她既然来了,就一定有要告诉的事情。我不以为然地说,我和她又不熟。要来托梦也应该是老头子,怎么是她呢?我倒是经常梦见祖父,在那边的世界也种了几十亩地,穿了件灰色的褂儿,像只鸵鸟一样躬身在稻田里。这样的场景出现过好几次,我觉得那个世界或许与这边无异,只是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享福的还在那边享福,当长工的依旧做了长工。
张兰的筷子停在半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知道这个梦的寓意了。她激动地说,奶奶的坟离水近,旁边就是一条河。我“嗯”了一声,她继续说,你不觉得你梦中的那个房子就是一具棺材吗?奶奶住的地方地势又低,一涨水,就能淹到她的房子,里面肯定就是泥沙啊。我错愕地看着她,似乎豁然开朗,那四方无窗的房子不是棺材,又是什么?张兰得到我的认可,情绪愈加高涨自信,她说,先人托梦,房子近水,后人不利。难怪,你这一生运势平平,才五十五岁,就整天叫着脖子痛、头痛。
我条件反射般地反驳道,我虽然只是师范学校出来的中专生,可那是什么年代啊,我爷爷当年可是放了一场电影,几个村的人都到了晒谷坪,像过节般热闹了大半晚的。但是,我的气焰很快便低了下去,张兰说的不无道理。我这大半生像钉子一样扎在了乡村小学。近年,乡村学校合并,一个镇上只留有一个中心学校。我终于被拔出来,重新换了一个地方,由班主任提成了教导主任。但是几十年过去,钉头已经锈迹斑斑,早无锐劲,只等退休。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出生时在她妈肚子里多待了两个星期,干什么比都别人慢一拍。读书上面像嗑瓜子般磕磕碰碰,最后读了市里的幼专,在幼儿园成了一个孩子王,天天嗲着声音和孩子们说话,男朋友都没有混到一个。对了,我还有一个妹妹潘知远,听说她一个人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到现在都是孤家寡人一个。我与张兰商量,那我们怎么解?张兰对我翻了一下眼睛,不是说那片坟地要迁出吗?
我先开车去了一趟后山,最近雨水充沛,荒草疯长,将祖父母的坟头掩盖得像两个发了霉的馒头。其实,这块突起的地方连山包都谈不上,就像一个被蚊子咬了几个大包的胳膊,有了几处起伏罢了。小河里的水已经溢出来,离他们的坟头不过几米远,腿伸长点,直接可以在里面洗脚。这条河往前两百米,是新建的一段高速公路。站在此处,耳边全是呼啸而过的汽车声音,驱逐了萧瑟之感,也占领了这里本应拥有的静穆。过了高速带,对面是一片新辟出的别墅区,房价让仅有一路一河之隔的乡下人咋舌。城市就是一个不断膨胀的胖子,我们村已经从乡下变成了城郊,很快就会变成城市的一个末梢。现在这条胳膊上,枕着我们村里的先人,按照时间顺序从东到西不断蔓延,密密匝匝地构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潘家村。他们的房子如同被风吹起来的鸡皮疙瘩,风把草吹得一浪一浪低下腰去,它们就一座一座高高低低地显露出来。我面前紧临的两座,似两个头挨头眺望远方的脑袋,它们被我制造得如此亲热。我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祖父一辈子除了干活之外,晚年清醒的那几年,常拿着钓竿在此钓鱼。祖母比祖父早走三年,但那时我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这样的心思。祖母曾经对妹妹潘知远反复交代,她和祖父生不同床,死不同穴。潘知远是和祖母关系最近的人,但是,她远在日本,在这个家早就失去了话语权。我坚决地选择让他们在一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那可怜的被我祖母奴役了一生的祖父就不该让她事事如意。不过,他们并未同棺同穴。他们更像邻居,就像他们生前,以堂屋为界,各自占据一间房。每日从各自的房间里走出来,像不同世界,也像不同时空的两个人。
我在离祖母几步远的地方点上了一根烟,我想象着她那瘦小,整个线条绷得僵硬的脸,索性离她更近一点。我还在地上爬的时候,她坐在那把专属的圆形黑色藤条椅上,一只散步的鸡和我差不多同时来到她的脚边。鸡在我身边拉了一泡屎,她没有抱起我,而是将自己和那张椅子挪得离我们远一些,好像我和那只随地拉屎的鸡才是同类。这样的场景,我当然不记得了。这是村里那些老人在世时讲的,用他们的话说,盘古开天地以来,没有女人这样当母亲和祖母的。他们每次见到我,都会说,那个天天摸鸡屎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
现在,哪怕祖母再厌恶我,气得从地里飞起来,也不可能像搬把椅子般将坟挪走了。关于迁坟一事,我并不着急。其实早在几年前,村里就已经有了风声,这片坟地是必须迁走的。最近似乎连日期都定了下来,一个新地方,必然会去旧迎新,要有新鲜的血液流动和滋养才能活下来。没想到,祖母到底沉不住气,来找我了。
我驾着车跟着导航仪里的声音,朝一个叫野马镇的地方开去。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一块接一块从我头顶上面飞过去,我离它越来越近。那个镇境内有一座山,叫凤山。它清楚地横列在卫星地图上。从高速上下来,进入省道,接着是乡道、村道。没多久,就见到一条河,如同门卫般挡住我这个外来者,我听得到河水流淌不息的声音,却不知它奔往何处。视野远处是连绵的青山屏障,近处是一小块长势茂盛的稻田。如同一副巨大的骨架之上,托出的一张秀气的脸庞。
这个地方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它算不上路途遥远,从出门到现在,仅仅花掉了四个半小时。我承认,如果不是张兰的警告,我只会在更远些的未来才能来到,或许,再也不来,就像无数桩想完成,却最终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人总是到一定年龄才想到去做某一件事。就像我的祖父,他将自己快丢完的时候,才想到要回家。这并非遥不可及的距离,是他一生再也没法回头的路。
2
当我将车停在河边,一步一步从起伏的稻田中穿过去,走向那座叫作凤山的山。我祖父最后三年的形象,也从我的脑海里走出来,达到了他在我脑海中最清晰的状态。
先出场的是他一对威风凛凛的浓黑眉毛。进入老年,它们像蝙蝠一样飞上了他的眉梢。他年轻些的时候,它们长在他脸上,配合他早已低眉顺眼的神情,就有了一种奇异滑稽的效果,像是一个惯于讨人欢喜的小丑故意将眉毛贴反了。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它们又与他的神情统一和谐起来。我祖父在记忆开始混乱和不断丢失的那些日子里,又慢慢从同一具身体里长出了另一个人。比如,他一贯温顺的性子突然布满了倒刺,脾气暴躁,见人就骂,有时冲到路上对着空荡荡的道路也要骂上几句。村里不知道他底细的年轻妈妈吓唬孩子,再不听话,把你送到潘爹家去。最后那一年,他的话语变得生涩难懂,高亢尖锐,和我们潘家村一马平川的腔调已是截然不同。
从不爱出门的他,某一天提着一个布袋独自出了门。从此以后,他就天天出门。每次路线基本固定,出了村口,一路向西南而去。因为我和张兰每日寻找的动静,大家都知道了他,他在乡间从未拥有过这般知名度。大部分时候出了村口,他都会被熟人发现,像牵头走失的牛般拉回来。最远的一次,等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爬过了离家七八里地的某个铁路桥,站在铁轨上,像一个游魂。一列载货的火车在我们的视野下,刚好经过他身边,他整个人好像在低空飞翔。有一次,他消失了。几乎一个村,包括派出所都出动了。我们最后将目标锁在了一个遍布野山茶籽的树林,那里有近百年快要成精的山茶树,也有淹没大腿的灌木。我们确实在那片山林里找到了他,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树下的衰草丛里,如一条已经归隐于大地的秋虫,我上前将他轻飘飘的身体抱起来,在初冬的山里待了三天,他竟然还活着。他早已经不认识我了,却抱紧我的脖子,像个孩子般干嚎,我要回家,回野马,回凤山!
当我走在路上,碰到了从那边过来的第一个人,他骑着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我大声喊道,老乡,请问后面那座山是凤山吗?他的车停在离我十多米的地方,我不得不掉头走过去。他对陌生的面孔有着自然熟络的从容,问道,第一次来?我说,是的。他说,现在凤山是森林防火特护期,不准游客进去了。前段时间,有人在那里搞烧烤,差点起了大火。我给他递上一根烟,他取下头盔接了过去,那是一张不算年轻的脸,看上去比我还长上几岁。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给我,我接了过去。他姓张,经营着一家农家乐,卡片上写着钓鱼、烧烤一条龙。我说,那下次来这里玩就方便了。我顺势向他打听一个叫潘青山的老人。他确认了一遍,肯定地说,没有这个人。我说,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他说,如果是出去打工了的年轻人,那我认不全。我说,不是年轻人,是老人。他说,住在这儿的老人,我都认识。一支烟抽完,他也没有想起潘青山是什么人。他几脚把摩托车踩得冒了烟,对我说,我们凤山一带没有姓潘的。
其实,这个人一开口,我就确定了这是祖父想回来的地方。哪怕他把我当作外地人,咬着一口走调的普通话。当摩托车的声音消失在远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祖母姓潘,祖父也姓潘,这应该不是夫妻拥有同样姓氏的巧合,而是因为祖父流浪在外,丢掉一个姓氏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个世上,除了我之外,不会再有人关心祖父到底从何而来。那些知道祖父是很多年的一个秋天来到潘家村的老人,都已按照顺序去了地下。他们说,祖父背着一个灰色讨米袋出现在村里的时候,全身的伤口都在流脓。那个年代,他们对于出现在村里的叫花子见怪不怪。这个叫花子应该是被饿狗咬了,不过那个年代,穷得连狗都少见,那应该是被人打了。村里的外姓,一个姓张的老头说,他屋里那时还给了祖父一个裹着红薯的饭团。最后,祖父没有再走出村子,晕倒在潘聘才家的牛棚里,潘家的牛棚里有两头牛。潘聘才是我祖母的父亲,潘家村最有钱的大户。那时啊,张老头每次说起这事,都会用手指着村西边那片山茶林的方向,在空中画一个大圈,再落回东边那片田里,他说,一大半个潘家村的地都是潘聘才家的。我问,后来呢?他咧着牙齿掉得空空的嘴笑,不再说话。后来,一张床,一碗稀饭救了祖父的命。祖父做了潘家的长工,又过了几年,和祖母潘学珍结了婚,做了潘家的第三头牛。
对于现在的潘家村,祖父上门女婿的身份并不是一件值得说道的事了。潘家村这些年接受了很多外来的人,姓氏早就变得五花八门。有从外地投奔亲戚留下的,有因为遭遇洪灾,家园变成了蓄洪区分流到此的,还有两户是外省来的三峡移民。只是在更早些的年份,碰上过年、中秋这样重大的节日,一个姓氏,沾亲带故且同在一个祠堂的本家亲戚常会聚在一起。每当这样的时候,常会因为祖母出格的表现,祖父的身份就像一个石头裸露在断流的河床上,不得不引起人的注意。
祖母穿着缀着盘扣的深蓝色棉袄,头发盘成一个大饼,用一个黑色网状的罩子套住,一根杂毛也不会探出来。我曾经在一个被尿憋醒的清晨,见到过她站在门边的晨曦里梳头发的样子,头发如同瀑布一样垂在腰际。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好看的人。都说潘知远长得很像她,而潘知远就是一个水灵的美人。祖母老了后,如同供桌上那些鲜亮的水果一样,虽然失去了水分,但是她的做派却愈加令人不敢亵渎。她那种做派,和村里那些带着孙辈的老太婆截然不同,她给自己搭了一个高架,将自己置于神坛,哪怕被那些孩子说成是修炼了一千年的老蛇妖也毫不在意。不好听的话,她听得太多,从来不把这当回事。从我懂事时起,她便作为全桌唯一的女人,坐在主位上,背部挺得笔直,神态严肃,在全族德高望重的男人中稳如泰山。她不常说话,男人们给她敬酒,从饭局开始到结束,她手中那小盅酒才喝完。女人们看着她笑,对她的特立独行都显示出一种敬而远之的包容。我一度以为是因为祖母地位的与众不同。有一年夏天,我们村的人在公路上遇到一个穿着棉袄的流浪汉,他蓬乱着头发,嘴中念念有词在我们的村路上游晃了几天。我们捡起石头朝他身上扔去,大家一边笑一边制止我们。他们同那个流浪汉说话,问询他从哪儿来,他的答非所问和惊恐表情引来一阵又一阵大笑,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东西,正是他们曾经施舍给祖母的笑容。在饭局开始前,他们都会故意站起来,东张西望寻找祖父的身影,嘴中叫着,潘爹呢?把他也请过来一起坐啊!
祖父在这样的场合,从未上过主桌。他将自己混于孩子们那一桌。有时,连桌都不上,帮着厨房里做事,埋着头和女人们在厨房就把饭吃了。他夏天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衣,冬天穿着套着灰色罩衣的棉袄,他对灰色的偏爱,一直持续到死。灰色成了他的另一层皮肤,将他隐藏起来。纵是这样,他和祖母之间做派、地位的巨大差异,是一定会被人讲起的。
我由此知道祖母是读过书的女人,听说读的书,比我和姐姐都要多。但是,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夸张,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乡下,识字的女人都是凤毛麟角。一只鸡,在那么多人的嘴中会被流传成一只凤凰。我曾经问过祖父这个问题。他难得地显出一种自豪,她学问大,什么字都认识,还能教潘知远写文章。我又问祖父,到哪里读的书呢?他摇头说,那我不知道。
祖父确实不知道。他面对祖母时,就像一个饿极的流浪汉,不管前面是什么菜,从不进行回味,只会选择一股脑吞下去。在我进入少年,我一度怀疑父亲是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完全不像有机会能制造出一个生命的样子。我曾经和潘知远讨论过此事,但是,她对此全无兴趣,没有回答我,只是斜瞟了我一眼,用蔑视的眼神告诉我,这是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和那些站在路上,对着我们家像流氓一样吹口哨的少年一样令人厌恶。我知道,她一定知道祖母的很多事情。要不然,祖母靠什么去教育她,让她几乎成了从祖母身上分娩出来的另外一个祖母。她酷爱黑色的裙子和白色的娃娃衬衣领,就算在夏天,衬衣领也会扣得一丝不苟,她从不穿凉鞋,穿着厚厚的齐膝的白色袜子。背部挺得笔直,像有人时时在反扣着她的双肩,不让脖子前倾。她吃饭,喝汤从来不会发出一点声音,穿着冬日拖鞋的时候,像只猫走路一样,不会弄出踢踏的声音。她一点不像从我们房子里走出来的女孩子。村里人说潘冬子像她的祖母,而我则像那闷棍子打不出半个屁的祖父。没有人说,我们像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想着过去,凤山已到脚下。两座高大紧临的山峰像母鸡的两个肥硕的翅膀,将整个山村包围在自己怀抱里,脚下如小鸡般簇拥着一圈人家。和现在大多数农村一样,除了几声鸡啼狗吠,站在屋前好奇地打量着我的,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几个穿着短裤,赤着脚,既忸怩又天真的小孩,见到生人,笑笑后像受惊的小鹿一般躲进屋里。这片老了的土地生长出了一大片新生的东西。几幢带着尖顶和罗马柱,却又裸露着红砖外墙的乡村别墅,两层宝盖头,有着宽大堂屋大门的楼房,一色竹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它们一起覆盖了过去所有的痕迹,包括祖父从这里走出去的脚印,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几乎问遍了山脚下所有人家。无论是潘青山、胡青山、张青山,都没有人能从脑海里挖出一个与青山有关的人。
天黑的时候,我按着名片地址去了那个农家乐。张哥正接待一个来搞聚会的单位,忙得不亦乐乎。好几个人正围着烟熏火燎的烧烤架谈笑风生,架上放着一只已经萎缩的全羊。另一边,为篝火晚会准备的木头已搭建得像个宝塔。他一见到我便关心地问,人找到了没?我摇头说没有。他一边给只剩下轮廓的羊身撒下一大把辣椒粉,一边问,上午和你说了半天,你都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年纪了呀?我笑了笑说,如果活着,应该一百零几岁了。他张大了嘴,问道,是你什么人啊?这时,站在他旁边的女人打掉自家孩子伸向羊腿的手,大声喝道,烫不死你!
篝火点起来的时候,农庄里热闹非凡。舞台的声音,像一群嘶吼的野马,向对面的山头奔去,让整个山都有了回响。我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从我步入天命之年之后,孤独似乎就成了我的亲兄弟。我没有兄弟,这时我想到了应该更加孤独的潘知远——我们多少年未见了呀。
我给她发微信:我梦见祖母了。我在屏幕上耐心地敲下了事情的始末,我告诉她,自己已经来到了祖父的故乡,野马镇的凤山脚下。潘知远的信息很快回了过来,速度之快让我很是意外。我习惯的是,我晚上发过去的信息,有时要等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收到回复,内容简洁,如同电报一样。她回道:等疫情结束,我想回家一趟。我才做了手术,已出院。
潘知远用了家这个字,让这些年冰冻的情感瞬间解冻,我的眼眶被它冲击得决堤。疫情还没有开始时,女儿潘月和张兰去过一趟日本,临走前,我在微信上告诉了一声潘知远。她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只是冷静地回复了一句,好的。潘月回来后一脸兴奋,姑姑对她们很亲热,根本不像我说的那样冷血。姑姑拥有一个电子公司,她们去参观她的公司,碰到的每个员工都会对她们鞠躬问好。潘知远替她们买了一大堆东西,其中几大盒治疗灰指甲的药水、用于跌打损伤颈椎痛的久光膏药贴是给我的。潘月那日站在镜子前问我,我长得像姑姑吗?我其实早就发现,她的脸型和眉眼都和潘知远神似,但是那种神韵却完全不同。我说,不像。潘月嘟着嘴,她都说像呢,她还鼓励我去日本留学呢。
我想,岁月、疾病都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潘知远躺在手术台上时,她一个人签下手术知情书时,一个人安静地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时,一定和我一样,轻易地就回到了过去。我的双眼雾气腾腾的,写道:潘冬子,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如果你回来,我们的家永远欢迎你。如果不愿意走了,就留在潘家村。
(本文节选自2023年第3期《芙蓉》中篇小说《黑箱子》)

许玲,1979年12月出生于湖南岳阳,现居常德。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原创版》《湘江文艺》《芳草》《清明》《湖南文学》等刊,有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曾获《湘江文艺》双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长篇都市小说《向前三十圈》《南回北归》等。
来源:《芙蓉》
作者:许玲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