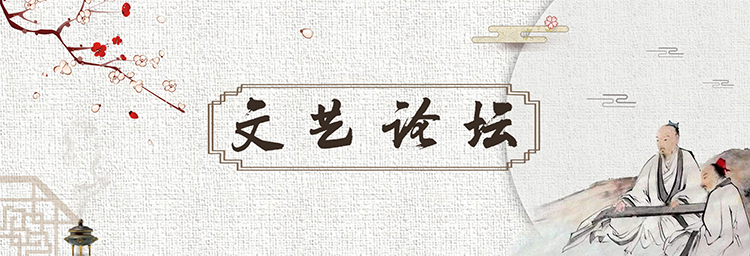

文本、历史与经验的“及物性”
——略论张清华的文本批评
文/赵坤
摘 要:从批评逻辑来看,文本批评是张清华讨论文学史、阐释文学现象并深入哲学美学思考的基础。正是借重各个文体中众多文本的讨论,张清华形成了他兼及文本、历史、现实以及生命经验的“及物性”批评特征,既活跃于文学现场又深入文学史研究。因此,有必要沿着其文本批评的踪迹,展开批评史意义层面的讨论,对其批评活动进行美学化观察,廓清当代文学批评脉络里那些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化时刻。
关键词:张清华;文本批评;生命经验;精神现象学
“唯一漫长的工作,是你不敢开始的工作”,迈克尔·伍德在评价萨义德写作“伟大的开端”时,曾引用过波德莱尔的这句话。此刻想起它,是因为这种杀人还诛心的描述实在是适合形容我眼下的惶恐。不同的是,伍德是用此话来激赏萨义德写作的难度以及他在现代主义框架下讨论后现代主义“意图与方法”的骑士精神;而在我,则完全是一种面对庞然大物的不知所措、斗量海水的冒失和盲人摸象的尴尬。这当然不是我在给自己接下来的浅薄论述找借口,也绝非为了历史中间物的文章宿命提前做铺垫,而是晚学后辈面对学术巨无霸时的影响焦虑式的自卑。我也知道这与青年该有的“反抗权威”的社会期待严重不符,但面对张清华教授这样一位重量级批评家、作家,且从不以权威自居的前辈学者,我对自己能否准确地理解其一二并在某种浅层次的维度上与之对话,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自我怀疑。以上内容只是想说明,对于一位著述等身的批评家,张清华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精彩论断以及他在当代文学批评现场中的卓越表现,甚至作为渴望“一次性生存”的学人典范,在已经获得诸如孟繁华、周海波、王侃、吴俊、何平、张学昕等众多著名学者的充分讨论后,本文对于如何避免“徒劳”的尴尬,已经放弃了心灵上的挣扎。唯希望能够踮踮脚,向上兼容而有所收获,也勉强算不辜负培浩兄的嘱托。
一、文本批评与文学史观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张清华教授的文学史研究、文学现场研究以及文学批评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等,既全面、独立又彼此高度关联。其中,广泛的文体涉猎及其对应文本的充分讨论,形成了他文本批评具体展开的结构意识与思维材料,无论是文学思潮、现象、作家作品论,还是文学史研究,几乎都以此为基础。
以他的成名作《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为例,大概是因为感受到巴尔扎克的传奇、雨果的浪漫以及莎士比亚的复杂,受这些伟大艺术作品的影响,很早就有“文学现场感”的张清华自觉地沿着黑格尔式历史理性的逻辑按图索骥,敏锐地发现了当代中国文学正在经历一场自五四延宕至今的关于“现代性价值”的再确认,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先锋文学是真正从精神、价值和情感记忆等方面重建了当代文学的实践运动。他所讨论的先锋文学也因此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是集合了启蒙主义的内核、现代性价值以及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形式的文学现象或文化潮流,涉及马原、洪峰、莫言、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徐坤、叶兆言的小说,徐敬亚等人的朦胧派诗作,先锋戏剧实验作品,甚至六七十年代的“潜在写作”等所有具备“现代性叙事”特征的文学文本。对此,张清华的判断明显是刻意反“知识化”的,“在思想精神的层面,它(先锋文学)是一场持续的变革,在其早期,是以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为基本内涵的启蒙思想运动,在其后期,则是一场以个体本位价值与现代性认知为基本内涵的存在主义思想运动;在艺术上,它的早期是混合了前现代的和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在它的后期则是混合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诸种艺术冲动,并且派生出‘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学思潮与运动”{1}。而这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判断,实质上是批评家对现代性逻辑的两种文化的理解,“启蒙的问题根本上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启蒙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其精神内核在实践层面上分裂成了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极端,一个是理性主义,一个是非理性主义:在西方,这两者至少从历史逻辑上是矛盾和互否的,但在中国,它们却注定是互为纠缠一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都不能单独解决中国的问题,并独自构成现代性的内涵”。{2}
这就使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先锋文学文本在不同形态里对存在主义复杂主题的隐秘表现。比如余华小说叙事中的存在隐喻并不限于延续现象学的时间意识或存在主义式的死亡景象,更有对生存本身悲剧性的深刻认识。在命运轨迹的偶然性、随机性、不可知性等宿命感的表达中,余华在文本中构建了他的存在寓言:“如他1995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隐喻,不断地靠‘卖血’——即‘存在的部分的消失’——来保证并‘感知到其存在’,直到这种‘以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的行为成为习惯和‘嗜好’,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结与存在的消亡。这同样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巨大的寓言’,一个完整的‘象征的存在’。在《世事如烟》等作品中,余华又刻意展现了存在本身的某种虚幻性、偶然性与名定性,人事实上已被删减和省略为数码符号,‘一切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示下展开其运动……如同事先已确定了的剧情’。许三观们的命运,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又有什么不同呢?”{3}再比如格非小说中极致的命运偶然性书写,类似《陷阱》《傻瓜的诗篇》《褐色鸟群》《没人看见草生长》等,无一不是通过人的存有间性的彼此相互脱离,反思萨特式的“物的存有和人的存有互相脱离”。尤其经历了荒谬、诡异、匪夷所思的历史时期后,格非小说形成了某种刻意的“错位”情境,将人物鬼魂化、事件传奇化、生活的具体场景虚幻化,似乎存有本身永远处于一种“‘从未证实’过而又永远走不出‘相似’的陷阱的一种假定状态中”。{4}类似的文本批评还有很多,在辨析先锋文学的个中差异时,张清华发现存在主义观念结构了先锋文学的命题,并因此催生出与之相适配的具有革命性的叙事形式,而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刻,新的叙事及其美学效果也反身成为存在大命题不可或缺的部分,让当代文学的存在主题变得更为吊诡、复杂而又无比精彩。
这便形成了从人文主义的启蒙接力转向个人主义的关键性时刻。在张清华教授“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逻辑论断中,先锋文学的存在主题带来小说叙事革新的同时,也收缩了现实主义书写的范畴,始自20世纪40年代的宏大叙事逐渐转向了个体的生命经验,积极乐观的情感基调也随即被存在主义的感伤情绪所取代。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全能英雄的主角光环慢慢消失,那些囚困于命运里的普通小人物,开始成为故事里的主人公,并由此延宕了许多年。对此,张清华与他的文本对象除了共同迎接“时代的感伤”,似乎也没有什么文学以外的办法。在分析徐坤1994年的小说《先锋》时,他第一次流露出面对“感伤”的心理结构,“小说以反讽和嘲弄的戏剧性和喜剧性语调,对当代激进迭变的文化精神、艺术思潮以及当代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状态作了尖刻而生动的描绘:在不但象征了中国古代文明和近代历史的崩溃,而且还暗示着当代中国启蒙主义文化之溃败的圆明园废墟上,一群名叫‘撒旦’‘鸡皮’‘鸭皮’‘屁特’的艺术家,在自身的贫困与他人的嘲笑中营建出一个充满自我谑虐的‘艺术王国’。在这里,一切文明和现代艺术的观念不只是处在颠覆和结构的状态,而干脆就是溃败、堕落与游戏的状态,一切指称都演变成了刻意的丧心病狂的‘不确定性’与‘互文性’的误读与游戏。在反讽式的语境里,他们拼装着他们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形式以及文本”。{5}多么会心的理解与阐释!在一场终将到来的精神转折期里,张清华和他的同时代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高涨与失落以及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挤压后的普遍性“感伤”,最终留给时代的表情,是一种“必要的停顿”。
以上几则小例试图证明的是,在文学史中理解文本,或通过文学文本廓清文学史,这原本是文学研究极为常规的方法,但好的研究者会在私人阅读的过程中敲碎被动知识化的硬壳,找到构建个体文学史观的秘诀。其中,强悍的“主体性”无疑是关键。在张清华的先锋文学思潮研究中,大量深刻的文本批评是基础,为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解释,也将以往很多处理成“断裂”(甚至无法处理)的个案都纳入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来。而作为启蒙主义的延宕线、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全球影响之一,对先锋文学思潮的研究也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和汉语新写作因此在一种确证的现代化叙事中,获得了某种“整体性”。
二、视野、方法、立场
这里还需要再次提及“学院派”。尽管作为批评家的张清华几乎与“学院派批评”的概念同时发生,但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很快显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从他的视野、立场和批评方法来看,不仅有“学院派”必需的理论功底,更有批评个体的才情,这使他讨论汉语新文学时常秉持宽阔的视野和自觉的泛文本比较意识,尤其在融通了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不同文体以及精神分析学和知人论世说、存在主义与生命体验美学等中西学之后,更显出极具个人风格的生命本体论特征。
倘若我们对张清华的文本批评做一番“考古”的话,会惊讶地发现,最初进入文本批评的场域时,他是带着古典文学和西学两套阵法的。比如古早时期的《“仙女尘夫”模式:一个古老而幻美的主题原型》《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选择与回归——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术精神》等,是自觉受到民族文化的古老原型与传统艺术形式的启发,先于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等方法。《“仙女尘夫”模式:一个古老而幻美的主题原型》中,张清华比较了两种古典文学的原型,即“才子佳人”与“仙女尘夫”。他认为“才子佳人”作为不断延续的道德理想,是中国人现实性爱结构里的最高表述形式。相比之下,“仙女尘夫”却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审美倾向,既是国人情爱现实欠缺后的某种想象性表达,也是一种“伦理主义对人性眼中桎梏的代偿形式”,也因此更值得追问其美学价值。他依次列举了《九歌》中的《山鬼》、宋玉的《高唐》《神女》、应玚的《正情赋》、阮瑀的《止欲赋》、王粲的《闲邪赋》,还有曹植的《洛神赋》等早期关于人神恋情的书写。而伴随文学的发展,“仙女尘夫”的结构开始有了新的变形,仙子、鬼魂或人世间气质近似于此的女子形象,更新了原有的模式,“刘义庆所撰《幽明录》中的《旁阿》一篇写石氏女因爱上旁阿的英俊,便离魂而奔,与之私会。干宝《搜神记》中《吴王小女》一篇写吴王小女紫玉死后仍以魂魄与清人韩重欢会的故事。这个故事为以后描写人鬼恋爱的作品提供了典范模式”。{6}他还在隋唐传奇、宋代话本以及清代的小说作品中找到了相关原型的各种变体,比如《离魂记》《长恨歌》《霍小玉传》《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柳毅传》《牡丹亭》《红楼梦》《镜花缘》等。这些完成了经典化的古代作品不仅都带有“仙女尘夫”的影子,甚至还共同结构出中国情爱文学的美学精神,即“‘仙女尘夫’作为一种古老而常新的爱情模式表现了我们民族在冲破传统禁忌、冲决生命的时空障力与自然法则,在探索与追求幸福性爱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他们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世界,在冲破的伦理道德禁锢中获得超越一切的美妙永恒的境界”{7}。显然,在张清华的阐述下,这些以原型方式连缀古典文学史的经典文本,也正是通过这一结构的不断变形,延展出一条意义深刻的所指链,表达了古老的东方式浪漫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对待生命情感的态度。
当然,还是要提到莫言研究。在那篇著名的《叙述的极限》发表之前,张清华已经发表了《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选择与回归——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术精神》这些转引率颇高的文章。他几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边倒的西方理论阐释里,将莫言研究重新拉回到古典美学传统的视野:“莫言小说文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处于一种为多重因素所激活的状态之中。人们在他的小说中读到了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读到了现代人的诗情与梦幻。而在我看来……莫言更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有的现代的和民族的魅力。究其原因,我以为是莫言凭着他天才的感悟能力和身后的民间与传统文化的修养与自觉,从传统小说艺术中汲取了最具活力的因素。”{8}如果说此后的张清华对于莫言的文本批评成为批评界重要的话语资源,那么90年代初的他就已经找到了理解莫言的密钥。到了新世纪,张清华更是从更多的长篇文本(尤其是莫言90年代以后的重量级长篇)中,条分缕析地找出莫言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与本土美学艺术观的关系,比如《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与“完整历史长度”同在的悲剧历史观念,《红高粱家族》《四十一炮》重返古代哲学观念内核的过程,《檀香刑》等叙述方法上的本土化色彩与传统美学的深层次关系,等等。
美学选择也是美学接受。在90年代初就选择莫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张清华在认同莫言的叙事方法与艺术形式外,也借着莫言的文本批评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观,也就是一种沟通中西方的生命本体论。构成这一思想内核的,有尼采、弗洛伊德,有莎士比亚和海德格尔,甚至还有茨威格、歌德和荷尔德林等(如果细数下去,这个名单可能无尽长)。必须要申明的是,他根本的生命逻辑依据的还是古老的东方式的生命体验,一种“以生命意志为核心的艺术主体对于世界的感知”,一种“通过对外在世界的审美感知而实现内在生命体验”的人文主义方法。这里有必要对笔者之前的判断做一个节奏上的更新。大概十年前,笔者曾尝试讨论过张清华的精神分析批评,认为他在“承认虚无的无解以及对抗虚无的无效性”后,选择了为自觉意识填土,以增强主体性的重量,具体到“强化自我,摆脱超我而独立,增加视觉的范围,扩大组织,以至于认识到本我的新部分”{9}。这个观点虽然在今天似乎也算说得过去,但依然有必须更新的部分,那就是在讨论格非的《望春风》时,我们看到的那个与他的批评对象惺惺相惜、彼此心领神会的张清华,“说到底,‘望’春风不是过客和观赏者的态度,而是凭吊者的态度,是死者的态度,也是消逝了的儒里赵村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几近终老的赵伯渝已没有风景,所有的风景都失散于时间和历史之中了,有的只是痛彻心扉的虚无,以及永世无助的孤单与苦难”。{10}体验过虚无后,采取策略的抵抗是少年热血、是人类永恒的激情创造,也是西方式的、尼采或荷尔德林式的与魔鬼作斗争的“积极虚无主义”;而唯有接受失败、接受生命存在的本质、接受历史中间物的命运以及抛物线式的个体生命轨迹,才是真正接纳了世界,吞下了命运。
三、“结构”意识或个人风格
如果继续讨论张清华的文本批评,还应该列举他的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新批评的众多实践,并列出那些已然进入批评史的著名篇章,细数有关“极限”“减法”“哀歌”、本土化的“精神现象学”等广为流传的关键词。但这在张清华君已然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标的物后,未免有些“天真的重复”了。从批评史的意义展开,或者对其批评进行美学化观察,似乎更适合这一历史化的时刻。借用文学阐释学的长时段视域,文学对象物入史的过程中,如何在批评现场中对目标对象进行发现和过滤是基础也是必要的程序。这既适用于文本批评的对象,也适用于文学批评家。其中的作用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文学研究的“阐”“诠”逻辑,即任何时代里具有“当代性”属性的文学对象物,都要在现场批评中经历一番竞择,只有那些符合批评标准的文本才能被选中,去经历不断浮动的批评标准和美学选择,完成通往文学史的第一步。这就意味着,处于鄙视链末端的现场批评,其实难度更大,更能考验站在烽火线上的批评家。
从张清华的批评踪迹看,他最初的文学研究已经观照到批评现场了。只是过于擅长总体论的批评风格遮蔽了他文本批评的部分,显得不那么“现场”。其实,像《增值与误读——十余年来诸多文学现象的再思考》《历史逻辑与20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化策略》《历史话语的崩溃和坠回地面的舞蹈——对当前小说现象的探源与思索》等早期批评中,不但有细致的文本阅读,甚至还有为文学史筛选文本的无意识自觉。比如同一时期对王朔和刘玉堂的文本批评,都是从文学语言的维度对作家作品的解读,选择的文本对象的时代关注度却明显不同。尤其是已经单独做过莫言、张炜、贾平凹、王朔的作品论后,选择刘玉堂的《乡村温柔》,除了有批评家的敏锐,还颇具文学史家的眼光:“这部小说在我看来不仅在现代乡村生活叙事的历史链条上有所恢复和创造发展,确立了一个以纯粹民间与喜剧性的视角‘重构’ 当代乡村历史的文本范例,而且还通过对当代民间话语特征的精细生动的模拟再现,深刻形象地喻示和分析了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与乡村民间文化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尤应视为他独到的发现。”{11}他重点分析了刘玉堂的文学性语言,尤其是文本中语言的有意误读,慧眼识别了小说中的“误读”分别将三重文化要素同时集中于当代乡村,通过各种具体的语用习惯完成了乡村文化语境的构造。比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本是诗情画意的原始表述,在乡村语境里,却是同时带有“红色话语”“白色话语”和“黄色话语”三种功能的双关句。它将革命意识形态、文人抒情以及乡野俚语黏合到一起,表达了当代乡村文化的混杂性以及乡村语言被改造后的荒诞与破碎。对于政治历史的后遗症如何通过语言改造乡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构造,在这一层面上,张清华为现场批评的文本选择搭建了批评标准。
对“文学性”的敏感和自觉也是始于他的文本批评,一种从解构的狂欢里逐渐冷静下来,有意寻找和建构的批评意识。“匪行小说”“潜叙事”“潜结构”“精神分析的方向”等原创性批评术语的提出,大都源于此,且由此,现场批评中的问题意识召唤了文学史研究的展开。比如对于“匪行小说”的命名与提出:“什么原因使得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出现了这样一种具有相当热度的小说现象呢?”“为何要以土匪、盗贼、兵痞或绿林侠客一类人物来作为承载物呢?”{12}在集中分析了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烟》《美穴地》《五魁》、杨争光的《黑风景》《赌徒》、朱新明的《土匪马大》、闫欣宁的《枪队》、刘国民的《关东匪与民》、冯苓植的《落草》、尤凤伟的《金龟》等相关文本后,古典侠义小说与江湖社会另类的平行空间作为激活人性人情的古老文化结构,成为新历史小说反叛阶级道德标准以及二元对立美学原则的原型。但土匪流寇毕竟不同于绿林好汉,“匪行小说”是张清华有意区别二者的新命名,既表达了时代的反叛性,也继承了传统美学的文学性。
相比之下,“潜结构”与“潜叙事”的提出,似乎更完整清晰地呈现出张清华的批评理路。这个明显受到精神分析学影响的说法,从大胆提出到小心求证,融贯了他对西方形式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深度思考。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不断拆解后,他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逻辑的“文学性危机”,比如对传统的消长、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性重建”的影响等。在这一逻辑下,启蒙或者革命就变成了现代性价值主导的文化时间轴上的阶段性产物,加上后现代主义本身的破碎与虚无,如何在一种弥漫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价值,就促成了他在解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自觉的建构意识,一种以“重建文学性”为目标的“批评的结构”意识。也就是说,张清华近期频繁在文章或研讨发言中提到的“文学性”问题,其实早在世纪之交的“潜结构”与“潜叙事”中就已经埋下伏笔了。就具体批评实践来讲,“潜结构”与“潜叙事”无疑是对革命文学中“无意识构造”的描述,这才是隐藏在正大的政治主题下的革命文学文本能够真正打动人心、流传下来的核心奥义,也是张清华尝试描绘出的“文学性”所在,即一种意会高于言传、原型或要素遍布于中外与古今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之中的、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内核。当然,就像他本人一再申明的那样,重提文学性绝不是要将所有的“非文学研究”踢出去,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也不能这样做。重提文学性的前提是,一则,当下的文学研究似乎更多地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文本”“社会学现象“或“历史材料”,忽略了文学本身;二则,既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等新方法使当代文学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与新高度,那么,不妨广泛借重,以此来补饮“文学性”的文学研究。{13}
这似乎已经足够证明,一个积极的、友善的、深怀人文主义精神的、生命本体论的批评家,对同时代汉语文学的鼓励、期待与热爱。尽管这真诚的情感时常遭到误解,但好在认同和理解的同道要多得多,学者王侃的高度共情就是典型:“在当下语境里,做一个‘唱盛派’需要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勇气。‘唱盛’总是容易粗暴地划归为‘政治献媚’并进而被认定为是‘灵魂失贞’和‘学术变节’,仿佛只有‘唱衰’才是‘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战斗意志’唯一可以选择的形象。”{14}这是王侃在读到张清华的《肯定近三十年文学的理由》后写下的。在那篇文章里,张清华以极大的勇气送上了他对当代文学的赞美:“我发现俄罗斯时代的批评家——最近我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觉得他毫不吝啬地用充满赞美和激情的语言来赞美同时代的作家,赞美同时代俄罗斯文学灿烂的景象。但是当代中国的批评家不敢,没有人有这样的勇气说最近三十年或者至少从80年代中期以后到新世纪初这将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汉语新文学诞生以后的最辉煌时代。”{15}显然,张清华对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盛况心驰神往,他敬重那些灿若群星的伟大作家,也同样敬重那些有能力与之对话的杰出批评家。大概比起批评之限与批评之难,避免“与杰作为敌”是他对话文本、追想历史、获得生命经验的及物性时最为警惕的。
注释:
①{3}{4}{5}张清华:《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第230页、第231页、第245页。
{2}张清华:《文化实践和精神自否——20 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选自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 171 页。
{6}{7}张清华:《“仙女尘夫”模式:一个古老而幻美的主题原型》,《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8}张清华:《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9}赵坤:《灵魂的描摹或历史的隐喻——张清华的精神分析学批评概述》,《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10}张清华:《秋鸿春梦两无痕——读格非〈望春风〉小记》,《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11}张清华:《大地上的喜剧──〈乡村温柔〉与刘玉堂新乡村小说的意义诠释》,《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12}张清华:《走向文化与人性探险的深处——作为“新历史小说”一支的“匪行小说”论评》,《理论学刊》1995年第5期。
{13}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14}王侃:《学院派、美学复辟与批评家的自否精神》,《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
{15}张清华:《肯定近三十年文学的理由》,《上海文学》2008年第6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及理论建构”(项目编号:22AZ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赵坤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