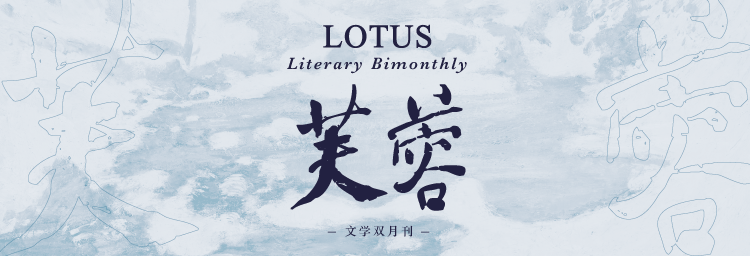

接受(中篇小说)
文/王凯
一
小学二年级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和杜大头去爬树。那棵树就长在基地卫生队院子后面,大到我们两个都合抱不住。我爸说他当年刚毕业分到基地时,整个营院统共只有一棵树,他说的应该就是这棵。由于这棵树太过粗壮,没办法用平时双手抱树的办法爬,所以我们一直没去尝试。但那个下午我们还是决定去爬一下,毕竟其他的树我们已经爬腻了。我们在树底下转了几圈,杜大头让我先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不上,他说他想先看我爬。这个理由听上去毫无道理,可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其实并不懂得多少道理,于是我就提了提裤子开始爬。树干虽然抱不住,好在它有那么一点儿倾斜,树皮上又有许多裂缝和孔洞可供踩踏,所以爬起来并不算太难。我一直爬到很高的地方,然后骑在一根横枝上喊杜大头上来,喊完后正想起身站在横枝上,可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我想那大概是塑料凉鞋在树枝上打滑的缘故——一脚踏空就从树上摔了下来。目睹了这一切的杜大头在树下怪叫了一声,撒腿就跑得没了影子。我以为他是去旁边的卫生队帮我叫人了,毕竟那棵树距离卫生队后墙不到20米,就算杜大头没有——他确实没有——司马光砸缸那样的聪明,但哪怕是个傻子也应该知道去找医生求救。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一块纱布去学校时,才知道这家伙根本没去卫生队求救,而是一溜烟跑回了家。
“我是回家了呀,我得回家,我妈让我4点前必须回家。”杜大头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再说,又不是我让你掉下去的,是你自己掉下去的呀。”
杜大头的话听上去十分无赖却无懈可击,搞得我也没办法生他的气。从树上摔下来那会儿,我浑身动弹不得,感觉胸口某个地方被堵住了,攒了好半天力气才终于喘出了一口气。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这个念头本身也几乎把我吓死,于是我本能地在树下尖叫起来。这垂死的哀鸣翻过卫生队的后墙又筛过金属网纱窗,好容易钻进了队长的耳朵。他派了个卫生员循声跑来把我抱了回去并包扎了一番,然后告知闻讯赶来的父亲我并无大碍,不过是轻微脑震荡而已。那几天,我总感觉晕乎乎的,后脑勺上包了纱布的地方一跳一跳地疼,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脑袋上总有一小块地方不长头发,以及我对八岁以前的事情毫无印象的原因。
毫无疑问,我八岁之前的记忆被摔坏了,成了一块无法读取的内存卡。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尽管十分零散,但我却深信不疑。比如,我能记得住一年级学过的古诗和十以内的数字加减,但却不记得我在教室的铁皮炉子上把自己的棉鞋烤出了一个洞。还有,我对基地幼儿园那排平房和院子里的滑梯和转椅都感觉熟悉,可对这里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印象。我姐说我曾在家里帮她赶走过一只老鼠,我却不太相信这事儿,因为我每次见了老鼠都会抱头鼠窜。仿佛时间的河流上安装了一道闸门,我溯流而上时都只能在它面前止步,压根看不到闸门那边的景象。这样一来,我所有的记忆都是从这道闸门或者说那次坠落开始。而此前如何跟着母亲随军来到基地,以及如何上了幼儿园之类的事则统统付之阙如。不过记不住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记不住就相当于不存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再说这可能还是件好事呢,至少可以让我避免了一些悲伤。据我妈回忆,去年我一个要好的同学跟着他爸妈转业回老家了,为此我好长一段时间都闷闷不乐。
“人家走的时候你还哭哩,哭了好几回。”我妈说,“你还给人家送了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我觉得我不可能这么大方,可我妈又不像是骗我的样子。我所经历的事情要别人说了我才知道,这感觉十分奇怪,所以我同样不相信我会为了一个同学离开而流泪。就像杜大头,他要走的话我肯定不会哭。我从树下摔下来他都没有帮我叫医生,一想起这事我就感到气愤和难过,可是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和他一起玩。因为除了杜大头,我也没什么别的人可以玩。大点儿的孩子总喜欢欺负我们,而小孩子动不动就哭还流鼻涕。而杜大头尽管头长得大了些又有些罗圈腿,但至少我们还能玩到一起去,再说我自己近视而且还有鸡胸,也没资格嫌弃人家。换句话说,在1983年乃至以后的几年间,没有比杜大头更好的选择了。
二
由于从树下摔下来的缘故,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认识杜大头的了。他就那样晃着他的大脑袋存在于我记忆的片头,胸前系一条被他用牙撕咬成一缕一缕的红领巾,感觉跟邦德出现在007的片头那样自然且无须解释。还有就是我们在玩的问题上往往都能达成共识。这一点可能是与没有大人介入有关,因为他们都忙着上班,几乎没什么时间来管我们,不像现在的小孩,永远都被大人死死地盯着。
先说我爸。我爸长着一脸钢丝一样的胡茬,这让我感觉他已经很老了,但要算起来,他其实不过才四十岁。作为基地司令部技术室的工程师,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在训练场地或者龙头山背后的靶场待着,虽然同属于基地,我却很少能见到他。母亲在陕北老家时是小学民办老师,教授从语文数学到音乐体育在内的所有课程。随军到了基地之后没有老师可当,于是成了基地印刷厂的一名职工——那时的基地居然有个印刷厂,可见当日的盛况。有时我带着杜大头去印刷厂车间里玩,他对那些轰隆作响的机器很有兴趣,会长久地凝望着一张张白纸放进机器里,出来时就印满了漂亮的铅字。那些盛在一个个木框盒里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铅字也是他喜欢的,他一直想不明白那一颗颗铅字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很肯定地告诉他那是铸造出来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铸造。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排字间偷出几个铅字,然后用胶布缠起来做成印章。我给我们两个各做了一个,但他嫌印出来的字小,有一次自己钻进排字间去找大号铅字,可是那些反刻的铅字他一个都认不出来,由于他在排字间里待得太久,接下来两天,他都说晚上睡觉时满眼都是明晃晃的铅字。当然,必去的还是走廊头上那间大库房,里面堆着数不清的麻袋,麻袋里装着切纸机切下来的各种废纸条,我们最喜欢其中的牛皮纸条。这种纸条叠成弹弓用的子弹,比白纸叠的子弹打得更远并且更疼。
这是我爸妈的情况。下面说说杜大头的爸妈。杜大头他爸是基地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长得又矮又瘦,杜大头说这可能是因为他爸每天都要加班。不仅加班,他爸还经常要去兰州和北京出差。兰州我不知道在哪里,但北京我们都是知道的,那里有著名的天安门,上面还飘着一排红旗,这让我感觉杜大头他爸相当厉害。我们在营院里乱逛时,他经常指着办公楼三层的一扇窗户说他爸就在那里面上班,但因为那栋灰色五层大楼门前高高的台阶上永远站着卫兵,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上去过。这可比我爸上班的地方强多了。我爸他们的技术室只是办公楼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平房小院,任何人都能随便进出。从这点上说,当干部的可比搞技术的要厉害多了。办公楼进不去就算了,但杜大头他妈上班的基地服务社完全是可以进去的。在我看来服务社可比印刷厂好多了,里面又大又亮,镶了玻璃的柜台里面摆着各种东西,而且不会像印刷厂那样轰隆作响,说句话都要贴在耳边使劲喊。更重要的是服务社墙角的木头箱子里还有冰棍儿,我们要是去的话,没准儿杜大头他妈会给我们吃一根。可惜这都是我想的,因为杜大头从来不肯和我去服务社。他说其实他妈想去的是印刷厂,可惜她不识字,而印刷厂印出来的纸上都有字,她就没办法去印刷厂上班。杜大头很怕他妈,可能是因为他妈长得十分高大,看上去足有两个他爸那么宽,头上烫着雄狮一样的卷发,所以杜大头的大头非常像他妈。一般情况下,杜大头他妈都是下午4点钟下班,在这之前,不管我们在干什么,杜大头都会立刻停下来跑回家去,哪怕我从树上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也不能阻止他回家的脚步。如果他妈进门了他还不在家,整个家属院就会听到持续不断的叫喊声,那声音在家属院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得到,没有任何一个话剧演员能有这样无死角的音量。只要杜大头听到这个声音,立刻就像被电打了一样面色苍白,因此我和他在一起玩时,他都会习惯性地拦住任何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大人问:“叔叔,现在几点了?”
虽然杜大头的活动时间受到严格控制,但仅就活动内容来讲,我们依然是自由的。比起如今的小孩,我们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且无须支付任何费用。不像现在,城市的小孩子们连一头真驴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去骑了。他们小小年纪就是消费者,不管干什么都要出钱,哪怕去郊区农村摘个果子也得付费,而我们从来不用。这就是戈壁滩的好处,不像城里,哪儿哪儿都挤得要死。比如下午放学回家后,我们可以打玻璃球,主要玩法是在地上挖个小坑看谁先把它弹进去。或者玩烟盒,把它们一张张折成三角形或者长方形。这个就不细说了,因为每种游戏的规则都相当复杂,写下来起码得三页纸。玩烟盒我和杜大头互有胜负,赢到和输掉的烟盒数量总体差不多,但打玻璃球——水青方言里这东西叫“daidai”(声调均为二声),应该就是“蛋蛋”或者“球球”之类的意思——这方面杜大头不行,他输了我有二三十个各色“daidai”,但最后他又死皮赖脸地找我要回去了。“这是我从我家的弹珠跳棋里偷出来的,我妈要知道了我就完了!”杜大头这么一说,我立刻就想到了他妈那头卷发和雄壮的身躯以及永远板着的脸,有些不寒而栗,只好把那些好不容易赢来的“daidai”还给了杜大头。可是接下来,杜大头又拿着刚从我手里要回去的“daidai”跟我玩起来。
当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暑假。戈壁滩的夏天其实并不热,即使三伏天夜里不盖被子都会被冻醒。即使是白天的烈日,只需要一片树荫或者屋檐就可以解决。那个时候,基地院里的杨树和围墙外的麦田都是绿的,而且还可以吃到冰棍儿。在那些漫长的夏日,我和杜大头手持弹弓,裤兜里装着小石子——那些纸折的子弹是专门用来打人的,而小石子则相当于实弹——在偌大的营区里闲逛。营区后面有很多高大的兵器库房,宽大的木门顶上是小格的玻璃窗,我们一个下午就能打碎好几十块。回家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射击沿途的路灯,直到某天我被我爸抓住打了一顿之后,这项活动才宣告结束。弹弓没有了靶子,我们就去掏鸟。基地家属院后面有几排空平房,门前水泥小路的缝隙里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我和杜大头常常从十分低矮的后墙爬上去,掀开屋顶上的瓦片找鸟窝。麻雀最喜欢在瓦片下面做窝。这件事十分有趣,因为你掀开的瓦片下面可能是废弃的空鸟窝,也可能是鸟蛋或者是还没长毛的光腚鸟崽子。我们曾试着用铁皮罐头盒煮过鸟蛋,不过大多数都在沸水中爆裂了,露出了蛋壳里刚刚成形的小鸟,最后我们只得放弃了吃鸟蛋的想法。至于那些张着淡黄色大嘴的光腚崽子,都被杜大头带回去喂了他家的猫。
寒假相对来说就差一点儿,但考虑到有一个可以穿新衣服和放鞭炮的春节,也就跟暑假有得一比了。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我每天出门都会装满一口袋的瓜子和拆散的鞭炮,手里捏着一根燃着的白棉线,直到吃完瓜子放完鞭炮才回家,那些天我的舌头上肯定会有嗑瓜子嗑出的血疱。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家属院角落里的小树林捡树枝烤土豆吃,要么搬来石头去砸旱厕里冻成塔状的大便。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冒险型的活动。像钻大院里的防空洞,或者翻进家属院的空平房里探险。有一回我和杜大头在一间厨房里找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棕色玻璃瓶,晃一晃发现里面还有半瓶液体。他说那里面可能是酒,让我打开尝尝。好在我还比较聪明,先拧开盖子凑过去使劲吸了一下鼻子。霎时间,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天灵盖,仿佛一根钢毛刷从鼻孔一直捅进肺管,让我半天喘不过气来。几年后我学了化学,才明白那瓶子里装的应该是浓盐酸,如果当时我喝下去的话……这让我在之后数十年的岁月里依然不时感到后怕。
三
真要说起来,与杜大头有关并令我长期后怕的事远不止这一件。比如有一天放学时,杜大头约我去找他。我回家扔下书包就往他家跑。我们两家中间只隔着一排平房,现在想起来大概不到100米。他家门开着,我在门口叫了他一声,便撩开沙枣核门帘走了进去。在屋里我又叫了两声,却没人答应。我正准备去外面看看,一转头,他家高低柜里面一个没盖盖子的饼干桶吸引了我的目光和口水。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不安的心情,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只要我看到饼干就会想起这件事。因为那只红色方形饼干桶十分神奇,我只是看了它一小会儿,它就把我还很细小的右手吸进了它的圆形开口中。我无法抵挡这巨大的诱惑,饼干桶里的手指飞快地捏住了一片饼干,然后我就把那块表面带着颗粒的圆饼干塞进了嘴里。吃进嘴里的饼干不可能再原样返回饼干桶,这意味着整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会儿我倒不至于想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纯真无邪的过去这一事实,也不明白从此以后我卫生纸一般的心灵将布满越来越多的污点,我当时感觉到的只是强烈的惶恐,以至于我立刻退后了几步。由于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生出的负罪感,一时间我还无法辨别那种复杂的心情究竟是什么。它只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饼干的香甜和偷窃的耻辱左右开弓地抽打着我,相比之下,那些死于我手的雏鸟和鸟蛋都远未令我如此不安。我招架不住,只得冲出门去,结果和迎面而来的杜大头撞了个满怀。
“你这么快呀。”他说,“我刚去撒了泡尿。”
我不敢说话,否则杜大头可能会看到我嘴里的饼干渣,所以我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你干啥去?”他在我背后喊,“我家有饼干,咱们一起吃呀!”
我跑得更快了。我无法面对杜大头和他的饼干。我也不能告诉我爸妈,否则他们一定会将我痛打一顿。即使在我残缺的记忆当中,他们也不停地向我灌输诸如“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和“小时偷油长大偷牛”的道理。这种朗朗上口的论断给我造成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在不久的将来,我将成为一名偷窃各种食品的江洋大盗,最终被警察叔叔抓住,在高墙铁窗中度过可耻的一生。沉重的思想压力让我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而之前我向来以“白白胖胖”著称。为此我妈还带我去卫生队检查了一番。医生拿着听诊器前胸后背地听了一番后说我属于消化不良,然后给我开了一盒山楂丸。我从来没想到还有这么好吃的药,所以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告诉我妈我有点儿消化不良。但是山楂丸的疗效毕竟有限,我还是没忍住在某天把我偷吃杜大头家饼干的事告诉了我妈。我已经准备好了挨一顿痛揍,可意外的是我妈居然没有动用手边的笤帚,甚至连扫都没扫一眼。她的目光都在我脸上。
“这事确实很不应该,不过你能主动坦白,说明你自己也认识到错误了,你是认识到了,对吧?”我妈的口气听上去十分温和,这让我绷紧的身体也放松下来,“不过一定要引以为戒,以后可千万不敢再干这种事了啊!”
我妈现在虽然只是一名印刷工人,但民办老师的素质一点儿没丢。每次杜大头来我家,她都会笑眯眯地摸摸他的大头,问问他学习上的事情。但我去杜大头家可从来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因为除了杜大头本人之外,其他小孩在理论上是不能与杜大头他妈同时出现在他家的。杜大头每次叫我去他家玩都有着比按时上学还要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去的话,必须在下午4点前离开,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杜大头家里时,他总会不停地扭头看他家柜子上的那只闹钟。数学课他从来分不清大于号和小于号,对米、分米和厘米的换算关系也一头雾水,唯独讲到时分秒这一课时他比所有人反应都快。但不知是闹钟忘了上发条还是他妈提前下了班,总之有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俩在他家玩猫玩得过于投入,以至于忘记了时间正在暗中悄悄流逝。那只吃过光腚鸟崽子的大花猫长得很肥,特别是圆滚滚的脑袋很像杜大头,尤其喜欢人拿鸡毛掸子逗它。我们正玩得不亦乐乎,杜大头突然停了下来,像他家的猫一样竖起耳朵,紧接着就蹦了起来。
“完了完了,我妈回来了!”他说得一点儿没错,因为我也听到了门外自行车的声音。看看闹钟,那根秒针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你快藏起来,快点儿快点儿!”杜大头急得在屋子中央直转圈,看上去很像他家的猫在追尾巴,“我妈不让别人来家玩!”
杜大头的反应如此强烈,把我也给吓住了。好像我们是两个正在入室盗窃的毛贼,而主人的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孔。问题是我能藏到哪里去呢?他家和我家一样,都是三间平房,进门算是堂屋或者客厅,直往里去是一间小厨房,此外就是与客厅左右相邻、充作卧室的两个小套间了。客厅里除了大衣柜、五斗橱和高低柜之外就是一张写字台和两张凳子,一眼就能看个底朝天,而小小的厨房更是无处容身。情急之下我慌不择路,一头钻进了右边的卧室,进去才反应过来那是杜大头爸妈的房间。但也不可能再换地方了,只能躲在门背后,紧贴着墙角大气也不敢喘。那之前和之后,我好像都没再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以至于这短短的几分钟永远像一只河道上的航标灯,在我记忆中不停闪烁。这时候门缝里闪过一个影子,接着是门帘的碎响和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我希望杜大头能像王二小或者海娃那样把他妈引开,比如引到厨房或者另外一间屋子,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从包围圈里趁机突围。可就跟所有终将落空的希望一样,我根本听不到杜大头的任何动静,他自己可能也被突然出现的老妈给吓坏了,我只能听见趿拉趿拉的脚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最终朝着我藏身的卧室而来。这声音简直快要把我吓疯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落入杜大头他妈的手中。但除了束手待毙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出路,我只好闭上眼睛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万幸的是,杜大头他妈进了卧室之后并没有随手关门,这让我感觉到了一线生机。我后背拼命贴着门后的墙角,门的另一侧是窸窸窣窣的脱衣声,紧接着“咣啷”一声,我听出那是脸盆或者痰盂之类的搪瓷制品在水泥地面上拖动。然后她说了一句硬邦邦的山东话,我没太听懂,但听上去像在骂人。不知过了多久,那脚步又趿拉趿拉地走了出去,我歪头斜眼从门缝里往外瞅,只见一个穿着白背心和红裤衩的背影进了厨房。天哪,这一定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犹豫了几秒钟,然后从门后绕出来,猫腰从卧室门上那半截布帘子下面钻出去,又一头撞开泛着油光的沙枣核门帘,冲出几步外钢筋焊的小院门,拼了命地往外跑。“什么人!”杜大头他妈在后面叫了一声,那声音于我而言不啻猛兽的吼叫,差点儿没把我吓死,直到我跑过他家那排平房的房头才敢喘出一大口气。后来我才想起来,我完全用不着跑得那么拼命,杜大头他妈就算再吓人,那也不可能穿着红裤衩出来追我的。等我妈下班回来,问我衣服后背为什么是湿的,我才惊魂未定地讲述了我死里逃生的历险。我以为我妈会同情我的遭遇,哪知道她却笑得半天停不下来。
“你跑啥跑?大大方方出来打个招呼就行了呀。”我妈对我仓皇逃窜的举动不以为然,“人家还能把你吃了?”
我妈的话我不敢苟同,因为杜大头他妈对自己的儿子都那样凶,对别人的儿子能好到哪里去呢?“她是把杜小军管得太厉害了些,不过也情有可原,都说她生杜小军的时候难产差点儿要了命哩。”我妈又说。可等我问难产是啥意思时,我妈又像没听见似的走去做饭了。
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杜大头家。虽然我们还经常相约着一起上学,但我的确再没有踏进他家一步。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玩不成他家的大花猫了,不过对我来说并不算是坏事。至少这让我彻底失去了偷吃他家饼干的机会,否则以我那样薄弱的意志,很可能还会抵挡不住饼干的诱惑。从这个角度讲,我还要感谢杜大头他妈把我从犯罪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节选自2022年第6期《芙蓉》王凯的中篇小说《接受》)

王凯,1975年生于陕西绥德,1992年考入空军工程学院,历任技术员、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解放军文工团创作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小说集《沉默的中士》等6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来源:《芙蓉》
作者:王凯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