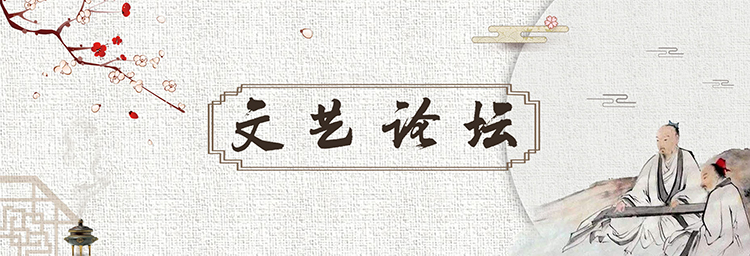

性别美学视角下的女性言说
——王安忆《天香》解读
文/陈文婷
摘 要:在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书写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是其创作重点,也是创作特色。小说《天香》更是把这种女性写作发挥到极致,以男性角色的缺失或失语、姐妹情谊的建立彰显了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构建了独特的女性人文景观,同时,以代际递传为起点,探讨了女性主体建立的途径,具有独特的批判锋芒和思想高度。
关键词:《天香》;性别美学;女性言说
小说《天香》以天香园里女性的故事为主线徐徐展开,以独特的女性言说开辟出女性书写的新领域,凸显了作品的女性主体意识,透露出作者的精神光芒。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从性别美学视角切入,探讨小说如何从性别经验出发,有效规避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提出女性自我言说的可能,实现难能可贵的与男性话语对峙的智慧和勇气。作家把女性作为重点纳入关注与思考的视野,小说在以宏大历史为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以女性群像主导小说叙事走向的创造性构思,显示出其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男性失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契机
小说《天香》在晚明历史的推进过程中,展现了上海贵族申家由盛到衰的历史,落脚为申家三代女性独立、自主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围绕天香园及天香园绣,塑造了以小绸、计氏(镇海媳妇)、闵女儿、希昭、蕙兰为代表的,包括和蕙兰有关的戥子和乖女等多名女性,涉及申家四代人,她们慧质兰心、个性鲜明,每个人身上都有着独特的、鲜明的、自主的女性个性特征。作品以她们在天香园里的生活,尤其是以她们的“绣”为主线,展现出一幅女性奋斗、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多彩画面。在围绕天香园展现的女性人物群像图中,表达出作者对女性个体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尊重和赞扬,折射出女性自我言说的心理与情感世界,寄托了对女性自我尊重、建构、重塑的愿望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的生存体验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家庭关系中男性角色的失语或缺失。两性关系向来就是人类社会各关系中最基本、最常见也是最难处理、无经验可寻的关系,但其对女性成长、生命历程却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诚如刘思谦所言,“女性主体性成长中,最难的是以爱情婚姻为关联的两性关系中的主体” ①。小说通过描绘女性生命过程中这道简单又繁杂的两性关系风景,来探究女性自我言说、个体成长、主体建构之路的可能路径。在话语叙事中,以两性关系中男性的失语或缺失,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提供了契机,将社会历史文化中本来隐匿于边缘的女性推送至小说文本的中心。
小说中,跟天香园有关的几个主要女性都经历了“父权制”观念的溃散或坍塌。这一点在小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小绸初在天香园的生活和初建的天香园一样有声有色,和丈夫柯海之间的相处兴趣相投、生动有趣。可是在柯海远游,出于无奈纳了闵女儿为妾之后,她就彻底把柯海拒之门外,自此再与他没说过话,小绸把过往的生活进行了断崖式的割裂。闵女儿入了天香园后,慢慢知道了自己嫁进来给小绸造成了伤害,也知道了柯海心思从来没在自己身上,就疏远了丈夫,一门心思放在绣上。柯海之于小绸和闵女儿,不像传统社会中的丈夫,是天是地一样的存在,而像生命中匆匆一瞥的过客,其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将小绸和闵女儿联系在一起。计氏和镇海之间的相处总是静静的,婚后生活和之前并无大异,镇海的心事也渐向佛事靠拢。第三代儿媳希昭嫁入天香园后,也和丈夫阿潜过了一段夫妻恩爱、甜甜蜜蜜的小日子,但一朝阿潜迷上丝竹之乐,竟跟随弋阳腔班而去,弃家出走,留下希昭独自一人。而申家孙女蕙兰所嫁的丈夫张陛,更是自小体弱、少言,蕙兰嫁过来后,两人过得如路人一般,甚少交流,新婚不久张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蕙兰孤儿寡母。小说在行文过程中,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男性渐渐隐去或失语,而女性形象渐渐浮出地表,变得鲜活起来。正如作者所言,“故事的行进就是男主角不断退场的过程”②。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一直是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甚至是缺席的存在,是作为“他者”的客体存在。几千年来,父权制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思想已经深刻印在女性心理上,成为她们难以摆脱且奉为真理的“集体无意识”,男性,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中的男性角色,既是女性心中抹不去的“夫纲”,也是她们无法逃离的主体存在。但在《天香》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言说。可以看到,在两性关系中,柯海之于小绸和闵女儿,阿潜之于希昭,张陛之于蕙兰,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是缺失的存在,更是在精神世界中的失语。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家庭中,将男性角色悬置或忽视,是从文化心理角度实现了对男性权威的消解甚至颠覆,通过女性的婚姻困境来展示女性精神世界的变化,借此强调女性的精神成长。
与此同时,和女性在家族关系中男性角色失语后重新审视这种关系的平静心态相比,反倒是男性在传统的两性关系被破坏后无法释怀。如柯海和小绸感情出现裂缝后,小绸的平静和柯海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闵女儿自然而然地把生活重心从丈夫身上移至他处;阿潜出走后穷困潦倒,希昭却走上了天香园绣楼,开始了有声有色的绣艺生涯;蕙兰在丈夫逝后,独自用绣技支撑起一个家,并收徒授艺……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说明女性并非完全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这些女性在传统关系颠覆后,于日常生活的挣扎、奋斗中,逐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明确了对生命的责任,肯定了自我的生存价值。在以男性为主角的传统父权制体制内,女性以清醒的主体意识,按自己的意愿立身行事,展现了作者鲜明的女性立场。
随着男性的缺失或失语,天香园这些女性不得不承担起原本男性应该承担的责任,伴随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独立意识的增强。虽然天香园的外在主体还是以男性为主,但内在实际却是女性在支撑着,她们以绣艺为生存技能,打造一片女性独立自主的天地,这种错位关系给小说叙事带来戏剧性的张力。这些女性在自我意识苏醒之后形成一种自由自在、自信向上的状态,在生命发展中找到了个体生命本位,并以这种积极的、向上的精神影响他人。戥子和乖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戥子本来是婢女,看到蕙兰丧夫之后独自撑起一个家,慢慢意识到女性不依附男性也可以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她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处事方式,对李大、范小婚姻为不以为然,甚至骂其腌臜,为学绣艺甚至发誓不嫁人。乖女因小时破了相,上门提亲的不是残了手脚身子,就是让她续弦做妾,实在委屈,因此发出“ 我不嫁人”的感叹。在这些形象独特的女性人物身上,男性不再是她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自己的独立承担才是生存之本,作者以这些女性世界中男性的失语,实现了对男性世界的解构,以此质疑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权威,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
二、姐妹情谊:女性同盟力量建立的基础
一般来说,在传统父权制社会,女性对自己的定位是以男性为主,依附于男性,从属于男性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沉淀在女性心理上的性别“集体无意识”。女性在这种设定中以他塑和自塑的形式变成了符合父权制需要的“第二性”,成为经济上、人格上和心理上依附于男性的“他者”。天香园中的女人们,在遭遇到了原本神一样存在的男性缺失或失语后,女性精神世界的缺失如何填补呢?作者把视线转向了同为女性的她们身上,通过人物关系的变化,呈现女性之间建立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姐妹情谊,这种叙事既有历史层面的批评阐释,又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对女性同盟进行剖析,具有丰富的性别心理内涵。
天香园中最早建立起姐妹情谊的是小绸和镇海媳妇,这原本是妯娌俩,但妯娌俩原本不但没有姐妹情谊,反倒有一些抵牾。小绸虽出身世家,但家庭基业早已单薄,镇海媳妇嫁来时嫁妆摆了一条街,风光住进了楠木楼,小绸生了女儿,镇海媳妇却生了个儿子,柯海爱往楠木楼上与弟弟、侄儿玩耍,导致小绸夫妻间有些罅隙,便断定镇海媳妇是可恶的人。柯海娶了闵女儿后,小绸将自己和女儿闭于小院不与其他人往来,是镇海媳妇不计前嫌,连拉带拽地将她们与天香园其他人慢慢融洽起来。小绸和闵女儿同嫁一夫,关系既尴尬又疏离,也是镇海媳妇凭着一颗真诚的心,以绣品为中介,将原本应该水火不融的两个人拉到一起,闵女儿也为小绸设身处地着想,疏远了丈夫,三个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在父权制社会男性角色失语的情况下,天香园里的女性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中相互扶持,她们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姐妹感情。在镇海媳妇病重之际,小绸拿出压箱底的墨救了她,两人互换乳名。小绸和闵女儿共同给镇海媳妇绣的寿衣,荷包牡丹的“当归”,映衬出两人对她的不舍,更突显了三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深情厚谊。这不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的情感,而是基于姐妹之情的友谊。在这种友谊中,她们不但获得了精神世界的互相安慰和鼓励,也让她们认识到女性群体力量、女性友谊的可贵。
姐妹情谊的书写是小说在打造女性主体形象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姐妹情谊”(Sisterhood)是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一条重要术语,意指“女性间息息相关的意识与体验,是通过女性中心的视角及对女性的定义而产生的对自身的认同及肯定”③。在作家笔下,姐妹情谊来自女性内部的共情,因为两性关系中男性的缺失,她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情感,表现出作者对性别美学的独特思考。姐妹情谊的书写不仅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心,彰显了女性群体情感的强大力量,而且以此构成女性反观彼此的镜像,她们的个体定位不再是男性的“他者”,而是在和自己性别相同的女性角色上找到标准和方向。闵女儿在天香园受众人排挤,生活不顺遂的窘迫情形下,镇海媳妇第一个走上楠木楼把她带到大家的生活中。后来镇海媳妇过世,闵女儿便把这种情感转移到小绸身上,这有些出乎意料倒也符合人之常情,体现了女性以她们(姐妹)生活与命运为参照,对自己进行反思,做出的选择与行为。
天香园作为女性生活领域的核心地带,虽然免不了小桃之类的偶有抱怨和小气,但多数是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相互依靠的温馨场面。上述小绸、闵女儿和镇海媳妇姐妹情谊的建立过程,即从陌生到熟悉、从对立到友爱,是女性主体不断质疑、否定、拆解、辨认的过程。闵女儿在丈夫的冷落中支起绣架,将一腔心事都付诸绣艺,小绸在凄然的心境中作《璇玑图》,让人感叹。后来她们相聚在天香园西南角上的白鹤楼绣活,终至白鹤楼易名为“绣阁”,绣阁也渐渐吸引众人来绣活,形成一片旖旎的女性景观。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相互支持,以女性而非男性标准为镜像追求自我、重塑自我,以女性群体力量对抗父权制给女性带来的不公,对男权话语中心进行有力的消解与对抗。
依靠姐妹情谊建构对抗男性缺失的同盟还有蕙兰、蕙兰婆婆、戥子和乖女。蕙兰在天香园长大,从天香园出嫁,对天香园中婶婶、奶奶的姐妹情谊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才有对戥子和乖女出于姐妹般的同情和爱护。蕙兰在婆婆同为女性感同身受支持的情况下,才答应收徒授艺。从此,天香园绣阁中的姐妹情谊在张家小院的东屋里又延续开来,姐妹情谊固然有助于强化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但其主体的认同和确认还是基于漫长而多变的现实生活,基于女性主体敢于、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与选择的结果,而日常生活是女性产生共情赖以存在的基础。戥子从小为婢,但跟随蕙兰的过程中,姑娘的际遇使她深有感触,她终于认识到女性应该有一技之长才能安身立命,而乖女在男权社会以色识人的境遇中,更是不甘随波逐流。蕙兰更是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感悟,几位女子相聚在一起,她们虽然个性不同,甚至大异其趣,但对女性主体的追求让她们相知相守,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
小说中对姐妹情谊的书写着墨颇多,既是小说文本以女性叙事为着眼点出发,塑造了文学史中独特的女性角色,形成以小见大的叙事效应。同时,聚焦女性时代经验事实,并将其共有特点进行凝聚和升华,完成了女性群体性别主体的认同与建构。姐妹情谊的建立构成了女性自我体认行为的主要内驱力,这一过程既是女性心灵史,也是女性精神现象史。
三、代际递传:女性自我实现之路
在传统社会,女性面临许多生存困境,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中被妻子、母亲角色所桎梏,女性主体不得不退居于男性后面,甚至隐藏或磨灭了其主体性。虽然现代社会女性主体意识有所增强,但几千年来的父权制传统影响下,以男性为中心的影响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女性在自我主体实现的道路上依然面临许多困境,要受到社会生活、文化与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决定了女性自我发展与实现之路漫长而曲折。
小说通过女性主体确认的亲身经验提出了女性同盟发展之路,但传统父权制的观念根深蒂固,要想实现女性自我发展的长期性,姐妹情谊的力量显得有些单薄。与此同时,小说也通过人物塑造探寻了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即女性之间代际递传的接续力量,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根本改变“父权制”带来的沉疴,借此表达长久性地与男性对话的可能。代际递传之路立意深远,呈现出女性自我认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勃勃生机之势,是一条独特的、丰满的、有效的女性发展轨迹,为女性认知自身处境、主体成长提供有效参照。
在天香园女性的生命际遇中,两性关系中男性的缺失和失语虽然给她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和遗憾,但她们从其他女性身上获得温暖和力量,建立起牢固的姐妹情谊,以姐妹情谊为基础,她们又借助代际递传延续了这种精神。姐妹情谊以女性群体为基础,强调的女性之间的共情以及以此产生的力量。而代际递传在女性同盟的基础之上,侧重女性由于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承续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不同女性的个性特点、生存经验及技能的累加,也是女性自我实现的重要路径。
以天香园绣为契机,女性主体意识在代际递传过程中,对天香园、天香园绣的发展显得尤为可贵。其突出表现是,天香园绣的成功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闵女儿、小绸、镇海媳妇、希昭及蕙兰几个主要人物的智慧,包括戥子的辟发丝及其他女性在绣阁绣活的共同贡献。闵女儿嫁到天香园,带来了刺绣手艺,其绣工可谓炉火纯青,但绣样却还是以传统花样为主,形象虽逼真,但缺少一些意境。而小绸自小读书,临过元人的画,将诗书化进绣中,所以她针下的绣活就流露几分画意,自有一种雅致。加上镇海媳妇的从中调和,绣工和写意相互融合,促使天香园绣向前走了一步。希昭嫁过来之后,在小绸和闵氏的基础上,以绣作诗书画,终成绣画一派,让天香园绣更上一层楼,享誉天下。后来蕙兰新嫁丧夫之后,所绣罗汉、观音饱含禅的意韵,让天香园绣更加高远脱俗,进一步发扬光大。尤其是戥子独创的辟发丝加到绣工里,让天香园绣别具一番韵味。由此可见,天香园绣建立、发展、成名过程中,集合了天香园几代女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智慧,实现了女性个体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共同性的矛盾统一,天香园绣成为她们以技艺安身立命的根本且代代相传,其中女性的自主独立精神也次第传递,那一针针绣出来的是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感情寄托,更是女性自我赋权意识的延续。
天香园绣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多重的女性主体诉求,更是女性基于对独立、自由、自主身份的追求,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尊重,反映出作者始终如一的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和观照,代际递传实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长久发展之路,便有了像天香园绣一样沉甸甸的价值和分量,与男性力量在代际递传中逐渐式微形成鲜明对比。天香园中的男性虽个别取得功名,奠定了天香园的基础,但大多数逐渐归于碌碌无为。柯海虽有功名却并不以此努力,制糨糊、制墨却无一成功,镇海遁入空门,阿防开豆腐店,阿潜被丝竹吸引,天香园的男性似乎也在忙碌,但一无所获,而且一心只注重天香园表面的排场,殊不知天香园已是依靠天香园绣来支撑。作者曾说:“为了把故事聚集在女人身上,我必须把这大宅子的男人慢慢打发掉,这样女性的光辉形象才能起来。”④她对父权制下的女性价值立场与情感态度进行了审慎的思考,把女性言说与男性中心进行了审美置换。
除了姻亲关系之间相传之外,天香园绣并没有拘囿于血缘关系,而是打破了门第传统,真正实现了打破血缘关系的代际递传。作者安排从天香园嫁出去的蕙兰传授绣艺给天香园以外的人,把绣艺发扬光大,让她们自行撑起一片天地,实现了天香园绣流传于世、遍地莲花。在以男性为中心、为原点位置的世界,女性凭借知识、技能完全成为家庭、自己的支柱,完成了让人匪夷所思的蜕变,并将女性经验和生存智慧代际相传,在自我性别身份确认、自我价值实现上找到新的支点,成为女性自己的言说主体,着实是女性生命价值实现过程中令人欣喜的一幕。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作者对女性言说保持着澎湃的激情,以及她对女性自我实现路径冷静的思考,在历史叙事(时间主线)中引入日常生活(天香园绣)描写,以鲜活具体的女性日常生活作为“个人”进入历史的通道。通过女性之间建立的姐妹般的同盟关系,表现不同的女性个体,并非模糊不清的历史脸谱和符号。通过女性技能与精神的代际递传,呈现出女性自我成就独立生命价值与尊严的途径,一个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生存智慧、生活气息的个性化的具体的女性“个人”,为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注释:
{1}刘思谦:《生命与语言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中的主体性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②④王安忆:《王安忆接受早报专访谈〈天香〉》,《东方早报》2011年3月2日。
③谭兢嫦:《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91页。
*本文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博士科研基金启动项目“80年代新创文学期刊对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2020HNUAHEDF031)、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红色经典小说(1949—1966)的影视改编研究”(项目编号:2023-ZZJH-384)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陈文婷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