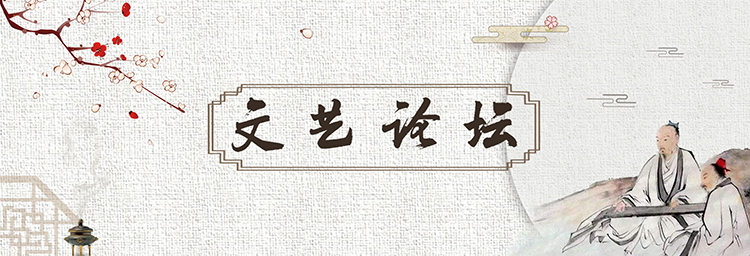

介入写作、现实主义精神和难度意识
——兼论新时代诗歌的审美话语尺度
文/刘波
摘 要:与新时期诗歌相比,新时代诗歌似乎变得边缘化了,但边缘化的处境也促使诗人们从内心的喧嚣回到创作的常态,让自己的诗歌承担起语言创造与思想启蒙之责。在这种责任意识中,对时代现实的介入变得至为重要。如何基于有感而发的写作来触及诗的力量感,就相应地要求诗人在孤独感的释放中为文字赋予某种悲剧精神,如此方可让诗歌抵达人文关怀的高度与深度。而怎样在介入现实中又不失诗意之美,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很多诗人在写作实践中挑战这一难度,并将其作为现实主义精神在新时代诗歌中的动态投射和转化。
关键词:新时代诗歌;介入写作;现实主义精神;难度意识
当有的诗人戴着面具写作时,他或许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体现在其作品中,可能就是诗歌之美与创造之难的不断撕扯。当代汉语诗歌曾因某些时代原因而受制于各种意识形态因素,或被当成一种“传声筒”,或成为文化反叛的工具,诗人们皆不同程度地丧失过内在的专业性和理想追求。朦胧诗的“我不相信”,“第三代”诗歌的“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都不过是在反叛中聚焦于个人意志的图解。而新世纪以来,诗歌审美虽然趋于多元化,但在这种多样的形态里,很多诗人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富于创造力,至少在语言的创新和陌生化上,有些诗人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当诗人普遍专注于日常生活审美,琐碎的经验是否造成了诗性的衰落?现实主义的式微是否让诗歌变得更加边缘化?一味地沉迷于小情小调是否又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难度?新时代诗歌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够不到极致美学的高度,而是缺少了诗歌写作在当下所持有的尊严,以及诗人对现实切入的锐利和深度。
一、边缘并非新时代诗歌的宿命
新时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先锋诗人们的写作不再讲求诗的社会功能,甚至一度反感这种说法。当我们在新时代重提诗歌要介入现实时,并非简单地用诗歌来替代宣传的口号,而是想以此激活诗歌的“正义性”。从更宽泛的理解来说,是希望诗人们担当起一种责任,以“求真意志”重塑诗歌“兴观群怨”之功能。邹韬奋有诗言: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当那些短小精悍的时事评论,以针砭时弊之力为读者所青睐时,它便发挥了文字的现实批判功能,它能以警醒的方式实现启蒙民众之责。当小说的先锋尝试已随着消费主义被裹挟而去时,诗歌到底又处于什么状态呢?诗歌需要承担救赎人心的重任,而诗人则需明确地亮出自己的立场:是想以自己的分行文字给读者带来美感,并提供一种前行的动力,还是作无谓的自娱自乐?这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伦理和责任问题。
在新时代,边缘并非诗歌的宿命,它很大程度上就是趋真的重要形态。因其边缘化,并无多少功利的出路,诗歌正好可以在“无用”的格局里守住清明。简政珍说:“当时代将诗边缘化,诗反制中央的就是展现语言活泼的生命力。跳跃性的意象思维超越体制内的文宣和政治八股。诗人透过这样具有生命力的语言,展延诗的生命力。诗的语言不是政治可以驯服的工具。”①语言的活力也可能就是诗歌的真相,除此之外,诗歌被时代边缘化的还是诗人与时代对接的缺失和创造性的匮乏,而非完全与世俗的妥协。很多人不愿去写“现实之诗”,大都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担心写社会现实之事,会出现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语言不占据主导地位,却倾向于成为道义承担的充分记号”。②当语言不占据诗歌的主导地位时,其艺术性很有可能会大打折扣。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但这只是降低了写作标准后的一种保守之举,而不是在充分意识到写作难度后去挑战诗的创造性。还有一种考虑,也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介入时代与书写现实,这一种可能已逐渐成为诗人们压缩艺术趣味的佐证。有的诗人甚至害怕写介入的诗歌,一方面可能出于“自我保护”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担心这样的写作会伤害到他那“小小的美学心脏”(朵渔语)。
诗人布罗茨基说,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而诗人们要用什么来抗拒现实?语言和思想。只有语言和思想的融合,才能产生真正的力量。抗拒现实不是要拒绝物质生活,而是反对一种普遍的被教化的“心灵缴械”。在现实中,诗人很可能就是一个孤独的反叛者,“我早已充分意识到写诗的背时,孤独就是存在,我喜欢孤独”。③这也是很多诗人不断强调“诗人是这个时代的孤儿”的原因:远离主流的喧嚣,留给自己一个清醒思考的空间。这种孤独,也是一种力量。诗人毛子曾说,诗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钉子户”,这个比喻对当下诗人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定位都形容得恰到好处。本质上的诗人既追求语言艺术,又富于良知和责任。可有些诗人在下笔时,要么极尽贬损之能事,要么刻意地去妖魔化,这两种极端最终都会导致诗歌深陷困境,被各种失败感所包围和裹挟。
诗人陷入“失语”的困境是否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对我们所处的困境早就了然于心:“由于个体的意识被同化,个体的隐秘被消除,个体的情感被一体化,个体不再有足够的‘精神空间’来发展自身,以消除自己的负罪感,凭自己的良心生活。”④当大多数人都被同化了时,诗人应该是一个异类。尤其是在趋于功利化的现实中,诗人与其他人所处的困境相同,但是,作为“时代的孤儿”,诗人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他们用语言表达抗争,以词语介入现实。而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凭自己的良心”来写作,在提供语言之美的同时,也为读者呈现诗性之真。
要达到如此目的和效果,诗人首先需要持守人格上的独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现实中,个人很容易就被各种意识形态所裹挟和规训,有时甚至会自我阉割。如何让自己在越来越多的诱惑面前保持善的情怀和人文理想,至关重要。“诗人必须一边写作一边追问写作的意义。不管流亡域外还是身处本土,诗人都不能不思考写作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写作不可能不与现实相抵牾。”⑤很多诗人在这种形势下要用诗笔写下变异的世界,重新还原真相。他们一方面需要反抗平庸,反抗与世俗名利的妥协,同时还要反抗自我对语言的放纵,这些反抗都要求诗人对笔下的文字负责。就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我希望写下的每个字,都能体现我对它的虔诚”。⑥正是虔诚会让一个诗人将自己的文字当作信仰,其对待信仰的态度由他在这条诗歌之路上走过的历程来决定,当然,这也取决于其内心的强大与否。
内心的强大与否,也真实地反映在诗人们的文字里。当很多年轻诗人追求天马行空的表达时,那还处于挥霍想象力的阶段,待他们意识到诗歌也是一种智慧的创造,可能会渐入“不动声色”之佳境。真正的好诗让人看不出多少外在的表演,所有的技艺都会内化到创造性的文字中。“写诗就是说人话,应该让一个个汉字活起来,到世界上去寻找它们贴心的对应物,让自己成为它们之间通灵的载体。”⑦黄灿然的诗歌《正义》,就是以从容对话的方式探讨自我的内心之境,这种对时代的介入虽然是个人化的,但又直接针对现实发言。因此,当个人化与公共性达成一致时,其让人信任的力量才会成为诗歌的态度,而不会因为偏见激起愤怒。愤怒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是诗歌的来源,然而,仅有愤怒是不够的,它必须联于诗人的理性思考。“如果诗歌对现实的心灵的介入,把对敌人的维度也包括进来的话,那么诗歌就有可能在终极的意义上阐述人类的现实,呈现我们的心灵,包括秘密、罪恶、黑暗。”⑧这应该是我们提倡介入写作的前提,否则,诗歌中只剩下愤怒,真正的诗意无法彰显,诗性正义便很难建立起来。
二、诗歌同样需要追求孤独感和悲剧精神的释放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中,既写玉箫,又写金钗,还有清露和红烛,而我们现在怎么去写这些东西?在当代语境下,我们怎样写现代之物才会有效且有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了古典社会的语境,诗人们再去写那些题材,可能有人会认为是文人雅士的腐朽,只可供茶余饭后消遣。但是诗人们如果下笔太随意、太自我,会显得轻浮,缺乏厚重感。这种厚重感需要诗人沉下去思考,而不是浮在表面上做些花拳绣腿的文章。除了充分发挥想象力来锤炼语言之外,诗人的思考中有没有历史意识,有没有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打动人心的文字,有没有在通向思想之真的路上回应来自良知的拷问,这些都是诗人们不得不去努力探索的问题。
曾有人在网络上直言:写诗很简单,文字分行即可成诗。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无怪乎诗人这一群体会遭人嘲笑。诗人的责任不只是写下分行文字,而是要看他的文字是否有创造性,是否将我们所观所思所想以共鸣的方式触及了个体生命的精神核心,是否以那些人生的细节丰富了整个文学的阔大空间。在介入性写作里,批判的意识当是一种立场,而锐利的笔锋则是一种美学,二者的彼此见证,才是对“诗歌简单说”的有力反证。“春风吹着祖国的工业 农业 娱乐业/吹拂着诗歌的脸/诗人 再次获得了无用和贫穷”(《诗人》)。诗人娜夜是在借诗抒发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感慨,同时也呈现了这个时代诗人的身份和处境。娜夜的介入是在直接表述和隐喻之间的交融里贯注了自我的思考,此时,她是孤独的,而诗歌又何尝不是孤独者的事业?尼采去世时曾说“连一个误解我的人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他没有对手,也没有可以交流的精神同道。
从尼采所处的孤独困境这一维度来看,也许悲剧感正是诗歌需要达到的精神高度。“面对邪恶,诗人大多都不乏愤怒,而我知道这是源于对人的爱。他们用艺术的形式表达这爱和愤怒的同时,使我们看到美。他们的财富只是良知、语言和手艺,却是在语言的石头中能找出钻石的发现者。”⑨诗歌可以书写幽默,但绝不是浅薄的搞笑;也可以充分地书写乐观,但不是盲目的无厘头。有了这样一种悲剧精神的要求,诗人在下笔时不可那么随意,包括其修辞表达和价值认同。所以,诗人首先得有一个思想的高度和境界,这决定了其语言和精神如何在一个标准上达到更高的层次。
80后诗人阿斐曾在其新浪微博中说:“我不认为诗歌有需要介入现实与否的理论争鸣。现实就摆放在你我身边,生而为人,必然要去感受身边事,有感就有声,发声为诗。如此而已。我不排斥浪迹于空想世界的悠闲诗人,甚至羡慕,但我做不到。”阿斐的立场很鲜明,他需要介入性的写作来召唤良知,这是他的诗学理念。同样,郑小琼更是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指涉了现实的残酷:“亡灵沿着黑色脚手架攀登 被钢筋/刺死的幽灵 哀伤之瓮装满沉默的贫穷/蓝玻璃的穹顶装饰黑夜 打桩机朝/大地哭泣 伸向大地深处触摸到/长眠地下的死魂 褐色吊车举起白骨/砖块像幻象中的词语 墙 门和窗之间/沦陷的句子被拆解 楼群一寸一寸升高/带着风 幽灵 青春在钢筋架攀援/死者用长发切开迸裂都市的根部/遇见成群的鱼飞过苦涩的深渊/它们眼里长着绿毒药的梦/笼罩在成长的男童身上”(《脚手架上的亡灵》)。郑小琼所写为变形的现实,她并没有完全照搬社会新闻中农民工在建造高楼大厦时的突然死亡,而是以多种带着重力的意象来对抗死亡的伤痛。诗人将个人经验和想象作了深度融合,让一起普通的民工死亡事件变成了幽灵的诉说和亡魂的低泣。这种介入性写作,就是对自我真实经验的重新加工,让它获得下沉的力量。
现在,有些年轻诗人沉于虚假的经验世界,而很难走出贫乏的困境。人类经验的贫乏,被本雅明称为一种“新的无教养”,这种“新的无教养”又引起了他的困惑:“经验的贫乏将会把无教养的人引向何方?引向从头开始,重新开始;以少而为,以少而建构;不瞻前顾后。”⑩经验的贫乏让写作从少开始,也即是从“贫乏”本身开始,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由“无知者无畏”引起新的创造与改变,也可能导致更为极端的贫乏。这种贫乏是思想和精神上的人文欠缺,缺少了一种汉语诗歌必要的厚重与深度。
思想的贫乏让很多诗歌成为“漂亮的废话”,这样的文字会让我们觉得乏善可陈。它不能对我们的阅读构成挑战,而被动地接受其实是思想懒惰的借口。尤其是对于真正富有语言创造力的诗歌来说,它更是某种张力和冲突在文字中的投射,并非一味地风花雪月或迷恋小情小调的日常之欢。所以,诗人不仅仅是表达一种“立场快感”,更需要在文字中渗透“智识乐趣”(刘瑜语)。毫无美感的口水式写作,是一种创作的极端化表现,而过度的修辞,同样也可能让诗歌变得毫无节制、繁复冗长。余怒的诗歌《居留地》由所有叙事的元素支撑,其间贯注着出其不意的罗列,诗人的急切心情,还有那快节奏的对话,不乏荒诞之意。但从余怒那些颇具荒诞色彩的诗作中,我们能洞察到他捕捉和把握住了一种个体和时代的内在冲突,这不仅是语言的怪异,还有那些独行的意象在其叙事中变形的位移。
由此来看,诗歌写作也要适当运用冷思维,让理性能在某一时刻控制情感,在思考、表达、迷惑与清理中寻求至美,这更需要的是节制。节制是冷思维天平上的砝码,它可让语言和情感达成一种平衡,以顺利地进入诗歌的理想国。当然,诗歌的冷思维不是实证哲学中“务实的理性”,它是一种把握真相的能力,诗人能通过语言表述寻求一种对生活的艺术转化。诗歌能给我们带来的全部价值,也许就是如此:在语言之内具有敏感、直白和新鲜的特质,在生活之内暗藏智性、灵动与现代意识。“每位大诗人都拥有一片独特的内心风景,他意识中的声音或曰无意识中的声音,就冲着这片风景发出。对于米沃什而言,这便是立陶宛的湖泊和华沙的废墟;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这便是长有稠李树的莫斯科庭院;对于奥登而言,这便是工业化的英格兰中部;对于曼德尔斯塔姆而言,则是因圣彼得堡建筑而想象出的希腊、罗马、埃及式回廊和圆柱。”{11}布罗茨基对这些他心目中的大诗人可谓了如指掌,确如他所言,这些大诗人都会有意识地在写作中打造一道独属于自己的诗学风景,那是他们得以成为大诗人的前提。
缺乏将个体和周遭现实都写成诗的能力,害怕介入时代与社会就会成为“非诗”,这种畏惧心理让很多诗人不敢越过题材的雷池,只能在语言技艺上寻求变化。有不少诗人担心,读者没那么大的胃口,什么都可以消化,因此还是保持诗歌的纯粹性为好,不奢求突破能为自己的写作带来多么精彩的华丽转身。新诗至今也已过百年,大部分诗人还是没能接续上古典诗人“目击成诗”的传统,所以只能在形式上做表面文章,触及不到诗学精神和思想的内核;或因胆怯和恐惧,没有建构强大的气场,也就难以找到更恰如其分的进入方式。
三、现实的难度与诗意之声
当边缘化成为一个时代诗歌的精神标志时,“无名写作”可能就是先锋诗人的日常状态,它是隐秘的,但具有潜在的力量。似乎也只有处于边缘状态,诗人的写作才会因为内心自由而富于独特魅力,从而接续上优秀诗人所创造的品格与传统。
如果一个诗人太过虚妄,或许下笔会显得空洞,当他藐视一切,那种昂首的自信为其带来的不过是因娴熟而有的匠气。如何创新,怎样提升,这是需要我们不断追问的话题,但是当很多诗人回头来看自己的作品时,很可能是一片支离破碎的幻影,总是捕捉不到聚焦的核心之点。那可能才是一个真诗人所能完成的全部使命:为真实的生活和存在真相而写作,而不仅仅是语言的游戏、小情趣的夸张,以及由非理性控制的浮躁与喧嚣。诗人在这个时代所获得的,不是一种有用的“功利化”,而恰恰应该是“无用之用”的精神助力,这才是其作品不致流于琐屑、空洞,而最终为读者所接受的根本之所在。
诗人的写作如何让读者产生信任感?杨克的《人民》一诗也许可提供部分答案,诗人没有写宏大抽象的概念,而是在解读很多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以及他们的命运。全诗一、二节,诗人以词语并置的方式,罗列各种人的具体身份,展现了一幅国人的群体生态图。第三节则打开视野,转换角色,从观察者过渡到思想者,因为诗人不仅要做事实记录,更要进行精神追问。之前列举了那么多类型的人,可是诗人说他“这个冬天从未遇到过‘人民’/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此为点睛之笔,也是对前述的注解。诗人没有道出何谓“人民”,但他以良知唤醒我们要正视现实,关注社会。这是一首回归常识之诗,它带着深深的及物性、悲悯意识、人文关怀和存在主义式的力量感。在此境遇下,书写信仰还是表达怀疑是选择的态度问题。它恰恰决定着一个人能否冲破束缚去完成关于现实问题的书写,去专注于对现实题材的再创造。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在《反讽的抒情》一文中说:“当我写些与政治无关的东西时,我觉得自己在空泛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当我写了任何我能写的政治问题时,我又会觉得自己背叛了某些生活中除政治之外的重要现实。”{12}很多作家在这两种情感的写作中无法取舍,摇摆不定。而与现实的短兵相接应是有良知的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因为现实主义题材里可能恰恰隐藏着个体的全部生存秘密与真相。生存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的人类权利,而是在物质与精神双重领域的满足。物质要求的实现仅仅是一个方面,精神追求和思想表达的自由境界,当是诗人所应获得的更高生存权利。只有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生存真相的价值所在。怎样在抗争中诉诸自身的权利,是值得每一个诗人反思的命题。
新世纪以来,萧开愚的《孩子们》《谁解救了谁?》等诗作,一反他在1990年代的那种玄学与晦涩的语言游戏,而直接介入现实,去为底层的现实呼吁和呐喊。“我不想愤怒,我不愿愤怒。/我只想快乐,只愿快乐的声音/伴随我的余生。/然而我越来越愤怒。/一天比一天愤怒,一秒比一秒愤怒。/为这些谎言,为这些柔软的暴力,/为这些用尽全世界的粗口也不能倾泻干净的人与事,/为这个冬天——只有它让我稍微安静一会儿,/只有它让我按下愤怒的暂停键。/然后放声大哭。”桑克的《愤怒》就是一个人遭遇当下人生现实时的愤怒之言。有良知的诗人无法做到对时代病症“眼不见为净”,他去关注和批判,去怜悯和同情,这是他给自己文字赋予的某种道义感。诗人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掩盖,不遮蔽,有一种释放的意义,但更多还是自我警醒。尤其是看多了残酷和荒唐,愤怒在所难免,而如何消除身上的戾气,诗人只有在冬天时才能获得短暂的安宁,但这安宁背后是诗人更深层的痛苦,一个人“放声大哭”或许就是最好的安慰和释放。诗人没有直接介入某个具体事件,而是将自己的日常体验和综合感受写出来了,虽然不乏隐晦之意,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感,尤其是他最后没有落脚于戾气,而是以“暂停的愤怒”收尾,这对于提升诗意是一个重要的转化装置。
很多诗人对介入现实并非持反对态度,只要有承担意识,都能够理解在这个转型时代何以要倡导介入的写作信念。“介入作为一种新的诗学态度,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针对历史进程的直接干预,因为诗歌写作充其量只是一种‘象征行动’,毋宁说,重提介入这个存在主义的命题,旨在呼唤良知的作用,诗人从‘词的立场’,即纯诗的立场,转向朝现实开放的综合文本的立场,似乎并没有导致诗歌品格的降低,如果诗歌的形式限度同样得到充分尊重的话。”{13}宋琳的观点也许能够代表一部分诗人的立场。而作为诗人,提供语言美学是其首要职责,保持基本的良知当是诗人之谓的尊严所在。
在此,我觉得翟永明和蓝蓝这两位女诗人当可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写作的镜像,她们的写作之花既在美学的范畴里获得了自我绽放,又在对时代和现实的介入中找到了对应的精彩。翟永明从女性主义的书写里走出来,迈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这并未影响她的细腻与真挚,相反,与现实的短兵相接使她获得了一种美学和思想层次的提升。其组诗《儿童的点滴之歌》,就是直接处理儿童群体在当下所遭遇的残酷现实这一主题,表现了成人世界道德的沦丧给无辜儿童带来的身体与精神戕害。诗人的批判和矛头所向,直指人性的扭曲,但她又并非直言其事,而是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对现实题材进行了诗意的处理,从而不失美学的风度。
注释:
{1}简政珍:《当代诗的当代性省思》,《诗探索》1995年第4辑。
②[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③于坚:《我的写作不是一场自我表演——2007年答记者问》,《作家》2008年第4期。
④[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14页。
⑤宋琳:《内在的人——在渤海大学“诗人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⑥[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李静译:《敬诗歌——在瑞典国王与王后招待诺贝尔奖得主宴会上的讲话》,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2页。
⑦罗振亚、雷平阳:《寻找宁静的力量》,《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
⑧欧阳江河:《诗歌写作,如何接近心灵和现实——在纽约“美华协进社”的演讲》,选自张清华编:《中国当代作家海外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⑨蓝蓝:《沙粒》,选自蓝蓝:《我是另一个人》,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⑩[德]本雅明著,王炳钧、杨劲译:《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11}[美]约·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
{12}[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反讽的抒情》,选自《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13}宋琳:《奥尔弗斯回头》,选自潘洗尘主编:《读诗》(2012年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再发现”(项目编号:18BZW1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刘波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