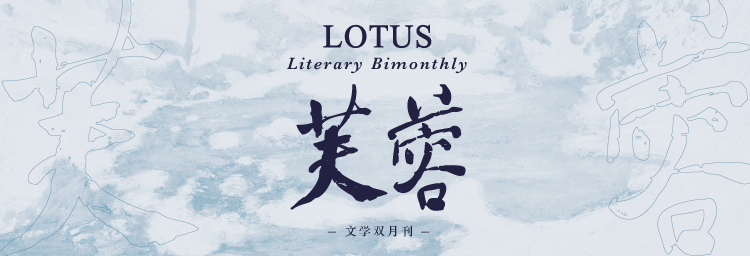

清风醉我(中篇小说)
文/吴文君
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不错,常有人指着我说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我嫌他们迂腐,却也飘飘然,看什么都眼带几分轻视。进了杭大中文系,我心气更高,只和成绩好有才气的同学交往,好酒、好舌战、好揽镜自照。只是好景不长,毕业后我没能留校,也没留在杭州,而是分回老家,进了一所乡村中学。
反正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管你什么学历,都是下到基层,从最底下做起。杭大的于师写信安慰我,叫我“既来则安”,切勿“心生怨诽”,沉下心来好好教书育人,将来总有一条好的出路。亲戚们则认为这是我眼睛长在额角看不起人的缘故,受点教训也是活该。只有我母亲提起这事总说我家没后台,不认识人,不然也不至于一脚踏进这么一个狗不拉屎的地方。其实这倒是母亲的偏见,这学校虽在乡村,学风却好,县里不少干部就是从这里毕业出来的,每年拨给的经费也充足,教师宿舍翻盖不久,算得上全新。我那间虽然朝西,却有一个小阳台,还有前任留下的几盆花,坐坐站站都很不错。我搬了被子铺盖和一箱书住进去,颇有点遗世独立闭关自修的感觉,自以为不出两年就会被人请去县里的第一中学。
认识我的都认定我迟早要走,上门做介绍的络绎不绝。女同事、女工、女裁缝、女医生、女出纳,我挑挑拣拣见了几个,话不投机,提不起兴趣再去见谁。说起来我只是看不中她们,嫌她们不读书,没眼界,不会打扮,城镇户口的不够漂亮,看着漂亮的又都是农村户口,突然听见有人怀疑我那方面有病,所以才这不好那不好地推托,也只有瞠目结舌,不知道找谁算这个账。再看见给我做过媒的人便绕了道走,一个都不想搭理。
那时我的心思也不在这上头,只想好好带班,有点成绩回县里,不久却迷上了越剧团的小花旦毛小云。
这事的源头在师母那里,她和于师来县里会老战友,顺便看个戏,给老战友的女儿毛小云捧捧场,把我和另外几个杭大校友也叫了过去。看完戏,散场出来,师母先回去休息,我们几个陪于师去吃夜宵。天冷,热菜热酒一下肚,大家兴致高了,说话也随便了。不知谁带的头,忽然笑话起我来了,说我看小花旦看呆了,嚷着要于师做媒,不是老战友的女儿吗?近水楼台啊!
我当时不承认,气他们明明都盯着毛小云看,倒把好色的帽子往我一个人头上扣,过后却生了心。休息天回县里,先去剧院看有没有毛小云的戏。那时他们一个月总有半个月在周边乡镇巡回,我找到剧团也没机会撞到她,心急之下还去杭州找过师母,听师母说了些她学戏的事,师母还说唱戏这碗饭总归吃不长,她的本性又是很老实的,与其攀附有钱有势的人家,不如找个有才华的人依托终生。
从师母家出来,我越想越觉得师母是赞成我找毛小云的,于师门下这么多学生,她也是高看我一眼的,我回去就给毛小云写了封信。寄出后左等右等不见回信,索性又写一封。
同校老师多已成家,下午放了学,一个个急急忙忙往家里赶。我不合群,吃了晚饭窝在宿舍里闲得难过。本来对那乡村景色毫无感觉,忽然出现一个写信的对象,就觉得一棵树、一弯残月、一堵老墙,都大有可写可叹之处。即使留校的同事晚上聚餐聊天,我也懒得参与,谈不了多久就觉得这些人目光短浅,凡事拘于现实,一开口,无非房子盖了没有,占了几平方米地,用了多少砖瓦,借了多少钱,准备几年还清,跟他们谈读书简直白费工夫。
十数天后总算盼到毛小云的回信,只是迎窗读了几遍才懂她意思,是叫我不要再往剧团写信,免得成为笑柄,团里人多口杂,下乡巡演更是同吃同住,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之前已有师姐受不了闲言碎语自杀,等等。我看得大失所望,倒在床上冷了自己半晌,看看吃饭时间到了,起来把她的信连同剩下的半沓信纸往抽屉深处一塞,想收手算了。没想到,吃好饭依着操场走了几圈,在台阶上坐到起露水,回到宿舍,又把那半沓信纸扒拉出来。只是写了撕,撕了写,总不满意。不久收到于师新书,借机去杭州找师母,师母也不多谈,只让我去湖边逛逛,散散心,随缘而行,不要太急于求成。可我到了西湖边,没心没思,看什么都不入眼。逛到孤山附近,又想坐个船,游个湖,又想回去算了,正拿不定,来了一队人拉起歌剧《茶花女》的演出海报。头戴白花长裙曳地的茶花女看得我心里一动,马上赶到售票处买了两张。自己花钱买票看歌剧,在我还是生平第一回。回县里天已黑,我在床上看书看到后半夜依然翻来翻去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上等着邮局开门,把票寄给毛小云,附上短信,告诉她我在客运站等她。
到了那天,我早早去售票大厅候着,忐忑不安看着一拨拨人进来,又出去。眼看发车时间不远,热了几晚的心止不住要凉,就见毛小云东张西望走了进来。卸掉台上的浓妆,像换了个人,看见我,也不说话,一阵轻风似的飘过去买了车票。我马上跟着也买了一张。进候车室坐下,我正想说点什么,忽然有人大叫她的名字,是个和她年岁相似的女子。“我们坐那边说吧。”她换了座位,两个人亲亲热热地聊起来,竟然一直聊到检票上车。还好那女子和我们不是同一趟车,要不然会说上一路吧?可气我们同时买票,却不是连座,我暗暗沮丧,她倒显得如释重负,一直到湖边人少的地方,才和我并排走在一起,吐一口气说:“你不知道我们团有些女人嘴多毒。”
“所以叫我不要写信,就是因为她们?”我有点轻蔑起她来了,那些人,还值得怕吗?
她张张嘴,我以为她会伶牙俐齿地说上点什么,不料抬手半捂着脸说:“别说头上一根白头发,身上有颗痣,有个疤,她们都会扒出来看,这些人就喜欢这么亲密无间——算了,不要说她们了。”她望着湖面说了句,“多美的湖!”把脸转向我,“怎么想到看《茶花女》的?前些天赵妈妈也去看了,还说我该可以去看看,别看做功唱腔不一样,天下的舞台本是一家。”
我听得惊奇,深以为师母在暗中又曲折地帮了我一把,把我去于师家,师母叫我散心,正好看到演出海报的经过说了说,问她:“师母跟你妈是老战友啊?”
“她们认识的时候我妈才十几岁,赵妈妈很照顾我妈,有好吃的总留给我妈,她真是不容易,宁肯拿枪打仗也不愿意嫁到有钱人家,两个小孩都在路上流产了,后来日子安定了,也没有再生。”
“咦,他们不是有个儿子在美国威斯康星吗?”
“那孩子是于叔堂哥的,抱过来过继的。”
“啊?”我大吃一惊,认识于师这么久,居然没听说过,这事是大家都不知道,还是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这真让我傻眼。
“你可不要跟别人说啊!”她叮嘱。
“这有什么。”我一边答应,一边又觉得她未免太胆小了。
“反正别说是我说的。”她不放心,又说,“这是他们的私事,不该随便说。”
“跟我说,不算随便说吧?”我说。
她有点着恼,也像撒娇:“你这样,不跟你说了。”说完只管看着别处,把脸转得只剩一点轮廓。
我顿然发现她的侧脸更美,像画册上的希腊女人,不,女神!直到现在,我已经从二十几岁的青年变成六十多岁的老人,也没再见过圆坨坨光灼灼到那样的脸,一看之下,竟然再也放不开,只知道死死地盯着。如果后来我不是疯了似的想在那上面吻一下,我和她也不会弄到那么糟糕的地步。这事应该怪我。可我又经常觉得不应该怪我。我就是迷上她而已。这个年纪的男人被一个女人迷上,不是再正常不过?荒唐的倒是后来的传言,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我在剧场买了让毛小云恶心的吃食才导致她对我的厌恨。我想不出是谁造的谣,也不知道它在剧团传了多久才变身成另外一种样子,再扑朔迷离星星点点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以为时间一长这种飞短流长自会消失。从杭州回来,毛小云几乎立刻恢复了对我的冷淡,我不得不拿出沈从文追张兆和的劲头,在信上做文章,倾吐、发誓,把茶花女的痛苦,妓女羊脂球的痛苦,为了一串假项链赔掉一生的玛蒂尔德的痛苦,每个都深度分析了一遍。当然信的最后我没忘记赞美她,让她相信她是我这一生唯一要追求的人,就是为了她我也要努力扇着翅膀从乡村中学飞出来。
不久,听说日本的轻音乐团要来杭州,我半试探半商量地问她去不去,她刚得了头牌花旦的口头封号,心情不错,没说几句便答应下来。我光想着伸手去托她的脸,除此心里一片空白。虽然当时是忍住了,但我没能忍到原先打算的一个月或者更久,那只是为了安抚我的冲动设定的时间。实际上,从那天算起,只过了五天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事。当时我们在外面吃了晚饭,其实是每人叫了碗面,为讨她欢心,给她叫了最贵的虾爆鳝面,自己只来了碗便宜的雪菜面。我以为这不算丢脸,毕竟我刚上班,口袋里没几个钱,省一点是一点,没想到她抢着付了钱,还把碗里的鳝片拨了些给我。推来推去当中,我们的感情陡然增进不少,吃完散了会儿步,我说送她回宿舍,她不仅没反对,到了宿舍门口,还同意我送她上去。
这晚她的团友们都去给团长的母亲贺寿,楼里冷冷清清,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没去。剧团的单人宿舍在一幢很老的小楼里,人字屋顶,淡绿粉墙,楼梯是木头的,走起来空空直响,晚上听着有点惊恐。她却是习惯了,如履平地,现在看起来粗笨的皮鞋后跟在那时纤巧而时尚,她一边走,一边说就是不想去,脸上少有地带着几分不屑。
我记得我随口说“不想去就不去吧”。要是我,我也不去,不想看有些人巴结的嘴脸。她是不是另有隐情,我根本没心思细想。我的感觉的全部触点都在即将和她相处一室这一件事上,腿是虚软的,头却很重,好像全身的重量都到了头上。
她住二楼,和我一样,也在最西边。这房子原先应该是有钱人家的私宅,走廊很宽,铺着菱形格子的木地板。房间被隔成多间后,已经看不出当初的样子,进去只觉得非常小,连床、床头柜都比别处小一截。屋角拉了根绳子,挂着她的衣服,有一件特别粉嫩像是戏服,一面穿衣镜靠墙斜放着,映照出室内的床铺以及看上去手足无措的我。
“你要坐坐吗?”她拉开椅子,朝我探一下头,出现在镜子里。
“这镜子真大啊。”我站站好,看着镜子里的她。
“哎,别忘了我是唱戏的,镜子头等重要!”她说着,好像知道我在偷窥她,抹了抹头发,退了两步,从镜子里消失了。我只好讪讪地说镜子于她,就像书桌于我,床可以没有,也不能没有书桌。“哎,我倒也喜欢读读书,可是不行啊,哪有时间。一下乡,净是睡学校野庙,洗个澡都成问题,别谈读书了。你房间里有很多书吧?”我谦虚说不多,其实我的藏书在杭大的同学里也不少了,书比金子值钱的年代里,书不只胜过金子,也胜过官位。何况镜子里的我不只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还有挺直的鼻梁,不高,却也绝不算矮的身高。一句话,说镜子里的我一表人才也不为过。想到中国人说才子配佳人,我没喝酒,却也醺醺然起来,好像站在一个粉色的美梦中。
看我沉迷四周却不说话,她不好意思地说:“你没见过这墙原来又土又黄,这我自己刷的,我妈还说了我一顿,几岁了,又不是小姑娘,弄这么粉!”我替她辩解:“可见拿过枪的人根本不懂这种颜色的好。”又说,“这才好看,才配得上你。”发现她又在镜子里了,我的声音止不住颤抖起来:“来,你走上前一点。”她不解地看看我,迟疑一下,毕竟听话地往前走了一小步。“再走上前一点。”她的顺从让我的胆子大起来,待她走到和我并肩的地方,叫她看镜子。“看什么?”她的喘息越发不均匀了。“看我们,般配吗?”我耳语一般跟她说,在下半身突如其来的震荡中化身成一根线,一个像精子那样拖着细长尾巴的东西,魂灵脱壳一样只想朝着她的身体飞去。这不能怪我,她离我太近了,太近了,近得我一伸手,就像梦里想过的那样捧住她的脸。
理智那种东西一旦丧失,另一种东西立刻乘虚而入,我的耳朵里就像有十几口钟在敲,当里当啷的乱响中,人的声音只剩下一个:“女人嘛,都是吃硬不吃软的。”——那是学校的勤杂工,绰号叫黑皮的经常挂嘴上的话,平时看着还蛮斯文——我都忘了什么时候听到的,这一刻却打破一切圣贤书,什么“未发谓之中”,什么“发乎情止乎礼”统统去他的三十三重天,直到腿一软,差点被她推倒在地,靠在墙上看着她的脸收缩,歪斜,变硬,硬成一块大理石,冷冷的,往外透出一丝一丝的寒气,这才好像醒过来了。
她看我愣着不动,提醒我:“你还不走?”
“这个,我……”我想解释两句,她又声音低沉地喊了一声,“走!”
我期期艾艾走到门口,不死心地回头看看她,想知道是不是还有挽回的余地。不料一只拖鞋对准我扔了过来,砸到肩膀,又飞过来一只。我跳起来躲,门从里面关上了,差点没把我的衣服夹住。
“毛小云?毛小云?”我贴着门轻轻地喊了两声,听着里面石沉大海一般没敢再喊下去。
总觉得走廊里有声音,有只光脚正在地板上悄无声息地移动,望过去却没有人影。说不定有人和毛小云一样没去喝那个贺寿的酒,而且说不定就在隔壁这间,这种不隔音的地方,只怕全让他听了去了。我瞟着那扇门,贼心也好色欲也好,到了这时再也荡漾不上来了。
毛小云那晚怎么过的,后悔放我进门?恨我入骨?我不知道。连我自己怎么过的也糊里糊涂的,人往楼下冲,脑子里就像有一大团火烧着。出了门,闷头闷脑沿着河两边的大街转了一圈,又转一圈。这儿也算是县里最热闹的地段,这时候的河面只倒映着绿豆一样的灯光,黯淡,飘摇。一个县城的晚上这么凄清,是我想不到的,只怕还比不上杭州的一个小角落。可就是这样的县城,我也来不了,只能屈居到更冷清更死寂的地方。我一边走一边凝视着河对岸的灯光,恍惚中竟然又走回到刚才吃面的地方,它其实这么小,这么蔽旧,一只十五瓦的灯泡就把四边四角全照亮了,连同一垛煤球三五个衣着寒酸的食客。面汤腾起的白烟里,我一眼看到我们坐过的地方,空着,两张冷板凳隔着空落落的台面相看无言。算时间还没过去半天,两个人抢着付钱、推让碗里吃食的镜头已经远如隔世。明明我们可以一天天热络下去,看剧、听音乐、吃饭、谈天,直到我这边张罗娶妻,她那边忙着嫁人,怎么成了这样子?我站在树下,像个落水鬼,从头到脚淋满凉水。情欲的厉害我还是第一次领教到。它会让你做出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刹那之间魔鬼附身一样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让你死不成活不成。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我心慌意乱地走着想着,不知道走到夜里几点,烧着我烘烤着我的那团火终于熄灭下去。我回到家,站在门口,钥匙转来转去半天开不开门。我母亲从里面帮我把门开了,穿着睡衣裤,拎起眼睛,看着我,像看外星人。我想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喉咙却空空的挤不出一个字。头一低,钻房间里去了。
“你倒是洗洗再睡啊?”母亲敲了几下门,怕吵了隔壁,嘀咕着走开了。
这房子是以前父亲分到的,一幢木结构的老房子住了两家人。我们这半边小一点,也有四间房。周围邻居都知道我父亲为了一个女人工作也扔了,在外面又生了个儿子,涎着脸回来找母亲签字,把婚离掉了。母亲没多说,只要求他出一半的钱把房子买下来,产权归我们,他也爽快照办了,算是给我们一个安身的地方。邻居都很帮着母亲,总说我父亲不好,没良心,好好一个老婆不要,去喜欢那种泼辣的外地女人。那年我刚读初中。母亲经历离婚后,管我很严,好像要把父亲管我那一份也一起管进去。我进了杭大,书读多了,和师友聊天多了,才醒悟到母亲是把我当成她理想中的丈夫来养育的,从坐相立相,说话举止,不轻易低头的气概,全有一套标准。我虽不情愿,却也习惯了处处听她的,望着窗外的一重重屋脊发了会儿呆,老老实实过去洗漱。怕她在床上竖起耳朵听着,没敢敷衍了事,仔细洗了脸,脚趾也像她在边上督查一般一一擦干,才回去睡觉。躺床上去故意弄出咯吱一声响,也是为了让她听见,免得不放心再偷偷跑进来看我。
(节选自2022年第3期《芙蓉》吴文君的中篇小说《清风醉我》)

吴文君,1971年生,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浙江海宁。作品散见《收获》《上海文学》《大家》《作家》《清明》等刊,收入各大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红马》《去圣伯多禄的路上》等。
来源:《芙蓉》
作者:吴文君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